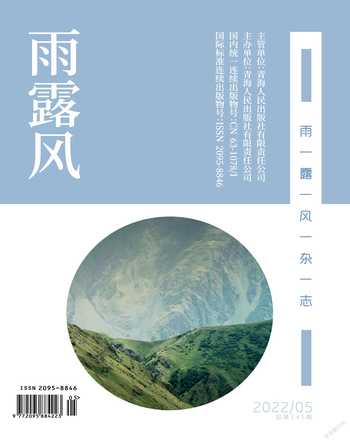诡谲的镜面:马洛伊?山多尔《烛烬》中的叙事阐释

摘要:马洛伊·山多尔的《烛烬》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了众多读者和评论家的青睐,甚至有人將其称为是马洛伊“在匈牙利乃至整个欧洲最为出名的作品”。小说充分运用“阻碍”和“延迟”等多种手段,在不确定性和空白之间,宛如有个诡谲的镜面,面面不同,色色相映,给予读者无限的阐释空间。从叙事批评和语义批评的角度分析《烛烬》,我们可以窥见其中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匈牙利民族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下精神归属问题的解答。
关键词:不确定性;叙事距离;含混;烛烬;叙事阐释
一、视角与转换:同叙述者的绝对话语权
马洛伊·山多尔出生于奥匈帝国的贵族家庭,一生穷困潦倒,颠沛漂泊41年,最终客死异乡。多年流亡海外的马洛伊毕生坚持使用“孤独的匈牙利语”进行创作,哪怕知音寥寥,仍然故我。这是《烛烬》虽然问世于战火纷飞的1942年,但直到1990年末才算真正进入读者视野的一个重要原因。
41年之前发生在城堡外密林中的“狩猎枪杀事件”,一直让将军亨瑞克耿耿于怀。当时二人站在灌木丛里,面对着“在不可言状的黑暗中恣意生长”的森林,300步之外警觉的麋鹿从丛林中走出。出人意料的是,亨瑞克并没有当场揭穿这场“阴谋”。在随后的晚宴中康拉德始终保持缄默,将军意外发现妻子克里斯蒂娜和康拉德之间的“千丝万缕”。克里斯蒂娜最终选择用漫长的沉默来面对亨瑞克,康拉德也不辞而别,与亨瑞克分道扬镳四十余年。
从整部小说的视角来看,《烛烬》的叙事是以一个合一叙述者或者说同叙事者的视觉展开的。所谓合一的叙述者,即在叙述的过程中,文本是作者本人说出或者写下来的,浸透着叙述者的主观意志和精神。叙述接收者(即“受述人”)面对的故事来自这个源头,而从叙述文本形成的角度来看,任何叙述都是叙述者选择经验材料后加以特殊安排才得以形成,叙述者有权决定叙述文本讲述的内容,以及最终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在《烛烬》中,马洛伊·山多尔操纵着作为一个具有绝对话语权的叙述者——将军,他看上去是“全知叙事者”,再度重逢时,他不想表露出自己怀疑的一切,以“我”的追述评论和想象为主线去“还原”41年前的真相,始终让自己和康拉德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时而向旁观者的身份过渡。通过将军的叙述这一纽带,马洛伊展现了两位老人复杂的心理状态,将发生在过去的事情、41年的空白和真相巧妙地结合起来,无疑将小说的艺术向真实性又迈进了一步。
通过“回避”策略,马洛伊将亨瑞克和康拉德、作者和读者同时置于一个四维世界中。从将军的视角出发,跟着他追溯过去,了解当年的丛林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将军的回忆就像一个取景框,靠着这个取景框移步换形,故事被层层展开。在这样的叙事策略中,叙述者拉开了读者与主人公的距离,增加了作品的层次性和客观性,并为读者留下了耐人寻味的空间。马洛伊同时使用两种叙事视角从而引起读者阅读视角的变化,宛如摄影中的镜头一般忽远忽近。我们只能从字里行间去捕捉人物的内心世界,读者不能再按照传统的阅读方法揣摩作者的真正意图,或者说跟在作者预设好的“陷阱”之中,而是必须接受这种叙事视角带来的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中左支右绌,独自一人去体验小说中人物的冲突。在一个“作者已死”的环境中,读者不会受到作者本人价值观和情感态度的影响,而是根据自己往日的阅读积累,在阅读过程中进行一步步的认知重建。也就是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当年的真相究竟如何,每个读者都能有自己的见解。
另外,在合一的叙述中,叙述者的叙述也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好枪手,我只要稍微偏一下头,子弹就能从我耳边呼啸而过,也许能够射中麋鹿。我知道,只需我做出一个动作,就足以让子弹留在枪膛里。但是我还知道,我无法躲避,在那一刻,我的命运已经不取决于我自己的决定:有什么事情已经酝酿成熟,根据其自身的程序与模式;有什么后果该要发生。”[1]这一大段剖白不仅激起了康拉德的情感,也让读者跟随着亨瑞克一起,在康拉德的神态中去捕捉真相,或者说其实读者们此刻就在客厅,凝视着两位老人,而作者却在冷眼旁观。这种阅读体验使得读者极其容易陷入亨瑞克或者说是作者的“陷阱”中,在真相和怀疑之间徘徊,并且很难判断过错的那一方。
正如罗伯特·弗莱所说,“一位无所不知的作者在其间展示着一些未及于表的素材,好像它们是直接从人物的意识流中流出来的一样;作者则通过评论和描述来为读者阅读独白提供向导”,内心独白永远包含着作者的叙述干预,包含着人物特定之外的叙述者的声音,即评论家所说的“双重声音”。在独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亨瑞克对于阶级差异有着自身的理解,他认同自己的旧贵族身份,称康拉德为“另类”。[2]亨瑞克作为一个叙述者,向外界讲述自己与康拉德之间的过往,在叙述中创造出两个层面的价值:其一是叙述出来的关于将军与康拉德之间的故事具有可读性;其二是叙述的同时也展现出亨瑞克自己的内心活动,这个心理活动与二人之间的过往,与读者都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在绝对的话语权中,使得读者不自觉地代入,仿佛将军阐述的一切就是真的,康拉德确实曾在丛林中对着亨瑞克举起过抢。
二、含混与歧义:典型的空白艺术
含混,是西方文论的重要术语之一,其表征之一是小说呈现的故事“似是而非”。为了达到“似是而非”的目的,山多尔费劲巧思,借用大量的空白艺术将答案抛向未知。[3]伽登在《文学的艺术作品》中指出“每一部文学作品在原则上都是未完成的”,从这一点出发,似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小说的结构。
在《烛烬》中,山多尔从亨瑞克的角度去回忆41年前的诸多往事,叙述者“将军”作为第一叙述者与康拉德的记忆无缝地整合在一起,成功建构了一个叙述的框架。从表面来看,它有利于完成对将军与康拉德之间少时相识相知故事的有效讲述。由内思之,《烛烬》讲述的故事,也有可能只是亨瑞克的一面之词,这就赋予了小说内容极大的蕴藉性和张力。
首先,马洛伊运用“摄影型”的视角变化,在“近”与“远”中拿捏着足以控制读者的尺度,借用亨瑞克的叙述从一开始就为读者布下陷阱,带读者穿梭在事情的真相与未知中,而对整个故事的封闭性全然不知,被“控制”的读者们看到的始终是一个有待补充的故事而不是全部。FBA36950-8D4E-49F1-AAC2-EF008192992C
其次,在《烛烬》中,作者将康拉德塑造成一个弱者的形象。將军将康拉德视为释放和寄托痛苦的载体,另一方面,康拉德自身也面临着生理上的苦难,哪怕是听到最普通的音乐都会让他嘴唇颤抖,这种痛苦只有在将军身边才得以减轻。虽然是互相作为对方的痛苦输出媒介这样一种畸形的关系,二人还是成了莫逆之交。这样的不对等关系使得读者轻易掉进康拉德绝对有杀死亨瑞克的先验之中,但正是因为康拉德在面对亨瑞克的问题时,少言寡语,将军回忆和判断的真实性就瞬间降低了,故事呈现出一种“雾里看花”的美感。
最后,故事戛然终止,这就在作者与读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留下一个广阔的空间。将军的一系列内心独白甚至可能是自己的臆想,也可能确有其事。唯一可以得到“真相”的证据——克里斯蒂娜的日记本,最终却被投进了壁炉的柴烬中。将军用片段言语搭建起来的41年前的事情切面,真相究竟如何,康拉德保持沉默,读者不知道,马洛伊本人也没有给出答案。这就“召唤”着读者去想象,凭借文本中的空白来完成情节与人物的“填空”。
希利斯·米勒认为,一部小说或者某一时期的小说究竟是封闭式的还是开放式的,这是一个难题。“一部表面上看起来具有封闭式结尾的小说,仿佛总是能够重新开放,这使得结尾的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4]50在《烛烬》中,将军将客厅恢复成41年前的模样,与康拉德秉烛夜谈,他迫切想知道康拉德本人对于当事件的真实想法,但又害怕自己承担不了知道真相的后果,于是左右摇摆,踌躇不定。故事的最后,将军和康拉德默默告别,两人都在深深地叹息。而那幅克里斯蒂娜的肖像被重新挂起,将军平静地走向自己的房间,康拉德是否举起过枪,仍然无从得知。
希利斯·米勒进而指出:“真正具有结束功能的结尾必须具有两种面目:一方面,它看起来是一个整齐的结,将所有的线条都收拢在一起,所有的人物都得到了交代;同时,它看起来又是解结,将缠结在一起的叙事线条梳理整齐,使他们清晰可辨,根根闪亮,一切神秘难解之事均真相大白”[4]51。依据这个思路,小说叙述到将军和康拉德告别就戛然而止。康拉德打算住在伦敦直至死亡,将军心态平和地走向房间并与妮妮吻别,克里斯蒂娜的肖像被重新挂起。看似对所有的人物都有了交代,但将军与康拉德,二人漫长的一生还剩下十几年,是否会重新见面?横亘在二人之间41年的秘密是否就此隐去?在实际上,开放型的空白结尾赋予小说无穷的丰富性和蕴藉性,这个故事随时可以再次“解结”,继续讲下去。就像小说自身讲述的那样:蜡烛燃尽了,可是小说并没有结束。
《烛烬》问世于1942年。1949年至1989年期间,马洛伊·山多尔一直流亡于海外,前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匈牙利一直处于分裂中,其作品在匈牙利的译介和传播几乎陷入停滞状态,他甚至认为“这个世界不需要匈牙利文学”,一方面是选择外语创作迎合多数人的口味,另一方面是坚持母语创作但因为语言问题与读者渐行渐远,两难境地之间,马洛伊还是选择了后者。正如约瑟夫所言,一个国家的文学创作,有时看似在国际上默默无闻,但或许比波谲云诡的政治变革更能真实地反映国家现实。《烛烬》中将军和友人之间无法跨域的鸿沟,正是作者当时心里矛盾的反映。[5]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我们甚至可以将亨瑞克和康德拉的角色视为作者对东西方文明之间、对个体职责和祖国命运之间的深刻思考。当世界秩序颠覆,而新的秩序远未来临时,匈牙利民族该何去何从,《烛烬》就是山多尔给出的答案。
三、结语
马洛伊·山多尔生于世纪之交,可以说是“生来逢时的在场者”,他亲历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及美苏冷战等重大历史事件,也见证了匈牙利政治体制的变革。作为“奥匈帝国进步市民阶层”的代表者之一,马洛伊勤勉、爱国,有社会责任感,尊重学识。可以说,《烛烬》的不确定性代表了作者对于当时匈牙利民族出路的困惑。德国纳粹进驻匈牙利后,匈牙利几乎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人们需要在这样一个混沌的状态下重新审视自我,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这也是文学的时代任务。马洛伊在海外漂泊41年,几乎半辈子都处于自我的放逐状态,面对困境,他本人给出的解答正是其叙事阐释中所体现的那样——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追逐意义,在混沌的现实中竭力去探求出口。
作者简介:曾艳华(1998—),女,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参考文献:
〔1〕马洛伊·山多尔.烛烬[M].余泽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2〕陈瑞莲.论马洛伊·山多尔早期小说的现代意识(1916-1948)[D].长春:长春理工大学,2020.
〔3〕符晓.《烛烬》的含混与歧义[N].文艺报,2019-07-12(004).
〔4〕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M].申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黄夏.流亡在昨日的世界[J].新民周刊,2016(08):111.FBA36950-8D4E-49F1-AAC2-EF00819299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