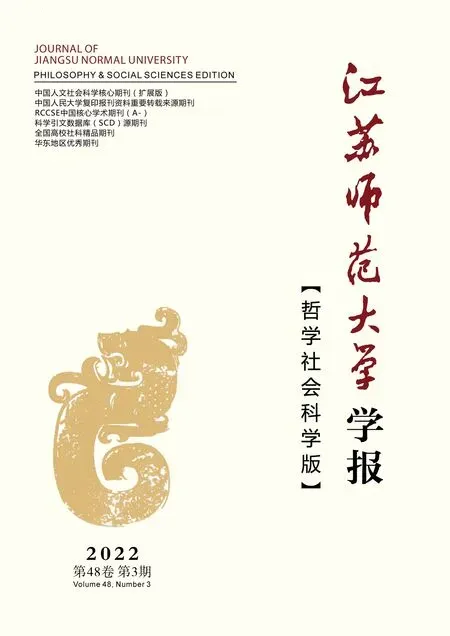人力资本理论文献综述
王增武 张晓东
(1.中国社会科学院 金融研究所,北京 100732;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北京 102488)
一、引言
当前,在政策的制定、公共舆论和学术研究方面,创新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话题。当然,中国在创新领域方面已取得突出进展,不管是研发投入总额还是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都有较大提升,均居于世界前列。在研发的产出方面更是产生了重大成果。专利申请量已居世界第一,且申请数量不断上升。中国经济面临着重要转型,首先是经济增长速度的转型,其次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对人力资本的重视是不能缺少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而且在劳动收入分配、人力资本匹配方面占有主导性地位。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分析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我国更好发展人力资本、配置人力资本,促进创新,进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分配的研究不仅从经济层面促进国家均衡发展,促进经济均衡增长,而且在道德层面、公平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人力资本进行全面梳理,进而对人力资本形成更深入的认识,促进人力资本更好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将对不同时期的中西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梳理,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与各方面的研究进行分析,最终提出自己的看法。人力资本理论正式提出的时间较晚,20世纪60年代才形成较为完整的人力资本概念。此前,虽然人们了解到个人工作技能及工作经验的重要性,但是没有系统地形成人力资本的概念,也没有对人力资本概念进行较为全面的界定,更没有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及回报进行测量,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对人力资本的认识十分浅显。20世纪60年代之后,经济学家才正式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对人力资本进行界定,并将其要素进行分类。此后,人力资本在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力资本的应用使传统理论解释不了的一些现象得到解决。人力资本主要的应用方向是解释经济增长及收入分配。随着数学知识和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经济学家也通过定量分析来考察人力资本投资的数量以及回报率。
相较于西方,中国关注人力资本较晚,且对人力资本的研究更多在应用层面,在理论层面提出的创新型理论和模型较少,更多的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和数据对西方理论中国化,并结合具体数据在收入分配、人力资本效率、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测算方面进行研究。
在人力资本理论形成之前,人们就认识到知识技能的重要性,发现个人能力对促进经济发展、生产水平提高以及个人收入有重要影响,关注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配第(William Petty)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指出,人的素质的差异会使生产力也不同(1)[英]威廉·配第:《政治算术》,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3页。。魁奈(Francois Quesnay)也发现了培养人才的必要性,他指出:“构成国家强大因素的是人……,人本身就成为自己财富的第一个创造性因素”(2)[法]佛朗西斯·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6页。。亚当·斯密(Adam Smith)对人力资本论述得较为详细,他表示,个人经过教育而获得的技能和知识是固定在学习者自身的资本。自身的技能和知识是其财富的组成部分,与土地和机器相似,都是国家的固定资本。投入一笔资金进行学习,通过学习可以赚取更多的工资(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7页。。
在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形成之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提出了重要的人力资本思想。他在《经济学原理》中对人的技能及能力作为一种资本的经济涵义作出新的解释,他指出:“老一代经济学家对于人的能力作为一种资本类参与生产活动的认识是十分不足的”(4)[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8页。。马歇尔把个人的能力分为通用能力与特殊能力,通用能力是智力与知识、责任力、决策能力,特殊能力是工人的体力与熟练度。他同时说明了人力资本投资的长周期慢回报和家族以及政府的作用,用替代原理来说明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的选择,等。
二、西方人力资本理论
(一)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
20世纪60、7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在不同研究方向上的探索都发现了人力资本理论对解释一些问题(主要是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进而对人力资本进行深入研究,建立起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雅各布·明塞尔(Jacob Mincer)在研究收入分配时注意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他是最早研究人力资本的学者之一。他在1958年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一文,该文第一次用数学模型来分析居民收入分配与接受的培训量之间的关系(5)Mincer, J. (1958).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nd Pers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 66, pp.281-302.。他从影响收入分配的视角出发,推翻了之前的理论,即收入分配主要与智力能力或者运气有关,而运用斯密的补偿理论和个人选择,个人选择与经济活动有很大相关性,在分析收入分配时不能忽视,因此将其作为研究收入分配的因素。个人选择影响个人收入分配有两种方式:一种与个人对风险的偏好有关,对风险偏好的不同导致个人收入有所差异;另一种则是由于个人在职业选择上不同而在收入上进行相应的补偿,即亚当·斯密提出的补偿理论。个人选择有很多种,对应的补偿也不同,在这里,明塞尔将培训差异作为个人选择的要素进行研究。然后通过逻辑分析得出收入分配与人力资本有密切关系,并通过实证验证这一结论。之后,明塞尔又发表了《在职培训:成本、收益与某些含义》一文,他通过对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和影响进行分析,运用实证,得出结论,即人力资本中在职培训的投资回报率很高,不低于正规教育,且投资量也很大,但是,职培在当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6)Mincer, J. (1962). On-the-Job Training: Costs, Returns, and Some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0(5), 50-79.。
西奥多·W·舒尔茨(T.W. Shultz)是因研究经济增长而关注人力资本的,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土地、资本和劳动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因素,其中土地相对固定,因此,经济增长的模型主要包括资本和劳动力两个因素。但舒尔茨从实证中发现,从实物资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三个方面,并不能完全解释生产力的提高。“二战”结束以来的研究数据也表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发现了一个相对较大的“剩余”,即资本和劳动无法解释的增长。在“二战”中受到巨大破坏的国家恢复得很快,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经济也可以快速增长。这说明还有其他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舒尔茨经过逻辑推理分析认为,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
舒尔茨也是最早研究人力资本的学者之一,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现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性,并一直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发表了关于人力资本的开创性文章,其中包括《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与经济增长》《对人投资的思考》。1960年,舒尔茨作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在年会上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主题演说,对人力资本进行了系统阐述,这是其人力资本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7)Schultz, T. W.(1961).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舒尔茨对人力资本作出了界定,对人力资本的构成进行了分析,他得出结论:人力资本是固化在劳动者自身技能、知识以及个人劳动能力的要素,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一类有效率的经济发展要素。人力资本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人员数量、从事有用工作的人员的比例以及工作时间是数量的特征。为了方便分析,只考虑影响技能、知识和类似属性的质量要素,这些要素会影响特定的人从事生产工作的能力,进而提高人工(劳动)的价值生产率,产生正回报率。人力资本对社会进步具有巨大的意义,但人力资本的获得需要成本。不管是知识还是技能、能力,都是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产物,高技能的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舒尔茨不仅定性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还利用收益率法定量测量了人力资本投资占比最大的教育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国家经济总量中,比例高达33%,说明教育对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
在《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舒尔茨把人力资本分解为五个部分:1.医疗保健设施和服务,也就是可以影响人的预期寿命、体力和耐力、精力和活动的各种支出。2.在职培训。3.正规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4.成人教育计划,特别是农业方面的校外学习计划。5.劳动迁移,也就是个人和家庭为了得到更好的就业机会而进行的迁移。不同人力资本投资形式获得的人力资本是不一样的,如前四项是通过各种支出及投资提高一个人的健康水平与知识技能等生产力水平来积累人力资本,而最后一项则是关于如何最有效地利用一个人的生产能力。
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他不但首先提出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使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学一个新门类,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且深度探究了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和方式,并在正规教育的投资收益率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进行了数据化的研究。舒尔茨对建立人力资本理论的诸多贡献,使其荣获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也有局限性。他比较注重宏观方面的分析,主要是定性分析,对微观方面的分析较少,他的理论缺乏微观上的支撑。因没有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各个因素进行具体化、数据化的分析,而显得有些空洞。在人力资本的形成方式方面,只对正规教育作出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没有对其他方面进行精确的分析,因此没有形成一般化的模型(8)Schultz, T.W.(1961).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加里·S·贝克尔(Gary. S. Becker)是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推动者,他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1960年后发表的论文及著作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力资本》(9)Becker, G.(1975).Human capital(2rdEditi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和《生育率的经济分析》(10)Becker, G. (1960).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 NBER Chapters, in: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pages 209-240.。如前所述,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宏观方面的分析,而贝克尔则主要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在《人力资本》一书中,贝克尔研究了正规教育的成本及其收益,论述了在职培训对个人及国家的经济社会意义,讨论了人力资本投资和个人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他在人力资本形成这一领域,关于各种教育、在职培训和其他类型人力资本投资过程进行的研究,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他对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贡献是:注重微观分析,弥补舒尔茨偏重宏观分析而较为缺少微观分析的局限,并且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与收入分配等方面相结合。他得出结论,在预期收益的现值大于、等于支出即成本总和的现值时,劳动者才会愿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个支出就成为人力资本投资,目的是为未来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贝克尔也对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的成本与收益以及年龄-收入曲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以实证分析对其理论进行验证,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人就业水平和经济收入的影响,提出了如何估算人力资本投资量和收益的方法。他的理论局限性主要是继续使用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的界定,没有对人力资本的本质进行分析,也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全面的研究。
舒尔茨聚焦于人力资本的宏观分析,贝克尔专注于人力资本的微观研究,而丹尼森则注重于人力资本理论的计量分析。在用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劳动和资本对国民收入增长所产生的作用时,会产生大量难以用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成本来解释的“残值”,丹尼森对这个“残值”作出了逻辑性的解释,他最大的研究成果是通过精细分解来进行计算,他得出结论:美国1929-1957年经济增长中有23%来源于教育的发展,也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积累(11)Denison, E.F.(1962).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lternatives before us. Literary Licensing,LLC.。
从总体上看,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使人在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肯定,人力资本理论重新证明了人特别是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高质量的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一时期人力资本理论的特点在于全面分析了人力资本的涵义、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以及人力资本的“知识效应”。同时,丹尼森把消费真正纳入了生产过程,把人的消费视为一种重要的投资,这一创新也带来了资本理论、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革命性变化(12)Denison, E.F.(1962).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对当时的经济学来说具有开拓性意义。人力资本理论指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人们所得到的知识和能力同样是一种资本,该资本是人力资本,区别于物质资本。一定程度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有相类似的属性。人力资本的质量更高,收益率也更高,因此人力资本是更为重要的一项资本。人力资本理论冲击了许多传统的社会观念,传统观念认为,如果把受教育当作创造资本的一种形式是对人格的践踏,侵犯人的权利,是不道德的,是对正规教育的贬低。而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指出,这种传统认识是有局限性的,教育不仅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还能增强人们工作能力,提高劳动效率,提升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还可以增加国民的收入。后来,理论界认可了人力资本理论,普遍认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思想,赞同丹尼森的增长来源计算法准确地证明了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同时也认为贝克尔的《人力资本》一书为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学科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总而言之,20世纪60年代初,在舒尔茨、贝克尔等人系统地提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后,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人力资本的成本、人力资本积累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以及人力资本和收入分配的关系等等,很快变成了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向,尤其是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在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企业和企业家理论、制度经济学等方面,人力资本理论也有重要应用。人力资本理论不仅在理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国家政策的制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各个国家日益重视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理论的广泛传播,使教育对个人经济收入和国家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巨大作用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增加教育投资日益成为各国共识。20世纪60年代后,各国政府都大幅度增加对教育的投资,以提高教育水平。
(二)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舒尔茨、明塞尔、贝克尔和丹尼森等人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和形成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此后,罗默、卢卡斯等学者从经济增长方面深入拓展了人力资本理论。1980年代后,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使信息传播成本大大降低,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对经济增长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催生了知识经济背景下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与数学知识和理论相结合,构建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
罗默和卢卡斯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他们把技术进步内生化,构建了知识积累模型,即AK(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模型。
罗默在1986年发表的文章《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出了著名的罗默模型,他把知识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引入模型中说明知识积累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方面,专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的积累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而增加,因为随着资本的积累、生产规模的扩大、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劳动者可以学到更专业化的知识;另一方面,知识具有“溢出效应”,随着资本的积累、生产规模的扩大,知识也在不断流通,每个企业都可以从其他企业或者单位、学校获得知识、技术和经验,整个社会的知识总量也因此而增加(13)Romer, P.M.(1986).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罗默构建了生产函数:
Fi=F(ki,K,xi)

根据罗默的假定条件和生产函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专业知识的积累是递减的,因此,当其递减速度大于全球技术、知识积累的增加速度时,生产规模报酬是递减的,当单个厂商知识的边际生产率等于其折现率时,经济增长是停止的;2.当专业知识积累的递减速度恰好等于全球技术、知识积累的增加速度时,生产规模报酬是不变的,也即经济会按一个固定的常数增长;3.当专业知识积累的递减速度小于全球技术、知识积累的增加速度时,生产规模报酬是递增的,增长率增大,模型是发散的。
罗默构建的模型可以把知识技术进步内生化,但其有两个缺点:首先,这个模型最终是发散的,所以没有均衡解;其次,该模型认定知识积累即资本积累的函数,也就是国家资本越多,其增长就越快,与经济现实不符合(14)Romer, P.M.(1990).Endogenous technology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卢卡斯在1988年的论文《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中,明确提出其经济增长模型(15)Lucas, R.(1998).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卢卡斯把舒尔茨定性的人力资本理论和索洛提出的技术决定论的增长模型相结合,并加入自己的思想,发展形成了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即:
h'(t)=h(t)δ[1-u(t)]
上式中,h(t)为表现为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h’(t)为人力资本的增量,δ是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u是全部的生产时间,[1-u(t)]为脱离生产的在校学习时间。
上式说明:若u=1,那么h'(t)=0,即没有人力资本积累;若u(t)=0,那么h(t)按δ的速度进行增长,即h’(t)达到最大值。因此,卢卡斯在模型中认可工人在非生产时间从非正规的或正规的学校教育及培训中积累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人力资本研究的重大贡献是把人力资本作为变量融合进增长模型中。1960年代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的人力资本理论也提及经济增长的问题,但他们没有将人力资本和教育看作内生变量,而是将其当作外生变量,因而无法构建定量模型。罗默和卢卡斯则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其经济增长模型中,同时也克服了经济均衡增长取决于劳动力增长率这一外生变量的缺陷。
(三)人力资本测量
人力资本是在个人身上体现出的有助于创造个人、社会和经济福祉的知识、技能、能力和属性。人力资本的定义是较为简单的,但其测度却比较困难。如果无法准确地测量人力资本,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政策则不能体现其科学性。因此,摆在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面前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测量不可直接观测到的人力资本?
现在,常用的人力资本测量方法有六种,六个不同的项目,可归为两类:一类是基于货币的测量方法,有两种:CWON(The Changing Wealth of Nations 2018)和IWR(Inclusive Wealth Report);一类是基于指标的测量方法,有四种:WB HCI( the World Bank’s Human Capital Index)、UN HDI(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Index)、IHME HCI(Institute of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Human Capital Index)和WEF GHCI(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Human Capital Index )(16)World Bank.(2018).The human capital project. Washington, D.C.USA.。
CWON使用终生收入法计算人力资本,货币计量的基准为2014年的美元。对于工资的确定,首先通过应用Mincer方程的估计参数得出了按年龄、教育和性别划分的工资状况,然后根据各个机构数据库提取的总就业和雇员薪酬来确定估算的工资值。其具体公式如下:

该方法研究的是一个人的终生收入,在此方法的假设中,工资及人力资本由年龄及受教育年限决定,收入可根据此人每年的收入加总得到,等于当年收入+未来收入,未来的收入由存活率、年龄及受教育年限决定,由此来测量个人人力资本。
IWR计算与教育相关的人均人力资本,以此来衡量人力资本存量,货币计量的计算基准是2005年美元的购买力平价,其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he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E”的人均人力资本,ρ为教育回报率,P5+E为受教育程度等于或大于E的人口,w为员工的平均薪酬,T为预期的工作年限,δ是折现率,P为总人口。
此测量方法只研究平均受教育年限为E的人均人力资本,其等于总的人力资本除以总人口。总人力资本用工资衡量则等于受教育年限为E人的人力资本乘以平均薪酬再乘以平均教育年限为E的人数。
WB HCI是一个指标,该指标的子指标包括教育和健康,WB HCI的值在0~1之间,1代表最理想的情况,因此指标的实际值体现了和理想情景的差距。该指标衡量的是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情况,以此来说明当前教育和健康投资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WB HCI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p为当前出生孩子存活的概率,p*为全部存活的基准,等于1,Φ为每多上1年学的生产率提高值,SNG为预期未来教育的年限,S*为完全的有质量的调整教育基准,等于14年,γ为每增加一个健康指标,生产率的估计回报率,ZNG为预期的未来健康,Z*为完全健康的基准,等于1。
该方法主要研究如今实际的人力资本水平与理想状态下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从存活率、受教育年限和健康水平三个方面进行比较,人力资本水平可用存活率×教育的投资回报×健康的投资回报。
UN HDI的指标的子指标包括健康、教育和收入,通过标准化指数的几何平均值得到。UN HDI关注的是当前的发展状况,其3个子指标是同等重要的。
IHME HCI也是一个指标,该指标的子指标包括预期寿命、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和教育水平,该指标衡量的是某新生儿队列的预期人力资本水平。
nLxt为第t年x年龄组的预期寿命,FHxt为第t年x年龄组的功能健康状况,转换为0到1的量表,l0为开始的新生儿队列,Eduxt为第t年x年龄组接受的教育年限,Learnxt为第t年x年龄组的平均标准化考试成绩,转化为0到1的等级。
该方法研究的是某新生儿队列的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由健康和教育决定,等于平均健康水平乘以平均教育水平,一个人的健康水平等于预期寿命×功能健康状况,平均健康水平等于总健康水平/人数,平均教育水平同理。
WEF GHCI的子指标是能力、部署、开发和技能,每个相应的子指标都通过使用多个指标并遵循与以下公式基本相同的公式来构造。4个子指标在总体GHCI中的权重相等,而这些子指标中针对特定年龄组的数据则按人口加权。
这六种人力资本的测量方法不管是基于货币还是基于指标,都各有优劣,既要考虑选取的要素及比重,还要考虑要素的可计算性。由于数据统计的困难,各种人力资本测量方法有许多要素没有放进模型里,最常用的指标是教育、培训和健康等,但人力资本的其他要素,比如劳动迁移成本、医疗成本等要素没有纳入指标,这是以后使人力资本测量更精确化的研究方向。
回顾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有早期人力资本思想、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结合、人力资本测量等研究方向与发展阶段,不同时期的人力资本的主要研究方向和目标是不一样的。其主要历程是先有对人力资本的模糊概念,而后形成更精确的定义,初步形成人力资本理论,此后则将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现在则重视人力资本的精确测量。将人力资本理论更逻辑化、精确化,能更好地衡量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同时也可以使经济增长理论更精确、更完整。
三、中国人力资本理论与应用
中国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认识相对较晚,20世纪80年代才对西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研究,目前更多的是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实证研究。
(一)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西方已经构建了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我国学者通过对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发现,其建立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时,要么专注于教育,将人力资本指标单单看作学校的正规教育,要么强调健康,但没有对人力资本作出具体的构造。杨建芳、龚六堂等学者在对经济现象及现有理论进行详细分析后,建立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即人力资本由正规教育和健康水平按照道格拉斯形式的组合构成(17)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验》,《管理世界》,2006年第5期。。且在该内生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都对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杨建芳、龚六堂等学者首先建立了加入人力资本的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利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构造:Y=KαHβ(AL)1-α-β,并对其进行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参数并不符合索罗模型,也就是加入人力资本的索罗模型并不能描述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β值高达0.83,虽然说明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但显然是对人力资本的高估。杨建芳、龚六堂等建立的加入人力资本的索罗模型是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单独的生产要素引入生产函数,只考虑了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加入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将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完全归于人力资本积累,因此高估了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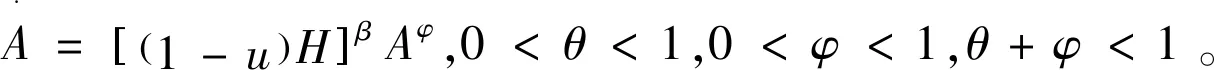
运用改进后的内生增长模型对我国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85-2000年每隔两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及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相似的,因此,研究人力资本及进行实证分析时需要综合考虑教育和健康两者的作用,必须兼顾两者才能得出正确结论。β的预测值大于α,说明人力资本积累比物质资本更能促进经济增长,但物质资本积累速度远远大于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因此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物质资本贡献的28.8%。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协同贡献高达40%,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影响。
(二)人力资本测量
人力资本测量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十分重要,不仅能够验证之前提出的理论是否正确,检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能够通过运用具体数据来指导政策的制定,还可以以此来计量每个地区的存量及积累速度,进而构造各级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绩效指标。在世界经济发展低速的环境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愈加重要,各国对人力资本更加重视。国际上对人力资本度量逐渐完善,中国人力资本测量研究可以与国际合作,以加强国际影响力。对人力资本的精密测量也可以完善中国国民账户,在中国资产负债表中完善人力资本的指标。
国际上已经有许多较为成熟的人力资本测量方法,中国的数据统计工作较为落后,很多数据是缺失的,测量系统也未建立,国内学者只能通过现有的方法及数据对人力资本进行精度有限的估计。主要有收入法、指标法,或者直接采用教育水平法来估计人力资本水平,这些为研究中国人力资本测量及存量和分布作出了较为重要的贡献,但也存在很大短板,由于数据不易获得、参数估计存在难题、技术方面也存在困难,因而没有形成完整的人力资本测量体系,中国的人力资本测量方法也没有被国际社会所认可。李海峥、梁赟玲等研究了国外人力资本测量方法,结合中国数据改进终生收入法,对1985-2007年的人力资本进行了测量,并预测了2008-2020年的人力资本水平(18)李海峥、梁赟玲、Barbara Fraumeni、刘智强、王小军:《中国人力资本测度与指数构建》,《中国经济学》,2010年第8期。。
终生收入法是将个人预期生命期的终生收入进行折现加总来衡量一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如果人力资本有价格,那么其价格必然等于个人可以获得的收入,以此用货币衡量人力资本水平。使用终生收入法可以更好地利用人力资本的各个指标,包括教育、资历、健康情况等,比单纯的指标法更加全面完善。李海峥等学者将生命周期划分为5个阶段,不同阶段使用不同的计算公式来测算人力资本,且从后往前,先计算最后阶段的收入折现,依次向前计算,最后加总。还可以根据性别、地区、城乡等划分成不同群体,分别对参数进行优化,从而使人力资本测量更加精确。
生命周期的5个阶段分别为退休状态(男性60岁及以上,女性55岁及以上)、工作但不接受正式教育(25岁以上但未退休)、上学或工作(16-24岁)、上学无工作(6-15岁)、不上学也不工作(0-5岁)。其指标分别为存活率、年龄、升学率、受教育年限。
经过对1985-2007年中国城乡的实证分析,估算中国1985-2007年的人力资本总量与GDP及固定资本的比值。发现人力资本与GDP的比值在总体上是下降的,1985年占比30%,此后逐步下降,2007年只有18%,其原因是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小于GDP的增长速度。
(三)人力资本错配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如果人力资本错配则会导致人力资本的浪费,降低人力资本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当今中国技术密集型部门和产品生产部门之间的人力资本错配问题是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问题。李静、楠玉等学者在研究中国人力资本的配置与效率问题时,提出中国如今的人力资本的增长已足够大,质量也有非常大的提升,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已经排在全球前15位,但研发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与其他高研发投入的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研发资本与研发人员之间存在错配。另外,研发人员在行业之间也存在错配的问题,最需要高精尖研发人员的计算机与电子行业以及制药业与美国等国家相比占比较低(19)李静、楠玉:《人力资本错配下的决策:优先创新驱动还是优先产业升级?》,《经济研究》,2019年第8期。。
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实现蛙跳增长,减少与高技术国家的技术差距和经济增长差距。但通过实证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技术落后国家与技术先进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一直在拉大,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时有很大阻碍。高精尖技术不是单独存在的,更多的存在于以人为载体的人力资本中,而引进的先进技术与原本的人力资本不匹配,则会导致引进的技术无法落地。因此,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引进的技术能否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如果不考虑人力资本水平而盲目引进高精尖技术,则会使技术与人力资本不匹配,无法促进经济增长。因此,需要测量并了解人力资本水平和优势,引进相应的技术,以促进经济发展。
李静等人不仅从定性角度对人力资本错配进行分析,而且建立了对应的模型,对消费者、教育与人力资本错配,劳动力类型与人力资本的市场失灵,政府行为、中间品部分的转型和错配的解决等问题进行建模分析,并讨论了人力资本完美匹配下的经济增长。李静等人分析的前提假设是经济转型中,代表高质量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其供给会不断波动;转型过程需要政府规制技术密集型企业,促进其向创新型企业转变。
李静等人建立了迭代模型,消费者存活两期,第一期教育并就业,第二期只消费。在此迭代模型中,受教育者得到的工资超过不受教育者很多,大家才会选择接受教育,与经济增长预期没有关系。如果只靠市场配置,人力资本的需求和工资水平都是由厂商利润最大化决定,人力资本的错配乃至零供给都是有可能的。且如果企业一直靠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进行生产,依赖市场配置资源则会导致人力资本供给不足到人力资本供给过剩的阶段。这也说明了政府干预市场的原因,单纯靠市场无法保证人力资本的供给,单纯靠市场保证人力资本供给又会带来错配。政府通过税收对消费者接受教育进行激励,通过知识产权对企业进行补贴,从而实现人力资本适配。解决了人力资本错配问题,人力资本完美匹配,则会促进经济增长。
(四)人力资本分布与收入不平等
工资收入的分配和不平等问题既关系到经济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稳定、人民幸福。通过经验数据发现,发达国家的收入和工资分布都是呈现“橄榄球型”,而不发达国家的收入分布状况则呈现“金字塔型”,且当同一经济体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进程中,工资收入分布状况也会逐渐从“金字塔型”向“橄榄球型”转变。
王弟海、龚六堂等人研究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投资回报率对教育成本和收益的影响,经济发展对工资收入分布状况和不平等的变化的影响。当经济处于低速发展时期时,由于资本相对缺乏,利率水平(即资本投资回报率)很高,个人教育投资的成本相对较高。因此,需要较高教育年限的职业(以下简称高教育职业)的工资收入同需要较低教育年限的职业(以下简称低教育职业)的工资收入会相差很大。一方面,为了使高教育职业具有很高的工资收入和教育回报率,在教育投资成本较高的情况下,高教育职业人数相对少于低教育职业人数。所以,在经济低速发展时期,工资和收入分布会呈现“金字塔形”,不平等现象也比较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的积累使利率水平(投资回报率)不断降低,个人选择高教育职业的机会成本也不断下降,高教育职业和低教育职业的工资差距会不断缩小。另一方面,高教育成本的降低也使选择高教育职业的人数增加。在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和工资分布逐渐由“橄榄球形”向“金字塔形”过渡,不平等现象也逐渐改善。
此外,王弟海、龚六堂等人还研究了教育选择和职业分化对持续性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因教育不同而出现职业分化的情况下,由于不同教育年限的成本不同,即使个人的所有其他特征都相同,也会出现工资和收入的持续性不平等。这种由于生产方面的性质决定的持续性不平等,同个人偏好、能力和年龄的差异所导致的差异一样,是不可能消除的。
四、结语
人力资本理论对解释经济社会现象有重要意义。将人力资本内生化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可以更好地说明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经济增长,同时,利用人力资本理论也能对收入分布等社会现象进行模型构建,而模型的精细化又要求对人力资本的精确测量,进而促进人力资本理论的科学化、准确化。
人们已经认识到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在物质资本成本和回报率不断降低的背景下尤其明显。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者质量,使其与经济发展相匹配,以推动经济发展,已成为社会共识。
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各国日益重视通过教育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教育投资等。除教育外,健康也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投资形式。
人力资本供给与需求匹配越来越受重视。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当今人力资本数量及规模庞大,但技术创新仍有所欠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力资本投入与实际需求不符,人力资本供给与经济发展需求不符,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存在偏差。除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外,提升人力资本供需的匹配度应成为国家重视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