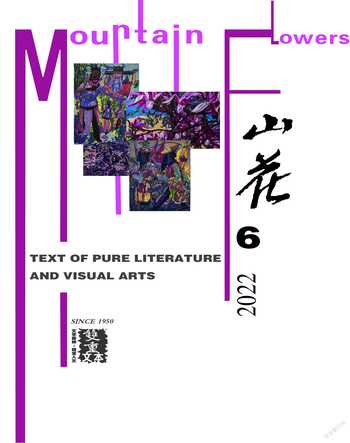城市之光
吴文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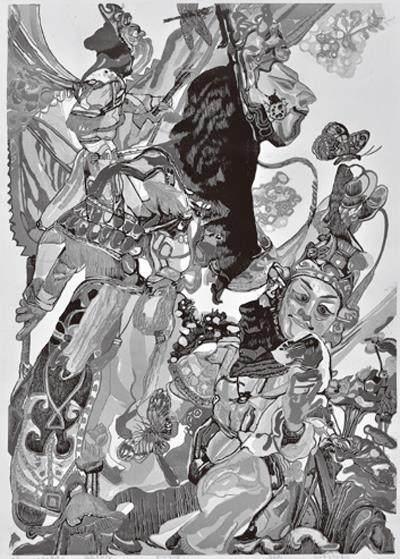
到洛杉矶后,发现“最后一家书店”就在旅馆附近,走过去不到一公里。
好多年前,我也算是喜欢逛书店的人。有一年去北京,碰上大雪天,最后一晚从王府井书店出来,手里拿着精装本的《局外人》,就好像蓝色封面上的加缪在无声地指引我,完全感觉不到扑面而来的风雪寒气;祖母还在世时,每次去上海,坐地铁1号线到陕西南路下,看到季风书园敞亮的玻璃门,最新出书的大幅海报,我总要进去待一会儿;尤瑟纳尔的《何谓永恒》是在淮海路的三联书店买的,说不清为什么,只是推开那扇门,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和外面的世界或者不如说和时间完全无关的地方。
有时,我觉得我是没地方可去才去书店的;有时,又相反,觉得我就是因为喜欢去书店,才不愿意去别的地方。
即使这样,渐渐地,为了少花点钱,在书店看到想买的书我也不买了,而是记下书名,到网上去买。正是因为我这样的人太多了,才导致了书店的减少吧?其实书店存在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买书这么简单。书店是有自己生命的,和作為单体的书一样,有着自己的灵魂和意志,而读者,只不过在跟随和寻找与自己相近的灵魂和意志罢了。
可我又能怎么办呢?实体书店因无以生存而减少,这种窘境在洛杉矶看来也差不多。
反正时间充足,本也想专门留出半天给书店,这天,逛了时报大楼、小东京回来,走到一个街口,看见书店就在对面拐角上。
没错。是“最后一家书店”。是这儿。
门厅很小,光线也很昏暗,存了背包,走到里面,却是一个空间巨大的所在,感觉就像放大数倍的王府井书店或者季风书园。二楼做了中空设计,十几根白色的大圆柱分布其间,书架像琴键一般依次排开,柱脚边的空地成了摆放座椅的好地方,不过更多的人还是选择坐到相对边缘一点的地方,放上一堆书,再细细地挑选,就此消磨一下午也很不错。
有趣的地方在二楼,走在走廊上,看着抽象的现代派绘画,全然料不到会走进满是魔幻风格的地方,就像一不小心来到了霍格沃茨的格兰芬多学院。果然有间密室般的小屋,绿色的墙,用过十几个世纪的古老书架塞满深红色封皮的书,射灯和一盏躲在角落里的落地台灯配合着制造出幽暗神秘的气息,好像哈利·波特刚刚还在这里,和他最好的两个朋友密谈;或者,刚有一个修士,挟着书神色冷淡地离去,留下几缕难以捉摸的气息。小屋中央有一张同样古老的长条凳,我却不敢坐下,感觉每本书都沉默地以不同的波长和频率打量着我,在问我是谁,是不是有勇气探知隐藏在神秘或神圣经典里的未知之谜。奇怪的是,在我逗留的那一会儿里,始终没人进来打断我的臆想,直到一个力量把我赶了出去——你可以走了!是的,我就是来看看的,那么,看过了,可以走了。整个二楼都由各不相同的神秘空间组成,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顺从地被推入下一个空间,始终没有遇到同行者。这个神奇世界的最后一环是一个由成千上万本书搭起来的拱廊,仿佛接受书给予的意想不到的洗礼,作为一个喜欢书的无知者,我既兴奋又惭愧地穿过那里,回到日光灯照射的现实世界。
这家书店之所以出名,还因为数量庞大的二手书和黑胶唱片。有几张唱片光看封套图案就很心动,只是,我也没唱机呀,兴趣所在——仍然是书。随机地抽出一本,一看,是个短篇集,作者欧内斯特·凯恩斯,之前从来没有读过,排在五个短篇之首的是《十一月漫长的一天》——此时正好是十一月,这不也是我的十一月的漫长的一天?其后几篇,连我这种词汇量少到不够阅读的人也能不费力地读出来:“灰色的天空,就像一棵树。”多好的篇名!当然,肯定的,就买这本吧。
此次孤身旅行的每一天都是“十一月漫长的一天”。
不同于临时遇到的“最后一家书店”,几天后,沿海岸线到了旧金山,“城市之光”是出发之前就写在行程计划里的。
虽然,我只是知道——而不是读过——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至于《金斯伯格文选》,多半是冲着封面上那句“深思熟虑的散文”(想弄明白怎么样算深思熟虑)买回来,没等读完,就搁到书架上去读别的书了,仅仅知道这个秃顶大胡子因为诗集《嚎叫》掀起过“垮掉的一代”文学巨浪,出版这本诗集的城市之光也成为了先锋文学的圣地。
在木心的《文学回忆录》里,“垮掉的一代”大约占了三讲的容量:大战后遗症;人性崩溃的普遍现象;既破坏社会,又残害自己。即使如此定义,木心也不否认对凯鲁亚克的喜爱,“他不做家禽,要做野鸟、野兽”,“他写成十八本小说,有种。晚年回到现实主义,有心肠,有头脑”。
尽管《金斯伯格文选》的译者认为“垮掉的一代”所导致的误读、曲解在于:中文“垮掉”一词总让人联想到:堕落,颓废,没落,腐朽,败坏……可是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Beat Generartion所传达的并不是简单的“垮掉”就能表示的,以缩略语BG代之更为恰当。然而“垮掉”的印象一旦在脑中成形,不是轻易能改的。印象里从来没有跟人聊过他们、他们的书。 “垮掉的一代”对我来说更像一张标签,贴在地球另一面的某处,是世界文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是印在历史纪年里的一个我其实并不明其意的词汇。
一家老书店,曾经大名鼎鼎且硕果独存的独立书店,1953年开设创办以来,已经有六十多年历史了。除了是“垮掉的一代”的大本营,这里还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平装书店,储存流通过大量的现代经典文学作品;也是诗人、作家和活动家的集会场所,先锋书籍和思想不断萌发之地;还是旧金山文学的风向标、核心地带和精神指引。
如果还算是读过几本书,到了旧金山就必须去一趟城市之光,好像是这样吧。
这天我给自己设定的路线是:城市之光书店——圣方济亚西西堂——圣彼得圣保罗教堂——北滩,意大利街。吃好早饭从联合广场附近的旅馆出发,沿着格兰特大街直走一公里路,左转,走过短短的凯鲁亚克街,看到满是涂鸦的那面墙就知道到了。
两个徒步旅行者,一对年轻的情侣,卸下背包,半躺半坐在城市之光的图标下。我羡慕穿红衣戴绒线帽的女子,大概他们从很冷的地方来,可以坦然地在此短暂入睡。绕过他们,转向朝着哥伦布大道的书店正门。261号,“City Lights Books”,尽管我更习惯于从“光”的笔画中找到光,而不是从“light”中找到光。棕色钢质门窗,天色把玻璃一角染成鲜亮的蓝色,橱窗里陈列着书和海报。门厅很窄,两个店员站在柜台后面小声交谈。互相问过好,我往右边的书架转过去,感觉就像走进上海随便哪一家书店,只除了让我觉得头晕眼花的英文书目。0ACCFF6C-45F8-4E25-9A51-820836312E3D
好在,度过最初的不适应期,我还是从摆放有序的书中认出了詹姆斯·鲍德温,伟大的非裔美国小说家,一个“真正的必不可少的”作家,可我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只是看了看面朝读者摆放的那本,是叫《街上的无名者》?(中文译名是《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
之后,我几乎有点兴奋地认出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就像我认识她似的。其实我只读过她的《猫眼》和《使女的故事》。这几本应该刚出版不久,是叫《帐篷》?《石床垫》?和保罗·奥斯特的书摆在同一格架上。没想到奥斯特的书这儿有这么多,我差点想买下企鹅出版的他的《玻璃之城》。至于“手和嘴”——肯定不是这么翻译的,不知道有没有中译本;《幻影书》,我已经读过了,译者是我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
我还想找找门罗,可惜没有找到。
算了,这些书,就我这点英语水平,买了也只能当成纪念物,而不是读物。
在这里,最应该买的不是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吗?
通往二楼的楼梯墙上挂着老照片,有鲍勃·迪伦和金斯伯格拍于1965年的合影,大概是为了专辑而拍的一系列照片中的一张。那时的鲍勃才二十四岁,想必不会想到五十一年后会以“民谣歌手”“吟游诗人”的身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金斯伯格那时就已满嘴大胡子,竟有几分像莎士比亚——他的确曾和莎士比亚一起在正统且有分量的《哈佛评论》里同时受到批评家的礼遇——也有几分流浪汉气质。下面一张是尼尔·卡萨迪的单人照,面带笑容,沐浴在加州极其灿烂的阳光下。回来很久了,我才知道凯鲁亚克对佛教的兴趣正是开始于和尼尔·卡萨迪的相识之后。
刚到营业时间,人很少,二楼更是几乎没有人。书架上全是诗集,简直就是个诗歌小屋,窗边有小桌和摇椅。这里更适合找本书,懒散地坐下来,看,或不看,沉思冥想,发呆,看太阳,任脑子里的念头冲来撞去都行,没人会来管你。没人会来干涉你,认为你不合适待在这儿。
可是单词组成的墙透明而确凿地竖在面前,变成结结实实的障碍。不好好学英语果然不行啊!我甚至没发现还有地下一层,又逗留了一会,觉得吸足了书的气息,就出来了。
晚上查到“垮掉的一代”博物馆就在边上大约一百米的地方,隔天又重走了这段路,补拍了几张书店的外景,拐了个急弯,找到百老汇大街540号。
站在门口望进去,突然之间像倒退了三四十年,回到1990年代或1980年代的某天。还不只是时间的问题,真的有些破旧啊。这地方显然首先是一个书店和纪念品店。我差点又想买本书,差点又忘了我读不了。博物馆在一块布帘后面,买了票,唯一的一个管理员示意我可以进去参观了。
我还是有点局促。可这有什么好局促的?和我所在的小城的名人纪念馆相差不大,掀开帘子,就像进了一所有些年头的私宅。一个大房间划出的走道,玄关,会客室,住过工作过的痕迹被完好地保留下来,完好到觉察不到主人已经离开了很久,而且再也不会回来。
墙上的照片记录着他们的某个重要时刻;“去他妈的讨厌”装进了镜框;还有怎么都少不掉的“HOWL”,和中文的“嚎叫”读音上出人意料地相似和相通;橱窗里摊着手稿,桌上放着用过的印章、打字机。
在这里,金斯伯格的光芒盖过了凯鲁亚克。早在1959年的美国独立日上,大胡子就铿锵地说出:“美国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崩溃,诗歌才是人类洞察自身灵魂处秘密的真实记录。”“因为物质主义而发疯的美国,……已经不再是惠特曼笔下那野性而又美丽的美国,不是梭罗笔下的那有历史意义的美国——在那儿,每一个人的独立精神就是一个美国。”嚎叫了很多年后,1973年,大胡子的诗集《美国的衰落》问世,次年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也是这一年,他成为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尽管政府和某些主流批评家仍然不那么喜欢他,可事实是,他已经堂而皇之跻身于主流。对他最确切生动的一条总结是:“总体来说,金斯伯格的诗犹如X光线,四十年来美国社会主体的相当大的部分都被它透视无遗了。”(海伦·文德勒)
无法否认,曾经饱受人们嗤之以鼻的反叛诗人及其坚持的BG理念、价值观,包括生活方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主流社会认同,还跨越时空,在世界其他地方产生持久的影响。
这就是“垮掉的一代”真正的价值吧?
金斯伯格的一张漫画像摆放在醒目的地方,随便待在屋子的哪个方位都能看到他那标志性的秃顶和大胡子,他戴着一串佛珠,手舞足蹈。对,是佛珠,差点忘了,大胡子和凯鲁亚克可都是佛教徒。
皈依了佛教的金斯伯格不但在人生理念方面(比如生与死等问题),而且在革新英语诗歌方面,从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佛教禅宗那儿也大受启发。不懂中文,并不影响他喜欢阅读中国古典诗歌译本(比如白居易的诗)。
凯鲁亚克在求佛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点。他曾以书信的方式提醒金斯伯格,苦难是生存的基石,这是佛教最首要的真理。很难相信,真是很难相信,写《在路上》的凯鲁亚克会总结出佛教對于存在的三大条件:首先,存在包含着苦难;其次,是无常,周围环境的转瞬变幻;第三,自我,没有永恒的自我。即没有任何形式的永恒,所有存在的基础都是变幻的,没有永恒的小我,也没有天堂里的大我。除了宽阔的宇宙,别无他物。
不仅如此,他还曾在著作中多次提到佛教的四大圣谛。除了上述的苦难、无知和苦难总有终结、解脱的办法,还总结出解脱苦难的八正道:正见,正觉,正言,正行,以及我无法归纳为两个字的正确的劳作、正确的思考、正确的精力和正确的等待。
和我之前读到过的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不完全一样。就禅宗或是经典佛教渊源而言,凯鲁亚克没有老师,他是靠着自己的直觉去了解佛教的。庇护——这是凯鲁亚克对佛教最基本的理解:“在佛中,我找到了我的庇护;在佛法中,我找到了我的庇护;在冥思者中,我找到了我的庇护。”很少有批评家评论他,难得有人采访他,少有试图去了解他的传记作者能够问及其佛教思想和其根据。不过,还是可以引凯鲁亚克常常从《金刚经》中引用的一句话来概括:所有关于存在本身的概念,不存在本身的概念,至高存在本身的概念,至高不存在本身的概念,都只是概念,是随心所欲的。0ACCFF6C-45F8-4E25-9A51-820836312E3D
身边传来脚步声。一对父子——也可能有三个人——用比我快得多的速度一边看,一边走到前面,不见了。
那么,还是有人会来这里——“垮掉的一代”博物馆,集结了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和光辉的地方,一个地板踩上去空空作响的房间,一架其实由别人捐赠而并不是金斯伯格弹奏过的钢琴,一个空寂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有人进来的地方。
早先这里就是艺术画廊,画作遍布其间,在一扇注明后面是煤气表室的门上有一幅城市街道图,扭曲的房子,扭曲的云朵,像凡·高画的,也像在南加州读文学博士的上海作家钱佳楠的手绘风景。还有一幅画是身穿蓝衣服站在蓝色背景前的凯鲁亚克,像极了毕加索蓝色时期的风格。
——走到这儿,已是参观线路的终点,一辆车停在眼前。不易觉察的时间之灰落下来,悄悄覆盖在上面,给它添了一些疲倦,一些沉静。我知道这不是凯鲁亚克“在路上”的那辆车,可我还是相信这就是那辆魔幻般的汽车,让凯鲁亚克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主义,即使它现在已经永久地停下来了,而他也早已消失在那条路的尽头,杳无踪影。
没有不改变的物质,人不仅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甚至“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凯鲁亚克通过《最后的话》写出了他的领悟:……莫扎特和布莱克也常常觉得不是他们自己在执笔,而是缪斯在歌唱,在写作……当艺术作品在时空一体中顺着思维而流动时,就达到最好的效果。……要用言语来打破语言的障碍,你得沿着你自己的思维轨道。
沿着你自己的思维轨道——可能这就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了。
离开博物馆之前,唯一的管理员表达了对我的感谢,如果我的英语好一点,我会告诉他,嗯,他们影响过很多人,或者也正在影响我。不过,我想我看到了他的诚恳,他也一样看到了我的诚恳,虽然我什么也没有说。
走进书店,到走出书店;走进纪念馆,到走出纪念馆,只过去短短的一个多小时,身和心似乎起了微妙的变化,我不再是一个多小时以前的我,很难像医生诊断疾病那样明确自己到底被什么改变了。马路上一切如常,三三两两的人,带着陡峭坡度的马路,常常让我误以为在上山。上山,下山。远处层叠在一起的高高低低的房子,从房子的间隙里露出湛蓝平静的海水。我仍然是一个人,一个游客,想要像格非说过的那样,“到一个遥远的地方,才能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这地方没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所有的人我都不认识,或者刚刚认识就要离开他们,Nita ,多米娅,每天笑容可掬问好的旅馆值班经理……然而我一点都不孤独,走在若干天以前还只是地图上的直线或弧线上,像一条鱼,游在陌生的水域,无数色彩斑斓的鱼从我身边游过——这就是那些天我在路上的感受。
回来很久之后,查了资料,我才知道,城市之光书店的创始人劳伦斯·费林盖蒂本身就是一位成就卓著的诗人,一生获奖无数,入选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院士,被旧金山市授予桂冠诗人称号。除了诗人、出版人,他还是画家、小说家、剧作家、文艺批评家、和平主义者、活动家,以及海军军官。正因为选书的标准不是“会畅销的书”,而是“城市之光书店认为应该畅销的书”,书店得以在互联网和流行文化的夹缝中坚守,并保留住自己独特的气质。
2020年4月,我被一则澎湃的新闻惊到,难以相信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令城市之光陷入了危机。书店自3月份关门停业以来,现金流完全断绝。书店为了员工的利益,不让员工接受和处理网络订单,同时停业期间坚持全额发放薪酬,使得现金消耗巨大,已难以为继。为此,书店在4月9日发起了众筹,目标是筹款30万。好在众筹上线不到12个小时,已经筹集到11万美元。尽管城市之光的创始人劳伦斯·费林盖蒂,这个一生致力于找到自己聲音的人,已于2021年2月22日去世,享年101岁,书店终究生存了下来。无论是“城市之光”,还是“最后一家书店”,至少直到目前都还在开门营业。
多久没在书店买书的我,只想以便宜的价格多买几本书的自私的我,仍然期望一家开了很久的书店存活下来,不要被奶茶店、披萨店、麻辣烫店取而代之;期望这家书店的一个书架里仍然找得到小说诗歌;期望这家书店把我指向哪本书,而不是我自己想读哪本书。是不是可以说,一家书店,是一座城市不可缺少的一点光芒?好在上海依然有三联书店,杭州依然有晓风书屋,苏州依然有诚品书店。虽然求知书店和席殊书屋已从我所在的小城消失很多年,但新华书店却换了一种姿态,吸引着我走进去,找个地方坐下。
一本本出自不同之手的不同的书,以它们的存在,冲淡我在生活中遭遇到的昏暗。从少年到现在,一直是这样,没有变过。0ACCFF6C-45F8-4E25-9A51-820836312E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