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地球已48小时了
斯科特·凯利 玛格丽特·拉扎勒斯·迪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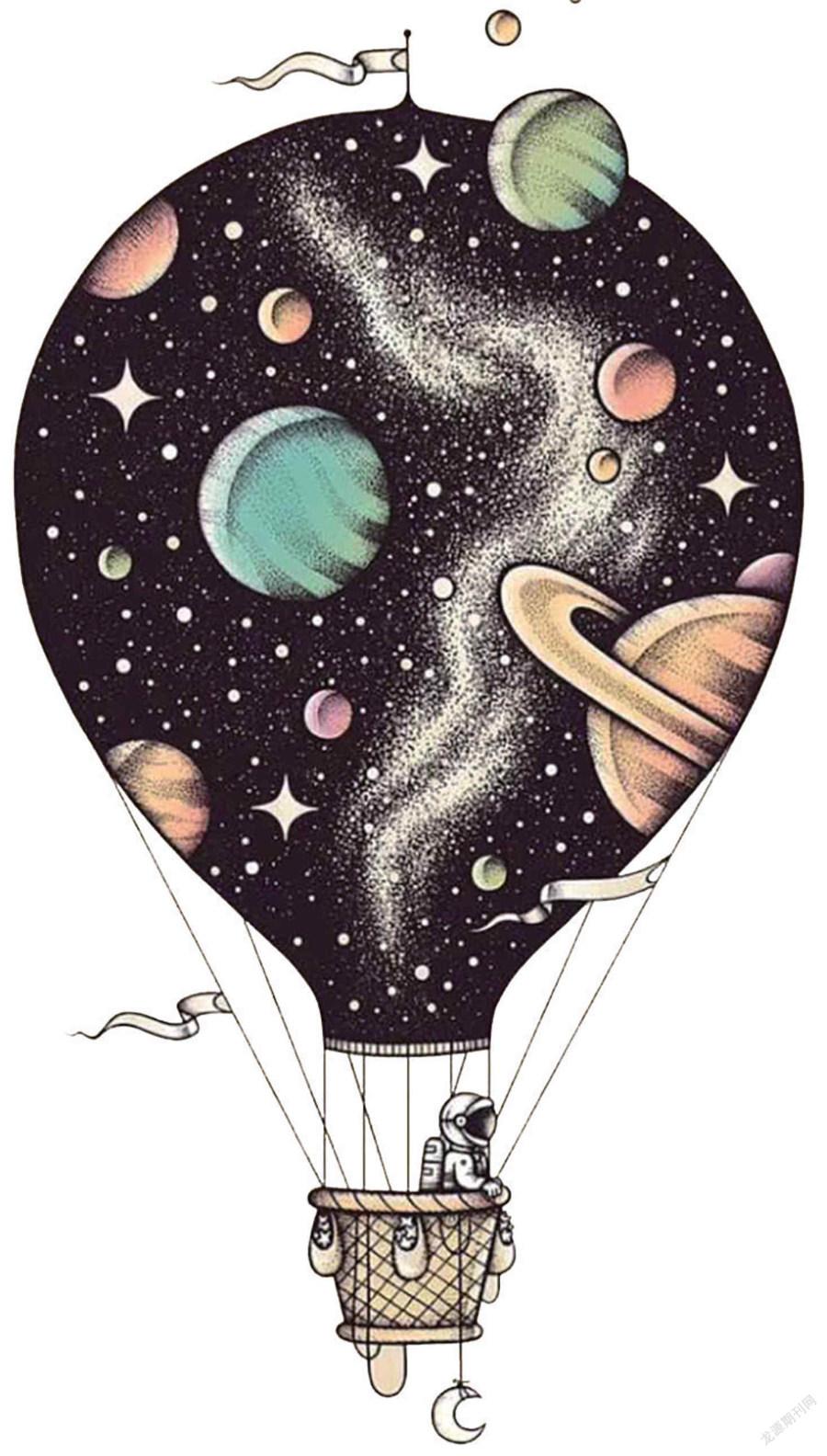
此时此刻,在休斯敦的家中,我坐在餐桌的一端,与家人一起共进晚餐:我相恋多年的女友艾米蔻;我的女儿萨曼莎和夏洛特;我的双胞胎兄弟马克,还有他的妻子嘉贝丽,他们的女儿克劳迪娅;我的父亲里奇,以及艾米蔻的儿子柯宾。
坐在餐桌边与你爱的人一起吃饭,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许多人每天都在做,无须多加思考。但对我来说,这是一年来我梦寐以求的事情。我无数次地幻想着吃这顿饭的场景,现在终于美梦成真。
不过,这一切似乎并不完全真实。我许久未见的所爱之人的脸,大家的闲聊声,银质餐具的叮当声,玻璃杯中的葡萄酒——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即使重力使我坐在椅子上,这种感觉也很奇怪。每次把玻璃杯或叉子放到桌上时,我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些尼龙搭扣或胶带把它们固定住。我回到地球已经48小时了。
我撑着桌子,努力站起来,感觉就像一位老人离开躺椅。
“我吃完了。”我对大家说。大家哈哈大笑,劝我去休息一下。我开始了通往卧室的旅程,从椅子到床约有20步距离。走到第三步的时候,地板似乎猛地一颤,我撞上了花盆。这当然不是地板的错,只是我的前庭系统正在努力适应地球的重力。我正再次习惯于走路。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绊倒,”马克说,“你做得很好。”对于从太空返回重力環境是什么感觉,他也有经验。我从萨曼莎身边走过,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她对我笑了笑。
我顺利到达卧室,关上门。浑身疼痛。所有的关节和肌肉都在与重力的压力对抗。虽然没有呕吐,但我依然觉得很恶心。我脱掉衣服,上床睡觉,感受床单的触感,毯子盖在身上的压力,还有枕头的蓬松。所有这些都是我之前错过的东西,我还可以听到门外传来的家人的欢笑声。因为卫星电话的声音失真,我一年来都没有真切地听过这种声音。
伴着他们的欢声笑语,我坠入了梦乡。
一束亮光唤醒了我,天亮了吗?不,只是艾米蔻来睡觉了。我只睡了几个小时,但我觉得神志不清,要挣扎着让自己清醒一些,才能动弹一下。我想告诉她我的感觉有多糟糕。现在,我感到非常恶心,发着高烧,身上好像更疼了。这跟我上次任务结束后的感觉不一样。这次更糟糕。
“艾米蔻!”我终于叫了出来。
我的叫声吓了她一跳。
“怎么了?”她摸了摸我的胳膊,又摸了摸额头。她的手凉凉的,不过正好,我很热。
“我感觉不太好。”我说。
我已经去过4次太空了。2010年到2011年,我在国际空间站上度过了159天。而艾米蔻像以前一样,是我的主要精神支柱,陪我经历了整个过程。那次返回地球,我也有一些身体反应,但不像现在这样。
我挣扎着起身,摸着床边,双脚着地,坐起身,站起来。每一步,我都觉得像在流沙里战斗。最终,我站起来,双腿疼得可怕,除了这种痛苦外,我感觉到了更令人震惊的事:似乎全身的血液都在涌向双腿,就像倒立时血液都冲向脑袋一样,只不过方向相反。我可以感觉到腿部正在肿胀。我向浴室挪动,小心地把重心从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左,右,左,右。
我进了浴室,在灯光下,看着双腿。这简直是肿胀而怪异的树桩,而不是腿。
“哦,天哪,”我说,“艾米蔻,来看看这个。”
她跪在地上,按了按我脚踝的一侧,脚踝就像水球一样被挤扁了。她担心地抬头看着我说:“我都摸不到你的踝骨。”
“我感觉皮肤在燃烧。”我告诉她。艾米蔻疯狂地检查我的身体。背上,双腿的背面,头和颈部的背面,凡是与床接触的地方都布满了奇怪的皮疹。我可以感觉到她凉凉的手轻轻地抚过我起皮疹的皮肤。“看起来像一种过敏性皮疹,”她说,“像荨麻疹一样。”
我洗完澡,又挪回床上,想着我应该做些什么。通常情况下,如果我醒来发现自己起了皮疹,我应该去急诊室,但医院里没人见过在太空待了一年后造成的病症。我爬回床上,想要找到一种躺下而不碰到皮疹的方式。我能听到艾米蔻正在翻箱倒柜地找药。她拿来两颗布洛芬和一杯水。她坐下来,我可以从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呼吸中,感受到她对我的担心。我们都很清楚我那份使命可能带来的风险。我们在一起6年了,即使在无言的黑暗中,我也非常理解她。
我一边努力让自己睡觉,一边很想知道,我的朋友米哈伊尔·科尔尼延科是否也腿部肿胀,是否也起了让人痛苦的皮疹?
米沙和我在太空中一起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现在他在莫斯科的家中。我怀疑他也有同样的症状。毕竟,这就是我们自愿参加这项任务的原因,为了发现长期太空飞行如何影响人体。科学家会在我们的余生中研究我和米沙的身体数据。我们必须更多地了解如何克服太空飞行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人体和思智,否则我们的航天机构将无法深入更远的太空,到达火星这样的目的地。
太空任务存在风险,比如发射的风险、太空行走的风险、返回地球的风险,生活在一个以每小时17500英里的速度环绕地球的金属容器中,我们每一刻都面临风险。人们经常问我,明知风险存在,为什么还自愿参加这项任务?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几种答案,但没有一种答案让我自己感到满意,它们都无法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常常做一些奇怪的白日梦。我幻想自己被安置在一个很小的空间中,这个空间小到无法让我躺下。我蜷缩在地板上,知道自己会在那里待很长时间,无法离开,但我不介意——我有一种拥有自己所需的一切的感觉。留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在那里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事,这种想象一直吸引着我。我觉得,我属于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