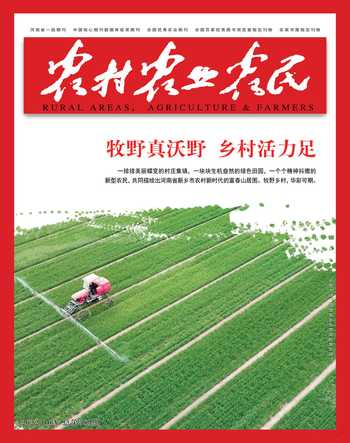玉米往事
黄泽岭

记忆中,童年的乡村总有玉米的身影。那大片的玉米地葱郁繁茂,宽硕的玉米叶油绿发亮,大大小小的玉米棒顶着红色的“胡子”,有种英姿飒爽、玉树临风的感觉。而玉米带给我的童年诸多快乐、满足、辛酸、温暖,像一杯调和的鸡尾酒,绚丽醇厚,饮过一口,五味杂陈,一言难尽。每每想起,那些关于玉米的往事便随着玉米的清香袅袅而来,氤氲弥漫,挥之不去。
春季或麦子发黄季节,人们将玉米种子撒下,不几天小苗齐刷刷地就出土了。绿叶绿杆,直直地站着,没有多余的姿态,虽然给人呆板生硬的感觉,但那柔和的、蓬勃的、象征生命的绿,却能给人以无穷的希望。我喜欢玉米亭亭玉立的身姿,绿油油的叶子,红红的、柔软漂亮的玉米须。玉米须摸起来光滑、细腻,像少女飘逸的头发。等到玉米出须,绽出饱满的粒,就是农民半载辛苦最好的回报。大片的玉米地与那小小的村落相辅相成,恰当地融为一体,你装点我,我美化你,共同组成黄土地上最美好的风景。
那时,每到周末或放学后,我和几个小伙伴便会挎上篮子拿上铲子,飞奔向玉米地,辟一方安全的天地,把玉米苞剥开一点点,看籽粒饱不饱满。不饱满的,随即把苞子合上,别给大人发觉;饱满的就用指甲掐,稍一用力,就听扑哧一声迸出乳白的浆液,便是上好的选材了。挑选成熟饱满的玉米棒子,再捡些干树枝点燃来烧玉米吃。一穗穗颗粒饱满散发着淡淡清香的玉米棒子在火里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烧焦的玉米外焦里嫩,热腾腾、黄澄澄,吃后口齿留香,通常是吃完了烧玉米,我们就变成了活脱脱的张飞。然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视大笑,那时吃烧玉米似乎把泥土味都品得稍有醉意。
小时候偷玉米的经历最是刻骨铭心。20世纪70年代初,贫穷笼罩着村子,饥饿占领着每个人寡淡的肠胃,炊烟总是孩子眼里最美的风景。贫瘠的土地上,庄稼长起来了,粮食在阳光下酝酿成熟,总叫人心生渴望和力量。夏天,村子里大片大片的玉米在蒸腾的暑气中摇曳生姿,看着叫人心里踏实、满足。那时还没有分田到户,玉米都是生产队的,等到玉米收了,各家各户才能凭着劳力和工分分得一些玉米,因而我们这些半大的毛孩子常常会忍不住到田里偷些玉米烤着吃。待灶膛里的火烧旺了,把青玉米连着苞谷壳插在火棍头子上伸进灶膛里。火苗很快包裹住玉米,玉米须如毛发般瞬间蜷曲化成灰烬,绿白的苞谷壳则慢慢收缩、变黄。看着玉米外皮由一点开始,像晕染般一层一层地渐渐由黄转褐、变黑,内心的喜悦和嘴里的口水也随之晕染开来,那感觉无比地神奇、美妙。一面黑了,翻过来再烤另一面,三五分钟的工夫,青嫩的玉米棒子就变得黑咕隆咚,灶膛里开始有轻微的声音响起,有玉米的甜香扑鼻而来。拿出火棍,在灶头轻轻一顿、一敲,玉米就滚了下来。孩子们常常等不及玉米凉透,就捏着玉米一头,在灶面上敲打起来,敲一下手被烫得直嚷嚷,扔下玉米,把手伸到嘴边哈上几口气,再拿,再敲,再叫,再扔,再哈气,几番下来,玉米外的黑灰没有了,露出黑、黄、褐、白相间的玉米粒来,那香味更是浓郁,唤起腹中的馋虫。啃上一口,外焦里嫩的玉米粒,有点脆,有点糯,有点甜,满满的香,让所有的味蕾跳跃,让全身所有的细胞愉悦、欢欣。贫乏的时代,因为烤玉米的香甜美味而不再苦涩难耐,也因为自己的劳动而不再被生活所困。
尽管玉米好看,地里也好玩,可是我们小时候一点都不喜欢吃玉米面。那时候是人工筛面,玉米外壳没有清理干净,味道就有点苦涩,还非常粗糙,吃起来口感不好、难以下咽。那时候家家户户口粮都不够吃,所以不但玉米羹是饭桌上的常备,更多时候还要吃红薯干、红薯馍,蒸红薯、煮红薯,吃得胃里直冒酸水。
明代卢青山诗云:“玉米秋成晒满场,长杨丛立守其旁。老翁更持老烟杆,斜阳影里袅微香。”小时候在生产队剥玉米是件辛苦而快乐的事。秋风起了,玉米地已是一片缤纷,黄绿相间的叶子,衬着枯黄的玉米穗,有些别样的繁华。那些早前鲜红的玉米须日渐干枯变成深褐色,有气无力地耷拉着。有些玉米穗皮已经裂开,露出金黄的玉米粒,有点衣衫褴褛的落魄。逢着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开始收玉米了。妇女们三下两下就撕去包谷壳,轻轻一掰,金黄的玉米穗就告别了玉米秆。妇女围裙里的玉米穗源源不断地倒进男人们等在身后的箩筐里。欢声笑语里夹杂着男子高亢洪亮的号子声,整个村子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空气里弥漫着玉米秆被折断后发出的淡淡的清甜味。
玉米晒上一两天,队长就通知村民去大场剥玉米了。这剥玉米的活儿是根据剥下来的玉米粒的重量来记工分的,所以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集体出动,带着木盆、簸箕、板凳儿赶往队里的大场。大场中间金黄的玉米堆得像小山,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耀眼的光芒,散发着老玉米独特的香味。各家在玉米堆旁找块地儿、围个地盘儿就开始抢玉米、剥玉米了。抢玉米大凡是孩子们的活,在大人的吩咐下,我们把颗粒整齐、粗大匀长的玉米穗扔进簸箕里运到自己地盘上。我们爬上玉米堆,再跟着玉米滚落下来,惊叫、欢笑还有争抢、打闹,仿佛不是来挣工分,而是在游戏。抢了一阵、玩了一阵便被大人叫去剥玉米。剥玉米看似轻松,其实不易。为了能剥得快,大人们都拿出了“秘密武器”——铁制的“蓬椎”。这“蓬椎”头尖尖的,长长的椎身有个凹槽,还有一个木头柄。大人们用“蓬椎”椎玉米可谓神奇,左手拿着玉米棒,右手握着“蓬椎”,对准玉米根部的一个缝,用力一推,边推边轻轻左右摆动,眨眼间,两三排玉米籽儿就哗哗地落到木盆里。被椎过的地方露出暗红色的玉米芯,像被拔光牙后的牙齦。剥玉米就是顺着被椎过的空排处,用手掌跟将玉米粒一排一排剥离玉米芯。开始还觉轻松,没剥几个,手掌就开始发烫,那掌跟的皮似乎被磨得几近透明,能看出鲜红的血肉来。玉米芯上飘出来雪花似的碎皮屑,时常呛得我们咳嗽不停。晴空之下,生产队的大场上热火朝天,家家户户铆足劲儿,大人小孩谁都不敢懈怠,场上的玉米在全部剥完之前,没有人回家吃饭、喝水,甚至连尿都憋着。因为每一斤玉米籽儿都关系到工分,关系到年终分红,关系到缸里的粮食、碗里的口粮。在那样一个时代,拼命劳动是唯一的选择,为生活,也为生存。
元代谢应芳诗云:“远客相过说帝都,黄金如玉米如珠。内园人歇催花鼓,市肆尘生卖酒垆。”而今,玉米已不再是稀缺物,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进口的甜脆玉米、转基因的大个玉米等在超市里都可寻见,各种玉米加工的食品比比皆是,只是再也吃不到老式灶膛里烤出来的嫩玉米了。一方面,村子里的土灶已经难得一见了,煤气灶、电子炉、烤箱,终是烤不出童年的味道;另一方面,玉米的种植经历若干年的更迭,品种似乎改良了、变多了,却早已不是当年的纯净土壤里种出来的味道。泥土变了、水质变了、肥料变了,玉米种子也都是种子站(实验室)统一配送的。于是,超市、菜场里一年四季可以买到的玉米,总是少了一点田野、乡村、亲情的味道。
[责任编辑:朱松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