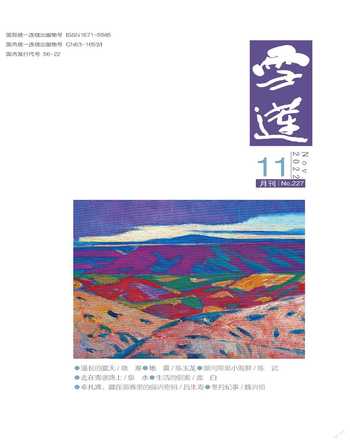她房间里的雾
第一次到她家里做客,在玄关蹲下脱鞋时,一只蓝色的鹦鹉突然在头顶出现,伴着清脆的叫声朝我扑过来。我吃了一惊,赶紧往角落里躲去。蓝鹦鹉在空中盘旋一阵,兴许是因为无法击中目标,又晃悠悠地飞回到在衣架上搭起的树枝上。“没事的,豆豆不会乱咬人。”她反复安慰我道,于是我知道了这只鹦鹉叫豆豆。
可能是因为很少见到陌生人,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豆豆对我有显而易见的攻击性,因为只要我出现在它视野里,它就会气势汹汹地飞过来,带着那根亮闪闪的铁链子。但她总是跟我强调豆豆不会咬人,这只是一种表现亲昵的动作,因为鹦鹉都喜欢站在人的肩上,从而和人类开展平等的对话,也许这时候它就不再认为自己是只鸟了,而是同样具有高度智慧的生物。
半是因为感觉我怕鸟的表现太丢脸,半是因为她的不断劝说,我稍微安下心来,准备和豆豆打一个照面。下次再去她家时,我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放风出来的豆豆在树枝上观察了我一会儿,果然禁不住诱惑飞过来,落在我肩上。我感觉到那苍劲的爪子扎在我的皮肤上,我屏住呼吸,感受它横着踱步一点点走到我耳边,本以为它会就此停下,但没想到它接着就开始啄我的耳朵。那突然一下的刺痛让我浑身紧张起来,也许倒不是多疼,而是那种面对未知危险的本能,让我下意识地拼命甩开它,而豆豆也焦急地扑腾翅膀试图抓住我,最后我以高速摇摆的频率驱走了豆豆。豆豆尖叫着在客厅里四处乱窜,把细碎的落羽抖得到处都是,像一阵蓝色的雾。她及时出现,在一片狼藉的现场抓住豆豆的链子,把肇事者拖入鸟笼。
和豆豆建立友好关系的首次尝试就这样完全失败了。接下来的时间,豆豆在笼子里晃着脑袋听我们谈刚看过的电影以及对电影风格的偏好,不时发出附和的叫声。
只有豆豆被锁在笼子里,我才敢认真地与其对视。从这个安全的视角看,它其实是很漂亮的鸟,长着尖尖的栗色的喙,喜欢仰着头从吸管中吮吸清水。两腮是鼓鼓的,有些婴儿肥。它的羽毛是淡蓝色的,整个上腹部则泛白,像是洗旧的球鞋。尾巴是前宽后窄,有点像企鹅,这使得它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但在树枝上却能始终保持平衡。回到笼子后,它总是在那根斜插进栅格間的树枝上走来走去,双爪握住枝干,总让我疑心这样会不会很累。有时候它也会坐下来,肥硕的躯体遮住了下面的爪子,看起来就像端坐在榻榻米上,非常温驯。它就这样一动不动听我们说话,让我渐渐感觉到它也不是那么可恶,当然这只在我们之间隔着什么障碍的时候。
一开始去她家的时候,其实和她还只是普通朋友关系,在那么逼仄的空间里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那是老北京国有工厂集资建的筒子楼,客厅里没有开窗,如果把通向阳台的门关起来,白天也和黑夜差不多。开着昏黄的日光灯,在下面摆着两把椅子,不管什么时候都感觉像秉烛夜谈。
在无话可说时就站在鸟笼前逗豆豆玩,好像又找到了一个可以逗留的理由。她教我喂豆豆吃鸟粮,把西蓝花梗、面包屑和苹果切片递到栅格里,豆豆马上就凑过来埋头啄起来。如果此时问它“好吃吗?”它就会从喉咙里挤出一个清晰的词“好吃”,无比笃定和满足,这是它最早学会的人类语言词汇之一。当然此时投喂的只是小零食,豆豆的主食得专门调配,把几种网购的杂粮按比例倒出来混合在一起,放进鸟笼的食盆里。但一向挑食的豆豆会先吃最喜欢的黑瓜子,其次是火麻子,再次是白瓜子、黍子、小米等,除非饿到极点,坚决不吃玉米糁子。
豆豆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好像不管争论什么或是突然失去了话题,就可以把头望向鸟笼,看它在做什么,就会感觉到生机勃勃,跟春天到了一样。它就是好莱坞电影中的转场镜头,衔接着所有类型故事的起承转合。
她见我慢慢喜欢上观鸟,以为我对豆豆完全放下戒心,便再次提出把豆豆放出来。我同意了,我已经看到过好多次豆豆停留在她肩上的样子,在她看书或伏案工作时一动不动,或把一只爪子抬起来舔一舔,或是用鸟喙梳理自己的羽毛。而且据她说即使豆豆啄你的耳朵也不会很疼,它只是想帮你掏耳朵而已。我想我做好了让豆豆给我花式采耳的准备。
这次把鸟笼打开,豆豆在栅格上爬了一会儿后探身出来,向上纵身一跃飞到了衣架上,在房间里巡视一周后果然向我飞了过来。我按捺住自己的紧张心情,仍旧靠在椅子上看手机。实际上我的手机屏幕已经自动休眠了,我借着手机镜面反映出它此时此刻的样子,影影绰绰的,但能看得出摇晃的大脑袋。过了会,豆豆在我肩上蹲了下来,把爪子收到了腹部下面。当时我并没有为那异常的安静而困惑,直到感觉到肩上一股热流喷薄而出,我终于反应过来,豆豆拉屎了,转过头就看到衬衫肩部有团墨绿色的东西。我大叫一声站起来,豆豆也受到了惊吓,迅速起飞逃到半掩的卧室门上。
后来我才知道豆豆眼下两岁左右,在鹦鹉的世界里算是进入了青春期。所以它暴躁的坏脾气似乎就可以理解了。我慢慢不再惧怕它,因为我发现它啄人并不疼,也可以通过观察免于被它骑在身上拉屎的命运。
说实话我觉得豆豆这个名字有些俗气,叫“豆豆”的宠物实在太多了,上街时如果喊一声“豆豆”估计不知道有多少阿猫阿狗会转过头对你吹胡须瞪眼。但她的豆豆却是一种较为稀有的鹦鹉品种,应该起一个更加熨贴的名字。当然,这点小心思我从没跟她提起过。
豆豆青春期的爱好之一是疯狂啄房间里任何可以移动的物体,特别是有生命的植物。它用锋利的鸟喙把阳台上种的番茄、鼠尾草、多肉植物从土里掘出来,一时间它经过的地方横尸遍野,全是啄烂的根茎。还有一次啼笑皆非的经历,豆豆不知道哪次在搞破坏时顺便将它日常吃的生葵花籽丢到阳台花盆土里,过了一段时间土里就发出了芽,长出了一根向日葵。
这种无心插柳的好事当然并不常见,很快它就闯下了另一个大祸,在她回家加班写文件起身去卫生间的间歇,把笔记本电脑键盘上的“delete”键咬了出来,从此这个键就无法正常使用了。不知道豆豆是否装着一颗哲人之心,以此告诉我们人生没有退位删除键。
豆豆自知犯下大罪就飞到了门洞上,它总是这样逃避处罚,虽然处罚无非是大声训斥,顶多在脑门上弹两下而已。看见被兴师问罪,它就接二连三飞到别的地方。
我很快學会了如何把豆豆抓捕归案,前提当然是我已不再惧怕它。我慢悠悠地踱到它下面突然抓住它的链子就往回收。它扑腾两下就放弃了挣扎,站在你手心里,无辜地望着你。刚才发生了什么事了吗?那一定不是我干的。它叽叽喳喳地叫着,说不定是这个意思。见我无动于衷,它开始忏悔,“臭豆豆,臭豆豆”,它一边点头一边不停地叫,这是它学会的有限人类词汇中的另一个,似乎是在骂自己。我冷酷地把臭豆豆关进笼子里,它今天的放风时间当然因此泡汤了。
据说豆豆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她回忆起刚从饲养场把满月的豆豆带回来的场景时总像个老母亲一般百感交集,那时它个头和我们的拳头差不多大,羽毛还没有完全长出来,全身呈现出深蓝色,装进笼子后蜷缩成一团,非常安静。养育小鹦鹉和照顾小婴儿特别相似,每天要煮小米熬成的米糊喂它,定期把它放在盥洗池里洗澡,给它梳理身上的羽毛。
那时她在豆豆的笼子边放儿歌,放了半年它几乎什么都没记住。豆豆学会的第一个词是“peek A boo”(躲猫猫),这来源于许多儿童绘本里经常出现的互动游戏。触发机关时用双手捂住豆豆的眼睛,然后迅速撤掉,在重见光明的那一刻豆豆就会叫出“peek A boo”,这当然是反复练习的结果。不管是对婴儿还是鹦鹉,语言教学都得和具体的事物对应起来,让能指和所指重合起来,并不断强化这一印象。接着就开始教豆豆算数,对它伸出一根手指不断重复“1”,终于让它在手势和数字之间建立联系。再伸出两根手指重复说“2”,它也慢慢掌握了。但伸出的第三根手指再也没有收到回应,豆豆的算术水平最终就停在二进制的层次。
当我见到豆豆时,它已经是一只淡蓝色的少女鹦鹉,度过了并不漫长的童年后,它进入了叛逆的青春期。不再像往常那样粘人和听话,热衷于闯祸和逃跑。对,忘了说,豆豆其实是一个小女生。
那一年夏天和她去一座海边城市旅行,出发前的傍晚我提着豆豆的鸟笼去答应收养它的同事家,那是在步行十分钟距离的另外一个小区,经过朝阳门外繁华的市景。一路上豆豆发出剧烈的尖叫,趴在笼子门口,使劲啄门上的铁钩,前额几乎要从栅格中挤出来,露出一小撮蓝色羽毛。也许它是想飞出来看看这个广阔的世界,然而即使此时我打开笼子,生性自由的它如愿以偿地飞向蓝天,在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城市里它大概一天都没法生存下去。这种二元悖论可能是所有养宠物的人都会面临的。
告别豆豆后,我们乘火车一路南下,在海边玩了三天。那座城市因为上世纪初的殖民史而建起星罗密布的欧式建筑,红墙黛瓦的小楼随着高低不平的地势层层叠叠地往海边铺展,像波浪一般起伏着,繁盛的树荫点缀其间。登高望远,目力之极是大型油轮和货船所停泊的离岛,已经渺茫得像是海市蜃楼了。日光倾城,山川楼宇历历在目,感觉美好的未来如此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几乎触手可得。我们看倦了风景,双目相对,拥抱在一起,也许是那个时刻让我们坚定了要继续走下去的念头。
回到北京继续为生计而奔波,我和她搬到了一起住,开始挑选结婚礼服、拍婚纱照。生活的最大变化无非是所有的决定都得为对方考虑。每当我们在客厅餐桌上吃饭时,豆豆也在笼子里埋头吃着鸟粮,时不时会看我们一眼,兴奋地叫一声。也许在它的意识里它是我们这个小家庭的一员,而且和我们一样严格遵照一日三餐的生活范式。
没过多久突然爆发的疫情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对我们而言最大的变量是延宕了计划举办的婚礼。工作单位宣布居家办公,我们宅家的时间大大增加了。第一次感受到“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的惬意。我每天早上睡到自然醒之后,躺在床上看书,豆豆飞进来有时停在我肩上,有时在我打开的书页上走路。我看累了就合上书,撸一会鸟,豆豆似乎很喜欢别人抚摸它鼓鼓的双颊,也很愿意躺在你的手心里,让你捋顺它的羽毛,据说那是因为它身上那些羽管会在抚摸的过程中裂开,从中长出新的羽毛来。
在经历了一次差点有陌生人闯进家里的乌龙事件后,我们在客厅安装了一个家用监控摄像头。这样平时即使出门在外也能通过手机软件随时查到家里的情况。当然,这个摄像头安装后从未派上过用场。
有次我们在美术馆看展时,莫名其妙地突然想起豆豆,并好奇它独自在家时到底是什么模样,就打开了手机软件的实况影像。镜头斜对着客厅往外开的防盗门,视野里包括那个笼子。我们看到豆豆的脑袋悬在小窝的边缘一动不动,它毛绒绒的身体完全隐藏在窝里,看不出来是否在睡觉。我对着手机的麦克风喊了一声,“豆豆”,家里立即响起我的喊声,似乎还有回声。豆豆的脑袋立刻探出来四处张望,什么都没发现的它冲着外面凶巴巴地啾啾叫了几声,好像在警告那未曾现身的神秘人,老子不是好惹的。大概它压根没有听出我的声音。
很早之前就听过宠物界的一种说法,猫咪从来不把自己当做宠物,而是认为自己就是主人,所以养猫的人老是自称为猫奴。但猫和人的互动还是很频繁的,时不时会跳到你怀里撒个娇。而豆豆似乎冷淡得多,它不会笑,不会哭,叫声都差不多,除了羽毛会随着心情变化而竖起来或变蓬松外,看不出它究竟是开心还是悲伤。
其实很多时候我实在搞不清豆豆到底是怎么看待我们的,虽然曾一厢情愿地认为它把我们当做亲人,但好像它也从未作出过什么特别亲昵的举动。自我初次认识它以来,好像豆豆对我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只不过是我慢慢熟悉和接纳了它,开始在心中赋予它的动作一定意义。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豆豆此时落在我肩上和第一次见面时究竟有没有区别呢?我实在感受不出来,这些疑问也许永远无从获知答案。
更现实的一桩考虑是很快我们即将迎来我们自己的小生命,如何处理豆豆就成了一件必须面对的严肃问题,毕竟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孕育新生命的家庭最好不要饲育鹦鹉。犹豫了很长时间后,在老家父母的反复劝说下,我们终于下定决心把豆豆送到一个喜欢鹦鹉的朋友家寄养。至于寄养的时间,我们双方都没有说破。
豆豆寄养在外面的时间里,家里顿时清静了许多。大概是因为没有豆豆起哄,隔壁家养的狗也很少叫起来了。有时候我走到客厅里莫名觉得少了些什么,慢慢想起来一则寓言,很久以前一个师傅带着三个徒弟修行,为了决定由谁继承他的衣钵,师傅给弟子一些钱,让他们用最便宜的东西充满整个房间,最后,一个徒弟想到一个妙计,买了一支蜡烛,用烛光充满了整个房间。我想我们房间里缺少的大概就是某种可以充满房间的声音。“好吃!”“臭豆豆!”“壹!”
寄养家庭的小女孩很喜欢鹦鹉,经常发来豆豆的微视频。豆豆像往常一样进食,在被投喂零食时大叫“好吃”,放风时在房间里飞来飞去,累了就停在小女孩的肩上。似乎完全没有认生的样子。这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之前的猜测,其实在豆豆眼里我们并不是特别的存在,顶多就像农村田垄间的稻草人,不管换成什么都没太大差别。
“十一”假期前夕那家人计划出行,要我们把豆豆再接回去,此时离豆豆离开家已经过去了小半年,对一只鹦鹉来说是很漫长的时间了。打开笼子,豆豆兴奋地飞出来,在房间里旋转一圈,落到客厅衣架上,它四处张望,似乎在打量这个陌生又熟悉的空间。我无法当面质问它,你是不是早就忘记我们了?
考虑到寄养并非是长久之计,而且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后复工复学的推进,那家的小女孩马上就要开学了,大人不可能由着她一直养鹦鹉。我们需要给豆豆找一个永久的新主人。她在宠物收养论坛里逛了很久,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小动物爱好者,住在京郊,家里有三条狗三只猫,还有一只刚去世的八哥,想领养一个会说话的鹦鹉,豆豆正符合她的要求。在她之前发出的帖子中,家里就和动物园一样,众生平等,猫猫狗狗平时都可以上炕,就是不准打架。我们在网上和她聊了一会儿,觉得她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新主人,就决定把豆豆送给她。
即将送走豆豆的前一天中午,我吃完饭准备去上班,打开门的那一刻,听到后面传来一声清脆的“bye bye”,然后又连续叫了几声,那是我们很久之前教豆豆学会的,看到家里有人要离开就说“bye bye”,然后就奖励给它水果粒。这次回家之后当然没人顾得上再教它温故知新,没想到过了这么久它依然还记得。我也回头对豆豆说了一声“bye bye”。豆豆歪着脑袋点了点头。在那一刹那我真的有种错觉,以为它其实是一种具备高度智慧的生物,它记得我们所有的好意与亏欠,宽容与自私,快乐与悲伤,并深藏在心里。
在新的一年来临之前,一个寒冷的周末下午,新主人如约开车来接豆豆了,我和她拎着鸟笼走下楼,穿过积雪还未融尽的小区,在路口瑟瑟发抖地等待着。新主人开着面包车过来了,车窗慢慢摇下来,露出一个二十多岁女孩的脸,一口京片子。我们本来准备了许多Q&A(问答)口径,想耐心地告诉她豆豆的习性、爱好、口味甚至是词汇量等,但那个女孩豪爽地打断了我们,“不是有微信吗?回头再聊吧,今个儿天这么冷。”我们把豆豆的笼子抬进后备箱,看它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发出紧张时才会发出的叫声,坚决地关上车厢门。女孩挥手对我们说:“宝贝儿交给我就放心吧,不会亏待它的。对了,它叫什么?”“叫豆豆。”我身边的她急忙说。还是有点俗气啊,我心里想。面包车点火开动,加速驶出这条林荫道,在路灯的照耀下那团拖出的尾气呈现出明亮的蓝色,车开出很远后仍像夜雾一样膨胀开来,把我们已经看不见的豆豆笼罩在里面。
在回家路上,她慢慢告诉我这个名字的来历。四年前,她和朋友开车去远郊的宠物饲养场挑选一只鹦鹉。那是一个很大的农家院子,里面有一圈平房,老板拿着一大串钥匙领着她去打开其中一间屋子。推门进去的一刹那,此起彼伏的鸣叫像潮汐一样涌过来。双眼好不容易适应昏暗的光线,她看到许多根木桩上挂着密密麻麻的笼子,像一大片结出鸟儿的小树,里面伸出无数双渴望的眼睛。她在黑暗中绕了一圈,终于在众多看起来几乎毫无差别的小鹦鹉中选了刚满月的一小只,浑身深蓝色,蜷缩在角落里,好像脾气有点不好。“就选它了,它有名字吗?”她问。“当然有了,它叫豆豆,它们都叫豆豆,每一只都是。”那个人笑着回道。 “好的,豆豆出来吧。”她打开了那个笼子,从此就有了属于她一个人的豆豆。
【作者简介】王文,1993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北师大法学院硕士毕业,现居北京,从事国际法相关工作,业余写小说及散文。作品见于《萌芽》《朔方》《莽原》《百花洲》《上海文学》《山东文学》《安徽文学》《当代小說》等文学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