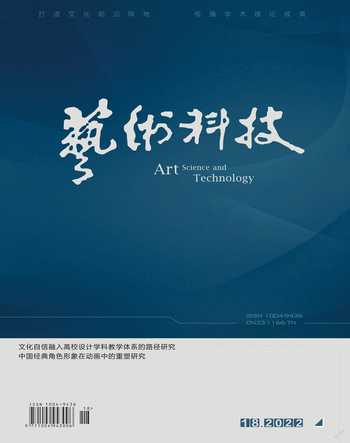清水江文书开发利用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摘要:清水江文书是研究黔东南苗侗民众社会生活的第一手历史文献,现已发现的清水江文书主要时间跨度为明成化二年(1466年)至20世纪50年代,具有400多年历史的文书一直都以流域内人民的日常生活为中心。此类文书具有强烈的归户性特征,至今仍发挥着特殊的参考作用,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已取得很大进步,也获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目前,清水江文书的相关开发利用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但不容忽视的是,文书的开发利用还存在许多问题。文章立足这一现状,对文书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侧重点失衡、知名度不高、出版碎片化、征集难度大等困境进行探究,并有针对性地给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为清水江文书的可持续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关键词:清水江文书;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K8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18-0-03
清水江发源于贵州都匀,流经麻江县、凯里市、台江县、剑河县、锦屏县等多个地区,是贵州对外交流的天然通道之一。自明朝开始,清水江流域的杉木逐渐为外人所知,该地区逐渐形成独特的木材贸易,也成为当地人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木材贸易的刺激下,区域内的林木经济繁荣发展,形成了以林木经济为主,包含其他生产生活活动的系列契约文书,学界称其为“清水江文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清水江文书逐渐进入学者视野,几代学者共同致力于挖掘清水江文书的内在价值。在此过程中,清水江文书的开发利用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文书的侧重点失衡、知名度不高、出版碎片化、征集难度大等。
1 困境分析
1.1 偏重保护抢救,忽视研究利用
清水江文书以私文书为主,其持有者大多是民间普通百姓,民众虽然有一套历史遗留的方法保护文书,但就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其还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因此,文书保护工作成为当前清水江文书开发利用工作的重点,但是保护工作也出现了片面化的问题,即只注重抢救保护,忽视了研究利用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学界对于清水江文书的研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一,文书研究种类狭窄,这主要表现为重视林业契约,忽视其他文书。由于最先发现的是锦屏县的林业契约,并且清水江流域保存完好且丰富的林业契约为世界少有,因此学界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林业契约上。其二,文书研究视域狭窄。当前文书研究的切入点主要为法律、经济等方面,同一性问题研究较多[1]。其三,就文书而谈文书。清水江文书虽然是当地人民的生活写照,但是它毕竟只是私文书,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应当结合公文书及其他地方资料进行互证研究。此外,可以看到,文书的研究资料多为纸质,有关碑刻等相关文书的研究较少。清水江文书的开发利用与其学术研究密切联系,只有深入了解文书内容及其产生背景才能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文书。
1.2 知名度不高,未形成品牌效应
据估计,清水江文书现藏量丰富,大约为50万件。尽管文书藏量大且种类全,但知名度不高,主要为学术界以及政府相关部门所知。文书的开放性和内容解读效果较差,导致民众少有接触机会,这是清水江文书不知名的重要原因。而文书的知名度不高又導致了两个问题,一是难以吸引更多的专业人员,研究文书的人才队伍有限且缺乏活力;二是难以吸引大众目光,无法挖掘并发挥文书的经济效应。
1.3 文书出版碎片化,数字化程度低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清水江文书相关研究陆续展开,文书的出版工作也在持续进行当中。目前,已经出版的文书汇编资料主要有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主编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759)》(第一、第二、第三卷),张应强、王宗勋主编的《清水江文书》(第一、第二、第三辑),贵州大学、天柱县人民政府、贵州省档案馆等合编的《贵州清水江文书系列·天柱文书》,凯里学院、黎平档案馆合编的《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第一、第二辑)等。文书出版也存在部分问题:其一,由于文书出版方与编辑者不同,而且文书搜集工作持续时间较长,文书出版呈碎片化特征,同一村寨或同一家族的文书前后由不同的单位出版;其二,文书出版形式、文书题名规范等出版问题也并未得到解决。清水江文书数量较大、种类较多,有效整合与统一管理这些文献资料成为一大难题,建设数据库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尽管建设文书数据库的建议已经提出多年,但文书的数字化程度依然很低。许多文书数据库只供内部使用,外部无法访问,只有凯里学院与清华同方技术合作建立的“清水江文书数据库”能够支持外部访问[2]。这导致清水江文书学术资源封闭且利用率低,无法进行深入挖掘。
1.4 文书征集工作难度大
清水江文书目前已入馆数量大约为21万件,还有很大一部分散落于民间,因此一直都在进行文书征集工作,但近年来,文书征集难度也在不断加大。首先,清水江文书具有高度的归户性特征,文书主要来源于普通民众的家传契约。随着清水江文书征集工作在民间的开展不断深入,许多百姓都认为这些文书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不愿将文书无偿或低价献出。其次,文书对当地人民而言是重要的法律证据,文书中所指的标的时至今日依然清晰可辨。再次,文书是家庭传承的代表之一,民众出于守旧情结也不愿意献出文书。最后,市场上不乏投机分子借机收购文书,哄抬文书价格。总之,文书收集入馆是文书保护开发的起始环节,也是开展文书整体性研究的前提条件,而其较大的征集难度给文书保护和研究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2 对策分析
2.1 学科建设
在地方专门学问中,以徽州文书为研究重点的徽学已成为一大显学,但以清水江文书为重点的清水江学却还处于起步阶段。清水江学是“以当地复杂的族群及其所创造的灿烂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并“涉及民间契约文本及文本之外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内容”[3]。就此而言,清水江文书乃至清水江学的研究不应只谈文书,还需研究地方民俗文化,进而推进清水江流域文明世界的构建。清水江文书的长久发展应该以清水江学为参照范式,实现整体性研究。清水江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地方学科,当前主要有史学、法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汉语言文字学[4]等学科的人员对文书进行研究。就史学而言,目前主要的研究维度有民族史、文明史、家庭史、文书史、区域史等。若要应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需要结合清水江文书、家谱、民族志等文献资料,还要进行田野调查。
此外,研究人员的培养也是一大重点。其一,高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所以清水江学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以高校为依托,以高层次人才为核心;其二,可以定期举办学术交流活动,互相借鉴文书开发利用经验,实现共同进步。
2.2 加强文化宣传工作
当前文书开发利用工作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与大众对文书的认识有关,一方面是知名度不够高,另一方面是大众对文书所代表的文化形象产生了一定的误解。清水江文书的保护利用与大众有密切联系,要使文书走进大众视野,就要强化文书的宣传效果。首先,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不光要吸引专家学者参与,还要使民众知晓,提高文书知名度。其次,文书的宣传要注意文书本身的形象包装。文书集经济效益与文化信息于一身,但在大众宣传中要突出其文化形象,它应该是区域民俗文化传承的代表,并包含法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等向度。突出文化形象能够彰显文书内涵的重要性,有益于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到文书的保护开发工作中。最后,清水江文书并不是单一的文化现象,其宣传要和清水江流域的风土人情相结合,并联系现实生活,如苗侗民族的生活、生态、经济以及习俗传统等。
2.3 数据库建设
建设数据库是解决当前文书征集保护困难和利用困难的最佳途径,也是文书长久保存、福泽后世的科学方法。无论是文书的直接出版,还是文书的数字化建设,都必须解决其著录规范的问题。这在文书数字化中表现为元数据的规范问题,主要涉及“题名拟定”“责任人”“文书时间”“附注项”“收藏历史和馆藏信息”等方面[2]。
同时,文书内容的解读也是一个难题。清水江文书所涉及的主体民族为苗族、侗族与少部分汉族,文书主要采用“汉字译写”“汉字音译书写”“用意译方式书写”“音译与意译各半用汉字译写”的苗族或侗族语言[5]。此外,当地的语言创设还与人文地理环境有关,这加大了文书解读的难度。因此,清水江文书数字化建设还要注重其文字释意,可以建立一个专门的文字数据库,录入已经被解读的文字,不断充实数据库。如此一来,文书的内容才能够变得通俗易懂,其受众面才有可能扩大。总而言之,数据库的建设可以提高文书资源的利用效率,整合各个机构持有的文书,实现文书的活态保护。
2.4 功能开发
清水江文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学术界近30年也在持续研究。除了学术价值外,文书还具有其他潜在功能,如教育功能、旅游开发功能等。
首先,就教育功能而言,主要包括生态教育功能、历史文化传承、价值观引领这三个部分。清水江流域的林木经济发达,每年砍伐树木总量大,但该区域的生态依然保持较好状态,林木经济也处于良性循环中,这表明当地经济与生态发展相对和谐,对于优化现代生态保护措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些文书还以习惯法的形式规范人们对大自然的行为,这便是用历史信息来警醒现代人,使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观。文书中所蕴含的信息彰显了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有助于唤醒人们的历史记忆,传承民族文化。一些家书或者家谱中所蕴含的家国观念、伦理道德有助于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并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其次,就旅游开发而言,可以在文书藏量丰富的村寨建立参观体系,实现地域连接与资源共享[6]。另外,还要与当地的民族特色与地理环境相联系,使文书的内容有理有据,构建一个更立体的网络体系。由此可见,旅游开发也是提升文书知名度的方法之一。事实上,除了这两方面以外,文书还有其他功能,有待学界的持续挖掘。
2.5 厘清主体关系
清水江文书出版碎片化、封闭性、征集工作困难等都指向文书涉及主体关系复杂这一问题,因此有必要厘清此关系,为清水江文书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清水江文书保护利用存在政府、学界、社会的三维主体结构,三者所关注的重点各有不同,可以针对三者的侧重点理顺其关系。在这三者当中尤其需要注意的就是学术界,各个学科的学者是研究清水江文书的主要群体,文书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是其关注的重点,要防止出现各学者或各机构之间相互封锁的情况,建立相应的学术规范[7]。
2.6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清水江文书的征集保护工作遇到了许多障碍,这无疑加大了后续工作的开展难度。针对这一情况,要做好当地居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可采用榜样示范与说服教育两种方法。榜样示范法,就是首先挑选出一批觉悟高的村民或村寨,帮助他们做好文书的保护与征集工作,再给予适当的精神表彰,以此激励当地的其他民众向其学习。一方面要学习这些村民的觉悟精神,自觉接受征集;另一方面是要学习他们的保护方法,尽量避免那些未能被征集或发现的文书遭到损坏。而说服教育则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其一,相关人员要使民众知晓文书的重要性、文书的易受损性以及征集的目的。其二,要使民众认识到主动接受文書的征集保护是其责任,号召人们积极参与到保护和开发文书的相关工作当中。其实,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的在于感召民众,激发他们的自觉性并落实到实践当中。
3 结语
就现实情况而言,清水江文书的利用现状不容乐观,许多文书被征集后便无人问津。文书的保护抢救虽然是工作重点,但实施有效的开发利用才是保护与发展的长久之计。可通过建设清水江学、提高文书知名度、进行数字化建设、开发价值、厘清主体关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等多种方法破解当前所面临的系列困境。
清水江文书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历史现象,其与创设环境紧密相连,在开发利用过程中须结合当地人文地理特征采取相关策略。对文书实施开发利用工作是令其走进大众视野的首要方法,是促进文书活态化传承的核心手段。清水江文书记录了清水江人民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是可供现代人借鉴的历史经验。它是我国重要的民间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无法替代的多方价值。清水江文书的研究不光需要专业人才的参与,还需要更多文书爱好者加入,为清水江文书的长期发展出谋划策。
参考文献:
[1] 马国君,王紫玥.贵州清水江流域林业契约文书整理和研究综述[J].古今农业,2019(4):119.
[2] 陈洪波,杨存林.清水江文书数据库建设若干问题研究[J].现代情报,2013,33(1):38.
[3] 张新民.清水江文书的整理研究与清水江学的建构发展[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4(1):99.
[4] 钱宗武.清水江文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2(1):94.
[5] 杨庭硕,朱晴晴.清水江林契中所见汉字译写苗语地名的解读[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4(1):70-72.
[6] 高聪,胡展耀.清水江文书分布形态普查及民间分布式抢救保护示范点建设[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2,4(3):38.
[7] 徐晓光,吴平.政府与社会共谋架构下的清水江文书抢救模式与多重保护机制建构研究[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2,4(3):37.
作者简介:杨道会(1997—),女,贵州遵义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