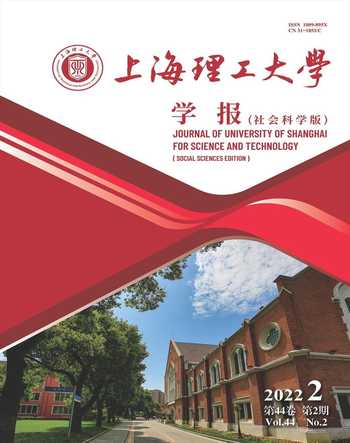《智利地震》和乌合之众的平庸之恶
许环光
关键词: 海因利希·冯·克莱斯特;《智利地震》;平庸之恶;乌合之众;《狂热分子》
中图分类号: I 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2)02?0161?06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22.02.009
德国作家海因利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Kleist)的短篇小说《智利地震》(Das Erdbebenin Chili,英译The Earthquake in Chile)讲述的是男主角青年家庭教师赫罗尼莫·鲁赫拉(Jeronimo Rugera)和其学生何塞法(Donna Josephe)小姐的悲剧爱情故事。他们的恋情被何塞法的兄弟告發,终致赫罗尼莫被辞退,何塞法被送进了修道院。他们在修道院的花园继续幽会。结果何塞法怀孕了,并在参加耶稣圣体节时发作了临产前的阵痛,舆论哗然。随之赫罗尼莫被投进监狱,何塞法被判火刑,后经法外开恩,改处砍头。狱中的赫罗尼莫羞愧伤悲,多次自杀未果。预计何塞法身首分离,赫罗尼莫准备自缢。突然地震发作,赫罗尼莫趁机从即将坍塌的监狱逃出。何塞法则从火海中抢救出她刚满月的婴儿,死里逃生。这对劫后余生的情侣在一座山谷中重逢,开始享受伊甸园般的幸福。他们原计划逃离本土,但临时去参加由教堂主教主持的感恩弥撒。在弥撒过程中,神甫历数本地的堕落和罪恶,严厉谴责赫罗尼莫和何塞法,说他们是伤风败俗的典范,点燃了人们的愤怒情绪。众人从人群中揪出了男女主角,并将他们乱棍打死。
关于这篇小说,国内外已经有一些零星的研究。赵薇薇认为小说表现的是父权秩序和母权秩序在自然条件下发生的碰撞,最终“在父权社会秩序的思维定势中重新臣服于父权秩序”[1]。刘午阳分析了小说中的暴力元素,认为文本中的暴力反映了作者“对启蒙宗教批判的延续”和“批判地接受启蒙思想的佐证”[2]。国外关于该小说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文本本身的解读。Grathoff 探讨了小说文本和1 647 圣地亚哥、1755 年里斯本两次地震间的联系[3]96。两次地震及其引发的相关讨论给小说提供了深厚的宗教背景。Fischer 认为小说后地震时期出现的诸般邪恶质疑了卢梭性善论的过于乐观[4]13。Schede 以专著的形式对本篇小说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认为小说揭示了“道德之恶是如何从自然之恶发生的”[5]20,其中对小说文本和各角色的分析尤具参考价值。不同于上述研究,本文透过作品中的父权、暴力、邪恶等表面现象,借助于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Le Bon)的《乌合之众》(法文原名Psychologiedes foules,英译The Crowd : A Study of the PopularMind), 德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 HannahArendt)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当译“恶之平庸”,此从众))”以及美国作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的《狂热分子》(The TrueBeliever)等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揭示小说悲剧背后乌合之众的平庸之恶,认为小说呈示的悲剧是在神权的背景上,由神甫鼓动引导并由狂热分子所推动实施的人对人的任意戕害和杀戮的群体运动。
一、乌合之众、平庸之恶、狂热分子
“乌合之众”源自勒庞的同名著作《乌合之众》。勒庞认为,群体轻信,易受暗示,易将幻觉当成现实;群体情绪夸张单纯,不允许怀疑,易走极端;群体偏执、专横和保守;群体中,情绪会相互传染,彼此暗示,个体会做出独处时闻所未闻的骇人之举;群体中有教养的人和无知的人没有区别。总之,群体“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等”[6]21。因而群体被勒庞看作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例如野蛮人。不仅如此,勒庞还观察到,个体一旦加入群体,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群体力量;那些原本施加在他身上的道德和法律约束荡然无存。用精神分析的话语来讲,那就是本我突破自我和超我的束缚,破坏力和犯罪行为瞬间爆发。《乌合之众》为解读那些原本无解的诸多群体性事件中普通人的变态行为提供了一把钥匙。这些人平素知礼义、识廉耻,乐善好施,一旦置身群体,却骤然无法无天,暴力血腥,恍若恶魔附体,像《智利地震》中的鞋匠那样。
“平庸之恶”源自犹太裔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Banality of Evil)。该书主角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chmann),资质平平,中学毕不了业,挖过煤,做过销售员、工匠(joiner),直到22 岁,几乎一事无成。这时纳粹运动蜂起,他投身其中,加入该党,成为党卫军的一员,并迅速发迹,最终成为纳粹德国时期屠杀犹太人“终极方案”主要负责者[7]100-109。然而在法庭受审期间,艾希曼的表现让阿伦特震惊:他其貌不扬,彬彬有礼,和其他普通人并无二致。正是这种“正常”让作者震惊和困惑:“这些人既非性倒错也不是受虐狂,他们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可怕地正常……这种正常比所有酷刑的总量还要可怕。”[8]373 在作者看来,这个现象超出现有的法律制度和道德准则所能理解的范围。艾希曼对自己犯下的罪行矢口否认,认为自己不过是在执行元首和法律的命令,远谈不上罪大恶极。他不仇恨犹太人,也未曾亲手杀害过任何人,充其量他“负罪于上帝,而不是法律”[7]93。极大的恶和平庸的人,其间的反差之大让阿伦特想到平庸之恶:不思考,盲目服从。这个特性让艾希曼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集团的主要帮凶之一,成为平庸之恶的代表,尽管他只是极权主义体制下制造出来的千百万庸众之一。此类庸众和乌合之众有着本质的联系:二者都是个体在群体中失去思考能力、无视道德律令、盲目服从等。
《狂热分子》的主题是群众运动。其内霍弗探讨了哪些人容易参加群众运动,他们的性格特征,特别是那些狂热者。结果作者发现:失意者、空虚者、自卑者、渺小者、自我否定者等最易成为群众运动的狂热分子;狂热分子急于参加群众运动,从急遽改变的世界渔利;狂热分子是一群嫉恨者;他们深谙自己的瑕疵与缺点,对他人的歹意与恶念特别眼尖,容易嫉恨,获得一种宣泄和解脱。此外,作者还提到,狂热分子是一群不能为自己负责的人,“不用负责任比不用受约束更有吸引力”[9]123。《乌合之众》也谈到过群体的责任感,认为“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6]16。差异在于,《乌合之众》里的群体不用承担责任,而狂热分子参加群众运动则是为了逃避责任,得到“免于自由的自由”[9]32,二者本质上是一回事。群众运动为狂热分子提供了无穷的机会。
《智利地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乌合之众的平庸之恶范例,宗教的外衣则为个体的胡作非为获取免责的正义感和神圣感。
二、《智利地震》中的乌合之众和平庸之恶
《智利地震》中乌合之众的形成和平庸之恶的诞生离不开浓厚的宗教背景,它贯穿小说始终。这符合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历史真相。众所周知,17 世纪的智利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西班牙是个天主教为主导的国家,境内超过90% 的民众信仰天主教。宗主国这种深厚的神学背景直接辐射影响到了它的殖民地,使得天主教成为智利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并且影响至今[10]490,561,621。1647 年地震发生时,圣地亚哥居民以为“末日审判(das Jüngste Gericht)到了”,震后只有一所教堂幸免于难,第二天确实举行了感恩弥撒等[3]96。篇中遍布的修道院、教会、神甫、耶稣圣体节等字眼,说明宗教的印记无所不在。大自然造成的创伤,最终还需要一场感恩弥撒来平复,足见宗教的影响之大。这种浓厚的宗教氛围为后文乌合之众及狂热分子的血腥暴力埋下了伏笔。否则,篇中的群体运动和平庸之恶几乎不可能发生。因为正如霍弗所指出的那样,“宗教、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就是产生普遍热情的工厂”[9]3。
具体说来,小说中的乌合之众和平庸之恶经历了三个阶段,它和赫罗尼莫和何塞法的爱情悲剧是同步的。因私生子事件而被认为伤风败俗,分别被处监禁和砍头的惩罚,这是第一个阶段。彼此生命垂危时地震爆发,让他们成功死里逃生,这是第二阶段。他们参加感恩弥撒,被神甫煽动,暴民合力,最终导致悲剧的诞生,这是最后阶段。这三个阶段,第一、第三阶段是人祸,第二阶段是天灾。小说中人祸之凶残远甚于天灾。《智利地震》中的乌合之众出现在故事的第一和第三阶段,只是就其效果来讲,第三阶段远较第一阶段为烈。就其性质而言,第一阶段的舆论审判和恶意围观属于冷暴力,第三阶段现场谩骂和乱棍打死属于热暴力。这里的暴力无论冷热,本质上均属乌合之众的平庸之恶。
在事件的第一阶段中,当何塞法在耶稣圣体节游行队伍中因产前阵痛而晕倒,隐情败露时,引起极大轰动,她被作为罪女立刻送进监狱。未待满月,大主教命令,对她进行最严厉审判。即便如此,人们依然不依不饶,“非常愤怒地谈论这件丑闻,并且以尖刻的言词攻击发生这件丑行的修道院”[11]208。很明显,何塞法产后受到的严厉惩罚,舆论暴力难辞其咎,而大主教的命令更让乌合之众师出有名。尽管多种势力介入,包括修道院院长转圜,阿斯特隆家庭说情,和总督法外开恩,可是惩罚一点没减轻,对女主的火刑只是改为斩首,但“圣地亚哥的太太小姐们对此还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11]208。
这次群体事件的第一阶段,相对温和,大都还停留在舆论和围观的层面,但依然有主有从,主是神甫,从是由普通民众构成的乌合之众。
相比第一阶段,第三阶段暴虐而血腥。
先是布道者的借题发挥,煽风点火。在肃穆庄严的典礼中,但见神甫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将地震夸大成末日审判的警示和预兆,让听众毛发悚然。他特别提到圣地亚哥的道德沦丧,伤风败俗,认为发生的罪行不比索多玛和蛾摩拉轻,然后浓墨重彩地用赫罗尼莫和何塞法作为反面典型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说他们的罪行被人姑息,亵渎天主。神甫“用尽了诅咒的言词,指出了犯罪者的名字,并要求把他们的灵魂交给狱里的魔王” [11]221。Jeffrey L.Sammon 认定赫罗尼莫他们的性爱无罪,罪是神权强加的[4]33。神甫唯恐天下不乱,言行举止完美匹配了勒庞关于鼓动家的相关论断,“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6]23。神甫无形中担当了这次群众运动的领导者角色,一位感动群体的演说家。Schede 认为神甫是故事转折的关键,正是神甫像魔术师那样用咒语招来(heraufbeschw?rt)了这次流血事件,神甫代表了教会和国家之间那虚空而世俗的公权之争[5]60-61。群体的情绪无疑是经由神甫借着宗教的名义被点燃的。作品中,正当赫罗尼莫和何塞法想溜走的时候,有人打断了神甫的布道,大喊大叫,要将罪人揪出来。这得到了好几个声音的附和,进而引起山呼海啸般的怒吼?教堂里几乎全体基督徒的声音“用石头砸死她,砸死她(steinigt sie)”[11]222。对这些民众而言,他们的石头对行淫者砸得越恨,越说明他们自己的清白,因为耶稣说过,“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约8:7)。正因为如此, 民众“怀着满腔神圣的义愤,凶残地抓着何赛法的头发要把她拖倒” [11]221。最终,赫罗尼莫和何塞法先后成了愤怒的牺牲品,被乱棍打死。此外,这场民众暴力还夺走了另外九条生命:一位是青春女子,另一位是费尔南多的幼子小胡安,这两位是完全无辜的。此外还有七个嗜血成性的人,这些人倒在费尔南多的剑下,他在拼死护卫怀中的两个幼儿。
与第三阶段的暴虐和血腥相比,第二阶段的天灾反面显得更为温善。地震将圣地亚哥变成了废墟,到处都是大难不死的灾民。人性却在这危难时刻焕发出光辉。人们互相帮助,共克时艰。人与人之间的嫌隙、怨恨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亲密无间,众生平等。何塞法用自己的奶水,喂食了一个饥饿的婴儿。这俨然是一个大同的世界,正如何塞法所感受的那样,昨日的灾难似乎是一件大恩惠。人类的物质财产遭到毁灭,博爱精神绽放异彩:
在目力所及的原野上,各个阶层的人们混杂躺在一起,有王侯和乞丐,有贵妇人和农家女,有官吏和雇工,有修士和修女,他们互相同情,互相帮助,他们从地震中抢救出来赖以活命的东西,都高高兴兴地分给别人,仿佛这场普遍的灾难,将所有死里逃生的人,都结成了一个大家庭[11]217。
人们交流着震后出现的诸多英雄事迹。他们平时默默无闻,无异常人,却能在灾难中像伟大的罗马英雄:勇敢无畏,藐视危险,欣然赴难,自我克制,勇于犧牲。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正如勒庞所云,群体可以杀人放火、十恶不赦,也可以勇于奉献和牺牲,其崇高甚至远超孤立的个体时所为[6]27。在此,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一群人,一群性情能够在瞬间翻云覆雨,天使秒变撒旦的人。
赫罗尼莫和何塞法的偷情——实则自由恋爱——为何会被无限放大,甚而至于十恶不赦呢?这离不开当时神权为主导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基督教主张男女婚姻的稳定以及两性关系的纯洁,对婚外性行为是严苛的。《圣经》说,上帝觉得亚当独居不好,之后待他熟睡,从他身上取出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夏娃作为他的配偶帮助他,并且训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创2:24)。人的婚姻生活开始了。此外,“不可奸淫”(出20:14),“你们要逃避淫行”(林前6:18),“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提后2:22),等等,均是主张人要自洁。上述常识对基督教世界来说是家喻户晓的,其中的一些教义更是深入骨髓。赫罗尼莫和何塞法敢于冲破教规的羁绊,偷享禁果,被忌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教主所做的,只是煽起了民众对违反教规者的仇恨,“以无尽的强迫和灌输去维护正统”[12]26,以达到维护教义的目的。
在神权主导一切的社会环境下,人们不但被迫停止思考、盲从,基本的人伦也会发生扭曲。比如《智利地震》中,赫罗尼莫和何塞法的恋情之所以败露,是因为何塞法的兄弟向父亲告发,导致连锁反应,直至悲剧诞生。小说结尾,混乱中,是男主的父亲自己主动指认揭发了自己的儿子,“这就是赫罗尼莫·鲁黑拉,老乡们(ihr Bürger),因为我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11]223。随之,赫罗尼莫就被一棍打翻在地。Schede 认为前文的“ihr Bürger”是一种“时代穿越(anachronistische)”,影射了法国大革命时的人伦错乱,赫罗尼莫的父亲有心之举则反映了教会势力对正常家国人伦关系的破坏[5]64-5。即使不论法国大革命,赫罗尼莫父亲表面上的大义灭亲,其中的人伦错乱却是真实的。从情理上讲,一般的父亲即便不能做到儒家的父子互隐(《论语·子路》),护犊则是父母的本能反应。上述种种逆人伦的行为,正是《圣经》所极力宣扬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太10:21)。基督也曾口口声声明言,他不是来叫地上太平的,而是要叫地上动刀兵。他要叫父子、母女、婆媳生疏的,媳妇与婆婆生疏,因为家人是仇敌。甚至爱父母子女过于爱他的,不配作他的门徒(太10:34-37)。何塞法的兄弟、赫罗尼莫的父亲能够做出六亲不认的行经,正是奉行了教义的结果。他们逆了地上的人伦,却顺了天上的圣训。巧合的是,艾希曼也有过类似的表示,“如果收到杀害父亲的命令,他无疑也会照办”[7]94。这说明,就扭曲人伦迫使民众盲从而言,神权和极权是相通的。
惨剧已经发生了,制造者不是英雄,而是一群庸众,一群烏合之众,一群不会独立思考的盲从者,打着宗教的幌子,借着群体的力量,激情杀人。这就是《智利地震》中乌合之众所造成的平庸之恶。但是如果没有小说中另一个关键人物,佩德里洛鞋匠,我们的解释拼图将不可能完整,更谈不上完美,毕竟,“群众运动以蛊惑者为前驱,以狂热者去实现,以行动者去巩固”[9]156,霍弗的上述观察是准确的。
三、作为狂热分子和刽子手的佩德里洛鞋匠
小说中的佩德里洛鞋匠(Meister Pedrillo)具有《狂热分子》所指称的失意者、自卑者、空虚者等主要条件和特征,缺的只是一个让压抑已久的激情爆发的机会。鞋匠原本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乌合之众中的一员,走到哪都是被忽略的对象。如果群体运动不来,鞋匠很可能就此寂寂无闻,了却一生,像大部分人的命运一样。群体运动一来,他借势发力,一跃变成狂热分子和刽子手,成为风暴的焦点人物,平庸之恶的最终实施者,像艾希曼那样。可以大胆地预测,如果没有狂热分子佩德里洛鞋匠之流的参与,《智利地震》中乌合之众所造成的平庸之恶即便能产生,其成色势必大减。对佩德里洛鞋匠可探讨的点很多,这里仅聚焦于一点:他对男女主角本无深仇大恨,何以能对他们痛下杀手而后快。
鞋匠对男女主角赫罗尼莫与何塞法的疯狂报复极有可能出于忌恨。男女主角的“偷情和伤风败俗”,和鞋匠原本是无干的。鞋匠和男女主角唯一的交集不过是曾经帮女主角修过鞋。然而鞋匠却伺机积极介入。在群体运动中频频动作的鞋匠,被Schede 称为“最血腥最充满忌恨的个体,撒旦式恶棍之王(Fürst der satanischen Rotte)”[5]61。然而此前,他是个规矩的普通人,以补鞋为生(Schuhflicker),处于社会最底层。女主则是贵族后裔,也是他的主顾之一;文中说鞋匠“认识她至少如她那双小脚一样清楚” [11]221。相比赫罗尼莫与何塞法,鞋匠自身的弱势明显。他们的高度鞋匠原本是无法企及的。如果不是因“偷情”而丢人现眼,男女主角是无可挑剔的。至少女子修道院院长就认为何塞法“平素品行端正” [11]208,想要减轻她的罪责。男女主角一朝东窗事发,鞋匠迅速占据了道德的至高点。从此,鞋匠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可以将男女主角踩在脚下,任意践踏。其实,鞋匠对他们的迫害行为不无私情。据Schede 的分析,因为主顾的关系,鞋匠对女主有被动的亲近,对她隐藏有一种性欲,奈何囿于阶层,她高不可攀,正如她优雅的小脚和他的粗俗恰成鲜明的对比一样。后来男女主角的丑闻曝光,“缩小了她的不可企及性”[5]61。据此Schede 推导,鞋匠觉得有理由在公众面前羞辱她,只要有机会,甚至从肉体上毁灭她。这些分析是入情入理的。鞋匠的忌恨、心理的失衡,或许正因为他自己的劣质而生发,因为被忌恨的对象一般都是优越于嫉恨者的。正如霍弗所言,“我们无法恨那些我们鄙夷的人”[9]100。鞋匠对赫罗尼莫的质证,揭发和报复,所持心理和对女主角的心理如出一辙。作为假想的情敌,男主角尽管只是家庭教师,西班牙移民,但社会地位比鞋匠明显要高得多,文化素养、个人魅力等更是让后者相形见绌。品性的优劣也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关键时刻男女主角的优雅、奉献和担当,与鞋匠的落井下石恰成鲜明对照。
说鞋匠劣质其实不冤,尤其是在群体运动中,旁人是看在眼里的。城防司令的儿子费尔南多就曾气愤地指称骚乱中的鞋匠为“无赖”,建议海军军官将他逮捕起来,因为“整个骚乱全是他给煽动起来的” [11]223。费尔南多是小说中正义的化身,小说称他为“神一般的英雄(Dieser g?ttliche Held)”[11]224,言行举止颇具骑士风度。Schede 对费尔南多评价很高,认为他“代表了一种更高的道德和理念(Exponenteiner h?heren Moral, die als Ideal)”[5]60。正是费尔南多在小说高潮部分于血海中用自己的宝剑拼死保护一众女眷和弱小,成功地将无辜的伤亡降到了最低。在男女主角被害后,又是费尔南多收养了他们的遗孤并视为己出。因此,费尔南多对鞋匠的上述指控是可信的,也不过分。鞋匠确实煽风点火过多次,刻意将事情搞大。他曾含沙射影地暗指费尔南多和站在他身边的何塞法关系暧昧,并意味深长地暗指何塞法手中的孩子就是他们关系的证明。该婴儿实则是费尔南多和另一位女士的婚生子小胡安。鞋匠还煽动大家揪出男主角赫罗尼莫,致使后者现身并被乱棍打死。当众人不知道哪位是女主角时,又是鞋匠上前指认,因为他给女主角何塞法修过鞋子,有过近距离接触,清楚地知道她长什么样。小说末尾,至少两条人命是记在他的账下的,那就是死于他棍下的前女主顾何塞法,以及被他摔死在教堂台阶柱头棱上的小胡安。鞋匠凭借宗教集会之势,以主的名义,羞辱、谩骂、激情杀人,种种肆意妄为,还不用追责,至少全文没有交代他是否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总之,从平日的庸常之辈,到群众运动中的狂热分子,到暴乱中杀人不眨眼的恶魔,鞋匠的剧变并非个案。鞋匠在宗教集会上顺势爆发,有恃无恐,由平日的贫民、良民和顺民,一变而成为刁民、暴民和撒旦,成为一个平庸之恶的典范而不自知,如同艾希曼那样。
四、结束语
《智利地震》呈现的人伦惨剧,其本质是乌合之众的平庸之恶。自由恋爱、未婚先孕等婚前两性关系,现代社会司空见惯,但在神权统治一切的时代,却是为社会所不齿的大逆不道。该平庸之恶的诞生以神权为背景,由神甫煽风点火,并由另一些狂热分子如佩德里洛鞋匠者流所推动实施。他们借感恩弥撒发难,让它迅速蜕变升级为一场暴力血腥的群体运动。其时社会失序,道德失范,人伦被践踏,同类间肆意迫害残杀而不必担负任何责任。作品所描写的事件虽然发生在三百多年前,但作品所揭示的乌合之众的平庸之恶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