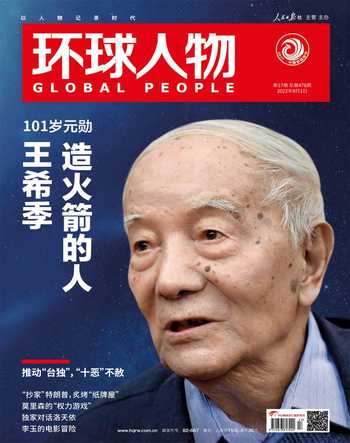他们书写的“大科学”工程史
刘舒扬

2022年7月24日,搭载问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中说,50年前,“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我在陕北梁家河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激动。习近平强调,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
“简单来说,火箭是一种载具,加上战斗部(毁伤目标的专用装置)就是导弹;放上卫星、飞船,就能将其发射上天,所以‘两弹一星中的导弹和人造卫星——有一半与载人航天直接相关。”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公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两弹一星”是新中国第一个“大科学”工程,即以大规模仪器设备、来自政府或国际组织的雄厚资金支持为特征,通常情况下会形成科学家群和技术人员群共同从事该研究。它留下了一大批人员、技术、设备以及党中央领导下的大力协同经验,这些力量是新中国科研体系的重要组成,在发展载人航天事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迄今为止,载人航天是我国规模最大、复杂程度最高的“大科学”工程。
从“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背后是数十万参与者半个多世纪的筚路蓝缕。如今,随着梦天实验舱运抵海南文昌,中國空间站在轨建造已进入冲刺阶段,载人航天工程到今年即将完成“三步走”规划。回顾往昔,它是这样开始的——
初遇
1957年,24岁的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生戚发轫来到位于北京西郊的一处园区报到。这里是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下简称五院),前一年刚成立,院长是大名鼎鼎的钱学森。
时间回到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前。时任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成员的钱学森跟随导师、咨询团团长冯·卡门在一个德国小镇,提审了已向美国投降的世界顶级火箭专家、V-2导弹总设计师冯·布劳恩。
V-2导弹最大射程可达320千米,破坏力巨大,是现代火箭技术首次成功应用于武器系统。纳粹德国使用它的目的在于从欧洲大陆直接准确地打击英国本土目标。审讯结束后,冯·布劳恩写出的一份名为《德国液态火箭研究与展望》的报告,让钱学森受益匪浅。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基本形成共识,要研制原子弹和导弹。钱学森的归国让这一进程显著提速。1956年10月8日,研究导弹的五院最先组建,由回国刚满一年的钱学森任院长。任新民、梁守槃、屠守锷、黄纬禄、姚桐斌等一批知名科学家应邀前来,任各大研究室主任。其中,任、梁、屠、黄后来被合称为“航天四老”;而23名“两弹一星”元勋中,这一时期在五院任教的就有5位: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姚桐斌。
可问题在于,除了钱学森,不管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久经沙场的军人,还是知名专家,谁也没见过导弹什么样。任新民回忆,钱学森同志是当时我国唯一在这个领域工作过的专家。为此,钱学森撰写了中国第一部航天专业方面的教材——《导弹概论》,讲最基本的原理,为大家“扫盲”。戚发轫也是台下的学生之一。上课前他还听到有人好奇,这么大的科学家怎么亲自给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上这门课呢?“钱学森在这门课一开始说,搞导弹绝不仅仅是靠科学家,而要有一批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基础的队伍。”戚发轫回忆道。
当时除钱学森外,还有梁守槃讲火箭发动机、庄逢甘讲空气动力学等,都是应导弹研制需要被调来的航空、火箭领域专家。“我们在做‘两弹一星时,很多事情是不清楚的,包括导弹、核弹应该怎么做,从科技角度说,大家都是一边摸索一边干。从管理的角度看,正是这一时期,开始形成了一种党中央领导下的大力协同的工作方式。”王公对《环球人物》记者分析道。在这种热火朝天的氛围下,新中国的导弹研制队伍逐渐成长起来。
与此同时,对苏联两枚导弹的拆解、仿制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根据此前中苏两国政府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将为中国提供两枚P-2教学弹。当苏联专家提出把中国仿制的导弹发动机拿到苏联进行试车时,任新民拒绝了,他说:“那我们中国的导弹事业永远无法独立了!”不久后,他主持建成了中国自己的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当苏联将所有专家撤走时,屠守锷显得很平静——他有思想准备,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85天后,1960年11月5日,仿制苏联P-2导弹而成的东风一号导弹在酒泉发射成功,中国彻底结束了没有导弹的历史。

1960年,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时的戚发轫。

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导弹研制人才,钱学森亲自撰写教材,并给大家讲了启蒙第一课《导弹概论》。图为1960年前后,钱学森(左一)在上课。
“国防新技术协定”不仅教给了中国科学家们关于原子能、导弹、火箭建设等领域的知识,更将“自力更生”几个字的写法牢牢刻在众人心上。距离酒泉1万多公里外的莫斯科,一名年轻人的人生也因这个协定改变了。根据协定,苏联将接收中国部分火箭导弹专业的留学生。为了让部分学生早点参加工作,1957年12月,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安排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三年级的8名留学生全部改学火箭导弹设计专业,25岁的王永志也在其中。在那个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年代,他很快决定,服从国家发展需要。1961年3月,王永志来到五院——在这里,王永志与戚发轫这两名年轻人生命轨迹第一次相交。
这时,戚发轫正跟着屠守锷、任新民等人为尽快搞出“争气弹”——东风二号导弹而昼夜奋战。尽管这枚导弹不会在东风一号导弹的基础上做大改动,只是将发动机和弹体结构等各方面尺寸加大,使其射程达到中近程的要求,但从仿制走向独立设计,这对中国年轻的导弹团队来说无疑是一个质的飞跃。1962年3月,东风二号导弹竖立在了发射架上,然而点火后仅仅过了69秒,“轰”一声巨响,导弹在不远处坠落,在戈壁滩上砸了一个大坑。

在苏联留学时的王永志。
当时还是基层技术人员的戚发轫第一次参与这样的工作,失败面前,他觉得“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心里非常难过,无地自容”。此后两年,屠守锷、任新民组织大家重新审查了导弹的总体设计方案,并对各分系统进行了大量研究试验,进行了许多重要修改。1964年6月,就在东风二号导弹再次发射前夕,意外出现了:当地高温天气导致导弹推进剂受热膨胀,所需燃料无法如数灌入,这将大大影响导弹射程,发射任务陷入困境。
带着“把一切问题都消灭在地面”的信念,第一次参加导弹发射工作的王永志“壮着胆子”敲开了钱学森的门,陈述了自己的想法:推进剂的成分之一酒精受热膨胀,密度也随之改变,同时与其他成分的配比会发生变化;若减少600千克燃料,导弹同样可以达到预定射程。钱学森对眼前这名年轻人的方案表示了肯定,并在新一轮讨论会上提出:就按王永志说的办。
6月29日早上7时,中国第一枚自行設计的中近程导弹披着“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的巨幅标语,准确命中目标,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这意味着中国基本掌握了独立研制导弹的复杂技术。3个月后,随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弹结合”提上日程。
1966年10月27日,在聂荣臻元帅的亲自指导下,东风二号甲导弹(由东风二号导弹改型而来)托举着核弹头直冲云霄,中国首枚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成功,终结了中国核力量“有弹无枪”的历史,中国跻身世界核大国行列。戚发轫记得,为了庆祝胜利,聂帅还请大家吃了手抓羊肉,香喷喷的滋味令他至今难以忘怀。
成长
“两弹结合”成功之后,由于导弹技术与火箭技术之间的相通性,戚发轫参加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王永志则在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后,就在总设计师屠守锷、总体部副主任孙家栋的领导下,分管中程导弹的总体设计和研制工作。

1966年10月27日,中国首次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1965年1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正式启动。两年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在即,钱学森担任院长并亲自点名孙家栋负责总体设计工作。
得知这一消息时,38岁的孙家栋正满头大汗地趴在火箭图纸上搞设计。“我一毕业就从事导弹研制,本想这辈子可能就搞导弹了,没想到和卫星结下不解之缘。”孙家栋感慨道。他按照专业配套,从各部门抽调了后来被称为“航天十八勇士”的18名技术骨干,组建起卫星总体设计部。35岁的戚发轫就是这1/18,而且还是卫星的技术负责人之一。“这件事情压力太大——‘我能干成吗?”他罕见地犹豫了,可最后,还是向前迈了一步,因为“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干什么”。
“科学家自己的研究旨趣与国家需求之间的平衡问题,长期以来都是科学史研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王公说,有时一项研究虽然无法从学术上引起科学家的兴趣,但只要有益于国家,一批科学家的研究就会发生转向。这不仅发生在研制“两弹一星”时,比这更早的20多年前,抗战爆发后,众多爱国科学家就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雷达、炸药、营养保障等抗战急需的领域。
戚发轫始终牢记几年前东风二号导弹第一次发射失败的教训:为了保证飞行试验成功,必须做充分的地面试验。条件简陋,没有低温实验室,戚发轫就去海军冷库模拟低温,连脚上穿的塑料鞋都被冻裂了;没有可用的计算机,大家就靠人力甩,模拟卫星上天后天线随旋转甩出的状态。

1966年10月27日,聂荣臻与“两弹结合”参试人员合影。国旗下方为聂荣臻。
1970年4月14日,戚发轫从酒泉赶回北京,随钱学森等人向周恩来汇报卫星发射工作的准备情况。他还记得,汇报完后总理问自己,上天之后能不能准确播放《东方红》乐曲,会不会变调?他老实回答:“凡是想到的、地面能做的试验我都做过了,就是没有经过上天的考验。”后来中央批准了戚发轫等人写的转场(把已经搭载了载荷的火箭从总装厂房转运到发射塔架)报告,24日晚9时35分,搭载卫星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5分钟后,各观测站几乎同时报告:“星箭分离,成功入轨。”基地司令一听,高兴地一拍戚发轫肩膀:“小伙子,成啦!”戚发轫不放心,说,不成,还得等着,还没听到《东方红》呢!确认乐曲旋律正常播放的时候,他才兴奋地跳了起来。许多人长期积压的情绪也在此刻爆发,戚发轫看到,“确确实实很多同志流泪了”。
东方红一号重173公斤,比前4个国家首发的卫星加起来还要重,预计工作时间20天,实际工作28天。今天,这颗“中国星”仍在绕地飞行。就在4个月前,它还被观测者捕捉到与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擦身而过,这是两项“大科学”工程跨越半个世纪的问候与致意。

左图:1992年,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图为坐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总控制室里的王永志。右图:2003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召开期间,戚发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外。7个月后,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并安全返回,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这之后,戚发轫集中精力研发了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返回式卫星等等。王永志则一直在和导弹、火箭打交道,先后参与了中程导弹、洲际导弹研制,并作为总指挥于1990年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式运载火箭“长二捆”。曾经的年轻人此時都已两鬓斑白,他们还不知道,俩人的生命轨迹将再次交汇在一起。
重逢
1992年,王永志60岁,戚发轫59岁,在快退休的年龄,他们正为同一件事倍感压力——这一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被批准实施,俩人分别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和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今年,当90岁高龄的王永志回忆起当时的心境,笑道:“用东北话说,‘压力贼大。”
“王永志此番任命,与钱学森的大力举荐有关。不只是‘两弹一星,中国的载人航天和钱学森也是密不可分的,他在大方向的把控上发挥了很大作用。”王公说。2005年神舟六号发射成功后,戚发轫等人到钱学森家中汇报情况。钱学森看戚发轫满头白发,还问起孙家栋和王永志的近况:“你们三个谁大?他们都好吗?”
载人航天事业是一个规模宏大、高度集成的系统工程,由航天员、空间应用、载人飞船、运载火箭等七大系统组成,要在其中统筹调度,谈何容易?王永志却在一开始就下定决心:大胆跨越,让中国飞船一经问世,就是世界水平。
他主张,飞船一起步就搞三舱方案。有人认为,三舱不如两舱简单,步子迈得太大。一番激烈论争之后,三舱方案最终通过。王永志说,要赶超三四十年差距,想一步到位,不是很容易的事,我这样为自己加压,也为飞船系统加压,是为了载人航天的最大成功。
戚发轫也充分利用了这种后发优势。国外飞船发展了几代,才明确其用途是作为天地往返的运输工具,建造空间站才是最终目的。中国飞船起步比较晚,从一开始研制就有明确的目的性,一步到位建成一种多用途的实用飞船,实现跨越式发展。
根据戚发轫的计算,一般来讲,航天产品的可靠性为0.97,也就是100次中允许3次失败,载人航天的安全性指标为0.997,二者合在一起,故障率为1/300000。换句话说,每天发射一次,30年都不能出事。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要把所有可靠性措施都用上。从神舟五号到神舟十四号,中国共有14位航天员飞入太空。“你看他们现在干得多好。有一点我就感到特别欣慰,一直干到现在,这就快30年了,我们一直是安全的。”王永志说。
近乎完美的记录背后,是航天人严苛的“归零”五条:定位准确、机理清楚、故障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比如发现一个插头坏了,原因是里面用的铜有问题。那么铜是哪个厂生产的、为什么会出现故障、今后怎么避免,这些问题全部要搞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把每一个环节还原到“零”的地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现任总设计师周建平就经历过这样的“归零”时刻。那是2001年9月,神舟三号飞船已运抵酒泉。进入发射准备阶段时,测试发现一个插头的其中一个导点出现故障。有人认为,飞船上还有近百个插头、上千个插针插孔,这个故障点不会影响发射,如果现在更换,飞船发射时间要推迟至少3个月。现场还聚集了500多名从外地赶来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有老同志不理解:我们航天队伍从来没有过进场后撤场的经历!但进度要服从质量,试验队伍撤场,插头全部更换,发射日期推迟。几个月后,神舟三号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并且保证了飞船往返过程中所有数据的真实、确凿、可靠。
此次飞行试验,连同接下来的神舟四号,都与载人飞行状态基本一致,这一切都是为首次载人航天做准备。2003年,神舟五号起飞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试验大队500多名科技工作者在给航天员的信中这样写道:“请放心,我们一定以实际行动实践庄严的承诺:确保神箭入轨,确保神舟正常运行,确保您安全返回!”2003年10月16日清晨,当航天员杨利伟自主出舱,向人群挥手时,王永志“一看到这么健康走出来,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戚发轫至今觉得,自己这一生受到的最高奖励,是杨利伟说的那句“中国的飞船真棒!”
对工作全情投入,对家庭就难免顾此失彼。戚发轫坦言,自己有这样一个任务在身,确实顾不上别的,也从没和妻子外出度过假。老两口的唯一一次出游,是1994年戚发轫在研制风云二号卫星时突遭卫星爆炸,不慎中毒,在昆明疗养了10天,他还对妻子承诺:“以后咱们多出来玩玩。”可身体恢复之后,戚发轫转头就把这话抛到脑后,再次全身心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连妻子身患癌症也没能及时察觉。妻子病重,他才发现,原来老伴一直在偷偷攒钱,希望有生之年两人再相伴出游一次。直到2001年病逝,妻子这个愿望也没能实现。
一路走来,面对这么多压力和挑战,戚发轫觉得,说来说去,支撑自己的还是对祖国的热爱:“爱国就要爱事业,爱国不爱航天,那不是空的吗?”他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神舟一号研制期间,社会上流行一句话“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不远处的中关村成为一片开放的热土,科研院所受冲击很大,人才不断流失。“我留不住啊,心里很痛!走的人没有错,但留的人我佩服他们。”花甲之年的他带着尚志、张柏楠几名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坚守岗位,终于在1999年成功把飞船发射上天。令他欣慰的是,从飞船总设计师的岗位退居二线之后,当年的几名小伙子也成长为载人航天工程中独当一面的总指挥与总设计师,神舟六号、神舟七号、神舟八号、天宫一号等先后从他们手中升空。
“这种对祖国深厚的爱在几代科学家之间都有非常鲜明的体现。”王公说:“王永志、戚发轫是在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培养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又把这种热爱传递给更年轻的一代人。所以我们说,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事业有传承,精神也有传承。”
这样的精神并不只在航天人身上有,在整个科学家群体中都有迹可循。一名在中科院工作的学者向《环球人物》记者分享了他的亲身经历:夜晚11点的园区街道,总能形成熙熙攘攘的自行车流,那是从办公区回到住宿区的人潮;凌晨2点向外望去,还能看到对面研究所里亮着的一二十盏灯。“大家平时也会自嘲这么累干吗,可一旦工作起来比谁都认真。”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著有“航天七部曲”的作家李鸣生告诉记者,在他看来,中华民族那种吃苦耐劳、无畏艰险、不怕挫折、敢于攀登、积极向上、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精气神,是孕育“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的肥沃土壤,并使其不断被发扬光大。
回望9年前,中国载人空间站名称正式公布,中国空间站被命名为“天宫”,核心舱被命名为“天和”。如今,“天和”牵手问天实验舱,第二个实验舱“梦天”也已在发射场区开展各项总装和测试工作。未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共同孕育的中国天宫仍将翱翔于九天,继续不断叩问无垠宇宙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