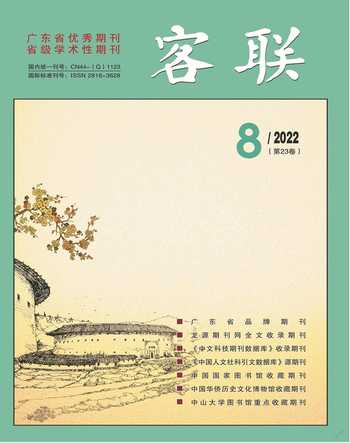烫样的审美分析
徐洵
摘 要:本文论述了“烫样”的基本发展脉络,认为烫样具有制作精湛、穷极变化、合于法度三大审美特征。
关键词:烫样、壶中天地
中国传统建筑模型在清代臻于成熟,其典型代表就是烫样。这种成熟同中国古典美学在清代进入总结期是一致的。从科学技术史看,烫样及其一系列的设计方法凝结了千百年来古人的智慧。同样,中国明清美学的一系列特征也集中地展现在烫样之中。可以说,烫样就是中国封建末期文化精神包括美学精神的感性显现。
烫样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封建末期文化精神包括美学精神的载体,这一方面与其设计和制作工艺相联系,另一方面同其文化特征相联系,两者互为表里。首先,烫样的功能主要是呈现园林、建筑的效果,及其内部装饰的效果。这种效果的展示依靠的是细节的深入表现,绝非概念性的呈现。其次,随着制作技艺的完善,壶天的艺术境界最终在烫样中找到了发展的空间。所以,这就使得烫样可以成为中国封建末期文化精神包括美学精神的载体,成为这一时期中华文化的代表性艺术。
一、烫样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类型
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独特性,与其所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所形成的工官管理制度和建筑设计方法有着深刻的联系。
早在《春秋左传》中就有“春,晋士蔫为大司空。夏,士荔城绛,以深其宫”[1]的记载。后来,历朝历代沿用并发展这一制度,以负责管理宫室、宗庙、城防及水利等工程的设计与施工。由于其在位者为庶人,所以只有极少数人被写进史籍,名扬于后世。
清朝在管理上沿用唐宋制度,分内、外工。[2]其中,内务府营造司的样房以《工程做法》为依据,负责设计图纸,并依照建筑物图纸所拟定的尺寸与式样,按照一定的比例,使用草纸板、秫秸、油蜡、木料等材料加工制成模型。因其制作工艺中有熨烫这一工序,所以称之为烫样。其中“样式雷”世家因祖孙八代主持清代官工建筑的设计、制做烫样而得名。
今所存烫样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尺寸从小到大可以分为五分样、寸样、二寸、四寸以至五寸样等数种。从内容看,有故宫、景山、圆明园、北海、中南海、天坛、万春园、颐和园、清东西陵等。其中又以同治时期重修圆明园时所制烫样数量最多,包括圆明园中路全部,如泉石自娱、同乐堂、上下天光、思顺堂、天地一家春,圆明园北路的恒春堂、廓然大公,南路的勤政殿,西路的万方安和等等。万春园有西路的清夏堂,中路的天地一家春等。颐和园有清音阁、治镜阁等。北海有漪澜堂、庆霄楼、静心斋、画舫斋、快雪堂等。中海有春藕斋、勤政殿,南海有瀛台等。故宫有延禧宫彩棚,景山有寿皇殿等。此外还有地安门、清东陵等处的烫样。从形式上看,主要是以下两种类型:一是单座建筑烫样;二是群组建筑烫样。其中单座建筑烫样,从形式、色彩、材料和尺寸数据上对建筑进行了全方位展示。而群组建筑烫样,则以院落或是景区为基本单位,旨在表现建筑组群的布局和周围环境布置的情况。[3]
二、烫样的审美特征
(1)制作精湛
为了使得烫样具有逼真的视觉效果,其使用的材料丰富,制作程序也较为繁琐。大体上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烫样的基本材料是纸张、秫秸、木头等,其纸张的选用范围集中于元书纸、麻呈文纸、高丽纸以及东昌纸(多用于家具、墙体、屋顶制作),并通过水胶粘合。木头使用质地较为松软且易于加工的红、白松(用于房屋框架制作)。制作工具包括簇刀、剪子、毛笔、腊板以及小型烙铁。
第二,烫样的制作方法以墙体和屋顶两类的制作方式最具代表性。
墙体的板料是将高丽纸、元书纸、麻呈文纸相互粘合晾干后形成的硬纸板,通过分段裁剪、涂饰加工后粘合而成。
屋顶首先使用黄泥做成胎模。并以高丽纸为底,贴在胎模上,再依次粘以麻呈文纸和东昌纸,待晾干后形成屋顶硬壳。通过剪切拼接的方式可以塑造重檐等复杂的屋顶形态。特别是使用“线香”粘接方式组成的瓦垄,通过上色或绘制图案,表现出质感。
其内部陈设,比如桌椅、几案等的制作步骤同上,只是做工更為细腻。[4]
精湛的技术是制作者不断钻研的成果,由于其承览的对象是皇帝,所以追求精美的制作是有其必要性。
(2)穷极变化
通过比对其与图纸、做法说明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完整还原与之对应的古代建筑。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与现实构成了映射关系,所以现实中小到花木大到景物设置,都可以在烫样中找到依据。透过阅览大量的作品,可以发现烫样的群组呈现模式是一种非自由的布局方式:它们在狭窄的空间中,通过毫厘之间的计算,营造出高度密集、体量纤小的景观与多变的建筑形态。为了解决拥挤的视觉体验,只有运用极尽变换的艺术手段才能形成富有层次的视觉效果。比如,每一建筑的开间数量、平面与立面的造型、屋顶的样貌、彩绘与纹样特点,甚至是内部陈设摆件等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表现出在不自由的艺术美中展现出超脱的变换法则。
通过在景观设置之间的对比与应和,这种穷极变化所塑造的结果就是展现出建筑之间的深度和谐以及各景观之间的精细匹配。比如,在烫样中将屋、池,甚至是具体的门与窗等景物的尺度进行缩放,以映衬整体相对较大的空间体量。在这个环环相扣的体系中,每一块山石、每一丛花木甚至是建筑内部的家具陈设,其形态与位置都是预先设定的结果,其作用绝对没有独立的欣赏价值,只可能服务于整体,并最终处于一整套完整又复杂的限制之中。
精湛的制作技术使得烫样具有复杂变化的基础。在狭小空间中呈现复杂的变化,就具有了视觉上的统一与变化。
(3)合于法度
传统艺术法则随着中华文化的长期发展而趋于完善。从烫样中,我们可以看见,纵是空间形态的千变万化,每一类景物的处置方式,每一类型的空间关系的处理效果,无论是从其尺度、风格、样貌、形态等各种因素还是从其整体布局上分析都已是无可挑剔。可见,设计师们都是按照最完美的形态和最成熟的样式创造出小至腰门、栏板、花台,大至池桥廊榭、亭台楼阁,并将空间的节奏变化表现出最和谐的韵律。我们称其为“与建筑对话”、“与自然和谐”,其实都是将这些设计手法转换成模板而被一一套用。最终被塑造成为最为合理,最为有效的构园方式。所以,空间内部的景物关系只有在这种程式的运作中,才会有其生命力。
将此类法则换置于烫样之中,就可以发现,如果抛弃了这种固化的法则而另辟蹊径,那么呈现给我们的只会是矛盾又混乱的置景关系。也就是说处于某种原因,这种法则统领了整个空间的一切元素,并使得繁杂的景物能够按照合理的起承转合关系被一一恰当地布置于其中。我们观赏它,不会觉得冗杂,反而看见了空间中的一切矛盾都被遮蔽甚至是被消解了,一切元素的呈现都是最为合理的,都是最为优美的,都是恰到好处的。这种合理其实是人为的控制结果,而非自然的生成。
当然,“自然”不是逃离人工的刻画而单独存在,只是自然所表现的特征应当是应和天地万物的运迈,契合宗法社会的不断发展。所以,“自然”本身就要在塑造天然环境的基础之上,通过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传达更为和谐的天人和一。
烫样的制作过程、呈现效果的多变性以及理法的限制共同构建了烫样的审美特征。其每一项内容虽然都是分别叙述,但其实彼此不可分离。正是由于此,烫样最终呈现出精微的视觉效果。在这种空间形式中,纵然应和了天地万物的发展,表现出天人之际的和谐统一。但受制于其形式,也绝不可能让人真切的感受到其中的深刻内涵,最终只可能浮于形式。一如黄宗羲所言,明儒于毫厘之际,使无遁影。
烫样的变化虽然繁缛,但非混乱,这是受制于法理框架的。其设计不是随心所欲的,是在法度的框架内去实现的。
参考文献:
[1] 十三经 下[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 原本,工部营缮司掌管外工,内务府营造司承办内工。到乾隆时期又在圆明园设内工部,专门办理园工设计事务。
[3] 梁启雄.哲匠录,中国营造学社编.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第4卷 第1期[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08.
[4] 黄希明,田贵生.谈谈“样式雷”烫样[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04):9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