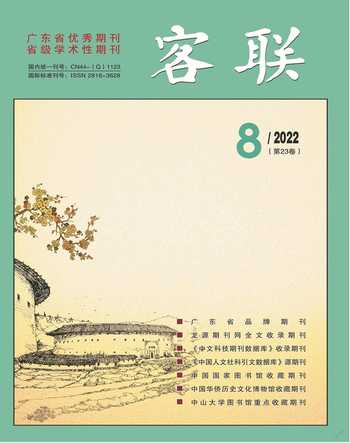澳门刑法中的必然故意
林磊鑫
摘 要:澳门刑法对于犯罪故意的分类不同于我国内地刑法犯罪故意的分类。内地刑法将犯罪故意分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两种故意模式,而澳门刑法则将犯罪故意分为三种,即直接故意,必然故意与或然故意。学界中对于必然故意的规定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内地刑法中也有必要引入必然故意的概念,区分明知危害结果必然会发生而积极追求的直接故意与明知危害结果必然发生而消极地接受,以此来区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的不同。另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明知危害结果会发生对这一结果所持心理态度就不可能是消极地放任其发生,只能是积极追求的心态,因此必然故意实则就是直接故意。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内地的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理论下,必然故意无法被涵盖在现有的两种故意类型中,因此必然故意实际上是第三种故意形态。本文通过厘清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中犯罪故意的异同,讨论必然故意究竟是属于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的一种类型,还是属于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中的第三种故意形态。
关键词:直接故意;间接故意;必然故意;放任
比较内地与澳门的刑法条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两地皆承认明知行为必然或可能会造成危害结果,积极追求结果发生的是直接故意;对于行为人明知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对这一结果的发生持消极放任的心理态度在内地被划分为间接故意,在澳门的规定中是或然故意;对于明知行为必然会造成危害结果,且放任结果发生的这一心理态度在澳门是必然故意,而在内地刑法中并没有明确划分,学界仍然有不同的声音。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刑法学界对于“明知必然发生而放任”这一故意的不同观点进行梳理和总结。
一、不同学说之比较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刑法学界一致认为“明知必然发生而放任”是一种故意而不可能是过失,因为过失犯罪要求行为人对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发生是排斥的,是违背了行为人的意志的。而“放任”的心态即意味着行为人对结果持的是一种可发生可不发生的心理,结果发生了并不违背行为人的意志,这里与过失有明确的不同。因此内地刑法学界对于“明知必然而放任”主要的讨论是这一心理态度究竟是属于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还是一种介于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中的第三种故意形态。
(一)直接故意
内地主流学说认为必然故意也就是直接故意,在这其中不同的刑法学者因为解释的理由不同又可以分为两种学派。
1、认识和意志相互影响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不存在“明知必然且放任”的心理态度。因为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意志因素以认识因素为前提,反过来,意志因素的内容又限制认识因素的内容。这就意味着持“放任”意志的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仅仅只会认识到其可能性而不可能认识到必然性。因此这类学者认为在“明知必然”时,不可能存在“放任”的心理状态。
2、不影响结果发生
另外一类学者认为必然故意持有的是放任的心理状态,但这种放任并不会对危害结果的发生造成什么影响。因为结果必然会发生,所以行为人主观上是“放任”还是“希望”并没有什么差别,都属于直接故意的范畴。我们可以从中推断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是行为人认识到结果必然发生即是直接故意,也就是说,这类学者认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区别在于认识因素,而意志因素方面是积极地追求还是消极地放任对故意的分类并无影响。
(二)间接故意
支持必然故意可以归类为间接故意的学者们认为区分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的标准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所持心态是积极希望还是消极放任。这类学者指出中国内地刑法条文中 “希望”和“放任”才是区别两种犯罪故意的标准。而在认识因素层面,对于行为人只需要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即可,无论这种结果的发生是可能的还是必然的都不会影响行为人是故意的认定。
(三)第三种故意
还有一些学者另辟蹊径,他们认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区分是由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双重标准共同决定,将“明知必然且放任”的心理状态归入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都不能很好地进行解释,那么就开辟一种新的故意模式,将这种介于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之间的故意独立出来,即澳門刑法里的“必然故意”也有学者称为“容忍故意”或“准直接故意”。这类学者认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之间应当有第三种形态的故意,这种故意的主观恶性大于间接故意但小于直接故意,如此区分有利于法官在实践中更加准确地量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二、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之独立性
前文提到一部分将必然故意归类为直接故意的学者认为故意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直接会相互影响,联系紧密。在这一部分,笔者将分别讨论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独立性,对这类学者的观点进行反驳。
(一)认识因素
必然故意的认识因素的具体内容是“明知必然会发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必然”是指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的一种客观规律,而刑法犯罪故意中的“必然”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指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的概率为百分之百,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的相同点是二者都是客观事实。“明知必然”是一种心理状态,就是指行为人认识到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的概率为百分之百这一客观事实的心理状态。很显然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发生概率的认识只与行为人的行为和危害结果本身有关。认为意志制约认识的学者忽视了认识因素的独立性,将“放任”推定为明知危害结果可能发生并不符合逻辑。
(二)意志因素
必然故意的意志因素是“放任”,澳门刑法中的用词是“接受”。无论是“放任”、“接受”、还是有些学者说的“容许”,都是指行为人对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发生不排斥也不追求,的一种心理态度。意志是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之所以会被刑法评价为罪过,受到刑法责难的主要因素。 “放任”虽然没有积极破坏法律,但也表现了行为人对法律秩序的冷漠。那么违反法律的事实一旦发生,行为人这种对法律秩序的冷漠也需要被刑法谴责。
(三)独立性
笔者并不否认甚至十分赞成如张明楷教授所说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也必须承认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有其独立性,而不是时时刻刻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张三与李四有仇,看到李四在独木桥上,便想要砍断独木桥,此时桥上还有无辜的王五。明知砍断独木桥必然会导致王五和李四死亡的结果,但张三出于仇恨,不顾王五的死活,砍断了独木桥,导致王五和李四的死亡结果。若我们只看到了认识与意志具有关联性,那么此时张三明知王五会死,对王五所持心理态度就不会是“放任”,而是“希望”,张三对于王五的死亡结果的主观恶性和对李四的死亡结果的主观恶性一样大。作为社会一般人角度来看,也会觉得这并不合理。这恰恰说明了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之间有一定的独立性,“明知必然”和“放任”这两种心理事实可以同时存在,那么“明知必然而放任”这一心理到底该如何评价呢?。
三、必然故意与直接故意、间接故意之关系
要评价必然故意首先必须明确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区分标准。目前学界主要的讨论是“意志说”与“双重标准说”。
(一)意志说
支持“意志说”的学者认为意志是决定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之间主观恶性不同的关键。因此这类学者将“明知必然而放任”归类到间接故意范畴下的一种类型,他们认为澳门刑法中将间接故意细分为了必然故意和或然故意。但目前理论界的通说认为间接故意必须发生了一定的后果才能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否则就不能对行为人进行定罪。因为在间接故意的情形下结果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如果行为人中途停止行为,危害结果没有发生,那么处罚这种行为就没有可操作性。对于前文中张三杀死李四与王五的案子,如果张三出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停止了犯罪行为,他对于李四的直接故意还需要处罚未遂,而他对于王五的行为是不是就无法定罪了呢?笔者认为张三对于王五的生命法益也造成了直接危险,因此不能按照间接故意理论认为其对王五不构成犯罪。
(二)双重标准说
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简单地以“认识因素”或“意志因素”之一为标准划分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都是不全面的,他们认为两种故意的区分是由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共同决定。这也是目前犯罪故意的分类标准的主流理论。此时的直接故意在认识因素上应当认识到危害社会的结果有发生的可能性或必然性,在意志因素上是积极希望结果发生。间接故意在认识因素上仅仅认识到了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意志因素是放任结果发生。笔者支持双重标准说。那么根据这种分类标准,无论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都无法囊括“明知必然而放任”的故意类型,因此必然故意就成为了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中间形态。
四、犯罪故意之再思考
前面我们讨论了必然故意无法被囊括在目前中国内地对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划分理论中,讨论了澳门刑法典中区分三种故意的历史原因和立法原因,那么是否意味着我国也可以引进第三种故意的理论?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澳门刑法典虽然规定了必然故意的内容,但经过笔者搜索澳门刑法的判决中并未发现直接明确地评价为必然故意的案例,往往以“至少为必然故意”这样的形式不与直接故意进行区分,或者是在法官断定行为人认识到犯罪结果“极有可能”发生时也认定为是或然故意。可以看出实践中必然故意的可操作空间较小,引入必然故意这个概念的意义不大。其次,实际上不同的故意之间虽有区别,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换言之,应当注重不同故意类型之间的统一性,只要认定了行为人有犯罪故意,并且区分过失,就能对行为人准确定罪,而对他主观上有无认识到结果发生的必然性,有无“放任”或“希望”这可以由法官在量刑中酌定,无需将这种司法事实判断置换成立法推定。最后,相较于引入一个作用不大的法律概念,刑法作为调整公民行为的、涉及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权益的社会规范,保持其相对稳定性有更重要的意义。
既然我国内地的法律没有必要引入一个新的犯罪故意的模式,那么该如何解决某些案件中存在“明知必然而放任”的情况呢?首先,立法上不需要单独规定必然故意的内容,但理论上我们仍然可以对故意理论进行讨论研究,丰富犯罪故意的内涵。在理论上可以扩大直接故意的范畴,将“明知必然而放任”纳入直接故意的内涵之中,并参照德国刑法典,将“明知且希望”作为一级直接故意,将“明知必然而放任”作为主观恶性低于“明知且希望”的二级故意。同时,实践中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必须明确还有一种主观恶性低于直接故意,而高于间接故意的第三种故意类型。在司法实践中考察犯罪人主观方面的时候,法官需要更细致地进行定罪量刑,对持不同故意程度的犯罪人“区别对待”,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
五、总结
笔者认为对于我国内地刑法来说,引入一个新的故意模式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刑法犯罪故意理论的逐步丰富与发展。因此笔者的观点是:因为“明知必然而放任”这一故意心态对于法益有了直接的危险性,在内容上更贴近直接故意,因此可以将其解释为直接故意的一种特殊类型,纳入目前内地犯罪故意理论中直接故意的范畴,但必须注意与直接故意中的“明知且希望”这一故意类型相区分。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贾 宇:《罪与刑的思辨》,法律出版社。
3.赵国强:《澳门刑法概说(犯罪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5.姜 伟:《论间接故意》,《烟台大学学报》,1995年第8期。
6.杨 波、王元建:《准直接故意的生命空间——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中间形态》,《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7.张 彦:《对“明知必然发生而放任”的思考》,《经济视角》,2011年第1 期。
8.李晓兰:《简述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中间形态》,《法制与经济》,2012年第3期。
9.杨 紅:《对直接故意特殊形态的探究》,《东方论坛》,2003年第5期。
10.周一心:《对必然性间接故意之否定》,《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11.林亚刚:《对“明知必然发生而放任发生”的再认识》,《法学评论(双月刊)》,1995年第2期。
12.王雨田:《明知必然发生能否放任?》,《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4期。
13.赵秉志:《论澳门刑法典中犯罪构成规范的完善》,《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9期。
14.赵国强:《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故意犯罪阶段形态之比较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2期
15.冯 涛:《犯罪故意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6.朱志闯:《犯罪故意意志因素比较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