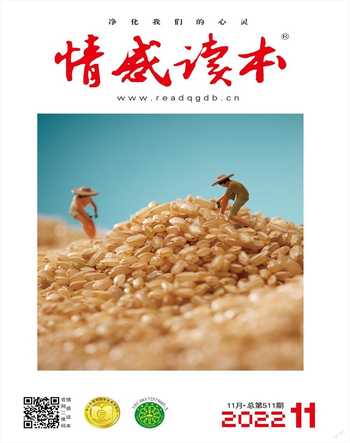“老兵”和军马
梁晓声
更确切地说,是那马首先发现了他。也许它并没能立刻认出他,而仅仅是因为他的一身绿军装,唤起了那军马求救的本能。
老兵其实并不老,才二十六岁。
八年前,老兵自然是新入伍的小兵,被分到了东北大地上的一处军马场。那军马场位于黑龙江与内蒙古的交界之域,广袤而苍凉。
军马场的兵也是兵。军训是照例的军营生活的内容。而驯养军马意味着“专业”。好比炮兵和坦克兵,对炮和坦克的性能必须了如指掌一样。多亏他在家里养过马,了解马,爱马,所以很快就成了“专业”最出色的新兵。他知道驯养军马仅凭自己养过一匹马那点儿粗浅的经验是不行的,便四处托人买来了有关的书籍,并且天天坚持记录驯养心得。他的军训成绩也很优秀。倘爆发了战争,他随便跨上任何一匹军马,都可以立刻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骑兵。入伍第二年他在新兵中第一个当上了副班长,第三年入了党,第四年当上了班长。他爱军马,更爱他那一班天天为军马的健壮早起晚睡的战士。第五年他被所在部队授予“模范班长”的称号。
他那一班战士中曾有人说:“班长爱咱们像一位母亲爱儿子!”
却立即有人反对:“他爱军马才爱到那样!对咱们的感情呀,比对军马差一大截哪!哎,你自己承认不,班长?”
正在替战士补鞋的他,笑了笑,没吱声儿。
众战士逼他作出回答。
无奈之下,他真挚地说:“其实呢,我是这么想的,我们为谁驯养军马?为骑兵部队嘛。军马是骑兵不会说话的战友。我们今天多爱军马一分,军马明天就会以忠诚多回报我们的骑兵兄弟一分。爱马也等于爱人啊!……”
于是战士们都肃然了。
有一天,他一个人躲在一处僻静的地方大哭了一场——家信中说,他家那匹马病死了。那匹马是他用在城里打工的钱买的,买时才是个小马驹子。他想,如果自己没参军,那匹马是不会病死的……
从此以后,他更爱一匹枣红军马了。它端秀的额头上,有像扑克牌中的方块似的一处白毛。他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白头心儿”。他家那匹马的额头正中也有“白头心儿”,只不过不是枣红色,而是菊花青色的……
那时他就已经开始被视为“老兵”,尊称为“老班长”了。尽管才二十三岁多点儿。已经欢送过一批战友退伍了,可不是老兵怎么的呢!当年那一批兵中,只留下了他一个,对于后来的一批新兵而言,可不是“老班长”嘛!
“白头心儿”救了他一命。那一次军马受惊“炸群”他从另一匹马的背上一头掼了下去。恰巧“白头心儿”随着受惊的马群冲过来,它一口将他叼起。否则,他将毙命于万蹄之下无疑。当马群安静下来,他搂着“白头心儿”的脖子,感激地涌出了热泪。由于在奔驰中还紧紧叼住他不放,“白头心儿”的嘴唇被撕豁了……
他入伍的第八年,裁军,军马场接到了解散的命令。骑兵这一兵种,因军事装备的越来越现代化,逐渐被认识到,已经不太可能发挥其在以往战争中的迅猛威慑力了。大部分军马卖给了“外蒙”。一小部分优秀的选送给各边防部队了。剩下几十匹略有残疾的,被处理给形形色色的人们了。有的从此做了普普通通的劳役马;有的做了什么风景区的观娱马,供游人骑着逛景致,照相;有的被什么特技马术队买走了,“白头心儿”便在其中。
“白头心儿”被买走时他在场。那马眼望着他,四蹄后撑,任买主鞭打叱喝,岿然不动。他不忍眼见它受虐,轻轻拍着它脖子,对它耳语般地说:“‘白头心儿啊,何苦的呢?乖乖跟人家走吧,啊?我不会忘了你的,有一天我会把你买回来,使你成为我的马的!”——分明,马听懂了他的话,马头在他肩上磨蹭了几番,生了根似的马蹄才终于迈动起来……
望着“白头心儿”被拽走,不知不觉的,泪水已淌在二十六岁的“老兵”的脸颊上。
军马场虽然解散了,但仍有诸多的后事需人料理。二十六岁的“老兵”,怀揣着一份退伍通知书,滞留了两个月。他又获得了部队授予的“模范班长”的荣誉。那是对他八年服役的最后的嘉奖。
他是最后离开军马场的官兵中的一个。那是一个冬日里的黄昏,他们列队肃立在已然空蕩无物的营房前,而营房后不远处,是一排排寂静的马厩。仰望着在风中飘荡的军旗徐徐而降,他仿佛听到营房中传出了笑声和歌声,仿佛闻到从马厩发出的草料混杂着马粪那种带着一股温热似的芳香。是的,对于他这名军马场的“老兵”来说,那种特殊的气味儿的确是芳香的……
上级批准他们可以鸣枪告别军马场。
连长允许他们每人鸣枪的次数可以和自己入伍的年限一样。除了连长和指导员,再就是他入伍的年限长了。
但他只鸣放了七枪。
指导员说:“老兵,我替你数着呢,你还差一枪。”
他双眼噙泪回答:“指导员,我不满八年军龄,差四个月……”
他话音未落,有人哭了。
如血的夕阳沉到地平线以下了,当广袤而苍凉的大草原夜幕降临时分,他们乘军车离开了军马场。回望着在视野中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的营房和马厩,他想——它们也将成为这大草原上光荣与梦想的遗址了。他想——他保存他“模范班长”的证书,一定要比大草原保存那遗迹更长久,更长久……
他突然拍着军车驾驶室的棚盖大喊:“停车!”
车停下了。
他喃喃地说:“我……我好像听到了‘白头心儿的嘶叫……”
然而其实只有风声……
这提前四个月退役的“老兵”,在归乡的途中,在一个地界毗连大草原的小县城里,竟然发现了“白头心儿”。更确切地说,是那马首先发现了他。也许它并没能立刻认出他,而仅仅是因为他的一身绿军装,唤起了那军马求救的本能。他循着马嘶声望去,见“白头心儿”也正望着他,卧在一幢砖房前。马旁,一根高木杆上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四个醒目的大字是——“吕记马肉”。“白头心儿”就拴在那木桩上。他走近它,见它那晶亮的大眼睛里分明的汪着泪。那军马以一种类人的哀怨忧伤的目光瞪视着他。
马肉店的老板告诉他,那军马在为某电影摄制组效劳过程中弄断了一条腿,看来废了,只有杀死卖肉了。
他蹲下查看了一番马腿,请求老板将“白头心儿”转卖给他。
老板出了一个数。那笔钱超过他的复员费,而老板却不肯让价。
“我白替你打工行不行?”
“多久?”
“直到这匹马能站起来了为止。”
老板认为他傻,认为那马永远也站不起来了,便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他从此一边打工,一边精心照料“白头心儿”。
一个月后,“白头心儿”奇迹般地站起来了。
老板被他感动了,没再收他一分钱,允许他将“白头心儿”牵走,并且,还白赠了他一副马鞍。
由于“白头心儿”,他自然没法乘火车。于是这“老兵”和曾救过他命的那一匹军马,朝行暮宿,向着他的家乡,开始了他们的“长征”……
途中,他度过了二十六岁生日。
两个月后,他老母亲看见一个胡子拉碴的,风尘仆仆的,穿一身军装的男人,牵着一匹瘦骨嶙峋的有“白头心儿”的长鬃枣红马蹒跚地来到家门前。
他激动地叫了一声:“妈!”
老母亲惊喜地认出他是她那参军八年一次也没探过家的儿子!
不是老母亲将儿子搂抱在怀里,而是儿子将瘦小的老母亲搂抱在怀里……
他惭愧地说:“妈,我的复员费几乎都花光在路上了……”
他又说:“妈,你看,咱们又有一匹‘白头心儿了!”
第二天清晨,他牵着“白头心儿”登上了家乡的山头,俯瞰着几处穷困得近乎败落的村子,他对“白头心儿”发誓般地说:“‘白头心儿,帮我把咱们的家乡彻底变个样儿吧!”
那一时刻,二十六岁的“老兵”似乎顿悟——军队给予他的,还有比“模范班长”之荣誉重要得多的东西……
马儿安闲地吃着青草……
陈吉清摘自《家载一生》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