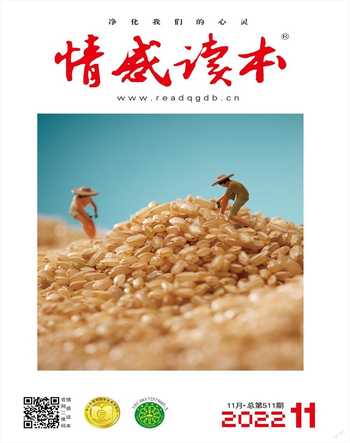父亲的唢呐
刘婷
父亲真的老了,腰不直了,背不挺了,早已没有年轻时的风采,甚至连气息都不稳了,我看着父亲憋红的脸,往事一幕幕在脑中回放,眼泪早已模糊了双眼。
一
我的父亲是吹唢呐的,说得好听点是“民间艺人”,说不好听点就是一个“吹响器的”。乡下的红白喜事,离不開唢呐,特别是那首《百鸟朝凤》,能让人听得心潮澎湃、神清气爽。
小时候,我对父亲非常崇拜,听着那些铿锵有力的唢呐声,觉得父亲是最厉害的人。
我渐渐长大,学费和家里的开销日渐增多,父亲只能接越来越多的“演出”,这些演出大部分都是办丧事的,往往凌晨就要出门,到半夜还回不了家。冬天的夜,特别冷,父亲蹬着自行车在寒风中奔走,要是碰上雨雪天气,回家的路就更艰难。
父亲从没觉得苦,他用演出赚的钱给我买烧饼,买玩具,看着我笑,他就一脸满足。
有一次,我半夜起来去厕所,发现母亲在厨房做饭,我很奇怪,大半夜的怎么还做饭啊。我跑过去看,母亲说父亲一有时间就去吹唢呐了,地里的农活都顾不上,这不,半夜去浇地了。
那时是初春,夜里还是很冷的,我听了一阵心酸,要去地里帮忙。我裹上军大衣拿着手电筒,去地里寻父亲。远远地看见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弯腰整理水管,一双大脚泡在冰冷的泥水里。“爸,我来帮你。”
“你咋来了,赶紧回家睡觉去,明天还要上学呢。”
“没事,爸,我都10岁了,都长成男子汉了,我来帮你。”父亲拗不过我,让我留下,却不让我踏进泥水里,说小孩子皮肤嫩,冻伤了腿可就坏了,只让我看着水井边的阀门。
茫茫的夜色中,父亲拖着水管在田地间不停奔走,他时不时地跑到我身边,问我冷不冷,可我却看到了父亲额头冒出的汗珠,寒冷夜里的汗珠。
天快亮的时候,父亲拉着我回家,他在床上眯了一会儿,就骑上自行车,背着唢呐,去赶演出。吹唢呐很费力气的,父亲吹一天,也就挣10元钱,可他从不觉得辛苦,还总自豪地说自己是“艺术家”。
暑假寒假的时候,父亲就带上我,响器班的菜是最丰盛的,吃饭的时候父亲恨不得把好吃的都夹到我碗里,生怕我吃不饱。
经常跟着父亲去响器班,我学会了敲梆子,缺人的时候,我就帮忙,虽然人小,但也像模像样的,我乐在其中,很是自豪。
二
转眼,我读初中了,要住校,学费也多了起来,重担都压在了父亲身上,于是,他越来越忙,有时候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演出,我见他一面非常不易。
一次课间,我站在走廊里,看见父亲站在教学楼前向我招手,我开心极了,飞快地跑过去,父亲问了我的功课,又从包里拿出我爱吃的烧饼夹牛肉,临走时,还塞给我10元钱。
可等我回到教室,几个同学就叽叽喳喳地围着我。“他是你爸啊,我好像在哪见过,啊,就是那个办丧事吹大笛的吧。”
“就是就是,原来你家是赚死人钱的,真晦气。”
“这在以前,可是下九流的生计啊。”
……
我听得面红耳赤,拍着桌子狠狠瞪着他们,他们才消停了。那节课,我根本没有听进去,满脑子都在想父亲的事,我引以为豪的父亲,在别人眼中,原来如此受歧视。
此后我在班级里,总能听到别人背着我窃窃私语的,长此以往,我变得沉闷消极,放假的时候,也不愿跟着父亲去演出了。
初三上学期,我的成绩开始下滑,班主任还特意把父亲喊来。从办公室出来,父亲的脸色很难看,一路上都没有和我说一句话,我知道,这次他肯定失望了。
回到家,父亲把我喊进屋,问我怎么回事,为什么好好的成绩会下滑。
我支支吾吾地没法说,最后下了决心:“爸,要不我不读书了,跟着你吹唢呐,也挺好的。”
父亲掐灭了手里的烟,看着我:“娃啊,从你出生,我就发过誓,一定不让你跟着我学这些,你想一辈子呆在农村?想面朝黄土背朝天?想在别人丧事上吹吹打打地挣点饭钱?”
“读书,才是你的正事,是我们的希望。”父亲说完,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从未见父亲如此严厉,看来他是真的生气了。那天下午,我就返回学校,抛开一切杂念,补习功课,因为我不想再让父亲失望。
三
中考的时候,我发挥失常,离重点高中分数线差了10分,父亲多方打听,最后得知需要拿3000元钱的择校费,才能入学。
我知道后说不去了,读普通高中也一样,父亲却坚持让我去读重点中学,邻居们都劝他说3000元钱能买一辆拖拉机了,可父亲不为所动,说拖拉机可以再买,读书可不能重新来过。
我不知道父亲跑了多少家亲戚,才借够这么多钱。只记得那个暑假,我跟着父亲一起去演出,不再惧怕别人的目光,父亲的唢呐声围绕在我身边,哪怕我听了千万遍,依然觉得美妙动听,悠扬深远。
暑假过完,父亲突然说要去海南打工,说他一个朋友在工地干活,赚钱很多。父亲的鬓角已有了白发,身材也不如以前挺拔,可还要为了供我读书,外出奔波。
临行前,父亲站在院内吹了一首《百鸟朝凤》,熟悉的旋律弥漫在院子里,我听出了父亲的恋恋不舍。末了,父亲把唢呐重重地交到我的手上:“你可看好了我的宝贝,周末回家记得擦擦尘土,要好好学习。”
父亲就此踏上了南下的道路,没有唢呐的陪伴,不知父亲是否孤单。他这一走就是一年,中间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看看,他总说车票贵,到春节了再回来。
放假的时候,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父亲的唢呐,擦去上面的灰尘,擦得铮亮。拿着它,总能想起父亲吹唢呐时候的神情,那种自信,那种悠然。可如今,为了养家,那双手搬起了砖,扛起了沙,早已磨了厚厚的一层茧子。
高中三年,父亲回家的次数很少,我看着他一次比一次憔悴,一次比一次苍老,而我,除了发奋读书,别无他法。
高考结束,我成功考上了省里的一所重点大学。父亲得知后,特地从外地回来,喜悦之情难以掩饰,席间,他喝了不少酒,眉飛色舞地拿起唢呐要给我吹一曲,几年不吹奏,父亲明显生疏了,可我们一家人都沉浸在这快乐的乐曲里。末了,我看见父亲悄悄地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那一定是开心的泪水。
四
大学四年,我一直勤工俭学,想给父亲减少负担,父亲得知后很是生气,责怪我不把心思用在学业上,赚钱的事不让我管。
常年在工地做劳力,父亲的身体状态日渐下滑,我大四那年,他在工地扛瓷砖时不小心扭到了腰,在医院住了好长时间才能下床,医生叮嘱他不要再去干重活了,可他还是偷偷跑到附近的小工地打工,母亲和我怎么劝都没用。
大学毕业后,我顺利地进了省里的建筑设计院工作,成了一名工程师。我深知父亲的不易,所以在工作上很努力,希望自己能早日站稳脚步,替父亲扛起家里的大梁。两年后,我认识了小菲,她是一个善良温柔的女孩子,我们恋爱了,我想给她一个家,可我也知道,小菲心里总期待能在城里买套房子。
我工作时间短,手里哪会有那么多钱,只能委婉地告诉父亲。谁知父亲第二天就坐车来到省城,从背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郑重地交给我,说里面存了20万元,都是这些年在工地攒下的,让我去付首付。
这张卡很轻很轻,但我觉得重若千斤,这里面每一分钱都是父亲的血汗钱。
我和小菲特意回到老家办婚礼,那天,父亲穿上了一套崭新的中山装,特意染了头发,看着特别精神。待到拜过天地,父亲从正堂拿出了那支唢呐,告诉乡亲们,他今天要吹一曲,庆贺自己的儿子新婚大喜。
院子里熙熙攘攘的都是人,父亲鼓起腮帮,手指灵活地弹奏,熟悉的旋律就又在院子里蔓延。父亲真的老了,腰不直了,背不挺了,早已没有年轻时的风采,甚至连气息都不稳了,我看着父亲憋红的脸,往事一幕幕在脑中回放,眼泪早已模糊了双眼。
婚礼过后,我接父母来到城里生活,起初父亲不同意,但拗不过我。小区附近有个中心花园,有一些退休老人,常常在花园里吹拉弹唱,我鼓励父亲也去亮亮手艺,果然,父亲一首唢呐曲,很快征服了很多听众。
现在,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公园度过,和一群文艺爱好者说说笑笑,或者合奏曲子,每天都很开心。父亲终于可以卸下重担,轻轻松松地吹着唢呐,那是我听过的最悦耳的曲调。
丁亮摘自《分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