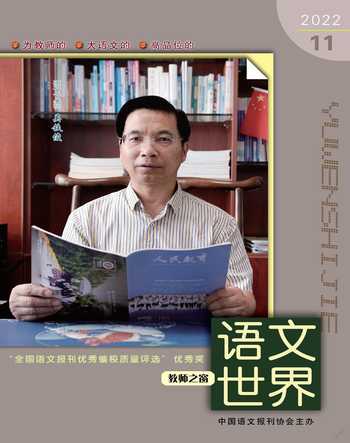孔子的“诗教”
叶水涛
孔子很有美学素养,也非常重视审美教育。孔子的美学情怀与审美追求是与他的政治理想连在一起的。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周代,其实是上古时代的社会。上古时代的社会是充满原始色彩的,人们对外在世界充满着好奇,对大自然既感到神秘又怀着深深的恐惧,有限的认知能力常常需要借助想象的帮助。于是,他们所看到的世界是未分化的世界,主观和客观的分界不那么清晰,万事万物都被视作是有生命的,是能对话和共同生活的。因而他们的想象非常的大胆、新奇和丰富,具有泛审美化和泛艺术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孔子时代尚未完全消失。孔子则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是特别具有艺术与审美气质的人。
梁漱溟先生说,中华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他举例说,同样面对屋子漏雨,西方人的直接反应是,哪儿漏了,为什么漏的,怎样让它不漏;中国人则是另一种反应,屋子漏了一时不能修复,那就承认这个现实,“留得枯荷听雨声”,从滴滴答答的漏雨声中,获得一种审美的惬意;印度人有一种虚无化的“空”,无所谓漏雨或不漏雨,可以選择无视它。这种文化视角的分类,到底有多少科学和严谨性姑且不论,但中华文化有其早熟的一面,主要是诗性的早熟,而非全面的成熟,或许是合于历史事实的。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在今天看来有点奇怪。“不学诗”怎么就不能讲话,或不会讲话呢?但在那时,“诗”是一种“普通话”,在政事和外交中广泛应用,所以,不学习诗歌就难以用语言交际。诗歌语言可以唤起别人更多的想象,作为外交辞令也就具有它的丰富性,让对方思而得之,心领神会。诗歌语言是艺术化的语言,具有审美的感情色彩,在外交场合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是最恰当的表述,也是富有解释张力的表述。明乎此,就能理解为什么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意味着不会搞政治,不适宜搞外交。孔子非常深邃地看到,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诗歌作为一种艺术语言,它审美化的表达方式蕴含着巨大的认识沟通的意义。
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对于非音乐的耳朵,再美妙的音乐也不成其为音乐。对诗歌艺术、对艺术审美,孔子之所以推崇备至,是因为孔子首先是一位有精湛造诣的艺术家,是艺术审美的行家。孔子在齐国听《韶》乐,竟然达到“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感慨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他平时经常操琴鼓瑟,击磬歌诗——“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甚至周游列国处于危急之境仍“弦歌不衰”。
孔子在教学中经常谈论艺术,让学生学诗习乐,他将“诗教”和“乐教”作为教导学生的重要课程。“吾与点也”,孔子的这一感慨之词,处于《论语》中最长的一段记述中,也是描写最为细致与具体的一段,其中心在对诗意人生的向往,对艺术审美境界的赞叹。
在孔子看来,美育就是一种情感教育 。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孔子看来,“诗教”有伦理道德教化与认识的功能,但首先是一种情感教育。“兴”,孔安国注为“引譬连类”,朱熹注为“感发志意”;“观”,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群”,孔安国注为“群居相切磋”,朱熹注为“和而不流”;“怨”,孔安国注为“怨刺上政”,朱熹注为“怨而不怒”。
在“兴、观、群、怨”中,“兴”是艺术的审美本质,意指在联想和想象中表现情感,这就规定了孔子的“诗教”是一种情感教育。“观”,指诗的认识功能;“群”,指诗的伦理凝聚力;“怨”,指诗的悲剧精神。因此,孔子的“诗教”在情感教育的旗帜下,强调了美育对于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尤其是人们伦理道德自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