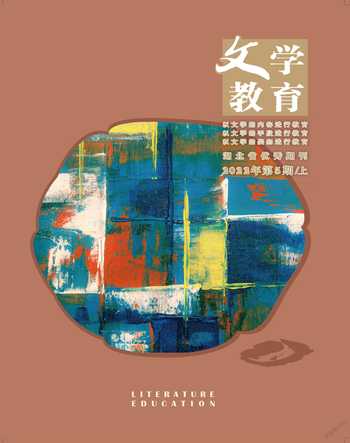陆游蜀中诗歌自我形象的仕隐矛盾
贾洪展
内容摘要:仕隐矛盾贯穿于陆游蜀中时期诗歌的始末,具体表现为“官吏”与“隐士”两种形象的冲突。首先,出于对抗金理想与个人前途的考虑,陆游具有强烈的为政诉求,并因此不满于边地的微职。但在理想受挫之余,陆游却转向了田园、佛道,以隐士的身姿追求内心的宁静。政敌诬蔑下的罢官更促使诗人自号“放翁”苦求自适,但这本质上是对现实痛苦的反抗,带有极强的伪装性。
关键词:陆游 蜀中诗歌 自我形象 仕隐矛盾
对于陆游来说,无论是抗金的远大理想,还是仕途的个人追求,都需要通过投身官场才能实现。然而南宋偏安一隅的处境、主和派把持朝政的局面,以及耿直的性格,却又决定了诗人注定对当时的政治生态存在抵触的情绪。具体到蜀中时期来看,这种仕与隐的纠结其实早在陆游离乡前的《将赴官夔府书怀》一诗中就已有所体现。诗人先是言说自身“病夫喜山泽”的现状,同时却又强调“抗志自年少”的追求;因为“有时缘龟饥”的困境,所以难免作出“妄出丐鹤料”的选择;对于这种无奈之举诗人自己也是“退懦每自笑”,正如一个自知酒量太浅的饮者“虽爱不敢釂”,对“厕朝绅”[1]99的行为整体保持着一种模糊的态度。这首诗是陆游在赴蜀之前对自己过往官场经历的总结与反思,我们可以将之作为蜀中时期陆诗创作的背景加以理解,这种仕与隐的矛盾也确实延续到了诗人八年间的作品中,并集中表现为“官吏”与“隐士”两种自我形象的冲突。这两种形象之间的反差已相当悬殊,而从内部来看,陆游作为“官吏”时在现实困境与内心追求的落差,以及作为“隐士”时在宁静闲适与苦求自适之间的摇摆,又都使诗人仕隐思想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
一.为官后方:边地困境与仕途追求
在应诏赴任夔州通判之前,陆游其实已经在山阴闲居了五年,但被重新启用的诗人却有所顾虑,不但在启程前心存“民风杂莫徭,封域近无诏”[1]99的偏见,在途中仍有“蛮俗杀人供鬼祭”[1]128的担忧。然而事实证明,这些顾虑都是诗人的刻板印象,后来也并未出现在创作于蜀地的陆诗中。刚刚抵达夔州时,陆游还抱有投身战场的幻想,甚至由此产生了对现实官场生活的排斥,在诗中不但对公务的琐碎颇有微词,还不甘向微职薄禄折腰。虽然偶尔会发出“责轻仍饱食,三叹愧无功”[1]144的感慨,但“沉迷簿领吟哦少,淹泊蛮荒感慨多”[1]145的不忿却更为常见。而将这种个人的境遇放到当时的整个官场加以观照,陆游“官吏”的身份则有了更多的悲剧意味。在主和派把持朝政的大环境下,陆游的政治主张本就是逆势而行,而诗人孤直耿介的性格则更不能为政敌所容忍。顶着“通判”的官名,陆游却处于“赖无权入手,软弱实如泥”[1]158的境地,并无多少实权。在去往南郑前线途中所作的《畏虎》中,诗人也吐露过对“彼谗实有心,平地生沟谿”[1]164的风险的忧惧。而之后以南郑幕府解散和被诬罢官两个事件为分界点,陆游又经历了两次重大转折,诗歌风格变得越发消沉。
在南郑前线时期,虽然官吏的身份已经被“战士”的形象所冲淡,但在诗中谈到官场现状时,陆游依旧怀着较为负面的情绪,“下愚不可迁,大惑终身迷”[1]190,深感无法融入当时的政治环境。而在王炎幕府被迫解散后,诗人被调往成都,“冬冬漏鼓催窗色,急急文书动驿尘”[1]396,从此开始了自己在西南后方辗转无定的仕宦生涯。在报国机遇得而复失的打击下,此时的诗人不再以对军旅生活的幻想作为衡量现實处境的标准,而是转向了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失望与忧思当中,“寂寞嘉州迎诏处,忽闻鼓吹却凄然”[1]252。同时,对自我的劝慰也开始出现在陆诗中,“一丘一壑吾所许,不须更慕明堂材”[1]269,这种安于后方微职的心态一直持续到淳熙二年。在任职蜀州参议时,陆游因政敌的攻击而遭免职,随后其对待官场的态度也从浑浑噩噩转向了激愤难抒。在被解职之初,陆游还在诗中故作疏懒以掩饰内心的痛苦,“老子从来薄宦情,不辞落魄锦官城”[2]138;然而随之而来的现实却更让诗人体会到了官场的残酷,“薄宦傥来难倚仗,旧交渐少每酸辛”[2]143,该时期陆诗所塑造的“官吏”形象也开始在“功业悠悠定已疏”[2]207与“大隐悠悠未弃官”[2]166这两种状态之间摇摆不定。
但身处对士大夫极为尊重的宋代,陆游其实还是期望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在实际的政绩方面,蜀中时期的陆游称得上是恪尽职守、勤政爱民,任职嘉州时在“只今憔悴客边城”的窘境中依旧能赢得“惟把丰年赠汉嘉”[1]249的美名。除此之外,诗人还针对时局积极建言献策,在担任史官的临安时期,陆游曾向宋高宗提议迁都建康以更好地谋划恢复大计,这件事直到蜀中时期也常被他提起,“梦里都忘困晚途,纵横草疏论迁都”[1]139。到了南郑前线,他又根据实地的勘察修正出了“却用关中作本根”[1]179的复国策略。除了一贯的抗金理想,这些行为也表现了陆游对重返政治中心的渴盼,说明他对仕途的追求也存在功利的一面。其实早在由临安启程赴蜀前,诗人就在向梁参政投赠的诗中直言“袖诗叩东府,再拜求望履”[1]103;对于远赴西南担任地方官一事,他表现得也有失风范,认为此举只是在“消磨梦境光阴”[1]119,与平生所志相差太远。整个蜀中时期,陆游也没有停止过追忆自己在京为官的时光,不但遥想京城的威仪,“忆瞻銮仗省门前,扇影鞭声下九天”[1]252;还留恋当初自己针砭时弊的气势,“少年论兵实狂妄,谏官劾奏当窜殛”[1]307;同时不免为奸佞当道的政局感到不安,“帝阍守虎豹,此计终悠悠”[1]222;最后反观现实,却只剩下了流落边地的无奈,“孤臣白首困西南,有志不伸空自悼”[2]39。虽然这种心态不可避免地反映着陆游对个人前途的追求,但在此之外我们也应意识到,在京为官其实也意味着更多筹划抗金事业的机会,爱国精神与个体价值在这一点上是统一的。只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我们才能真正把握陆游蜀中时期诗歌中“官吏”形象背后隐藏的内涵。
二.隐遁世外:田园佛道中的宁静
由于仕途的坎坷和政敌的排挤,陆游开始到官场之外追求闲适平和的生活,这种倾向反映在诗歌中则是一系列“隐士”形象的塑造,大致上又可细化为“从官场走向田园”、“从尘世遁入佛道”两类情况。在数量方面,对日常生活的书写本就在蜀中时期的陆诗中占据着较大的比重,在官场之外构造了诗人的另一种精神追求;而这些“隐士”形象的内在意蕴更是在这一时期帮助诗人完成了对痛苦现实的超脱,为其心态的调节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除了官场的打击这一直接诱因,陆游的固有观念以及教育背景也都影响着他对“隐士”形象的自我书写。
相比于官吏的客观身份,这种偏重于主观认知的“隐士”形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陆游排遣内心痛苦的需求。在赶往蜀地途中,诗人就曾因旅途的艰辛而产生过“历尽风波知险阻,平生错羡捕鱼郎”[1]122的逃避心理;而在现实的打击面前,陆游也时常心念归隐,“钟鼎山林俱不遂,声名官职两无多”[1]143;在不堪琐职束缚时也会偶尔放松身心,“但嫌忧畏妨人乐,不恨疏慵与世违”[1]150。相比于官场的争斗,陆游则更加乐于独处,“深居不恨无来客,时有山禽自赞名”[1]146;对乡野生活也极为推崇,“农家农家乐复乐,不比市朝争夺恶”[1]168;更是不止一次地在诗中引用张翰的典故抒发自己弃官还乡的愿望,“季子貂裘端已弊,吴中菰菜正堪烹”[1]194。在“渭水岐山不出兵”的局势下,陆游也只能更多地着墨于恬淡的日常生活,“雅闻崏下多区芋,聊试寒炉玉糁羹”[1]212;而在经历受诬罢官的极度愤懑之后,这种类型作品的数量更是陡增,“山于拄杖横时看,路到芒鞋破处休”[2]108,诗中的山野江湖成为了陆游释放负面情绪的绝佳场所。在提出“自我书写”这一概念时,福柯也有意地将“归乡”阐释为作者自我精神的回归,“你退回自己的内部,去发现——不是为了发现自己的过错和深层感受,而只是为了想起行动的规则和主要的行动律”[3]。这类“隐士”形象所代表的其实是陆游对失意现实的突破,本质上是一种主动追寻的自我慰藉。
陆诗中的“隐士”形象在遁入田园与山林之外还存在着另一重意蕴,即对佛道思想的体悟,而这可以追溯到诗人以往接受的教育中。在宋代三教合流的文化发展趋势下,陆游自小便执著于道家的“炼丹”“修仙”等观念,“然予方从事金丹,丹成,长生不死直馀事耳”[1]4,这种观念在蜀中时期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比如以领悟道法为乐的“眉间喜色谁知得,今日新添火四铢”[1]137。而佛教四海为家的修行也是为微职所牵绊的诗人极为羡慕的生活模式,“身如巢燕年年客,心羡游僧处处家”[1]141。在面对纷繁的俗务时,这些带有救赎意味的思想更是给予了诗人暂时摆脱现实痛苦的力量。身处龙洞阁的凄风苦雨,陆游运用佛家不受外物侵扰的思想加以自慰,“莫怪衰翁心胆壮,此身元是一枯株”[1]174;在经历前线梦碎后,也向成都当地的高僧寻求开解,“钵盂分我云堂饭,拄杖敲君竹院门”[1]227;在嘉州时期的沉郁心绪下,诗人更是有意识地将禅宗作为自我精神的避难所,“从今更拟著幽禅,半世伥伥真误计”[1]252。在这一点上,道家无为的观念与佛家清净的思想异曲同工,也对诗人的自我疗愈起到了类似的作用。陆游“一气推移均野马,百年蒙覆等醯鸡”[1]297的诗句,正是对老子“以万物为刍狗”思想的接受;“万钉宝带知何用,九转金丹幸有闻”[1]258,则是在世俗欲望和内在修行之间选择了后者;在被撤职后,诗人也是在“道室焚香勤守白,虚窗点易静研朱”[2]33的独处中寻求清净。这些带有宗教元素的作品都有着明显的自我对话性质,是诗人重新界定自我以消解官场挫折的尝试,陆游在这种创作目的下传达的其实是一种主观意识中的“和谐”。
三.燕饮颓放:故作疏狂的自适
在蜀中陆诗所有的“隐士”形象中,“放翁”无疑是最特殊的一类,这一自号的出现是陆游在被迫“隐居”后苦求自适的结果,因此带有很强的隐藏性和主观性。“中国的自传诗……在自我形象塑造中最有意义的并不是表现自我的与众不同,而是表现自我所经历的非同一般的人生痛苦和矛盾冲突。”[5]这种主观形象的背后集中隐藏着诗人内心的压抑,因此内在的矛盾也最为强烈。所谓的“燕饮颓放”虽然是来自政敌的毁谤,但陆游其实在诗中就已经表现出了这些容易被人用来罗织罪名的行为,具体又可分为日常生活的“燕饮”和心理状态的“颓放”。
在只身赶往南郑前线的途中,诗人就曾独酌以自遣,“糟丘未易办,小计且千石。颓然置万事,天地为幕帟”[1]164;在幕府因故解散后,陆游原本疏狂的“放”就与落寞的“颓”结合了起来,“诗酒清狂二十年,又摩病眼看西川。心如老骥常千里,身似春蚕已再眠”[1]202;在成都安抚使时期更是尽显“颓放”之姿,从报国无门的“烈士壮心虽未减,狂奴故态有谁容”[1]224,到放任自流的“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1]230,足见陆游此时内心的痛苦。赴任嘉州之后,陆游在心理上已经逐渐接受了告别前线的现实,诗风也由情难自禁的狂放转向了沉郁,“羁愁酒病两无聊”[1]234“宦情苦薄酒兴浓”[1]242。直到淳熙三年“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6],陆游在诗中写下“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2]54,这一称号终于正式确立。与之相称的是,诗人此后便开始在作品中刻意显示自身的“达观”,并在一定程度上将“燕饮颓放”这一原本的诬名化作了自我的标榜,不仅大肆豪饮,“胸次何曾横一物,尊前尚欲笑千场”[2]25,更是直言自己对仕途的轻蔑态度,“免从官乞假,且喜是闲身”[2]27。这些诗句似乎符合陆诗豪放的风格,但考虑到诗人对“官吏”形象的自我塑造,我们可以发现这其实是陆游对自我的欺骗,在显示对政敌的反抗姿态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为自己掩饰的成分。在借醉酒之机的自我披露中,我们还是能够透过刻意营造的洒脱不羁,感受到陆游对以往自我的否定:
悲歌流涕遣谁听?酒隐人间已半生。
但恨见疑非节侠,岂忘小忍就功名。
江湖舟楫行安往,燕赵风尘久未平。
饮罢别君携剑起,试横云海翦长鲸。[2]44
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樣,虽然任职边地且屡遭打压,但陆游却并没有将这些自身原因作为借口而敷衍塞责,反而恪尽职守并因此获得了嘉州人民的深切赞许。而正因在这样的政绩面前依旧逃不过奸佞的诽谤,诗人才会更加忧愤与消沉,“名姓已甘黄纸外,光阴全付绿尊中”[2]54,可见行为的疏放只是外在表现,事实与污名之间的落差,才是“放翁”与陆诗中其它自我“隐士”形象于内在的最大区别。这种独特性还表现在“饮”这一行为上,作为展现自身状态的外在工具,“酒”这一意象广泛出现在蜀中时期的陆诗中,但与日常小酌的直观记录或文人雅趣的随性营造不同,作为“放翁”的陆游在诗中多为“醉酒”的状态,而正是借助这种迷离的氛围,诗人才得以吐露出在清醒时难以表达的真实想法,也足见其内心情感的矛盾与压抑。
“官吏”与“隐士”这对形象本就是不可兼容的,因此先天带有无法调和的矛盾。在主和派把持朝政的局面下,陆游抗金报国的诉求注定无法实现,这也为诗人理想的受挫增添了无法挽回的宿命感。在爱国理想之外,陆游同时也存在着对个人仕途的追求;但残酷的官场和忧患的时局,也促使诗人主动向佛道与田园中寻求慰藉,塑造了多重“隐士”的自我形象。无端的迫害又使陆游在极度抑郁之下开始在作品中伪饰内心的真实想法,使原本客观的矛盾又横添了一份主观的纠结。陆游整个蜀中时期的自我形象以南郑和罢官为节点,呈现出愈发沉郁的变化趋势,仕隐思想的矛盾也在这一过程中被不断激化。因此越到蜀中后期,这种理想与现实、真实与伪装间的冲突就越严重,我们也只有全面审视诗人八年间的个人境遇和心态变迁,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该时期陆诗的自我形象在“仕”与“隐”之间的复杂状况。
参考文献
[1]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第一册[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
[2]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第二册[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
[3]米歇尔·福柯.著,汪民安.编.自我技术:福柯文选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80.
[4]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第九册[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180.
[5]谢思炜.杜诗的自我审视与表现[J].文学遗产2001(3):40-48+142-143.
[6]脱脱.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2058.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