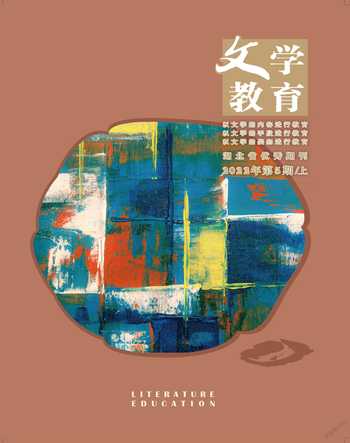郭沫若民国历史剧中反面角色写作成因
王明娟 王学振
内容摘要:郭沫若民国时期历史剧中塑造了秦始皇、赵高、魏安釐王、郑袖、侠累、车力特穆尔、宋玉、王聚昌、郑詹尹、张仪、侯嬴等众多反面角色,分别指向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汪伪政权和大量汉奸,其中融注了郭沫若的中西文化积淀和爱国情感。通过塑造反面角色的舞台形象并刻画其血腥的反动行为,郭沫若从逆向的角度揭示出社会变革和战争动乱的年代中反面角色所代表的反动势力对中华传统文化中英雄崇拜情結的依赖和痴迷,另外也透过反派人物及其行为的猖狂和残暴侧映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奴性思想对全民族抗战的负面影响和阻碍,同时反面角色的创作也是郭沫若与敌对势力斗争的产物,反映了他个人的文化反侵略思想。
关键词:郭沫若 历史剧 反面角色 写作成因
郭沫若在民国时期的六部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屈原》《高渐离》《孔雀胆》《虎符》《南冠草》中塑造了众多反面角色,剧作分别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变革和抗日战争为时代背景,代表人物有秦始皇、赵高、魏安釐王、郑袖、侠累、车力特穆尔、宋玉、王聚昌、郑詹尹、张仪、侯嬴等,分别指向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汪伪政权和大量汉奸,这些舞台形象是郭沫若中西学养和爱国思想的结晶,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国人的心理和精神。《战争心理学》中指出:人在战争中有自我实现和群体归属的心理需求。[1]37民国时期战乱和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触动了国民对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的认知和思考,历史剧中的反面角色为了实现自我,与社会群体成员发生矛盾,且采用极端卑劣的手段解决矛盾,这种行为的成因是几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积淀和现代启蒙思想碰撞融合的结果,同时也开启了特殊时期战争与独立的时代主题。
一.“英雄崇拜”情结的影响
郭沫若本人自少年时期就崇尚英雄主义,喜欢屈原、李白,留日的求学经历激发了他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从文化与时代的角度出发,郭沫若在历史剧创作中以中国传统的英雄文化为底色,针对抗战时期日军文化侵略和愚民政策的现状,在人物书写中渗透一种情与志的力量,目的是使民众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这里的情主要是指个人对国家、民族和他者的情感态度以及由此为动因而滋生的个人情感体验;志主要是指个人内心所坚守的观念、信仰和所追求的目标、方向。在英雄人物身上,这股力量表现为爱国情怀、民族情感和报国之心、为正义献身的信仰,而在反面角色身上,则体现为反动行为的动力和缘由。“英雄主义”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中是一种信仰和至高理想,无论是自我实现还是社会认同,都是被全员认可的荣誉和标志。反面角色内心对“英雄”的冠名同样充满渴望,确切地说,他们的行为动机是变了味的个人英雄主义。
(一)缓解认同危机
反面角色以血腥手段缓解其个人英雄主义的认同危机。剧中秦始皇、汉元帝、魏安釐王、赵高、侠累等直指蒋介石国民政府和汪精卫为代表的汉奸,他们都接受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有“英雄崇拜”情结,其个人自我认同和身份归属均定位在“民族英雄”和国家主宰者,由此引发的权力欲望和政治主导权的野心与他们现实中的专制强权和奸佞叛国行为完全背离,其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都出现了危机。反面角色把反动行为建立在其个人的绝对权力之上,消灭正义人士可以消除反抗力量,稳固反动政权,继续确保其个人地位不受威胁;采用残暴血腥的镇压和虐杀手段,掩饰了其内心认同危机的不安,通过限制和毁灭对手的人身自由和肉体生命,找到一种“唯我独尊”的存在感和虚荣心。《虎符》中魏安釐王先是一副胆小怕事的口吻以秦国强大拒绝信陵君的求救,后又展现出凶狠残暴的一面施以迷术拷问如姬核查其是否忠心,归根结底是对信陵君和赵国的势力有所忌惮,有借强秦之手灭掉争权对手之心,他以人杰自居且陷入对自我崇拜和政治野心之中,这实际上是一种寻求自我实现的行为,这一剧情设计恰好讽刺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剿共的行径。《棠棣之花》中侠累一面说自己辛苦,抱怨韩哀侯昏聩、每天睡觉不想动,[2]219一面又带着自我陶醉的神气威胁严仲子说:“和我作对,结果是丧家之狗!┈我手有搏虎之力,比姜太公还要足智多谋,谁能够把我怎样?”[3]220这完全是一副劳苦功高、位高权重的姿态,强调替韩哀侯分忧是为了在众人面前突显其重要性,这可以理解为自我认同的表现,威胁严仲子是以此为借口震慑反抗力量,为社会认同营造声势。后来的剧情中,侠累自言自语地驳斥严仲子合纵抗秦是以卵击石,“象他(指严仲子)这种主张才真正是祸国殃民的主张,而他偏偏在骂我卖国求荣!哼,我侠累卖了什么国?即使我就算把韩国出卖了,唉,我是卖了一笔大价钱的啦。”[4]220并许诺下属:“我将来做了魏国国君,不会辜负你”,[5]221这是为了博得外界舆论的认可给自己卖国开脱罪责,拉拢人心、为问鼎王权筹谋,满足他对社会认同的心理需求。投射到现实中,汪精卫选择依附日本军国势力,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可以满足个人自我存在感,做日本的政治傀儡意味着在反共军事行动和与蒋介石的矛盾中拥有话语权,在与日军、蒋介石国民政府、中共三方政治势力的斡旋斗争中充分享受权力带来的身份认同感以及个人“英雄主义”的心理满足感。
(二)获取优越感
反面角色通过实施性别压迫获取身份点缀和政治资本,满足其“英雄”情结所带来的优越感。
首先,反面角色认为男性对于女性身体的占有是天经地义的,红颜美色是英雄身份的点缀和装饰,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自古以来就有“英雄配美人”的传统,人们普遍认同这样的观念:男性主宰世间一切,女人就是工具、是物品,女人在战争中的首要价值就是“身体”的情色功能。汉元帝、秦始皇、包括昏庸的楚怀王、恶毒的车力特穆尔,这些以“英雄”自居的角色都是这样认为,汉元帝权衡政权与女人的轻重之后忍痛割爱并杀掉毛延寿泄愤、秦始皇骂赵高说自己虽然身体不太好但“精神”是极好的、南后郑袖假晕投到屈原怀中却转身向楚怀王告状挑拨楚怀王对屈原的信任、车力特穆尔对阿盖的垂涎唱词中极尽谄媚、还有王聚星对盛蕴贞的百般纠缠┈这种对女性强烈占有的表现背后隐藏着男性身为“英雄”的霸道和特权,也包括女人是男人附属品的性别优势心理。
其次,男性对女性的身体自由和命运走向有主宰权和支配权,反面角色坦然享用并贪婪索取女人在策反、献媚、权力制衡等方面所带来的政治资本和身体安慰,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女人的生命状态和人身自由。卓文君的出走表面看是对封建父权专制的反抗,但其父亲和公公卓、程两位长辈的强权压迫是有直接影响的;婵娟的死表面看是郑詹尹送毒酒造成的,但宋玉变节带来的失望情绪和张仪、靳尚暗中对屈原的迫害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聂嫈、春桃、怀清怀贞姐妹和如姬都是自杀,但却是受侠累、赵高、魏安釐王的逼迫和恶行的直接影响┈女性在父权制的笼罩下没有自主选择的机会和权力,只能以献祭和牺牲的方式被动反抗,因为封建制度赋予了反派足够的社会身份和权力地位的优势。
再次,男性采用情感哄骗、猜忌反间、死缠烂打、情感伤害等多种手段,打着情爱的旗号充分享受玩弄女性的乐趣,毫无真情可言。《屈原》中宋玉起初与婵娟的爱情是得到屈原的支持和关爱的,但后来贪慕虚荣、贪生怕死倒向南后,还跟子兰抱怨嫌弃婵娟丫头出身、古板,不能帮助他,是前途的障碍,[6]331显现出一副维权是图的势利嘴脸,这种变节和变心的言行对情感炽烈的婵娟而言是一种痛心的欺骗和伤害;宋玉在听说屈原失踪后不但不去追寻,还说:“先生疯了,不死比死了还坏,活着有什么好处?”[7]349这对素来忠诚追随于屈原的婵娟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的情感刺激;而宋玉却一面维护着其“志向远大”“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形象,一面对婵娟说:“讲气节,说话容易,做人不容易”,[8]347继续以言语哄骗博得同情和理解。在和婵娟的关系里,宋玉对外始终扮演恋人的角色,但却毫无爱情之举,最渣的是明明是毫无担当、背信弃义的冒牌“英雄”,却要为自己各种粉饰,毫无羞耻之心。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南冠草》中,王聚星出家做和尚躲避战乱,后抵挡不住洪承疇劝降时功名利禄的诱惑,为得到盛蕴贞分别找夏淑吉、夏盛氏帮忙游说未成,第二幕第一场最后的说明中:“(王聚星被夏淑吉和夏盛氏拒绝后)甚为苦闷┈对于出卖夏完淳一事,亦尚在踌躇,又因爱欲盘郁于胸中,正作最后之交战”,[9]343一番思想斗争的结果是,王聚星又当面纠缠盛蕴贞,以吃醋的方式诬陷、激怒和试图拥抱盛蕴贞,却落得个被拒和取笑的下场。与道貌盎然、虚伪浮华的宋玉相比,王聚星的求爱如上梁小丑般可笑,他对盛蕴贞的婚姻要求与出卖夏完淳是有关联的,剧中揭露他猥琐、邪淫又贪婪、无耻的灵魂,也展现出他深谙调戏、觊觎女性之术的一面,让观众看到,即使是在战争的环境中,男性在精神上对女性的调侃和消遣心理依然存在,不同的是,男性在两性关系中沿用了传统的欺瞒伎俩并不是出于真情爱,而是个人的“英雄崇拜”情结。
二.根深蒂固的主奴思想
反面角色的登台暴露了民国时期反动势力和民众心理的阴暗面,从文化与人的关系来看,此类人物的出现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弊端和劣根性是不无关联的。如前文所述,反面角色最擅长的就是高压手腕,在君臣、两性关系中都表现出强烈的阶级观念和权力欲望,这是对儒家积极入世和追求功名思想的曲解。孔子的“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勉励读书人勤奋治学、志存高远,以国家的任用作为个人身份认同的最高归属,于是科举选拔后的官职高低成为有志之士获得社会认同的标杆,世人对至高权力和尊贵身份抱以由衷的向往和自觉的服从,久而久之,民众习惯了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并达成思想共识:中国只有两种人——主子和奴才。
(一)主子思想
反派人物因为拥有至高权力或接近权力核心而自认为主子的角色,因此对英雄正义之士进行迫害不过是行使主子的特权而已、理所当然,而且他们私人的利益就可以代表并决定国家、民族的未来,这种心理和行为歪曲了儒家对个人身份、地位、阶级的定位。孔孟在治国方面皆倡导仁政和礼治,士子把追求功成名就和荣华富贵与民族情怀和家国之志融为一体,因此,儒家更看重与权力、地位相匹配的责任与义务,换言之,君王位高权重、统摄天下自然应担起人主的职责,以百姓安危为行为准则。与之相反,在历史剧中反派的思想深处,主宰社稷、统治民众的身份和地位却成为衡量其个人存在感的标志,而且稳固手中权力比国家兴亡更为重要,因此,剧中南后郑袖、秦始皇、魏安釐王都为了自保,对屈原、高渐离、信陵君、如姬等异己力量进行杀戮和清除。
(二)奴性心理
国民长期以来惯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奴性心理以及日本愚民政策的精神毒害,为反面角色的施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受众和接受环境。鲁迅在《铁屋子的呐喊》中曾经痛斥整体中国人“沉睡的”精神病态,指出服从于强权和暴力的奴性心理是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致命阻碍。[10]10时至抗战,日本为了实现“宣扬皇道,使不服从者服从之”[11]191的目的,采用以华制华和文化愚民等手段实施精神上的控制和驯化,利用中国人看重“英雄”名誉的心理,以权力和地位的诱惑分化抗日势力,同时以拯救者的姿态强调日本在文化上的优势和军事上的强大,打击中国民众的自信和反抗意志。于是,中国人的奴性出现了分化,少数处于上流社会的权贵内心认同主奴地位的区分,呈现出欺弱怕强的双面人格,也就是常说的“汉奸”。表现在历史剧中,以《棠棣之花》中的侠累、《高渐离》中的赵高为代表的奸佞叛国者对外向强权的日军(剧中是强敌如秦国的设计)屈从、对内对抗日分子和民众(剧中是屈原、高渐离、如姬等英雄人物)镇压背叛,一人分饰了奴才和主子两个角色:在统治者和弱者下人的面前分别经历从摇尾乞怜的奴才相到尽显主子身份的迅速变身,在抓捕陷害英雄人物前后也表现出从伪善示弱到狰狞狠毒的极端转变;变脸前的奴性都带有面具,比如《高渐离》赵高对秦始皇的逢迎、《孔雀胆》车力特穆尔对阿盖的谄媚、《屈原》郑詹尹对屈原的同情和文人宋玉的伪装、《南冠草》洪承畴的劝降,而变脸后则摘掉面具展露出凶残本相、手段残忍卑劣,对比强烈。
还有相当部分中国人的奴性表现为对抗战的冷漠麻木和反抗精神的匮乏。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和灾难史已经催垮了民众的民族自信心,长期的封建愚民统治让民众更习惯于服从和忍受;日本入侵后首先向中国人灌输的观念就是:中国是“老废的民族”,“支那国民性”已经彻底堕落,[12]12而且鼓吹日本的崛起和强大,汪精卫大肆宣扬“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主张;几部历史剧的创作和上演正值抗战最艰难的对峙阶段,国际上德意法西斯国家承认日本国的地位,国内正面战场有局部战败,武汉陷落后重庆大后方汉奸周佛海以逃避和无奈的态度传递消极情绪、摧毁抗日斗志:“没有一个人不想到讲和,又没有一个人敢于讲和,这些人都希望别人来讲和,而自己做主战论者”。[13]175如上所述,社会言论和战争形式让民众对于民族未来和战争结果持悲观心理,产生盲目的自卑感和得过且过的绝望情绪,缺乏反抗精神,这为血腥政治的实施奠定了最广大的受众基础。反映在剧作中,表现为韩哀侯、楚怀王、老梁王、段功等昏庸妥协主义者指涉现实中亵渎抗战职责、放弃抵抗的人和现象:比如《棠棣之花》最后一幕中韩哀侯听从侠累挑拨、帮助秦国灭魏时表现得昏聩不堪,先问秦使:“故尔贵国有事于魏国,敝国愿悉索敝赋,以效命于疆场,是这样吗?”[14]225又问侠累该如何跟秦国使者谈话,自己不大清楚,[15]226韩哀侯身为国君对战争和国家存亡是无所谓、听之任之的态度;《孔雀胆》中段功已从阿盖公主处得知了车里特穆尔的不轨之心,但却只是一声“哦”,没有采取任何反抗和自卫防御的军事行动,老梁王却更甚之,竟对车有惧怕心理,最后落得个全部被杀的结局。韩哀侯、老梁王、段功天真地认为一味妥协和退让更有利,但最终因不抗争失去了主动权,使得侠累、车力特穆尔等在毫无障碍的情形下施以恶行,反面角色的目标得以实现。
三.救国思想下的文化产物
(一)民族情感的宣泄
反面角色人物形象是郭沫若与阻碍民族发展和解放的敌对势力斗争的产物,其对待身体的血腥与暴力态度是作者个人对国家和民族情感的一种宣泄和爆发。
蒋孔阳先生在《美学新论》中指出:“能够描写丑恶的人不是丑恶的人,而是与丑恶作斗争的人”。[16]386郭沫若是中华民族跨进现代进程中的精神领袖和标志性人物,他早在《凤凰涅槃》中就已经以火山爆发式的身体观表达出“为革命献身”、“革命就要有牺牲”的信念,诗歌在表现凤凰涅槃重生的过程中对身与心的撕裂、毁灭、新生等场景的书写中充斥着剧烈的力量感和炽烈情感,这种冲击力与六部历史剧中正反角色的对抗与冲突在精神和灵魂层面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这么说,郭沫若本人情感饱满且表达方式奔放,内心向往以壮烈的牺牲和毁灭赢得革命的胜利,面对战争,他认可并推崇血腥和激烈的反抗方式。因此,反面角色的剧本人物是作者革命激情和爱国情感的变相表达,只是与《女神》时期相比,同为革命者的正面形象,凤凰在反抗黑暗势力的斗争中主动自我施暴,血腥和暴力是用来反抗的手段;而历史剧中,英雄人士在与反面角色的身体对抗中更偏向于是暴力的承受者,而且自残和杀戮都是被动的。
(二)文化反侵略策略的产物
反面角色塑造是郭沫若文化反侵略的一个策略,其存在促进了戏剧煽动情绪功能的体现。
首先,反面角色及其所实施的血腥行为本身就有自我否定的功能。赵清阁在《抗战戏剧概论》中指出:“戏剧就是宣传与教育的文化工具”,[17]4“戏剧家可以尽量运用技术发挥它、推动它;使戏剧的感染力普遍地影响到每个战时人们的生活深处,使戏剧直接地助长抗战必胜”。[18]6郭沫若时任国民政府第三厅厅长,考虑到国民党抗战文艺政策的严厉监管,取材先秦、元末、明末等战乱时期借历史人物发声是曲线救国行动;郭老在写作后记中自言:把有历史贡献的帝王秦始皇写为反派映射蒋介石,把张仪写为挑拨两国关系的小人暗喻汉奸,而且把象征抗日反动势力的赵高塑造得颇为成功。如此设计是迫于官方势力,逃避政府审查、保证正常演出,但实际上却收获了极为强烈的讽刺效果。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權为代表的汉奸群体的行为模式以血腥政治的方式被搬上舞台公开示众,观众看到了反派的虚伪和政治面具就想到了现实中的黑暗,演出本身就是反动势力的一次自我暴露,就像蒋孔阳先生所言:“丑在文学艺术中的美学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自己否定了自己”。[19]3861942年9月,《文化先锋》创刊号刊登时任中宣部部长、文运会主任委员张道藩的《我们所需要的的文艺政策》中明确指出文学创作不能写“社会黑暗”“阶级仇恨”“悲观色彩”“无意义的作品”“不正确的意识”,[20]169因此,《屈原》《棠棣之花》《孔雀胆》上演前的审查都屡遭压制。这种专制的文化政策说明国民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强权镇压的行为正是剧中血腥政治的翻版,自我讽刺意味十足。《屈原》公演结束后,山城的大街小巷宣泄着对现实的不满,[21]129蒋介石授意国民政府在《中央日报》《中央周刊》《文艺先锋》《出版界》刊登批评《屈原》创作的文章,意图消除《屈原》的政治影响。[22]131这更加证实了郭沫若创作策略的杀伤力,纵观来看,反面角色自我否定的效力要远超过与英雄人物的对比和衬托作用。
其次,反面角色及其血腥行为是作者在抗战时期文化育人思想的产物。民族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是成就郭沫若历史剧的一大要素,舞台上的反派人物和血腥行为还原了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的争战,属于“对内”;但观众席看剧的时代背景却是反抗日军侵略的国族战争,属于“对外”。内政与外交于社稷兴衰来说原本是性质不同的政治问题,各类反派的原型和舞台人物让二者发生了联系,教育寓意是多重的。一方面,“血腥”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自古以来的“尚武”传统。反派高压统治的结果是高渐离、聂政、聂嫈、如姬等人以武力争取自由,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抗争,并且要坚持到底,而当时中国的现实是反抗乏力、消极沉闷,尤其是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国民党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表现出了思想上的动摇。面对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言论和国际法西斯势力的施压,深谙中日文化渊源的郭沫若积极奔走于前线和大后方,在演讲时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先进和强大,号召广大文化工作者要像鲁迅先生那样“不屈不挠,和恶势力斗争到底”。[23]968可以看出,郭沫若强调面对敌人要采取强硬、不退让的态度,作品中暴君、汉奸、妥协主义者并没有成为最后的赢家,《棠棣之花》的最后一幕中,卫士甲乙深受聂政、聂嫈、春姑触动,说道:“我们要联合起来抵御秦国”,[24]269这已经是代观众发出了奋起抗击的呐喊;演出在所有演员的合唱中落幕:“去吧,兄弟呀!中华需要自由!如狼似虎的恣睢暴戾,要吞蚀赤县神州,人们反勇于私斗,而怯于公仇,去破灭那奴隶的枷锁,把主人翁们唤起,快快团结一致,高举起解放的大旗”,[25]270其中“私斗”和“公仇”就是要国民分清内乱和外侵的关系,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国民劣根性和铁屋子揭示国人麻木将死的灵魂,郭沫若通过正邪对抗让中国人看到团结抗战、血性武力的重要,同时由汉奸、妥协主义者对强秦的顶礼膜拜和落败下场体会到弱国无外交的现实。另一方面,反面角色及其血腥行为从批判的角度反映出作者的民本思想和民族意识。郭沫若在《女神》时期就推崇“人”和“人性”、歌颂民主自由和女性的伟大,历史剧选择先秦题材来写正是因为作者认为春秋战国时代讲究“仁”并把人当人看。[26]3如此看来,反派的专制与等级观念、虐杀他者身体、歧视女性的行为恰好是作为反面典型写进剧本,同时被遮掩在古代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之下,只不过忠的是暴君和昏君、爱的是敌国。根据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学术研究著作可以得出,他本人认可孔子儒家学派的“民本”思想,再具体点,这个“民本”思想是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的启蒙思想洗礼过后的,体现在历史剧中,“民”指的是人民,“君”和“国”则都是在中华民族或者国家的层面上来说。换言之,历史剧虽然是朝廷内外王侯与臣民、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背景,但主题上宣扬的却是人民至上的现代国家意识。设置秦始皇、魏安釐王、韩哀侯、楚怀王、老梁王等角色,目的就是讽刺、批判现实中反动势力和妥协主义者缺乏国家层面上的大局观和重视民心向背的政治观,强化观众的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以及人民力量的伟大;而反面角色及其血腥行为则可以说是众矢之的,是所有爱国的人民要推翻和颠覆的目标,英雄是人民的先驱和代表,他们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用死亡实现生命的超越,让民众在愤怒和悲伤中看到反面角色的罪恶。就像《棠棣之花》中聂嫈自杀于聂政尸首前,酒家女亲眼目睹后痛彻心扉地说:“我们的血汗成了他们的钱财,我们的生命成了他们的玩具”,[27]131这是对当权者黑暗统治的控诉;旁观的秦国卫兵甲则终于觉醒:“朋友们,你们有良心的,请来帮助我把这几位好人的尸首抬进山里去罢!朋友们,你们有良心的,请跟着我来,跟着我去山里做强盗去罢!”[28]135这是在呼吁全民起来反抗、为自由而战。
郭沫若在历史剧中批判了外敌侵略、封建文化的阶级压迫和强权思想以及严重毒害国民思想的劣根性,把民族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呈现出来,让民众反思遭受血腥与邪恶折磨的根源何在。反面角色除了反衬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还对全民抗战起到了警醒和鼓舞的作用,怎样才能实现自由独立,如何让更多人奋起反抗将侵略者驱逐出境,这是郭沫若塑造反面角色的根本原因,也是他留给观众最深刻的思考。
参考文献
[1](美)劳伦斯·莱尚著,林克译,战争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3][4][5][6][7][8][14][15][24][25][27][28]郭沫若著.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9]郭沫若著.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0]陆妙琴.论鲁迅对国民奴性心理的批判[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20(10).
[11][12][13]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16][19]蒋孔阳著.美学新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7][18]赵清阁著.抗战戏剧概论[M].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1939.
[20][21][22]李扬著.从第三厅、文工会看国统区抗战文艺1937-194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2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26]曹丹丹,论郭沫若抗战史剧中的日本文化因素[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06.
[基金项目]基金来源: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一般课题;课题名称:郭沫若民国历史剧的反面角色研究;编号:GY2018B05,主持人:王明娟。
(作者介绍:王明娟,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王学振,海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文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