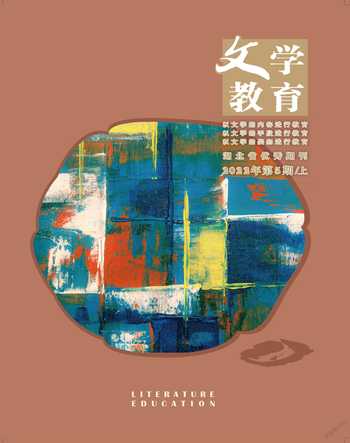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叙事视角
刘亚男
内容摘要:丁玲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用第一人称叙事者“我”的视角,巧妙的描写了贞贞在霞村发生的故事。同时在叙事过程中,叙事视角多次进行了巧妙地转化,用霞村村民的眼光取代叙述者我的视角,或者用贞贞自己的视角来审视现状,说出“我”所不知的事情。多重视角下展现同一个故事——贞贞苦难的生活遭遇,把不同视角下多面的、鲜活的、生动的“贞贞”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关键词:丁玲 《我在霞村的时候》 贞贞 叙事视角 创作倾向
叙事视点即叙事人是站在何种角度、以什么方式来叙事的着眼点。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对叙事视点进行了定义,叙事视点是指:“叙述故事的方法——作者所采用的表现方式或观点,读者由此得知构成一部虚构小说的叙述里的人物、行动、情境和事件”[1],“视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视角”,叙述视角在一部作品中一般有一个基本定位,但也可以发生变动游移,使叙事可以在更加广角的角度去摄取故事。一部小说叙事视角的载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叙事者视角和人物角色视角。
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通过不同的视角,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悲剧女性“贞贞”的形象。作品用“我”的眼光来进行叙述,“我”因所在单位政治部太嘈杂,临时去安静的霞村休养,在霞村的所见所闻。“我”是一个取景框,一切外在事物都是通过我这个取景框进行过滤后进入叙事视野的,这体现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文章的“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视角,小说中的主人公“我”作为第一视角,同时通过视角的游移,使叙述发生了巧妙的转化,呈现出霞村人、贞贞自己等人物的视角。这种视角的游移可以起到很多作用,比如设置悬念、制造冲突等,分析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的叙述者的眼中呈现的不同的状态,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这篇文章,体味作者精妙、完美的叙事艺术。
一.不同视角下的同一个“贞贞”
托多罗夫指出: “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以‘它们自身’出现, 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个观察点呈现我们面前。……视点问题具有头等重要性确是事实,在文学方面,我们所要求的从来不是原始的事实或事件, 而是以某种方式被描写出来的事实或事件。从两个不同的视点观察同一个事实就会写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件。”[2]本文立足于考察不同视点下的贞贞的命运。按照《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文章的叙事脉络和叙事视角重要程度,我们从三个方面去进行讨论。第一个是从“霞村人的视角”,通过村民的叙述来引出貞贞的故事;第二个是从“主人公的视角”,通过贞贞和我的谈话,以及夏大宝的自责中,引出事情的真相;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视角,即“叙述者的视角”,通过我的讲述,用第三者相对客观的眼光,展现了贞贞这个女性。
1.霞村人的视角
鲁迅先生的“看客”形象深入人心。也许在当时的社会,最大的悲哀不是中国人被压迫、被奴役,而是那些冷漠地咀嚼着别人痛苦的同胞们,丁玲受到鲁迅的影响,再现了那群“冷漠无情”的村民形象。小说从“我”到霞村开始写起,“我”通过村民的异常表现和吞吞吐吐的言谈中,巧妙地把视角游移到“霞村人”眼中,了解到“霞村人”眼中的贞贞的故事。
我刚来霞村便遇到了几个热衷于八卦的村民,作者对于这些村民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刘二妈“常常把声音压低,像怕什么人听见似的那么耳语着”[3]153;杂货铺老板“便眨着那双小眼睛,有趣的低声问我”[4]156,“邻舍的人全来了,他们交头接耳的,有的显得悲戚,也有的满感兴趣的样子,天气很冷,他们好奇的心却很热”[5]166。作者很巧妙的通过自己的经历,比如出去散步等活动,把叙述的视角游移到霞村人民身上,这种视角游移到霞村人身上的叙事,一方面可以通过对霞村百姓的神态描写,看出霞村人对于贞贞的态度,即在那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传统观念中,霞村人对贞贞的敌意;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他们疑神疑鬼的对话,顺理成章的引出贞贞的故事,同时又可以设置悬念,吸引读者阅读兴趣。
作者对刘二妈的言谈进行了相对详细的叙述,作为和贞贞有亲戚关系的霞村人,刘二妈总是想和我“报告”些什么,同时“我”也在细碎的刘二妈们的谈话中总结出了霞村人眼里的贞贞。
首先,贞贞在霞村人眼里类似于妓女形象,玉娃的“怕什么,不也是人么,更标致了呢”;杂货铺老板的“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打水妇人的“弄的比破鞋还不如”。这种具有伤害性的话语把贞贞放到了罪人的位置,霞村的人用一种异样的、排斥的眼光去看待她,这种言语中也包含了男性视角下的道德规范,比如杂货铺老板的“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两个打水妇人说的“弄得比破鞋还不如……”[6];“这种破铜烂铁还搭臭架子”[7]168。这些带有高高在上的、审视的眼光去看待似乎不如她们的贞贞,进一步增加了贞贞身上的悲剧色彩,贞贞遭受到除了日本鬼子带来的痛苦外,还受到了包括亲人在内的霞村人的言语伤害。
其次,贞贞是一个“倒贴”式的“不要脸”的形象,刘二妈谈论起夏大宝的时候说道:“他正经也不敢怎么样,偏偏咱们贞贞痴心痴意,总要去缠着他,一弄又怪了他;要去做姑姑还不是为了他……”,刘二妈话虽然委婉,但是在那个封建思想尚在的霞村人眼里,贞贞这种主动去追求男性的行为,已经被冠上了“不知廉耻”的标签,所以后期大家只会说“夏大宝倒霉”,却对贞贞毫无同情,因为贞贞违背了他们长期坚持的“守节”和“妇道”的观念,让他们对“异类”不自觉的排斥,甚至还会有一种高高在上的道德优越感。
这种群体性的注视下,演绎了贞贞被鬼子糟蹋后的“伤风败俗”和“厚颜无耻”的女性故事。
2.主人公的视角
根据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的“四分法”可知,这里的主人公的视角可以称为“内视角”。主人公是故事的亲历者,他们往往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事。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我”在阿桂的安排下,终于见到了霞村人口中的贞贞,这时的我作为一个听众,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的方式,把“我”的视角暂时转化成了贞贞的视角,使贞贞获得了自己故事的话语权,但是又把贞贞和我说的话截取了一部分来讲述,这次的我们通过贞贞了解了一部分事情的真相。
首先,我听到了一个坚强、勇敢、有责任心的“女英雄”故事。受到日本人和霞村村民伤害的贞贞,主动且坦然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一年多以前,因为革命被委派做间谍,在日本人那里获取情报。由于对完成任务有好处,也学会了一些日本話,她曾经为了及时送到消息,拖着病痛的身子走了一个礼拜,但是因为被很多人糟蹋过,染上了不名誉的、难医的病症,组织不在给贞贞派任务,便回来看看爹娘。贞贞讲到那些痛苦的日子,仿佛是局外人般冷静,正因为她言语中没有牢骚、没有悲凉,同时也从未想到获得同情,用文中“我”的话说便是:“正因为她受伤太重,所以才养成她现在的强硬,她似乎是无所求于人的样子”[8]165,这使我们更加心疼这个可怜的姑娘,一位机智勇敢的女性,却被那些蒙蔽在封建礼教下的霞村人诟病。
其次,从贞贞的言论中,作者并未提到贞贞和夏大宝的过去,而是试图从夏大宝和村民的口中去让读者联想当时发生了何事:贞贞父母嫌贫爱富,打算把她送给米铺小老板做续弦,贞贞反对这种婚姻,想和夏大宝逃跑,但是因为夏大宝的软弱而灰心失望,贞贞跑到天主堂做姑姑,意外被日本人抓走。在这里,夏大宝也是这场悲剧爱情的主人公,他也是站在贞贞的立场去讲述事情的真相的,所以夏大宝视角下的贞贞也是真实的贞贞。为何不让贞贞自己叙述那段往事呢?文中的“我”隐约给出了答案:“但我也不愿问她,看着她来,说几句毫无次序的话——但我看的出她却在想着一些别的,那些不愿让人知道的”[9]165;“我也不知道如何来开始我们的谈话,怎么能不碰着她的伤口呢,不会损坏到她的自尊心呢”[10]161。一方面“我”不想难为她,让她说一些自己不愿说出的事,另一方面,“我”也害怕自己会伤害到这个可怜的女孩,所以真相只能通过细枝末节来表现。
在这些细枝末节中,我们发现隐藏在真相下的贞贞其实是受害者形象——她是一个在父母的贪财和男友的懦弱下,不得不自己反抗包办婚姻,结果失败的苦难女性。这和霞村人眼中的贞贞形象完全不同,是贞贞和夏大宝这两个主人公眼中的真实的贞贞,在这里的贞贞是勇敢追求爱情,不屈反抗命运,为国奉献力量的女性形象。
3.叙述者的视角
叙述者的视角在申丹的“四分法”中被称为“第一人称外视角”,在作品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故事、情节都是通过叙述者的讲述才能够被读者感知。在小说中,贞贞这一丰满的形象表现是通过“我”的细致观察和精彩的描述去实现的。在“我”的眼中,贞贞从“那么坦白,没有尘垢”到“像一个被困的野兽,像一个复仇的女神”,再到“新的东西又在她身上表现出来了”,这一系列的变化,实现了贞贞这个人物形象的自我成长。
“我”第一次见贞贞时对她的描述:“那眼珠却被灯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就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洞开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11]161,一个历经坎坷的女性,对生活没有怨恨、没有失望,还可以保持自己的纯真,保持自己对生活的热情,在刚见到贞贞时,“我”就已经完全的否定了霞村人的观点,进而对贞贞给与了极大的赞赏,这里的“我”情感偏向十分明显,这个像阳光般的女孩,给我沉闷的生活带来了新鲜,所以“我”谈话的时候谨小慎微,十分担心自己会碰到这个美丽姑娘的伤口,打破这些美好,但是贞贞的表现却是“声音清晰,不显得拘束,也不觉得粗野”[12]162,这样的贞贞是美丽大方,也同样是对霞村人口中的“伤风败俗”“厚颜无耻”的形象进行了反驳。
贞贞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在身体和心灵遭受了巨大的的摧残之后,在利用自己的身体为组织提供情报之后,在苦难岁月即将过去之后,贞贞既不悔恨自己的过去,也从未痛骂她的敌人。即使对曾经伤害自己的夏大宝,也没有仇恨,她对一切都表现的很淡然,就像文中“我”叙述的:“正因为她受伤太重,所以才养成她现在的强硬,她似乎是无所求于人的样子”[13]165“贞贞早已经做出不要任何人对她的可怜”[14]167,这是因为贞贞自己很清楚,所谓的忏悔也好、憎恨也罢,都是毫无用处的,包括自己的父母在内,没有人可以体味和理解她自己的无尽痛苦。当贞贞把一切的痛苦化为一个微笑时,反而加深了读者的震撼,她用自己的方式,独自舔舐着伤口,这样一个勇敢对命运进行抗争的女性,“我”对她抱有“非一般同情可比的怜惜”,所以“我”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温暖她的灵魂。
在全文的叙述中,贞贞的形象就像王蒙形容的:“少年时代我读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贞贞的形象让我看傻了,原来一个女性可以是那么屈辱、苦难、英勇、善良、无助、热烈、尊严而且光明”[15]。王蒙用了许多形容词,很难想象这些品质可以溶于一个女性身上,但是贞贞她便是这样,并且还有更多的品质在增长。因为文章结尾“我”说:“新的东西又在她的身上表现出来了”[16]171,刘绶松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展示了一个叫作贞贞的、灵魂和肉体都曾遭受过极大损伤和破坏的、穷乡僻壤中的青年女性的深广的性格,从她身上,作者发掘了而且深刻地表现了一种强大的新生力量。”[17]贞贞还在成长,这个女性身上还有太多我们没有看到的品质。这是文本中叙述者视角下有光辉品质的贞贞形象。
不同视角下的贞贞表现出了不同的形象,为何会存在这样认知的差距呢?霞村人和“我”有何区别?作者丁玲这样安排又是有何目的呢?
二.不同视角下作者创作倾向探寻
文中的“我”虽然是一个游离在故事之外的“局外人”,但是这个“我”却起到了串联故事脉络线索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我”作为贞贞的朋友这一身份被叙述着,整部小说是开始于“我”到霞村,结束于“我”离开霞村;另一方面,“我”又作为叙述者,不断向读者讲述着小说中“贞贞”的故事,“我”去屋外散步,便看到了霞村人眼里的贞贞,“我”和贞贞谈话,读者便了解到贞贞这个女孩,即使“我”离开了,也要通过同事得到贞贞的消息。“我”是小说虚构的人物,但是一般我们都会把“我”视为作家自己,比如鲁迅《祝福》《在酒楼上》;巴金《憩园》;萧红《小城三月》等等,陆耀东在《评<我在霞村的时候>》文章中说:“‘我’的身份、思想感情,与丁玲其人都是极近相似的”[18]。这也说明,文中“我”作为叙述者在对贞贞进行描写时,也包含着作者丁玲思想感情的融入,作者力透纸背,对受到封建专制桎梏下的霞村人恨的那么鲜明,对贞贞这个女性爱的那么强烈,爱憎分明,给读者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力。那作者的创作意图是什么呢?学术界对于《我在霞村的时候》这本书的创作主题进行多层次的解读,但是本文强调的是作者对于不同视角下人物对待贞贞的态度进行分析。
1.憎的丰碑:受封建专制桎梏下的霞村人
鲁迅说:“创作总根于爱”[19],但是又认为“人的天性上不能没有憎”[20]。丁玲带着艺术家的勇气,为受到封建专制桎梏下,愚昧无知的霞村人做了逼真的素描。“霞村人”作为一个群体,集体排斥“失貞”的女性。她们甚至因为有了贞贞的存在,发现了自己的圣洁,并且因为自己没有被日本人强奸而感到骄傲。作者通过视角的游移多次对霞村人进行了描写,无论是那些犀利、冷漠的语言描写,还是小人、看客似的神态描写,都是作者想让读者看到的古老民族的封建魂灵。在这里,作家憎恨的是那些受到封建专制桎梏下的人民,这里的恨,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在里面。
反复回想作者写作意图,霞村人代表的是儒家的中国封建思想,它们轻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几千年来的封建贞节观念像一颗毒瘤,根深蒂固地长在每个中国人的头脑中,他们把女性的“贞节”看的比生命更加重要,所以才会出现“浸猪笼”“一女不侍二夫”等说法,也就有了祥林嫂(鲁迅《祝福》)到土地庙捐门槛来赎罪的悲剧,祥林嫂的悲剧来自封建社会和自己内心,但是乔以钢在《中国女性与文学》一书中提到:“(《我在霞村的时候》)深入到民族传统心理的建构中,将‘贞洁’这个古老的伦理道德观念放在民族灾难、民族斗争的大背景下重新加以审视,深刻揭示了贞贞这样的不幸妇女承受的双重苦难、双重悲哀”[21],贞贞的苦难因为回到霞村而被放大,这个生养她的地方,再一次无情的伤害了她,作者在此批判的便是这种不合理的封建残余思想,希望可以早日重视这个问题,早日铲除这些愚昧落后的“贞节观”。
封建思想不仅培育了女性“贞节”观,还有灵魂的麻木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霞村人对贞贞是残忍的,他们对贞贞受到的伤害无动于衷,并且毫不犹豫的补了一刀,以至于贞贞觉得,活在不认识的人面前,比活在认识的人面前好。可见,这些霞村的围观者对她造成的伤害,比伤害本身更加严重,他们时时刻刻的提醒着贞贞,似乎那些痛苦永远在追随着她。霞村人让我们知道,唤醒这些沉睡的人们刻不容缓。
2.重塑新我:在愤懑孤独中挣扎的贞贞
对于贞贞是否打破了传统观念成为时代新女性这一说法,一直是大家争论的重点之一。从贞贞的行动来看,她拥有旧时代女性没有的勇敢、乐观,她不像祥林嫂那样精神恐惧,也知道“人还是得找活路”,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但是贞贞真的对于“失贞”不在意吗?当然也不是的,从贞贞淡淡的言谈中,她是在意的,她是消极面对,不愿提及。比如她说:“既然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22]171,贞贞内心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干净的人,她难以原谅自己,也不愿接受这样的自己,所以她只想活在不认识的人面前,这是她逃避现实的一种选择,也是在自我和他人的贞操观念上给自己判了死罪。在这点上,贞贞是自卑的,是没有跨越封建道德观的。她与祥林嫂不同的是,她是在愤懑和孤单中努力挣扎的人,在接触了外面的新世界后,贞贞有了可以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她不相信任何人,她也不需要任何同情与怜悯。
作者是欣赏贞贞的,也许未来的贞贞可以真正地摆脱“失贞”的自卑心理,但是这本身便是一个长期的自我斗争过程,长期扎根的封建文化又怎么会轻易的摆脱,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课题。所以文章的最后,作者给了贞贞一个相对光明的前途——到XX去治病,XX指的是延安,听说那里是大地方,学校多,什么人都可以学习的,延安在当时对于贞贞是个“世外桃源”,不仅可以治疗身体疾病,也可以治疗心理疾病,同时在延安,贞贞是革命者,是个英雄人物,是个为了革命胜利而奋斗的战士,这有利于贞贞重新建立自己的尊严和自信,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就像冯雪峰在《从<梦珂>到<夜>》中说:“作者所探究的是一个灵魂——那可是更非庸庸俗俗和温温暾暾的人们所再能挨近去的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23],丁玲同样对贞贞给与了极大的期待,她相信贞贞的话很快就会实现了。
3.爱的大纛:无视世俗偏见的叙述者
丁玲在塑造贞贞的时候,笔尖始终蘸满了爱。叙述者“我”对贞贞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不在意外界的眼光,和贞贞像朋友一样相处,倾听她的痛苦,并且看到了贞贞身上那不为痛苦压倒,并且一心向往光明的闪光点,我是欣赏贞贞的,这不是出于怜悯或者同情,而是贞贞带给我的“新的东西”;同时我也是尊重贞贞的,从未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而是处处考虑贞贞的心情,文中的“我”不愿意伤害贞贞,不会问出贞贞不想谈论的伤疤。
“我”代表的是革命知识分子,从作者视角上看,是完全不同于霞村人的眼光和态度,作者平等的对待这位遭受苦难的女性,甚至有些崇拜她的勇敢和乐观,现代意识的核心是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命运的关注,但是想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又会经历多久?没有人知道,即使过去很多年,我们现在的大部分人只能做到不会像霞村人一样投去冷眼和蔑视,但是会不会真正做到丁玲这样,平等的眼光、理解的内心、包容的心态去对待贞贞?能不能真心的让贞贞抛下过去去过新的生活?这一切都是不敢确定的,这是我们今后的目标,也是丁玲令人敬佩的地方。
总有一天,贞贞在大众眼中,不在是以前的“失贞”者,而是拥有民族气节、责任感强,直[16]面生活的可爱又可敬的女子,我们会像丁玲一样,崇拜这个历经风霜又顽强勇敢的女孩。
丁玲谈到写作这篇文章时候说到:“我想了好久,觉得非写出来不可,就写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个时候,哪里有什么作者个人的苦闷呢,无非想到一场战争,一个时代,想到其中不少的人,同志、朋友和乡亲,所以就写出来了”[24]。
丁玲作为鲁迅的学生,是革命作家,写作即为了赞扬,也为了批判,从不同视角下的人们对贞贞的态度中,作者丁玲批判了封建旧观念,赞扬了敢于反抗的新女性。
参考文献
[1]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辞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61
[2]张寅德.叙述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65
[3]-[14][16][22]丁玲.梦珂:丁玲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5]王蒙.观察丁玲——我心目中的丁玲[J],原载《读书》1997年第二期186
[17]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M]//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354
[18]陆耀东.评《我在霞村的时候》[N],载《文艺报》1957年12月29日第38期.
[19]鲁迅.而已集·小杂感[M]//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32
[20]鲁迅.译文序跋集·《医生》译者附记[M]//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76
[21]乔以钢.中国女性与文学——乔以钢自选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304页.
[23]冯雪峰.从《梦珂》到《夜》[J]《中国作家》1948年第一卷第二期
[24]丁玲.谈自己的创作[M]//丁玲文集(第五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403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