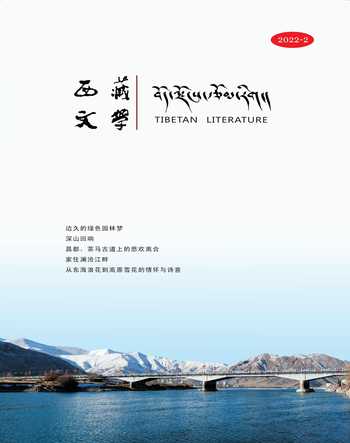先生的身教
程越
蔡美彪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不仅我们四个弟子,在我比较熟悉的元史学界,或者民族史、藏学等方面的学者,提到老师的时候大多用先生这样的称呼。我想,这体现了大家对他普遍的尊重吧。
从1993年进入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二十多年来,为了践行蔡先生的教诲,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先生从来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怎样做人,那么蔡先生是怎样教育我们的呢?慢慢地,我心中有了一个答案。
我是1992年立志报考蔡先生门下做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的。当时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随魏良弢师父、刘迎胜教授攻读西北民族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陈得芝老师的带领下,他们二位老师和丁国范、姚大力、高荣盛、华涛等学者群策群力,继承韩儒林先生的衣钵,把元史研究做得很有声色。我开始的理想是在本校继续攻博,做一名韩门弟子,后来因为感情上的因素,就想进京求学。记得那时想出国的人多,读研的人少,做学问的人穷,历史更是冷门,我求教了两个方向,最后定了投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笔试、面试通过之后在近代史所先生的办公室。先生的办公室大概有十二三平米,一张写字台,一铺单人床,主客共三把椅子,两个书架,余无长物。窗台上有一小尊白色的唐代仕女瓷像,每次我来看先生,在近代史所的大门口那里就能抬头看见它。从我认识先生,到二十年后再去拜见,屋内陈设一仍其贯。对了,只是变旧了,我们坐的椅子也老了,一坐就会陷下去。直到八十九岁,先生还从居住的东总布胡同来东厂胡同的这间办公室工作。
第一次见先生说的话基本不记得了,只记得一件事。那一年我写过一封信,表达进入师门的热望。先生这时拿了一张信纸对我说,你做了我的学生,不能让人家说连信纸都不知道怎么叠。先生亲手为我演示,要把抬头露出来,三折,再对折一小半,对折的小半向着抬头方位,象征自己向收信人躬身作礼。
读博三年是我最快乐的三年,专心向学,精力旺盛,对未来有各种憧憬。研究生院条件很好,每名博士生有一间单独的宿舍,同学们住宿在此,读书写作在此,年纪大的同学带了子女进京上小学也住在此。图书馆也很好,书很精,可以进书库随意借阅,特别是校风很宽容,每天下午呐喊一个小时的摇滚从来无人侧目。每个月至少有一次,我和同班的田澍师兄会乘公交到王府井北大街。那时没有手机,我们受经济条件所限也很少打电话,但是几乎每次去,先生都如约安坐在那里。先生给我们上课没有教材,多数情况下也没有事先设定的主题,往往是先生轻松自如地给我们讲着,不疾不徐,不知不觉换了一个话题,依然环环相扣,继续娓娓道来。其间,好像很少有人来打断,或者被先生桌上的电话分心,亦不会有人来叫开会。
还有一部分时间,我们会去先生家里,有时是听先生授业,有时就是去家里看看,其中一次是师母做白内障手术前去看望,还有一次是先生家换阳台窗户,我帮着照管一天。先生说过,他所向往的是旧式的师徒关系,什么事学生都帮着干,一点点也就通过研墨学会了书法,通过挨打学会了唱戏。十卷本《中国通史》1994年重印时,他让我们帮着整理过插图,核对过《中国通史》两种版本的异同。
1996年毕业参加工作,包括2004年进藏之后,我每年都会求见先生,先生有请必应,每次都会谈到我以不打扰先生用餐和休息为缘由主动告辞。先生多年来的谈话我做过一点记录,这里想先说一个总的印象。先生从来是平静的,没有动过任何肝火。先生在谈话中自然有评论臧否,但总是点到为止。先生有很多很多学术界的朋友,但他几乎从来不谈自己的交游,更不会谈自己的个人经历。先生往往谈的都是学问,滔滔不绝,不知不觉中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后来我发现一个秘密,先生当时谈的部分内容,之后往往会成为一篇论文的精华,但是他讲的时候绝不过于精专以致深奥难懂。当然,先生治的是中国通史,谈论的话题自然比较广泛,但是,先生不会说斗酒养狗的事情。
1993年9月6日,我们入学第一周的一个晚上,由修晓波师兄领着,田澍师兄和我第一次去先生家,坐了一个半小时。先生主要谈了几个问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個缺陷,是在整体把握与具体技术之间缺少分门别类的系统论述。希望我们注意不仅吸收现行教育中的西方思想,也从东方传统著作中寻求思维方式上的启迪。注意其他学科,把知识面拓得更宽。不局限于一个朝代,通贯地考虑问题。第一年什么书都可以读,读诗可以学习如何用最精炼的词句表达思想,读散文学习抒情说理,读小说可以学习把复杂的事件、过程明白地叙述,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断代史的研究倾向是在抗战中形成的,解放后沿袭下来,积久生弊。
不过,到1994年1月17日,先生已三次催我读专业书了,3月希望我极早定下论文选题。选题的确定有一个过程,先生开始说,可以突破断代,比如做纵贯元明清的专题,经过反复比选,到11月1日定下元代道观这个范围。1995年4月24日,先生和我商讨了论文大纲,改题为《金元时期全真教宫观研究》。随后的时间里,先生一章一章地审读我的论文初稿,特别是针对我的缺点,要求增加论述和分析,删节史料,注意行文的生动,写好最后一章结论。1996年5月7日,先生又提示我写作思路,指导我将结论重写。直到5月23日,我的《金元时期全真道宫观研究》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先生不仅教我们做学问,也关心我们的生活。读博的时候,我们似乎都很能吃,可王府井北大街上就没什么我们吃得起的东西,记得我和师兄第一次到所里上完课,出了东厂胡同,往南向长安街方向,沿街扫了一个来回,只找到一家拉面馆,一份大碗加一个卤蛋8元,吃得饱且能承受。先生很体谅我们,时不时地会请我们吃饭,跟着先生,我第一次吃了萃华楼的烤鸭,还吃了好几次翠花胡同悦宾饭馆,先生介绍这是改革开放后全北京第一家私人餐馆。国家对我们那一代研究生很好,读书不但不用交学费,还会发钱,我们这种没有工龄的博士生,大概是每月210多元。不过那几年物价涨得凶,津贴总不够用,我虽然打工挣外快,有时还得仰赖父母的补贴。先生几乎从来不提钱的事,有一次对我们说,《中国通史》要重印,他让修晓波师兄和我各做一册的索引附在书末。做完后,我们各得了一笔酬劳。我一直觉得,三天就能做完的索引即使需要做,也不是非得找我们做,先生就是为了变相补助我们,还让我们的名字印在了通史上。
先生和师母一直相互扶持,他俩是南开大学本科同班同学。一次师母在协和做摘除白内障、人工晶体植入的手术,我们在刘小萌大师兄带领下去探视,看病床上方的床头卡才知道,师母比先生年长七岁。师母很瘦小,每次去先生家,总是热情地给我们倒茶续水,过年的时候,还会让我们吃各种零食,然后坐在旁边听先生和我们交谈,偶尔会谈到她所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事情。本世纪初,师母患上阿尔茨海默症,我和曾艳一次带着女儿子玉去拜年,师母问了子玉六七次“你叫什么名字?”先生对我说,他彼时就不再出京参加学术会议了,因为要给师母做饭。2012年,师母离世,因为所在单位事务多无法请假,我在几个月后出差进京时,才到先生家吊唁。师母的遗像安放在他们的卧室,连同上次师母卧病,我进来探望,这是第二次进先生的卧室。我跪下来给师母磕了三个头,表达心中的歉意,见我这样虔诚,先生的眼眶也湿润了。退回客厅,先生递给我几本书,用红绸带扎着。我轻轻打开来看,不禁大吃一惊,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历史》初中教材四册,上世纪八十年代不仅我用过,当时上千万的孩子都学过,第三册的唯一编者赫然就是胡文彦——我的师母,师母还参与了第一册的编写……2015年,曾艳转给我一条新闻,先生向母校南开大学捐出平生一百万积蓄,以师母的名义设立“胡文彦助学金”,专门资助家境贫寒、学习刻苦、成绩优良的女生。
先生离开南开,入了北大,曾与罗常培先生合著《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决定先生人生的,则是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革”后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作为范文澜先生的助手参与写作《中国通史》。范老1969年逝世后,他更挑起重担,再战39年,从第五册起,一直主持续修到第十二册,使之成为贯通整个中国史前史、封建王朝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巨著。这时,广大读者仍然迫切希望有一本文字流畅、叙事完整,能从治国安邦、为人处世两个方面提供借鉴的简明通史。先生又在81岁的时候,毅然命笔,以3年之功,著成《中华史纲》。这本书虽仅30万字,却讲述了从原始人类在中国国土上活动直至清朝覆亡的漫长历史,可以满足各行各业朋友用不多时间浏览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概况的普遍愿望。
做先生学生27年,我从未听先生说过自矜的话。先生坚持不上主席台、不给别人写序、不做空头主编、不申请课题、不参加评奖,就是为了集中精力坐冷板凳,以独立思考、埋头苦干、不急于求功的精神,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学术事业,努力写出好看的中国通史。在西藏昌都地区工作的时候我去给先生拜年,带了一盒茶叶,先生说,下次不要再拿东西了,他现在一钱不取,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的几本书,都不取分文稿酬。2012年《中华史纲》出版,先生对我说,他婉言谢绝了别人作序的意思,自己写了一篇150字的前言。2020年5月7日,我到家中看望蔡先生,见先生瘦了一圈,我赶紧请教原因,先生说疫情期间无法再让小时工李桂根师傅到楼下餐厅买吃的,经常靠速冻饺子、元宵度日,所以瘦了十多斤。听说我调到西藏社科院工作,他对我说,学术研究致力于破解疑难、探索未知,做学问的人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不要求升迁,不要求褒扬。
做先生学生27年,我也从未听先生说过抱怨的话。今年1月14日凌晨2时先生在京逝世,3天守丧中我写了《先生的身教》初稿。3月2日,田澍師兄将他写的怀念先生文章发给我,之后不断修改完善,使我很受教育。这次追思会很庄重,很多老师和师兄辈的学者来参加,更让我感动。为了修改本文,我特意把读博3年每日所记中有关先生教诲的内容整理到电脑里,涉55日,共5000字。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所在的通史研究室在1994年前后非常艰难,面临解体的危险,他和我们谈的续编四卷、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计划,不知何故仅实现了一半。去年12月,我读到蔡先生写的《回忆范老论学四则》,其中总结:“范老逝世后,我们一些参加过通史工作的同志,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担负起中国通史未完成的编写工作。这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范老在时,已是困难重重。没有了范老,小组所面临的困难之严重,是不言而喻了。理论能力和常识的多方面的不足,是主观上一时难以弥补的缺陷。外界的干扰,也不时而来,编写工作几度难以为继。但是,每当我们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一想起范老是怎样坚持工作,一想起范老谆谆告诫我们的‘坚’字,就不觉增添了力量,重又振奋起精神。”(陈启能主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史学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87页)我由此体会,我们读博士期间,其实是先生牵头著述通史又一段困难的光景。但是我在当时是丝毫没有察觉的,不觉得先生的颜色有一点变化。
做先生的学生时间长了,我慢慢悟出来,先生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怎样做人,因为他全是用身教。这让我想起赵一曼烈士在就义前写给儿子的信里说:“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先生是我最敬佩的一位共产党员,先生虽然离开了,但是先生给我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一直是激励我不懦弱、不懈怠的不竭动力。
责任编辑:赵超
——写给我们亲爱的师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