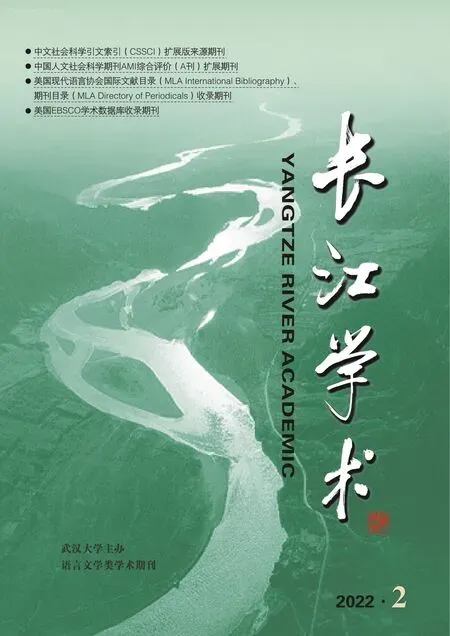现代悼亡诗中的智性抒情
——以臧棣《写给儿子的哀歌》为例
萧映 胡冰涛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悼亡诗的古今之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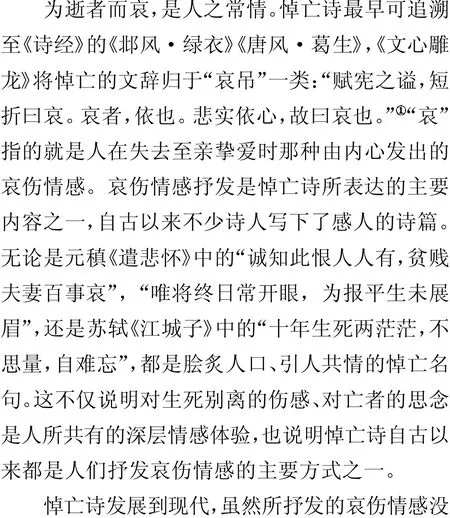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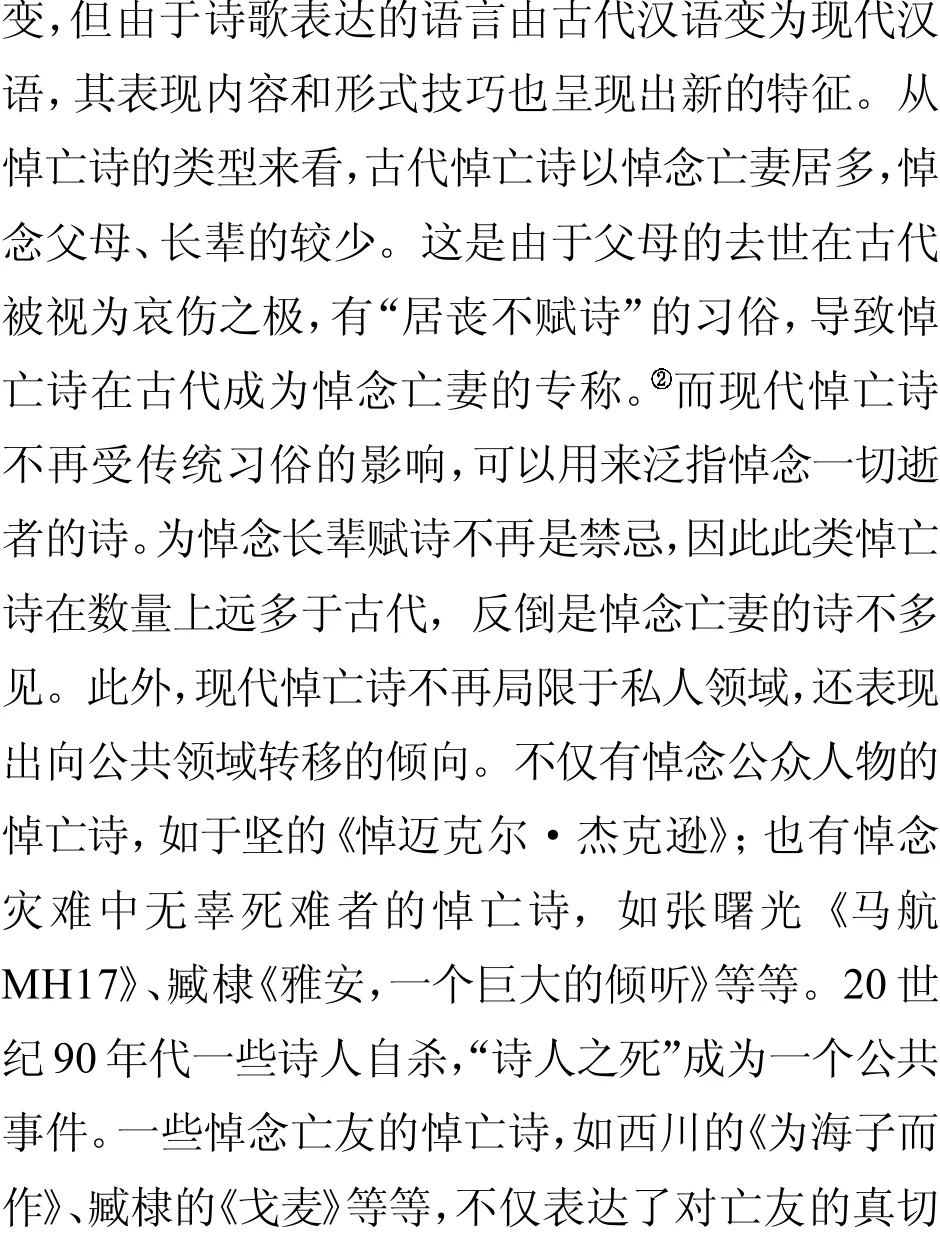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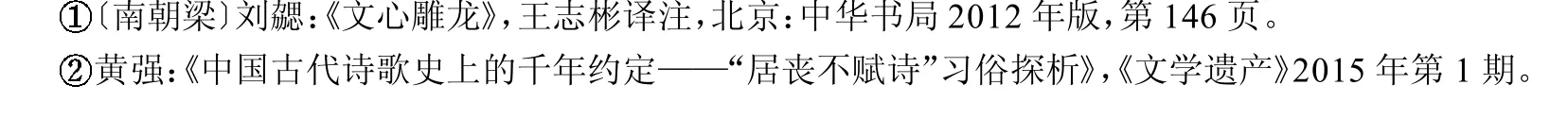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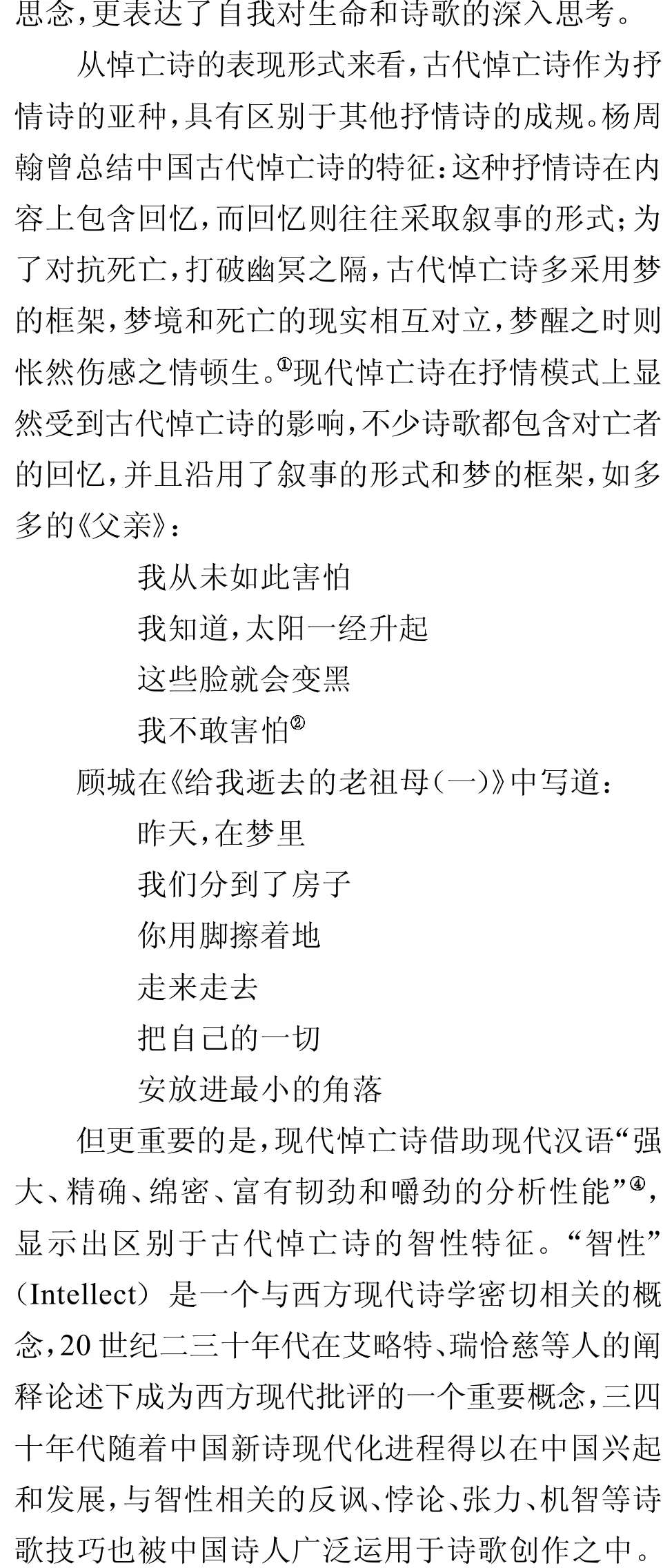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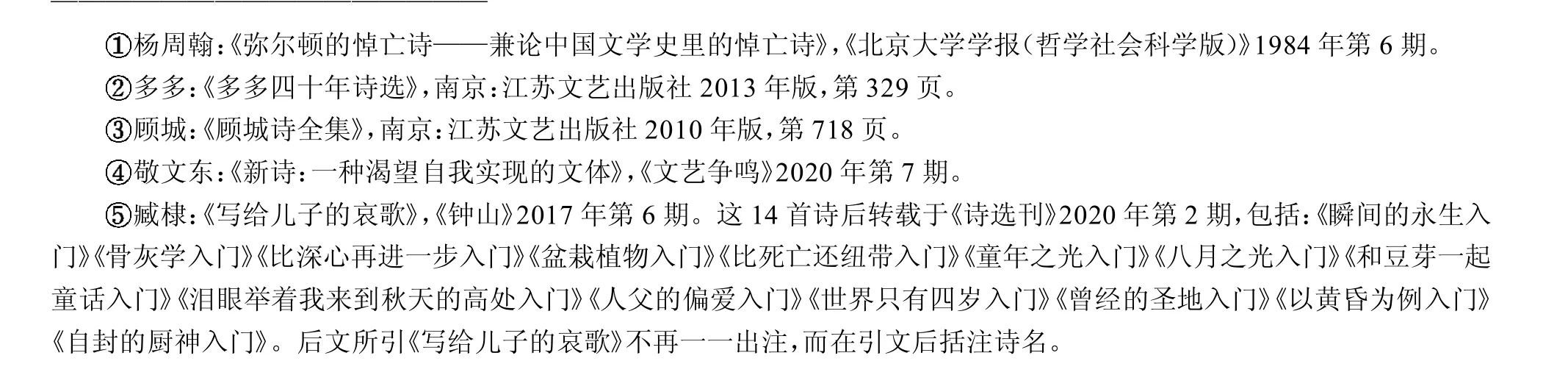
二、“情事交融”的叙事性技巧
对于现代悼亡诗来说,叙事同样是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但相比古代悼亡诗,现代悼亡诗并不依赖单一的叙事框架。特别是在20 世纪90 年代,面对开放的世俗世界和复杂化的经验,叙事性功能被诗人们大大开发,用以处理诗歌和现实的复杂关系。在现代悼亡诗中,叙事是平衡诗中智性与情感的主要手段,诗人通过场景、视角的变化以及人物刻画等叙事技巧来建构回忆中的日常生活,以此反衬死亡的残酷。
首先,现代悼亡诗的场景叙述多采用简明的处理办法,诗往往在开头就将空间和时间定格。《写给儿子的哀歌》中的场景叙述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直接点明事件发生的地点,如《盆栽植物入门》的第一句——“宜家的付款台前”,仅用一句便将一个极其生活化的场景拉至读者眼前,用准确的地点和方位给予场景实在感。二是将场景隐含在叙述之中。同样是生活场景,《和豆芽一起童话入门》的开头则是“小小的仪式里,一百粒黄豆/ 已在你的胖手指点拨下/列队完毕,等候在发芽中/找到新的捷径”,这里虽未直言,但显然是一个关于发豆芽的日常生活场景。而《骨灰学入门》中,叙述则发生于“炉膛的门打开时”,“炉膛的门”作为场景中的一部分替代了整体的场景,既具体又带有死亡隐喻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臧棣还多用自然景物作为叙述的背景。比如:
堤岸上,八月之光
轻轻抚摸着芦苇的耐心。
河面墨绿,穿梭的紫燕
如同从倾斜的天平上坠落的砝码
(《八月之光入门》)
平原尽头,这九月的黎明
犹如一面半旗,平坦在
稠密的鸟鸣里
(《泪眼举着我来到秋天的高处入门》)
艰难的拂晓,麻雀的喧哗
敲碎了黑夜的玻璃后门
(《人父的偏爱入门》)
隔着芦苇,两只白鹭
沿河道中央,由北向南,
结伴飞向它们的秘密家园
(《以黄昏为例入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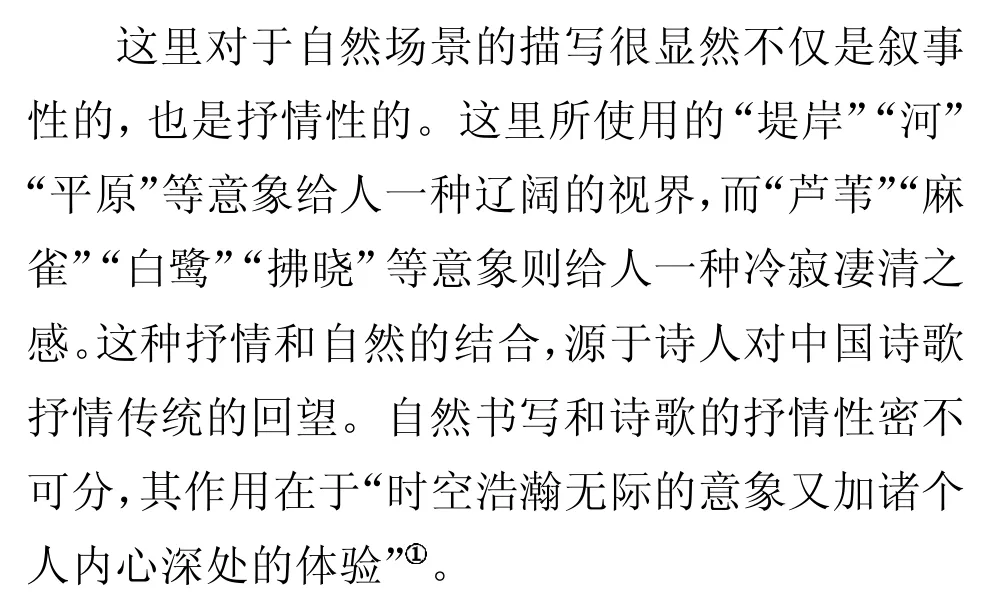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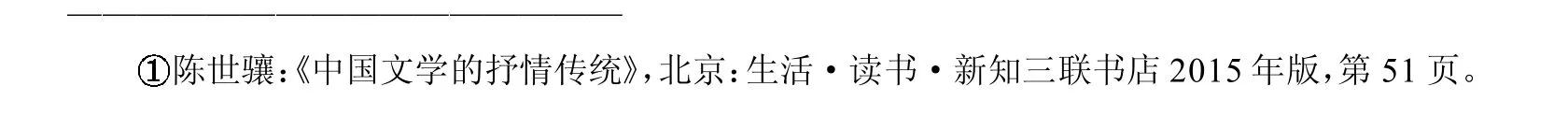
其次,从叙事视角来说,现代悼亡诗不拘于单一的叙事视角。《写给儿子的哀歌》叙事视角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来回切换,将主观感受和客观叙述结合起来,达到抒情和叙事之间的平衡。第一人称“我”在诗中有两个功能。一是真实还原父子的日常生活。比如,《和豆芽一起童话入门》中,在发豆芽的过程中“我”和“你”彼此互动,使叙述具有自然亲切之感。二是通过第一人称直抒胸臆,表达主观感受,如:
……我不祈求
父亲的思念会感动任何奇迹,
我只祈愿我对你的爱
永远都不会在时间的慰藉中
低于我对你的承诺
(《人父的偏爱入门》)
……我的怀抱里
仍有无形的沉重,它令无名的悲哀
具体到我甚至比上帝还愤怒
(《泪眼举着我来到秋天的高处入门》)
而在用第三人称叙述的时候,诗人常用“父亲”这一称谓,以此拉开和叙述对象之间的距离。特别是当面对死亡,作为父亲的诗人则常常被置于一个观看的视角:
最后的目击者不该轮到
父亲……就在离我
不到十米远的地方,而且还
隔着透明的大玻璃
(《童年之光入门》)
“玻璃”透明的性质可以使人看见,却又是一种隔断,“不到十米远”却是生与死的距离。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中,“我”也成为被描述、观看的对象,这不仅使叙述客观、场景切换,更显现出“我”面对死亡的无力感和现实的冰冷残酷。诗人的声音也随着叙述视角的变化发生改变,使冷静的叙述和感性的抒情在诗中相互渗透、交织。
最后,从诗中人物形象的刻画来看。诗人主要通过引述孩子的话语和准确的语言修辞勾画出孩子的形象。如在《盆栽植物入门》中,叙述了父子围绕“盆栽植物”的一场对话:
……你会记得
每周给它浇两次水吗?
“会的”。但标准答案应该是,
“我保证”。其实在内心深处,
我有点惭愧,我不该这么早
就让你提前熟悉承诺的语气。
“我还知道它叫瓜栗,原产墨西哥”。
这里,孩子的话语被直接置于诗中,显示出独属于孩子的单纯和天真。面对“盆栽植物”,父亲和孩子的话语显示出父子眼中的两个世界:一个是重视教育和承诺的成人世界,一个是简单快乐的童真世界。但相比之下,更能凸显臧棣风格特点的是,通过简洁精确的语言刻画人物形象。在死亡降临之前,孩子原本的生命状态是:
瘦瘦的,但精力却充沛到
由海浪点燃的东西
连海浪本身都已认不出来。
挥舞着,小小的生命旗帜
在蔚蓝的海风中难得一闪而现;
更清晰的,欢快的叫喊润色着
沙滩上的雀跃,直至童年之光
看上去,比生命之光还耀眼。
(《童年之光入门》)
“由海浪点燃的东西”“小小的生命旗帜”“欢快的叫喊”“沙滩上的雀跃”用一组名词性短语隐喻孩子的生命,诗人用动词“点燃”“挥舞”作定语,或以“叫喊”“雀跃”等词为中心语,使这些表现生命的意象带有明显的生机和活力。“由海浪点燃”并不符合语言的一般搭配,“海浪”让人联想到“海风”,而能被“点燃”的通常是“火焰”,这些隐现的意象让人联想到“海风”的吹拂、“火焰”摇曳的色彩与温度,以及“海浪”涌上岸边的声响。在视觉、听觉、触觉上的多方面效果使这些生命意象更添张力。而在死亡的笼罩下,孩子变化了形态:
等待冷却的骸骨仿佛还需要
一万年才能彻底冷却;
……传送带上,
除了有一个年轻的形状
酷似生命的浮雕之外,
炼狱里仿佛再也没有
别的东西,值得你试探一下。
世界太沉重,借着陌生的,
拿着扫帚的手,你留下
最轻的你
(《骨灰学入门》)
诗中“冷却的骸骨”“年轻的形状”“酷似生命的浮雕”“最轻的你”描述死亡状态下的孩子,“冷却”“骸骨”“形状”“浮雕”等词都带有冷感,且不再具有动态特征。在动与静、热与冷、喧闹与寂静的对比下,把回忆和现实、生与死分隔为两个世界。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无论是场景、视角的变化,还是人物的刻画,诗人通过叙事呈现出父子的日常回忆和死亡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诗中多样的叙事手法固然能体现诗歌的智性,但单纯的叙事只能呈现现实的表面,更大的挑战在于如何深入现实内部,将众多的事物联系起来以构成一个更大的“世界”。
三、客观对应物及其象征性
作为现代主义诗歌先驱的英国诗人艾略特,曾对诗人与诗歌的创造关系做过一个著名的比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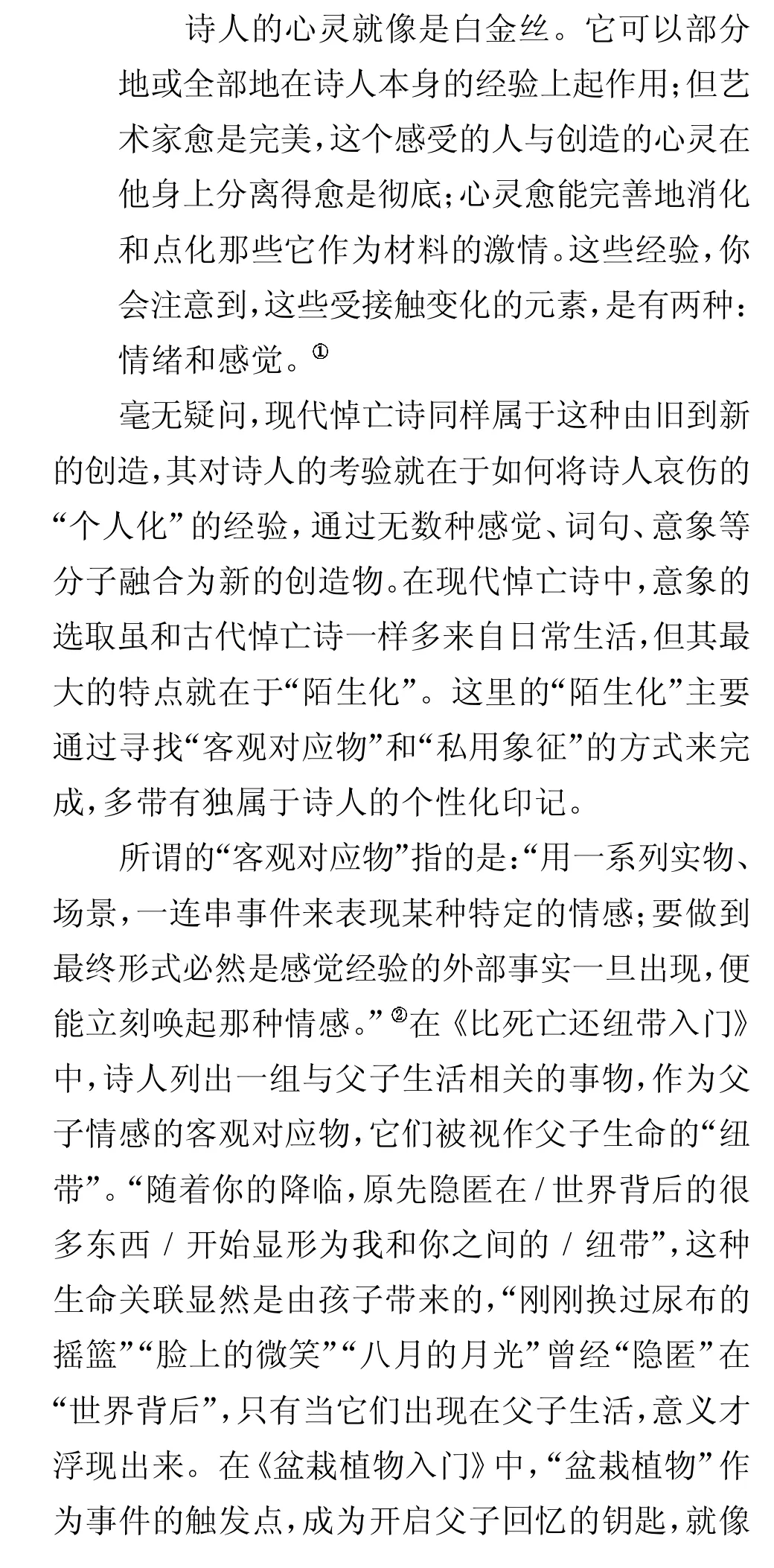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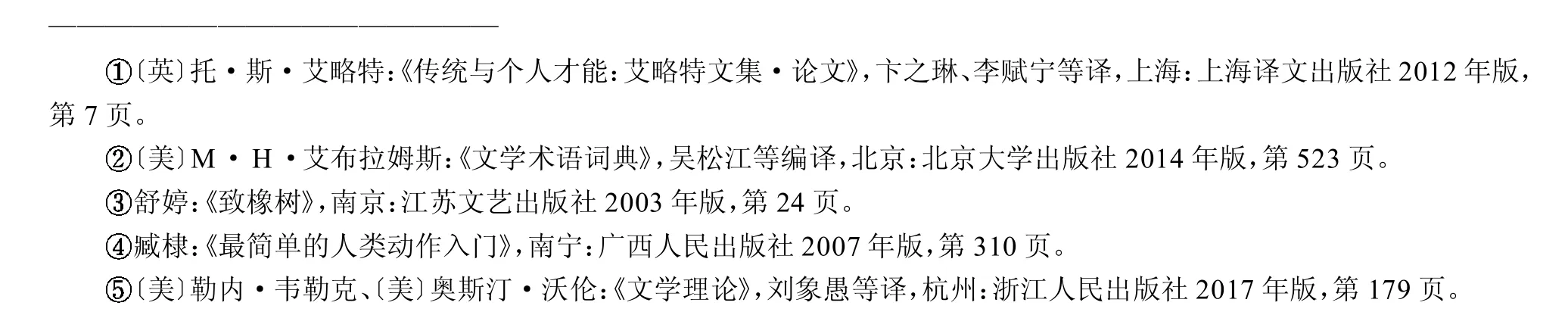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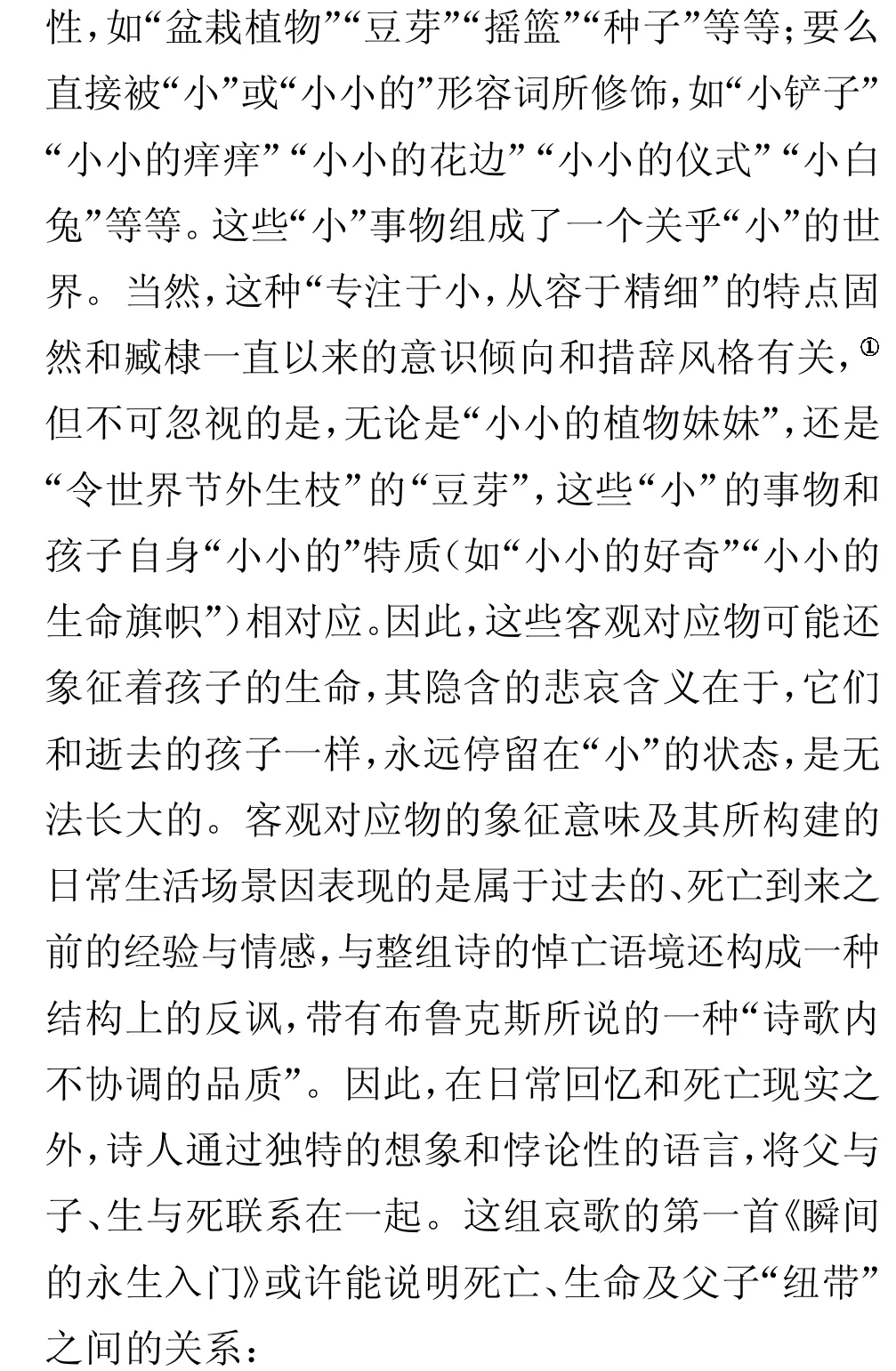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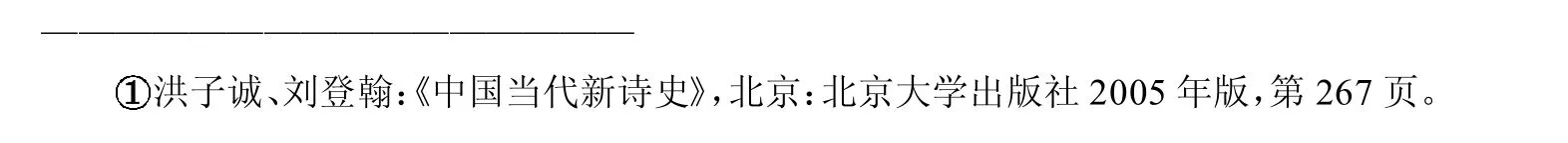
……感谢时间的洞穴
抵抗住了时间的变形,
依然幽深在生命的秘密中;
蒲公英、马齿苋、月亮草,
葡萄藤和山楂树的阴影
维持着洞口的秩序——
我从这边进去,黑暗是黑暗的方向
就好像丧失在沉重中
黑暗也是黑暗的仁慈;
你从那边进来,那渐渐缩短的,
我永远都不会称之为距离;
就好像隔着生死,我和你
因这比黑暗还要固执的摸索,
依然能组成一个怀抱——
仿佛再用力一点,瞬间的永生
就会屈从于我手中是否正握着
你曾用过的一把小铲子。
(《瞬间的永生入门》)
从诗题来看,“瞬间的永生”是个悖论性的短语,“瞬间”和“永生”所表示的时间长度几乎是两个极端,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诗人在诗中建构出一个超验性的生命空间——“时间的洞穴”。“时间的洞穴”可以看作一个既包含个人经验记忆,又包含集体知识性记忆的空间,它在时间上具有凝固性,因此可以抵抗“时间的变形”;并且“幽深在生命的秘密中”,“蒲公英”“马齿苋”“月亮草”“葡萄藤”“山楂树”等意象增加了生命的神秘色彩。父子被“死亡”分开,又在“时间的洞穴”中走向彼此。“黑暗”的意义在句子间游移,转变为“黑暗的方向”和“黑暗的仁慈”。而“瞬间的永生”最终能否实现,取决于“我手中是否正握着/你曾用过的一把小铲子”。这里的“小铲子”既是象征父子生命关联的客观对应物之一,其背后暗藏的父子间的回忆,也是“时间的洞穴”的组成部分,它和其他客观对应物一起填满了生与死的裂隙,穿越过去和现在,将生与死统一起来,使生命更加完满而充实。除了这首诗以外,组诗中的其他诗篇也有很多直接表现父子生命关联的句子,如“我成长在你的成长中;/你天真在我的天真中”(《曾经的圣地入门》),“而我们俩仿佛有相同的困惑,/ 我们困惑于我们可以互为玩具”(《世界只有四岁入门》)等等,都表达了父子生命融合的意味,他们一同体验、遭遇的世间万物既是父子情感、回忆的“纽带”,也是独具诗意的象征。
由此,诗人通过客观对应物和“私设象征”的方式将父子生命与万物联系起来,通过诗歌介入现实,重新建立起对世界的自我经验。
四、对生命与自我的哲理性反思
悼亡诗是为逝去的生命而作,因此无论古今,悼亡诗多包含对生命感受的表达,带有一种沉思冥想的特质。而现代悼亡诗不仅反思个体的生命经验,还常常将自我的生命感受和更广大的现实结合起来,由是从私人领域的抒情诗扩大到现实中的公共领域。
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人物,臧棣一直致力于通过诗歌反映现实,并由此构建一个独特的经验世界。“入门”系列作为臧棣创作的第三个系列诗,从创作意图上,和之前的“协会”系列、“丛书”系列有着某种承接关系——都是以一种独特的命名方式,把那些看起来细小却又数量庞大的事物联系起来。“入门”系列的“入门”一词很容易让人将其与某种教程类书籍相联系,似乎带着某种程式化的气息。但所关注的事物又是如此细微,它把人对世界的认知放在“入门”学习阶段,其实也是以谦卑的姿态承认人类的无知。这些琐碎事物的小,和其数量上的庞大形成一种反讽效果,使这种命名方式颇有启示性。作为“入门”系列的一部分,《写给儿子的哀歌》的创作延续了臧棣系列诗的创作理念,使原本极具私人性的悼亡诗没有停留于个人情感的抒发,而是通过死亡对自我和现实进行了哲理性的批判和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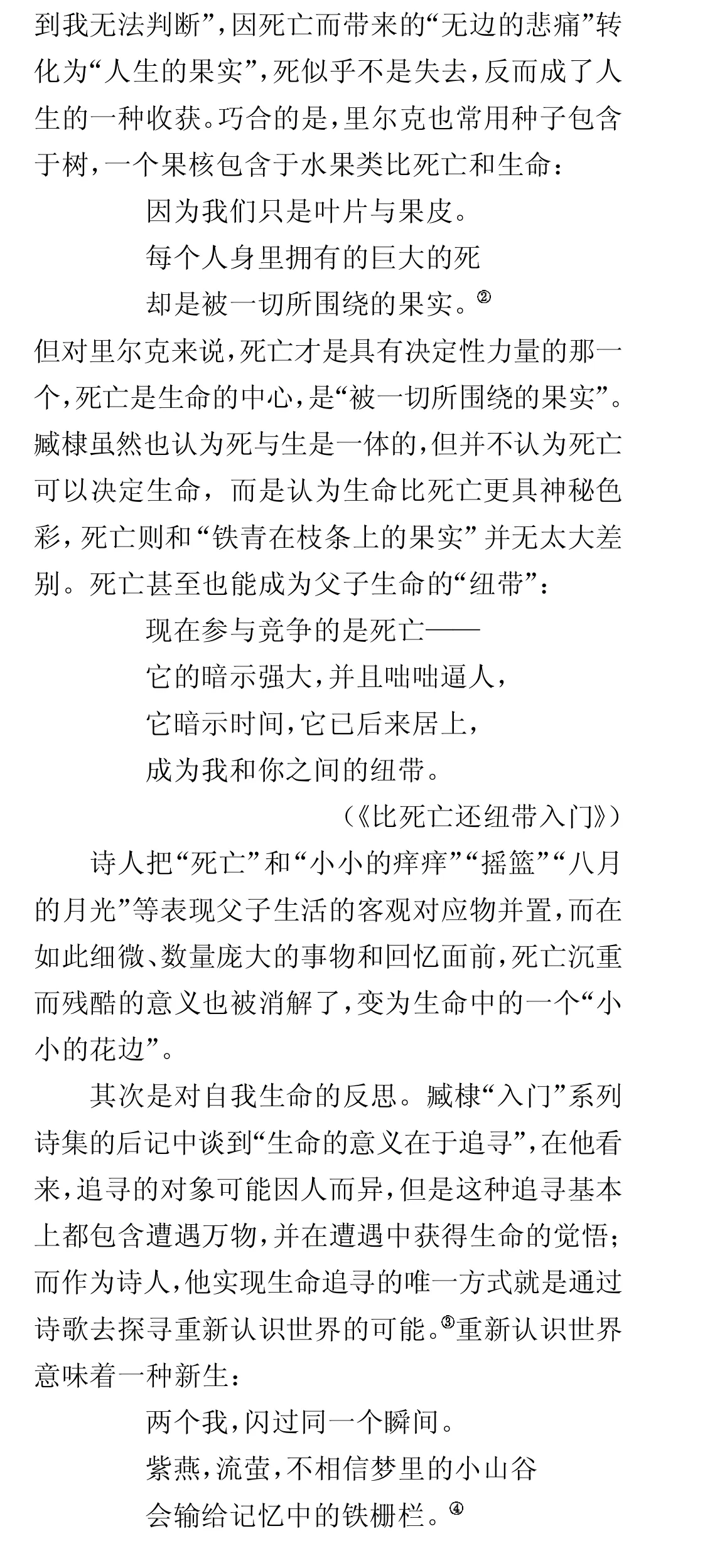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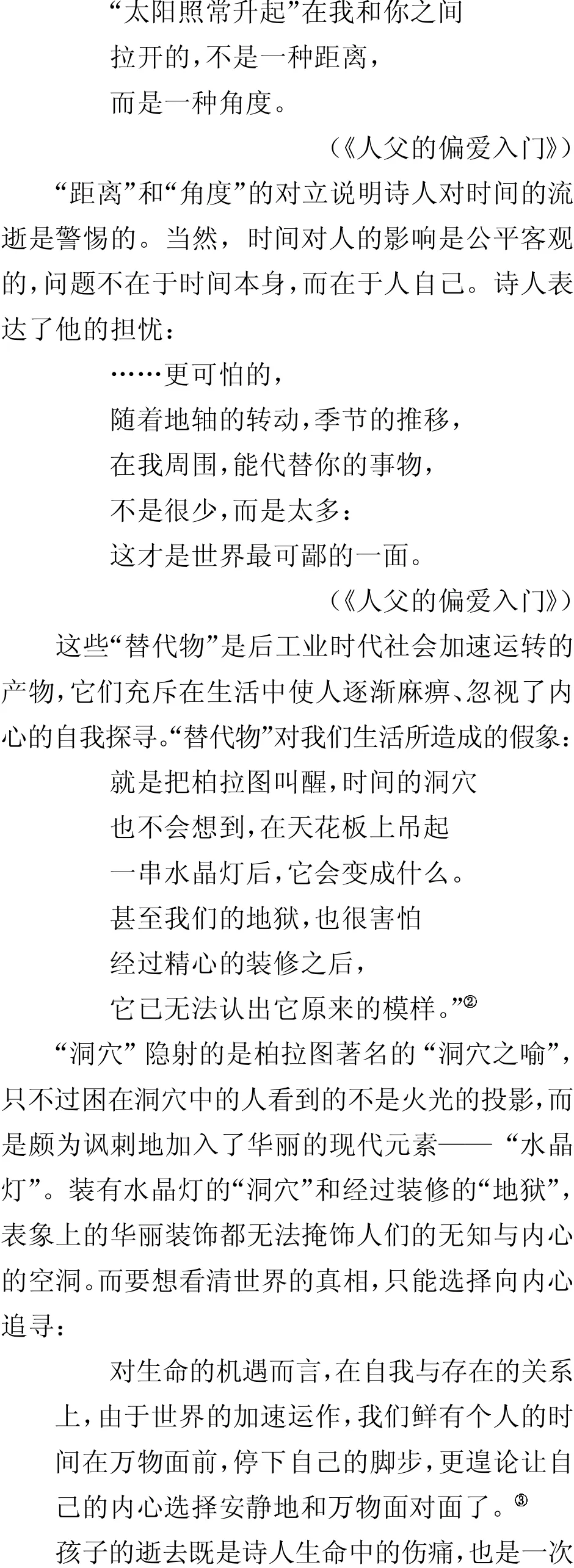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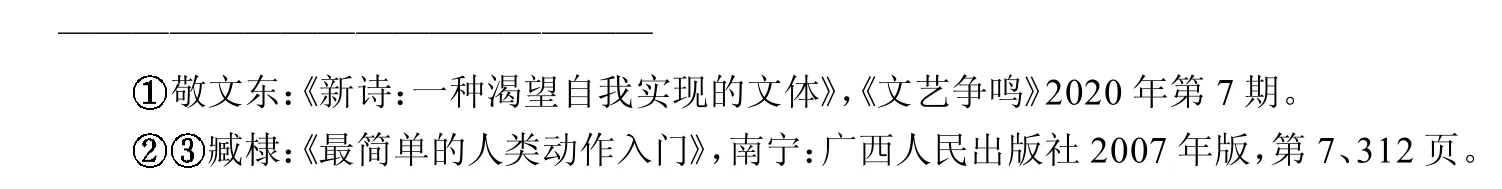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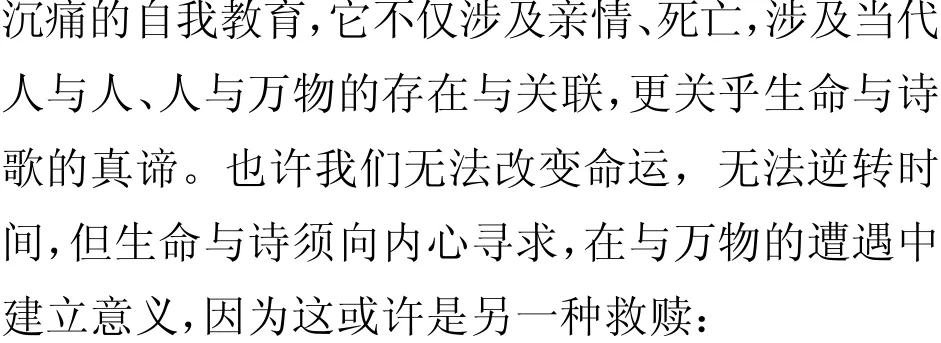
让我的安静
成为我们的见证吧。盛大的秋天
让午后的平原看上去
像一个刚刚磨完时间的种子的磨盘。
(《自封的厨神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