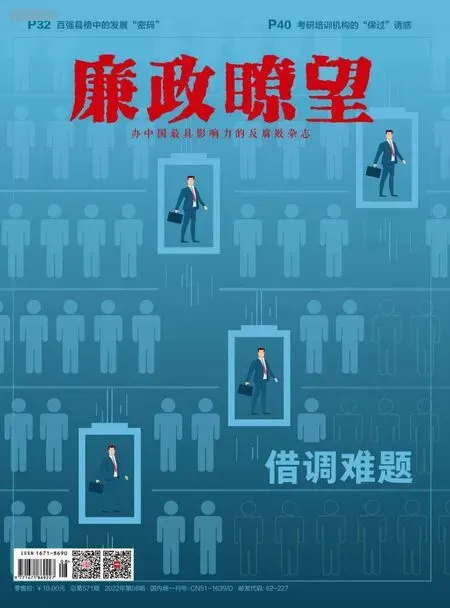追忆黄蜀芹:敢拍《围城》,尽情绽放
│文 本刊全媒体记者 李浩瑄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很多人以为这句话出自钱钟书小说《围城》,事实上,这是杨绛写在黄蜀芹导演的电视剧《围城》片头的话。
1990 年,还在骨折休养期的黄蜀芹坐在轮椅上完成了电视连续剧《围城》的导演工作。当年11月,《围城》在央视播出,以庆祝钱钟书先生80寿辰,一时万人空巷。
2022 年4月21日,83岁的黄蜀芹与世长辞。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和女性电影的代表人物,黄蜀芹留下《人·鬼·情》《青春万岁》《画魂》《围城》《孽债》等多部经典影视作品。她对女性的卓越想象和深刻探求,以及其作品现实世界与虚幻世界相交叉的表现手法,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奠定了她在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取代的地位。
“已经浪费了很长时间”
1939 年9 月9 日,黄蜀芹出生在天津祖父母家的老宅,取名“蜀芹”——“蜀”意为母亲在四川怀孕,“芹”取其祖母名,以示纪念。
作为戏剧艺术家黄佐临和金韵之的长女,黄蜀芹和电影的缘分早就定下了。黄蜀芹8岁时在桑弧导演、张爱玲编剧的《不了情》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男主角的小女儿,当时的大明星刘琼和陈燕燕是她在片中的父母。
黄蜀芹当时出演这个角色,其实是被大人们用好吃的“骗”去的,那次“触电”经历并没有让她走上演员道路。
上高中时,黄蜀芹喜欢上了苏联电影,到了十分着迷的程度。每个礼拜天,她都会骑着自行车到衡山电影院看电影。
考电影学院成了黄蜀芹少女时期的梦想,不巧,她高中毕业那年北京电影学院不招生。恰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刚刚开始,她就下乡劳动去了。两年后,20岁的黄蜀芹如愿考进了北电导演系。
在北电求学5年,黄蜀芹认为最大的收获不是拍电影的方式方法,而是接触到了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电影,感受到与国内截然不同的艺术精神和文化内涵。
1964年,黄蜀芹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文革”期间,黄蜀芹被迫远离电影事业,直到1978年才回到上影厂。
在这年,我国第三代导演的代表谢晋执导电影《啊!摇篮》,黄蜀芹到这个剧组做副导演,这时的她已年近四十。
“我终生感谢他,对我来说他就是救星。”黄蜀芹十分珍惜谢晋给她的这次机会,即使让她在剧组里干管驴的工作。
“我牵着驴子站位置,但是驴有时不听话,我就替驴站位,给掌机的人看,没问题了我们再把驴牵过来。”在此过程中,黄蜀芹不多言语,只是静静观察,终于完整了解了一部电影的生产过程。
1980年,黄蜀芹再次和谢晋合作,拍摄《天云山传奇》,这次她做了第一副导演。拍完后,谢晋宣布“黄蜀芹毕业”,可以独立拍片了。
第二年,黄蜀芹拍摄个人电影处女作《当代人》,这是部“命题作文”。
<1),且各件产品是否为不合格品相互独立.
“潇湘厂人手不够,来找上影厂借人。一线导演不能去,我作为能独立拍摄的新生力量,正适合去帮兄弟厂解决困难。”黄蜀芹曾回忆道,拍这戏的时候是大热天,在广西柳州,她晕倒过3次。“那时候只要有戏拍就好,管他什么呢。已经浪费了很长时间,不想再浪费了。”
用电影表达女性意识
改革开放后,“双百”方针重新提出,中国电影呈现出繁荣景象。
刚开始拍电影的黄蜀芹,基本都靠厂里分配任务。“不管是什么戏,哪怕是自己不太喜欢的,也要认真去拍,也要拍得一丝不苟。”黄蜀芹曾说,运气好有时候也能碰上她喜欢的题材,《青春万岁》就是其中之一。
这部根据王蒙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讲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初,一群不同思想性格、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子中学学生互相帮助、共同成长的故事。黄蜀芹有上女子中学的经历,对此体会更深。
不过,当时有不少人对这本小说持反对意见,认为将50年代描写得过于美好。黄蜀芹却认为,那时候的人就是那样,“很幼稚,傻傻的。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小丫头片子,爱疯爱玩,我想拍的是这种味道。”
也从那时候起,女性意识逐渐在黄蜀芹的作品中萌芽。1987年,黄蜀芹根据河北梆子演员裴艳玲的真实经历改编的电影《人·鬼·情》成了她的艺术巅峰之作。“一个女人画着大花脸,穿着厚底靴,在台上扮演男人,我觉得她太了不起了。”
受到父亲写意戏剧观的影响,黄蜀芹在影片中实写秋芸作为反串女演员的艰难经历,虚写秋芸的舞台表演,“一实一虚”两条叙事线彼此交织。
《人·鬼·情》是中国最早一批用女性意识和女性视角来呈现并探讨中国女性问题的作品。这也是黄蜀芹第一次与美术师丈夫郑长符合作,并听从其建议,将摄影棚全都蒙上黑丝绒,创造出特殊的视觉效果。无论从人物塑造,还是电影表现手法,或美学高度来看,《人·鬼·情》都在那个年代显得弥足珍贵。
黄蜀芹对女性艺术家命运的偏爱,还延续体现在她1993年拍摄的传记影片《画魂》中。
这部由黄蜀芹执导、张艺谋监制的强强联手之作,由于涉及女演员赤裸出镜,引发了不少争议。最后,这部电影被大篇幅删减后才顺利上映,黄蜀芹对最终呈现效果并不满意。后来,当人们重新审视《画魂》才发现,黄蜀芹大胆的镜头中仍是中国电影史上真挚且难得的女性表达。
“女性的观点,我自己从来没说出来过,但是我很明白,我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这个人,表达这个人。”黄蜀芹曾说。
老老实实为观众拍故事
作为导演,黄蜀芹并不高产,但她的作品大多都经得起时间考验。比起电影,观众或许对她执导的电视剧记忆更深。
1991年,《围城》在正式开播前,样片先在复旦大学文科楼试映,场面之火爆堪称传奇。钱钟书扎实的原著是剧本的坚实保障,黄蜀芹在拍摄中精益求精,也是这部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
“本来以为没人会看《围城》,刚开始拍的时候我很怕,这么学究气的东西怎么弄法?后来发现,只要老老实实把故事拍出来也不错。”黄蜀芹说。
事实也是如此,《围城》只有10集的戏,却拍了100天,平均10天才拍一集,称得上以电影的标准拍电视剧。
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喜欢看《围城》,一般观众更喜欢《孽债》。
《孽债》是根据作家叶辛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庭伦理剧,讲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插队云南西双版纳农村的上海知青返城后,他们留在西双版纳的孩子结伴搭乘火车到上海寻亲的故事。最后,5个来寻亲的孩子,4个失望地回到云南,一个入了狱。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城市知识青年大规模离开城市,到农村“插队落户”,很多人在当地结婚生子。1979年以后,知青开始返城时,国家还处在计划经济时代。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城市户口把关很严。知青返城只能落实个人户口,不能连带妻儿。叶辛塑造的返城知青,就是其中的代表。
黄蜀芹拍《孽债》的时候是1994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确立,上海市区许多老房子开拆,黄蜀芹感觉到时代大变革将要来临。她想通过影像留下上海过去百年间的生存环境、历史文化、城市文明。
“《孽债》为什么会受老百姓喜欢,因为那样的生存环境和大家的生活太接近了。”黄蜀芹用镜头真实记录了当年普通人局促的生活条件:7平方米的亭子间要住下全家老少、棚户区都没有拆迁、厨卫要跟邻居共用……
1995年,在沪上弄堂,《孽债》再次掀起了如同《渴望》放映时一般的全民观看热潮,创下了上海电视台42.62%的超高收视率。
黄蜀芹曾在访谈中说:“我不喜欢孤芳自赏,我很希望有观众。我愿意为每个层次的观众拍片。我希望给市民拍,也希望给知识分子拍,希望给有阅历的人拍,也希望给年轻人拍……”
遗憾的是,以黄蜀芹为代表之一的中国第四代导演是创作时间最短、承受压力最重的一代。当第四代导演起步的时候,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已经崭露头角。“我想如果给第四代导演们以同样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也许这一代人就会呈现出更多属于他们思考的力量。”黄蜀芹生前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