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嚎之夜
[哈萨克斯坦]欧热里汗·博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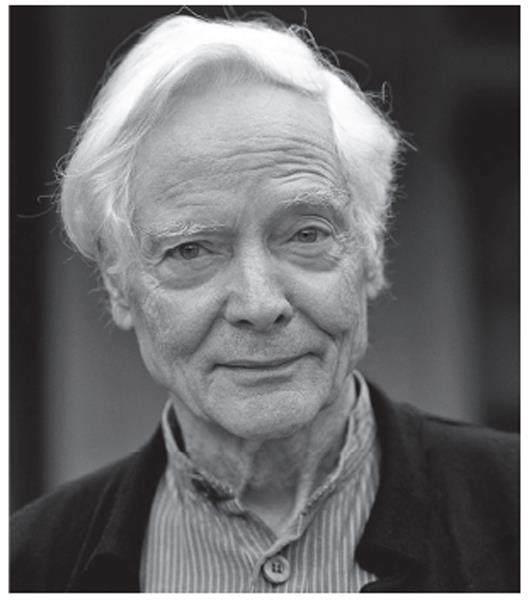
漫长漫长的冬夜……
每当这样的时刻,你总会想尽一切办法,想要逼出盈满身体每一个细胞的严寒。每当这样的时刻,总会想要大声地说出“去他的生活”。每当暮色四合,总会想到村庄里刚刚吃完一顿马马虎虎的晚餐,然后裹紧了被子即将入眠的乡亲们。冬季的日头越来越短,最后终于冷冰冰地凝结在了山顶。周围的一切都沐浴在银色的光下,仿佛裹上了白色棉被酣眠,与一年中的其他所有季节不同,与黑夜搏斗了许久,最终交融,然后一起进入了夜的殿宇。正当这时——原本漫长到似乎永远不会完结的夜,让一些许久未曾想起的思绪卷土重來,为心头绕上了一丝淡淡的莫名的愁绪。每当这时,你总会想要找出一切解解闷儿。
而牧人的生活则与此不同——就在一声声地呼唤着在冬牧场用蹄子刨食枯草的牲畜,将它们赶回圈里时,夜色已经悄悄地降临。然后,在饱饱地吃了一顿妻子准备好的饭食之后,那个牧羊人就享受地躺在火热的铁炉旁,开始读起了《阿拉》杂志。而那位在白雪蓝冰的野外举家搬迁的牧马人,则把脖子缩在驼衣里,在湿柴冒着青烟的火苗边,一边享受地吸着烟,一边陷入无边而沉重的思绪里。
村庄里的生活则是另一种——归置好了牲畜,清理好了院落,忙于屋外那些大大小小的事物,好一阵子都进不了屋。这时传来“快进来吃饭,都凉了”的抱怨,才不紧不慢地进屋。跟着一起进屋的,是一股股冷气,一直窜到了炕首。这时,那位乡亲一定会说:“把收音机的声音拧大一些,听听它今天说些什么。”说着,就脱下毡靴,让孩子去调收音机。拧收音机时,一定会有“吱呀吱呀”的像是撕破了喉咙的声音。对了,就在这时,这个家里刚刚读了十年级的女儿正穿上自己最好的那件衣服,描眉画眼地准备去看电影……刚刚落雪时就宰下的冬宰肉正在锅里煮着,端到餐布上时,火炉边的花猫也发出懒洋洋的喵喵的叫声,用力地伸展着身体。
那漫长的冬夜啊……
城市里则是另一幅景象。在这里,冬季的夜晚显得很短。急急忙忙地完成了工作,赶着去公交站。路上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夜里下的雪白天已经融化,这会儿变成了湿滑的泥泞,到处都是滑倒在地的人们。千呼万唤的公交车在夜色里终于呻吟着来了,奋力上车的人们相互推搡,相互拉扯,相互咒骂着都向着门里挤去。先是后门,然后是前门……用尽了全力,才能从前门挤进去半个肩膀。最开始,是骂人的司机,然后是嘟哝的妻子。等好不容易到了家,听到妻子生气地责问:“你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费尽了力气才回到家的人自然也难有好声气:“我忙着玩儿。”除了这句,似乎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你打开了电视机,电视机吱呀吱呀,只好静默地去关掉。而后,就悄然无语地翻身睡去。
就是这样一个漫长的冬夜,我将要出发。一开始,我并不想去。编辑一直请求我,我只好无奈地同意了。我们的领导是一个不会强迫员工干活儿的聪明、爽朗的人。虽然年轻,却早就顺利开启了仕途,早早提拔起来,让人觉得他很有前途。我接到命令后,就开始筹划起出发的事情。但要去的地方颇远,在哈萨克斯坦的东面,比阿拉木图冷十度,差不多到零下四十度,一定让当地的人不堪其扰。
州中心有汽车前往。不出所料,我正好赶上一月的严寒。一碰到汽车那冰冷的零件,手就好像要被剪断。我的衣服很单薄。对于还没成家立业,一两个月总要搬家一次的年轻记者来说,除了单薄的外套、没有护耳的人造革旧帽子、人造皮革手套和人造皮革制成的黑色公文包外,没有其他像样的财产。你会颤抖着在严寒中去往任何需要去的地方,奔波,奔波,赖以求生。然后年岁渐长,在这样的奔波中人到中年,就开始生病。年轻时什么都新鲜有趣,还感受不到。那些从脚底钻进的冷风总有一天会从额头冒出来……
我刚坐上汽车,人群就呼啦啦地上了车,似乎是我所要去的模范县的领导。他们穿着有五星领子的冬季大衣,有些人则穿着裁缝考究的短皮外套,头上戴着绒毛纤细的松鼠皮帽,脚上穿着雪白的毡靴,脸色红亮,散着热气,发出爽朗的大笑声。这样的时候,嫉妒会在人的身体里流窜,会希望自己并不是毕业于哈萨克国立大学,而是念完了兽医学院。但无论后悔,还是不后悔,你很快明白一切已成结局,只好全身心地发凉,继而蜷缩在座位上。汽车正要离开时,一个围着白色羊绒披肩的女孩走了上来。她拿出票来给调度员看了看,就坐在了我右边的空座位上。我心里暗暗有些高兴,觉得路上不会无聊了。
汽车发出轰隆的声响,总算要启动了。赶路的人们也窸窸窣窣地聊着天。寒气似乎更重了,口中的蒸汽在汽车里形成了雾气,窗上凝结了一层层霜。有些放了寒假、想要去探亲的学生把那些厚得像马掌钉的冰舔化,舔出一个眼睛大的洞来,从洞口往外看。编辑派我去出差时,我犹豫不决的原因之一是,明天就是新年。对于一期一会的新年,我原本可以和伙伴们一起度过,然后再出发。但想一想,我在城里还没有落下脚,也没有什么人邀请我。所以,想了想,还是决定即刻出发。在旅途上迎接新年,一定也是不一样的感受。
汽车启动,终于驶出时,我终于看了看身边的女孩。她很美,两边脸颊因为寒冷略微发红,她无声地坐着。她的衣服看起来也略有些单薄。稍微好一些的,似乎就是头上围的那条白色羊绒披肩,披肩衬得她的皮肤更加白皙。她总是低垂着眼睛,偶尔抬起睫毛,漂亮的双眸才会一闪而过。我想,她对于自己的美丽并不在意。她总是很温顺,似乎有无比沉重的心事。连身边的人,她似乎也注意不到。在这样的时候,贸然开口交谈,似乎也不太合适。
“窗边很冷吧?我们换个座位吧?”我说。她没有立即回答,像没听到似的看了我一会儿,才犹豫着开了口。
“谢谢,您的衣服比我的还要薄。”她说。
“但我毕竟是男人啊。”这是我想出的借口。但我这拙劣的玩笑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我们又陷入了无声的沉默。
天很冷。旅客都把头钻进衣领,像孵蛋的母鸡那样端坐着。只有那些穿着昂贵衣服的人泰然自若,似乎早就预料到了天气的寒冷,他们谈起今年冬天的寒冷,说起牲畜过冬的艰难,交谈的声音一开始略有些恼人。寒冷穿过我的人造革皮鞋,开始啃噬我的脚趾。我把两只脚敲击在一起,想要取暖。也许是感受到了我的窘迫,姑娘说:“你没有穿毡靴。”
她主动开口,倒让我有些高兴:“这该死的东西,我正好没有。”
“是什么?毡靴,还是钱?”
“两个都是。”
“您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吗?”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真的,我没分辨出来。她的表情没什么变化,淡淡地问道。
“怎么说呢……阿拉木图比较暖和……”
“嗯,明白。以后您要记住了,阿尔泰不是阿拉木图,还是很冷的。”
“当然,但这么冷的地方,也许不会再来。”
“大哥,生活的巧合,有时候自己是难以预料的。”
“你自己从哪儿来?”
“我也从阿拉木图来。”
“你在上学吗?”
“嗯。”
“在哪儿?”
“女子大学。”
“什么专业?”
“语言文学。”
“去哪儿?”
“奥尔侃村。”
“奥尔侃在哪个方向?”
“离诺沃斯特力卡不到五公里,在山里。”
“汽车会到奥尔侃吗?”
“司机说仅两公里的路,他不愿意浪费时间,会把我们放在路边。剩下的路,我们步行回去。您怎么问了这么多?”
“因为有缘做了旅伴,所以总想多了解一些。”
“那您是去诺沃斯特力卡?”
“对,我要写有关那个村庄的报道。我在报社工作。”
“我也猜到了,因为您问起问题来都单刀直入。诺沃斯特力卡值得一写。”她陷入了沉思。我不想打破她的深思,也不想刨根问底。我想起了编辑说过的话:“东哈萨克斯坦有一个诺沃斯特力卡的村庄,它城市化比较早,是整个哈萨克斯坦的文化和生活典型。为了表现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和农村建设的成绩,我们必须报道这个村庄。一家中央媒体已经写了一篇题为《哈萨克斯坦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文章。你要尽你所能,拍下文化宫、百货商店、房屋和餐馆,与工人会面,与当地的领导会谈,挖掘出深意来。”我没有感到惊讶,实际上像这样盖满了新型建筑的村庄现在一天比一天多。也许,城市和村庄的距离正在日渐减少……多么精彩而深刻的选题!因此,我将尽我所能,让农村建设的成果留在报纸的某一页。
冬季漫长的夜晚正在流逝,深夜降临了。目的地还很远,天气很冷,严寒肆虐。“看来会是一趟不愉快的旅行。”我在心里默默想。诺沃斯特力卡的那几位正打着鼾,进入了睡眠。女孩自顾自地盯着一处,还在无声的沉默之中。
汽车刚刚驶到山脚,风的脚步就越发近了。雪粒拍打在车身上,更加像狼在耳边嚎叫。风灌过早已老旧弯曲的窗户缝隙,好像那肆虐的风也在找寻着温暖的归宿。汽车时不时颠簸着,似乎想要摆脱这个大风肆虐、万物萧条的世界。人也被天气的寒冷所驱使,莫名地急躁,对什么都没有了兴趣。你会承认,世界上最舒服的事——莫过于呆在熊熊燃烧的烈火旁,并一千次地屈服于火焰的魔力。除了发动机的声音,耳边还传来外界的声音。我的眼睛被风吹过,仿佛看到风雪吹过的冰冷空旷的原野有一个赤着头、赤着脚的孤独的行人。有趣的是,那个孤独地踩着过膝的积雪的人——却好像是静静地坐在我身边的围着羊绒披肩的女孩。多么冷酷!我立刻清醒过来,转过头去看她。她把结了霜的窗户点化了一个小孔,正盯着外面。
“你在看什么?”
“我怕错过了下车的位置……”
“司机不会提醒吗?”
“有时也会开过头。”
“我提醒他一下。”我走到调度员旁边,提醒他到了奥尔侃一定停一下。
女孩温和地说:“谢谢您。您好像在想着什么大事。也许,是在想,文章要怎么开头,怎么结尾吗?”
“不,完全不是。我在……在想你。”
“而我也……”
“好有趣……”我心里一暖。
“是您……但也不是您……我该怎么解释呢?其实是像您这样总是旅行在外,总是坐着汽车或者骑着马的人。对了,我的父亲一直是游牧人,现在这个时间,他一定刚刚归置好牲畜,歇了歇脚,正准备喝晚茶。”
“他们在冬牧场吗?”
“是的,但冬牧场里村庄不远,紧挨着。”
“那你今天要去冬牧场吗?”
“要不去哪儿?”
“路上太可怕了,又是夜里,外面刮大风,又是寒冬。”
“哎,大哥,我对这里的自然环境都很熟悉,这条路我也走過无数次。我们这个奥尔侃村原先的名字叫狼谷,后来改了名字。虽然改了名字,但这么多年也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二十几户人家。奥尔侃是苏联的一个团旅,只有小学,中学要去您现在要去的诺沃斯特力卡。我也是在那里读完了高中。因为没有直达的汽车,我们只好搭来往的过路车,然后请司机把我们放在半路。然后步行去山里的家。我没必要瞒着您,尤其是冬天,太难了。而阿尔泰的冬天,又太长了,有什么办法?”
女孩叹了口气。然后,又靠近刚刚她用指头点化的小洞,擦了擦,朝着窗外望去。冻得发麻的膝盖和脚趾因为女孩的故事,已被我暂时遗忘,而现在又开始冷得发抖起来。车上的旅客都打着盹儿,看起来不太舒服的样子。除了汽车马达的声音,窗外风的吼声,还有刚才那几个人的鼾声外,周围悄然无声。
我默默地想:“都说世界如此奇妙,我看一点也不奇妙。平时也会这样坐上汽车去某个地方,有些人衣食无忧,有些人却饥寒交迫;有些人彻夜未眠,陷入折磨之中,有些人却呼呼大睡。总的来说,人生就是不断地羡慕别人的过程……而我身边这个乖巧得像绵羊的女孩呢?明天,有什么在等着她呢?她会幸福吗?如果没有幸福,她能找到吗?她在想什么?她有喜欢的男孩吗?她对我,是怎么想的呢?她会信任我吗?她叫什么名字?我们还会再见吗?……”
“大哥,您叫什么名字?”她突然问。
“努尔兰。你呢?”
“阿来。”
“很好的。”
“为什么很好?大哥。”
“你的名字很好……”
“我是在快天亮的时候出生的,所以父亲为我取名为阿来。我是在草原上来到这个世界的。”她的脸上有极美的笑容一闪而过。
我想:“人生真的很奇妙,昨天我还不知道这个城市里有一个叫阿来的女孩。而现在……连她的呼吸都近在耳畔,她的容颜也就在眼前。人和人总是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找到彼此,然后飞快地告别。总的来说,人生就是不断地找到和失去。也许就是这样……”
“读完了十年级以后,我在家给父亲帮了两年忙。”阿来用一种忧愁的眼神看着我,之前一闪而逝的笑容已经不见了,“我是家里最大的,剩下的八个孩子都还小。我想着不再念书了,父亲却一直劝我,‘我们的家族里也应该有一个老师’。父亲觉得愧对我。那天,他在信里说:‘今年的冬天很冷,女儿,豺狼野兽也多,放了新年的假,你跟老师请个假,回家一趟。我们都想你。’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
我想:“人生一点也不奇妙,像阿尔泰的冬天这样严酷,对有些人是彻骨的寒冷,对有厚衣服御寒的人却可能温暖如春。但不管怎样,我们不应该诅咒和悔恨。”
“您的话太少了。”阿来说,“您是想看看我说什么,还是就是这样沉默的性格?”
“我的性格确实比较重。但如果开了头,说着说着,就容易忘了情。”
路越发崎岖起来,我们的心跳越来越迟缓。风迎面吹来,汽车的前窗被雪粒盖住,司机隔一会儿就要擦去。世界上所有的寒冷仿佛都脱离了山谷,逃进了小小的汽车里。我感觉车外横冲直撞的风雪发出了鬼哭狼嚎的可怕声音。地面变成了巨大的冰球,仿佛永远不会消融,带着别样的寒意撞击着我的心。我无奈地向着阿来靠近,似乎在向这个娇小的女孩寻求庇护。她好像完全忘记了寒冷,乘上了飞速行驶的白色雪橇,早已消失在思想的荒野里。女孩也挨近了我。让我们结缘的,也许不是阿尔泰的大风,也不是冬季的严寒,而是连我们自己也未曾感知的青春之力,又或者是从心底羞涩地汩汩流向全身的细微的怦然,让我们忘记寒冷和陌生而靠近了彼此。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不知道阿来在想什么?真希望她把心底的一切都告诉我。那些忽远忽近令人捉摸不透的希望啊。这不是年轻人转瞬即逝的心动——这令人沉醉的甜蜜,让冰冷的身体也流淌着炙热的爱:这不是青年男女之间为之生为之死的相爱,不是将绝不动摇的心意公开的珍贵时刻,是稍后就会陷入思念的短暂相聚,是不必言说的默契。
穿着暖和的衣服,正在无忧酣眠的诺沃斯特力卡居民又开始了鼾声。
我的眼前,不知道为什么,在那连马耳朵都无法看清的大风雪里,总是浮现那个穿着单薄的衣裙,披散着头发,踏着过膝的积雪的女孩。我又一次被这个画面吓坏了。
“阿来,如果不唐突,让我送你去村庄好吗?夜这么黑,天这么冷……”
“不,不,大哥,您不要客气。这不太方便,别耽误您赶路。对我来说,阿尔泰的风和雪,都是看惯了的。”
汽车现在行驶的路十分平坦,又笔直。汽车只是驶过一道又一道山梁,到了峡谷才弯弯曲曲地前行着。平常这样漂亮的公路上,积雪并不会停留太久。风一吹,雪就飞舞起来,朝着峡谷去了。也许是因为这样,我们没有觉得累。但我的两肩好像压着千钧重担,觉得又累又麻,呼吸都不顺畅。我肚子有些饿了,又想到了善良、开朗的阿来。她的声音听起来也有些着急,可能在想着明天早上的事。即使是对于萍水相逢的我,她也是那么信任地倾诉着。她心疼牧羊的父亲,也总是提起年幼的弟妹。
“父亲他们一定刚刚喝完了茶,想着明天要早起,准备铺床休息了吧。您知道吗,大哥,我们奥尔侃还没有装电灯。供电公司直接沿着道路向着诺沃斯特力卡去了。他们说不必为了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村庄费周折,特意绕一个圈,以后还会有机会的。您知道吗,大哥,我们的村庄既没有俱乐部,也没有电影院和图书馆。只有卖餐具、布料和糖果的唯一一家商店。这家店就开在店主的其中一间屋子,店主总共也只有两间屋子。有趣的是,我们总是超额完成国营农场的计划,而我们的文化和生活状况就是这样……但您肯定瞧不上这样的小村庄,会沿着笔直的公路前往被树为典型的村庄,只看到和报道那样的典型。”
“阿来,如果你不反对,我想现在就跟你一起去山里的那个小村庄……”
“你在玩儿捉迷藏吗?”阿来轻轻一笑,她的笑声极美,让人想要一直听下去。而她的笑容又是那么妥帖。
“返程时您再来一趟。两三天以后,我也会回去的。”
“好的,我同意你说的。可是……”
调度员回了头,大声说:“谁要在奥尔侃下车?”正在睡觉的旅客开始挣扎着睁开眼睛,脱发蓬乱地想要醒来。他们说的第一句话都是:“到哪儿了?”
“到奥尔侃了。”
“这个小村庄叫奥尔侃啊,真是癞痢狗还喜欢号称是野狼呢。根本就没必要在这个村庄停留。”大家都不满地窃窃私语起来。阿来立刻站起来,背起那只小小的黑包,朝着门口走去。我也跟在她身后。汽车门开了,刺骨的寒冷立刻侵袭了车厢,几乎要割破我们的脸。微弱的灯光几乎可以忽略。不同刚才,呼啸的风开始微弱了一些,无垠的荒野似乎穿上了裹尸布,被死亡笼罩,陷入了虚无的黑暗。我目送阿来走进了那虚无的黑暗,最后一次请求她:“让我送送你吧。”
当汽车发动,再一次要出发时,她说:“回程时,请你一定来。大哥,我会等你。”她的声音依然那么好听。
就在这时候,我听到调度员和乘客说:“现在的年轻人就像鸡仔,眨眼之间就相识、相爱。”
我在诺沃斯特力卡停留了两天,在第三天出发了。我去的村庄真的美得夺目。它仿照城市建造,笔直的街道,排列整齐的雪白的屋子——你会觉得自己陷入了某种梦境。村庄并不大,但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好像被抛洒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州里、县里来了重要的客人,都会被带到这个诺沃斯特力卡。对我来说,这像一个陈列在展览馆的展览品。但我心里还是很满意。村莊的领导也很是好客、得体,都是像宝石一样优秀、夺目的男子。但我却觉得奥尔侃所有的财富和福气都被这个小小的村庄偷走、抢走了。紧挨着的两个村庄,怎么会有这样的天壤之别。“因为诺沃斯特力卡不在山里,而是就在路边……”我心里有个声音暗暗地说。
有趣的是,我隐约有些思念那天认识的那个披着披肩的女孩。相识虽然短暂,思念却很悠长。我是偶然找到她的,但也许我从前的人生都是在寻找她吧。也许,总会,那颗总是在找寻着什么的心终于找到了平静,在某个港湾停泊……这隐秘的愿望与渴求,让人永远追寻,期盼着明天。思念让人捉摸不透,在不断地追寻后精疲力尽。
早上,我坐上了去往县中心的汽车,然后在去往奥尔侃的路口下了车。快天亮时下了雪,道路变得非常泥泞。山顶出现了微弱的日光,洒落在雪地上,让人不能直视。那雪白的世界,陷入了让人难以描绘的美丽,只有雪橇留下的斑驳的轨迹,让人分辨出前往奥尔侃的道路,没有其他的路标。雪橇留下的两条轨迹,让人想起有些人终生难以重合的命运。我朝着山里那个小小的村庄走去。烟囱里飞出的炊烟在无风的夜里笔直地向着空中飘去,缓缓地消失在视线里。我甚至闻到那个离路边两三公里的村庄飘来的炊烟的味道。我其实并不着急。阿来,我想她一定在等我。明天,我们会一起回阿拉木图。“不知道她的父母会怎么看?”我敏感地想着。
我到达奥尔侃时,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中等个子,长着浓密胡须的漂亮的年轻人。他低垂着头,正在赶路。
“哎,小伙子。”我大声叫住他,“阿来家是哪一个?”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反问我:“你是她的什么人?”
“没什么,就是认识而已。”
“是那个……那个……村庄角落的房子。”他说完,就立刻转身走了。
我走进了村庄时,就听到了哭丧的歌声。我虽然不敢细想,但还是走进了这间房子,看到了戴着黑头巾哭得撕心裂肺的女人,身边围满了小孩子。他们跟着母亲一起,正在放声大哭。
我的心好像要跳出来了。女人抬起头,用流着泪的眼睛悲伤地看着我。我惊慌地问她:“阿来呢?”我的声音是那么突兀,那么可怕。
“我们失去了她,失去了……”冲天的哭丧歌仿佛在割裂我的心,我的痛深入骨髓,踉跄着跪倒在地,抱住了女孩的母亲。
就是那个风雪之夜,狼群包围了阿来,在村庄和路口之间的那条路上……狼群吃了阿来……我来到村庄边埋葬阿来的墓地。洁白的闪着银色光泽的雪地上隆起了乌黑的土包。阿来踏上了永恒的没有返程的旅途,乌黑的土地收留了阿来洁白无瑕的孩童一般的灵魂。
女孩的父亲似乎没有看到我,他盯着那个年轻的坟茔,许久许久都没有动一下。洁白的雪地上一滴一滴滴落的,是我们的泪水。羊圈里的羊在咩咩地叫着……这个世界上今后所有欢乐,所有忧伤和喜悦都不过如此,就像那样闲来无事啃啮着彼此身上的羊毛的羊那样……
我沿着村庄向着那个路口走去,最后一次回头去看阿来的坟茔,女孩的父亲像一块石碑一样,还站立在那里。
等我再回到路口,又看到了刚才那个年轻人和一群要去诺沃斯特力卡上学的孩子。有一个孩子很像阿来,也许,是阿来的小妹妹吧……她们冻得发抖,汽车还没有来……
“我和阿来是同学,和她在一张桌子上一起念书。”他的喉咙发出哽咽的声音,然后接着说,“阿来的口袋里有火柴,她一直点着火柴威吓狼群,直到火柴点完了。她看狼群一直围着她,又捡起雪橇上落下的一包草点燃。然后……然后狼群在雪地上很快就……然后可能是为了示威,把她的靴子和头发留在了雪地上。他妈的!我要拿着枪,一直杀到阿尔泰一头狼也没有。我要让他们灭种。那天,狼嚎了很久很久……”他哭了。
这时,开往诺沃斯特力卡的汽车出现在了道路盡头。
我第一次没有完成编辑交代的任务,那篇关于农村建设的文章也没有完成……
责任编辑:丁小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