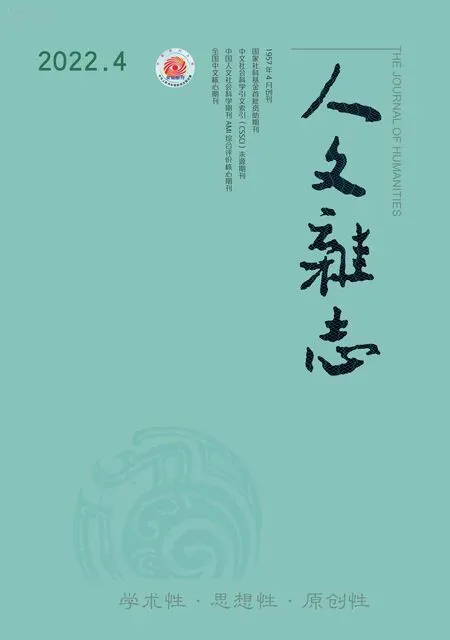《诗经》在中华伦理精神建构中的重要价值
李营营
关键词诗经 伦理 重要价值
作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中国在历史上有着丰富的伦理思想。但与国人认识世界的整体性思维有关,中国迟迟未建立起专门的伦理学学科。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伦理学学科才真正建立,由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西方伦理学、中国传统伦理学三个方向组成。但是,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导致中国传统伦理学人缺乏学术自信。
伦理道德是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以儒家伦理为主流的中国伦理精神有如江河行地,在民族精神的塑造中一以贯之,为中国的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传统伦理学蕴含着宇宙人生的普遍原理,是中华文化的基石与民族智慧的体现。中国传统伦理学应是最有理由具备文化自信的学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强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① 伦理学肩负着弘扬中国道德精神、推动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观念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任。伦理学者应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深入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丰富内涵。
《诗经》为五经之首,它在人文传承、民族精神塑造、经世致用等方面有着出色表现。历朝历代的学者对《诗经》青睐有加,进行了细致的字词注解、章句诠释、内容解读、义理阐发等工作。诗经学研究能够绵延数千年,除了政府的提倡和必要的外部条件外,主要则是由于其自身所蕴含的深刻的伦理文化精神所决定的。《诗经》根植于历史史实和现实生活实践,蕴含着崇尚道德、家国情怀、秩序和谐、天人合一等伦理精神,对人类健康发展和文明推进有着重要意义。
罗国杰先生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一书中指出,前孔子时期是中国道德观念和伦理思想的发端期,但“目前对这个时期的伦理思想还研究得很不够”。① 虽然《诗经》创作并非为了专门论述伦理思想,但却蕴含了前孔子时期伦理思想的精华,对后世儒家伦理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伦理精神都有深远影响。学者应充分挖掘《诗经》的伦理意蕴,促进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构建具有中国话语、中国气派的“国之德”。
一、《诗经》文本蕴含的伦理思想
中华道德文明源远流长,早在原始氏族社会的生活和劳作中就产生了团结、勇敢、敬惧等伦理观念。但由于缺少文字记载,远古时代的伦理思想并非清晰可见,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真正奠基时期是西周时期。殷周剧变使周人看到了民心在政权更迭中的重要作用,而民心与统治者的德性直接相关,因此周人变革前人的天命观念,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理念,塑造了重视道德的时代风气。诞生在这一时期的《诗经》是现实主义作品,具有贴近生活、诉诸情感、扬善抑恶等特点,或歌颂、或鞭挞,其内容大多围绕伦理道德与社会秩序展开。从《诗经》一书可以看到,道德观念已经清晰地贯彻到周人的个体修身、社会生活、政治统治、天人关系等领域。
第一,“崇尚道德、温润如玉”的修身伦理。殷周剧变使周人意识到民心与德性的重要,对个人德性的要求被确立起来。《诗经》中的“君子”“淑女”形象是重德风尚的集中呈现。君子的品性体现为温和,“温温恭人,维德之基”“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在人際关系处理中表现为温和适中的态度。“温”成为后世儒家伦理的重要范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诗经》多将君子比为玉,玉是周礼的重要元素,是谦谦君子的象征。君子通过佩戴玉饰使行有节度,如“佩玉将将”“佩玉之傩”。《礼记·玉藻》也记载“既服,习容观,玉声,乃出”,用玉饰的声响来规范步履节奏。后来,《荀子·法行》首次明确提出“比德”概念,将君子比为玉。可以说,《诗经》塑造的温润如玉的君子形象是后世儒家君子人格的原型。
《诗经》塑造的女性理想人格同样具有重视品德修养的特点,“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匪饥匪渴,德音来括”,皆指向品德之善。正如马瑞辰所言:“《方言》:……秦晋之间,美心为窈,美状为窕”。② “淑女”人格是美心与美状的结合,是内在善与外在美的结合。
在《诗经》时代就已形成了用道德感召力促进政治稳固的仁政思想的原型。统治者的德性与政权得失直接挂钩。周文王被刻画为个体道德和仁道政治的典范,《大雅》之《皇矣》《大明》《文王》《思齐》《文王有声》《假乐》称赞文王修养美德,实行德政,因此可以保有天命。《大雅·文王》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这种将道德等同于政治的做法,在后世儒家仁政思想中得到了具体充实,即孔子所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诗经》理想人格的尚德倾向影响着中国人的修身理念,成为后人修炼品性的一面明镜。
第二,“孝弟为本、友爱和谐”的家国伦理。周初实行宗法分封制,按照血缘的远近确立政治关系,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枢纽,权力层层下分。父系是权力的中枢,宗族是政治的联盟。亲情与政治密不可分,家与国密不可分,血缘亲情和政治统治高度融合。《诗经》多次出现“家”“邦”二字连用的情况,如“君子万年,保其家邦”“以御于家邦”。在家国同构的政治组织模式下,家族的“孝”“弟”伦理同时也是政治伦理规范。“孝”要求尊敬父亲宗族,宗法的国家是贵族的家天下,“孝”进而成为维护君臣上下等级关系的重要伦理基础。“弟”要求尊敬兄长,这样便可以稳定大宗小宗的等级名分。可见“孝”“弟”不仅是家庭伦理,也是重要的政治伦理。《诗经》“孝”德的内容包括对祖先的祭祀追孝和对父母的孝养,尤其强调对祖先的追孝,被称为“孝享”,它进一步巩固了周人的宗族意识。《诗经》中的《蓼莪》一诗是描写孝德的名篇,被方玉润称为“备极沉痛,几于一字一泪,可抵一部《孝经》读。”①
“弟”甲骨文写作“ ”,金文为“ ”,用绳索束弋之形。当中竖笔,像弋之形。绳之束弋,辗转围绕,盘旋而上,象征次序。在嫡长子继承制下,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贵为一族之长,拥有本族的神权、财权、兵权、法权,对本族成员具有统率、管理、处分之权,对所属劳动者有生杀大权。大宗的地位极高,“弟”德因而成为重要的政治规范,《诗经》“弟”字出现56次之多。《小雅·棠棣》是讴歌“弟”德的佳作,反映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的政治联盟的实质。孝、弟是《诗经》时代最为重要的伦理规范,到了后世,儒家也极为重视孝悌,被孔子视为施行仁德的基本条件。
在宗法血缘纽带的政治统治中,柔性的德治是最为有效的统治方式。与孝弟之德相类似,“友”德是周人处理包括家族亲情在内的社会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诗经》“友”字出现23次,数量庞大的宴饮诗反映了政治势力之间的友情维系。《鹿鸣》《常棣》《南有嘉鱼》《蓼萧》《湛露》《行苇》等都是宴饮诗。在宴饮活动中,礼节仪式传达出尊老爱老、尊卑有序等伦理理念。宴饮活动以具象的形式展现了分封制度下整体对个体的赐予,强化了个体对整体的依赖。在宗法分封制度下,周人以友爱的道德精神处理这种形式相对分散的利益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极大地增强了联合性和凝聚力。家国同构的组织模式把血缘亲情向外推扩,拓展为关心社会的伦理诉求,促进了个人、家庭与国家的良性互动。这不仅成为后世治国理政的基本模式,也是仁人志士实现人生理想的实践途径。
第三,“尊敬自然、师法自然、仁及草木”的山水情怀。“周”字卜辞为“ ”,金文为“ ”“ ”“ ”,为农田之形。以“周”为国号,正因为周原土地肥沃、善事农业。周以农业起家,农业的丰欠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周人善于遵从自然规律,运用自然条件。《豳风·七月》记载周人按照自然时令的更替安排农业活动。《小雅·斯干》记载周人利用植被、阴阳等土地综合条件进行建造活动。《小雅·鱼丽》“物其有矣,唯其时矣”体现出尊重动物生长规律的思想。后世儒家系统发展了“时禁”理论,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不违农时”,荀子“以时禁发”,都提倡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自然界的莺飞草长、山川风月皆可入《诗》,诗305首只有19首没有出现名物,形成了乐山乐水、师法自然的生态审美观。这种山水情结被后人继承发展,“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都体现了对山水意境的体悟和喜爱。
《诗经》传达了仁及草木、德及昆虫的生态保护观。《大雅·行苇》云“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把植物纳入道德共同体的范围。《王风·君子于役》将动物刻画为人类家园的一部分。后来,孟子“仁民爱物”思想,张载“民胞物与”思想,王阳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思想,都继承和弘扬了对天地万物的恻隐之心。总之,《诗经》时代的诗哲们把万物看作有生命的、充满情感和韵律的整体,把自然纳入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充满着宇宙的、生态伦理的道德情怀,成为后世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源头。
《诗经》虽不是篇篇都探究人生意义与生命价值,但它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传达了先民的生命体验和意义追寻,蕴含了崇德向善的君子人格、孝弟为本的家国情怀、以德治国的仁政理念、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在处理个体与家庭、社会、自然的关系方面,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后世的许多思想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诗经》文本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内涵,使其被历朝历代的学人所青睐,并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延伸出更深厚的伦理意蕴。
二、《诗经》伦理意蕴在后世的扩充
西周时期《诗》与礼乐制度紧密融合。《诗》从属于乐,是乐的歌词,305篇都是有声有辞的乐歌,有目无辞的“笙诗”仅有6篇,现存《诗经》是其歌词部分。《风》是带有地方特色的歌谣,采集之后被周代乐官整理,披之管弦,以备在典礼中奏唱。《雅》是宫廷宴飨或朝会时的乐歌。《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诗》三百篇无不经过乐官的编排,配以曲调,用于演奏。《诗》以乐的形式被用于典礼中,它不仅是民间歌唱和观风听政的辅助材料,更是周代礼乐制度的载体,属于官方文化的一部分。《诗》乐与禮的融合具有显著的伦理教化效果。《诗》配以曲调乃至舞蹈而为乐,在典礼仪式中被演奏演唱,《诗》、乐、礼三者合一。《诗》成为礼乐制度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依托礼乐以介入人的日常生活。礼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通过《诗》乐形式得到美好的呈现。《诗》以礼乐为用,把社会伦理标准变成个体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追求,把道德与审美融为一体,达到“乐以成德”的审美境界。
人是理性与情感交织的对象,道德行为的产生需要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的共同作用。道德理性是道德关系、规范、原则。道德情感是基于道德认知而对道德现象产生喜爱、憎恶、同情、痛苦等情感体验。《诗》、礼、乐的融通,正是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相互作用的过程。礼的实施主要是道德理性的淬炼过程。礼使人节制过分的欲望,有效化解社会纷争,规范社会各个领域的秩序,比如乡饮酒礼规范长幼之序,朝聘之礼规范君臣之序。礼的实施过程,塑造起符合道德规范的社会心理结构。乐的实施主要是道德情感的培育过程。乐是情感的抒发,《诗大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① 逻辑语言由于情感的推动而出现吟咏缠绵的变化,成为歌唱的艺术语言。这种艺术语言又可以反作用于情感,对人的意识、心理、精神产生震撼和引导作用,促进人的感慨和沉思。《诗》乐的运用,充分调动了人的情感之维,使抽象的道德变为丰富的情感生活。道德情感是道德行为的心理基础和推动力。道德法则如果不与道德情感相交融,则只能沦为苍白的理性空文,再高尚的道德行为也会半途而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知道“见义勇为”的道德知识,但见死不救的事却经常发生,这就是道德理性到位而道德情感缺失。道德知识与道德法则只有“悦我心”“合我意”,得到主体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关怀,才能真正发生作用。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君子的养成除了符合道德标准之外,还要在“六艺”当中修炼。在实践中,孔子主要主张进行“乐”的熏陶。“成于乐”就是运用了音乐对道德情感的培育作用。典礼中的《诗》乐表演,将道德观念融于艺术形式,通过诉诸理性与感性,使人产生高雅的审美情趣,感知并认同社会价值理念。《诗》、乐、礼一体,礼节仪式借助美好的旋律和歌词而成为超越理性认知的精神体验,凝练成翩翩风度的君子人格,建立起端庄典雅的精神风貌。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礼乐规定被新贵族的僭越行为所打破,礼仪形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不再能够反映宗法等级秩序。原先从属于乐的《诗》也开始摆脱乐的统辖,以独立的形式直接走近礼。当时的赋诗引诗现象,就是诗与乐分离之后的表现形式。赋诗即“不歌而诵”(《汉书·艺文志》)。人们在外交场合或朝会宴享中赋诗言志,《诗》成为重要的交流工具,甚至达到了“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的程度。引诗,包括言语引诗和著作引诗。前者如《左传》记载历史人物引诗,后者如《论语》引诗。虽然这时的礼乐制度开始松弛,但赋诗引诗仍然是礼乐制度的一种维系。在当时的外交礼仪、酬酢交往、燕乐嘉宾等活动中,《诗》都被派上用场。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的程度进一步加深。礼仪行为更加形式化,社会等级观念与政治秩序被破坏,乐因为礼仪的形式化而趋于散乱,出现“八佾舞于庭”的局面。礼乐仪式的逐渐退场,使《诗》的传播范围大大缩小,从外交、宴享的社会实用转向知识分子的著作引诗。
及至孔子,以恢复周代礼乐制度为毕生所愿,始终没有放弃对诗歌礼乐化的努力。在孔子的思想中,诗与礼乐不可分割,从属于礼乐。“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孔子时常从音乐的角度评论诗,“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诗》可以使人感发意志,观察社会,和睦人群,抒发怨愤,有效地服务于君臣父子的社会政治。可以看到,孔子的诗学观念具有浓厚的伦理化政教色彩,尤其是“可以群”的理念。孔子认为,《诗》代表着周代的礼乐文明,在周代礼乐制度下,《诗》的使用与礼乐制度融合为一,在协调群体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孔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认为《诗》在提升人的道德修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诵《诗》是学习礼乐的初级阶段。孔子对《诗》道德伦理价值的重视,为后来《诗经》走上完全伦理化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战国末期,《诗》始称为“经”。《礼记·经解》把《诗》《书》《乐》《易》《礼》《春秋》等典籍囊括其中,实际上就是将各书列为“经”。司马迁《史记·儒林传》“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首次将《诗》正式称为《诗经》。西汉以后,《诗经》之称日益普遍。此后两千年的《诗经》研究主要以经学方式展开,以汉、宋两个阶段最具代表性。
汉代,随着陆贾、贾谊、董仲舒等人对“五经”的重视与提倡,经学的意义被放大。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确立了“五经”的权威。《诗经》研究以齐、鲁、韩、毛四家最为出色。其中,齐、鲁、韩三家《诗》借助政治力量立于学官,与政治紧密结合,通过对经典的创造性解释,建立起经典与当代政治及社会人生的联系,在现实中落实经典的意义,以“通经致用”的方式争鸣于朝。《毛诗》一派则远离政治,专研《诗经》文本,思考《诗经》在道德方面的永恒意义。其代表作有《毛诗故训传》《毛诗郑笺》《毛诗序》等,《毛诗序》包括《诗大序》和《诗小序》。《诗大序》论述诗的本质、功用、六艺、四始、正变,是宣扬“诗教”的基础。《诗小序》进一步发挥《诗大序》的“诗教”理论,以史证诗,以美刺论诗。“美刺”之说是汉儒将《诗经》作为伦理教科书的理论支持。《诗》之正者皆为“美”,《诗》之邪者皆为“刺”,诗三百篇皆是出自诗人的善良动机。如此一来,《毛诗序》系统构建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意义。到了唐代,孔颖达奉诏编纂《毛诗正义》,全部保留《毛传》《郑笺》,并为其作疏,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颁行全国,成为推行政治伦理道德的国定教科书。
宋代诗经学主张冲破汉学的训诂研究方法,注重探究义理,对汉儒有关《诗经》的传注提出质疑和驳难。其中朱熹最具代表性。朱熹打击汉唐诗经学,主张摆脱《毛诗序》的羁绊,不拘泥于诗的时间、地点、人物、字词的臆断,通过反复吟咏直接体会诗的思想。朱熹认为,诗三百篇是人情感的直接抒发,情感表达是本,政教美刺是末,并非篇篇都有美刺动机,因此应该废黜汉唐诗经学的政教美刺体系。废黜汉唐诗经学政教美刺内容后,朱熹建立了新的理学《诗经》学体系。朱熹认为,正《风》、正《雅》、三《颂》具有内容的正价值,传达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伦理理念。变《风》、变《雅》多为乱世哀怨之作,具有劝惩以敦风化的功用。因此,从本质上说,朱熹仍是坚持儒家的教化理论,以诗说教,把《诗经》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教科书,其学术立场与汉儒并无二致。
可以看到,在整个封建帝制时代,《诗经》在促进个人品性修养、维护社会秩序和谐等方面的伦理教化意义得到了系统开发,但也存在诸多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牵强附会之处。比如对诗篇强加道德意义,如《关雎》是一首情诗,而《毛序》云:“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①又如虚拟历史,如《君子于役》是一首妻子思念征夫之诗,而《毛序》云:“刺平王也。君子行役无期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焉。”②
三、《诗经》伦理意蕴对新时代伦理道德建设的启发
直至20世纪,随着封建帝制时代的结束,对传统文化的大批判拉开序幕,传统诗经学也不例外。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主张推倒两千年来对“经”的崇拜,从民间歌谣的角度研究《诗经》,还其文学“真相”。郭沫若主张摆脱传统诗经学研究套路,全凭个人感受解诗。闻一多主张把《诗经》“当文艺看”。五四以来的诗经研究主要发扬《诗经》的文学性,摒弃传统诗经学“温柔敦厚”“圣贤之教”的诗教理论。这反映了人们根据时代需要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解读经典。它有积极的一面,扫除了经学研究中诸多牵强附会的部分。但文化的彻底否定主义使中国人深度怀疑本国伦理文化,认为《诗经》是偶然流传下来的诗歌而毫无伦理意义。自汉代开始,得益于政治权威的推行,《诗经》等儒家经典被定于一尊。但它能够成为两千年来一直被中华儿女竞相传诵的经典,却不是单靠统治者的提倡就能实现的,其根本原因乃是《诗经》本身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浓缩了中华民族对人、社会、自然的深刻思考。《诗经》蕴含的崇德向善的人格标准、孝弟友爱的家国情怀、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对人类而言具有超越时间的恒常意义,不管是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还是在信息化社会,都具有重要价值。
经过风吹雨打的洗礼之后,激进的现代人变得成熟起来,认识到全盘否定传统诗经学的弊端。钱穆先生指出,在《诗经》这里,“我们见到文学与伦理之凝合一致,不仅为将来中国全部文学史的渊泉,即将来完成中国伦理教训最大系统的儒家思想,亦大体由此演生。”③《诗经》是文学的,亦是伦理的,它有着崇德向善的伦理特性。刘毓庆教授在《百年来〈诗经〉研究的偏失》一文中指出,我们“必须清楚《诗经》的双重身份,它既是‘诗,也是‘经”,“它的经学意义要远大于它的文学意义”。④ “经”,经天地序人伦,“经书”蕴含着天地之常道。《诗经》蕴含着人生哲理、政治哲理,展现了中华道德文明发展的脉络,蕴含着中华伦理精神的精髓,对新时代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发。
第一,促进德育与美育相结合。道德教育具有半强制性,很难保证道德行为是出于个体的自觉。如果采用刻板的道德化育手段,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人的情感表达能力和思维创造力。那么,如何在进行道德建设的同时,不破坏人的情感和创造力?诗教呈现出寓教于美的教育方式。《诗》的文学属性和早期的音乐属性使其具有艺术之美。人在获得音韵之美、意境之美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认同其道德理念。《诗》早期“以声为用”的与礼乐融为一体的形式,则具有更为明显的教化效果。音乐不需要借助文字,仅通过旋律就可以在人的心灵深处引发共鸣,使人心甘情愿地服膺于道德理念,从道德他律轉化为道德自律。亚里士多德指出,音乐或其他艺术具有净化作用,“Katharsis可以纯净人的心灵,提高人的道德意识”。① 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期待人能够像喜爱美色一样喜爱道德。以审美的方法培育道德,就会使道德成为一件令人愉悦的事。主体处于感官愉快、精神愉悦的状态,此时的道德律令就有了享乐感和亲切感,使人乐于吸收到心灵里。
第二,以情感为抓手培育人、塑造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但这种重视并未在伦理学中得到应有的体现。我们的伦理学长期以来坚持以“应该怎样行动”为中心,而不是以“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为中心,注重对人的理智的开发,而忽视了对情感的培育。社会价值导向更多的是理智型的,学校教育也主要是智育。相反地,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不注重形而上的论证,而是注重情感和体悟。《诗》不是以实证、推导、理论分析的方法来实现道德教化,而是将义理融于诗境,以情绪感染的方式来达成某种共识,以情感为抓手提升人的道德境界。《诗》是情感活动的产品,极易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当我们涵咏诗文,其中对美德的追求、对和谐的期待、对天地的热爱,无不深深地感染我们。只有充分涵养了人的情感,伦理学的作用才算真正落到了实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注“理”字为“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于无撼而后即安,是之谓天理,是之谓善治。”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得到适当发挥而无憾,就是理。新时代的伦理学应充分发挥这种优长,注重涵养人的情感,使人的情感得到升华。以道德情感抵制理性的过度肆虐,以道德理性对情感贪欲进行适当规约,以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的合力塑造正确的价值取向。
第三,发扬“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萨特指出:“尽管文学和道德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但在艺术责任的核心中,我们看到了道德责任。”②《诗经》运用现实主义笔法,承载着美刺时政的社会关怀。它所蕴含的道德意义,使人产生高贵的生命体验。它所承载的礼乐精神,指引着中华儿女对于君子品格的向往。这种现实主义笔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忧国忧民、担当道义的文学传统,指引着仁人志士以笔为矛,匡扶正义。比如《窦娥冤》等文学作品富有道德教化和伦理意义,承载了艺术审美价值以外的道德价值。现代文论曾出现“唯审美”论思潮,以康德为代表,提出“审美无关利害”“美在形式”等观念,片面强调文艺的独立审美特质,割裂了文艺同社会的关系,否定文学艺术的道德价值。这种思潮导致个人化的写作风靡一时,一些文艺工作者甚至置良知于不顾,放弃对社会人生和真善美的观照,标榜丑陋、演绎庸俗,凌驾于社会道德规范之上。文学艺术不是道德说教的工具,但它不能脱离道德的约束。当文艺创作失去了道德之维,便会迎合低级趣味。比如,当音乐表现为和谐浪漫,则可以引导人的性情之正、行为之雅;当它发展为疯狂、暴露,则引导着情绪的癫狂和欲望的膨胀。我们需要用更文明的规范来引导人的行为,用更高雅的文学艺术来指引人的生活。文艺创作要秉持良知与操守,使受众在获得审美享受的同时辨别是非善恶,避免走向价值观的误区。
伦理文化的培育离不开历史的延续,它是一个民族世代积累的历史经验。传统诗经学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烙印,但其伦理意蕴却具有跨时空的永恒意义。因此,应促进传统诗经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中华伦理精神的建构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