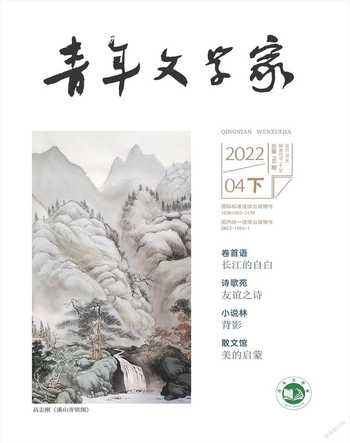似水流年
张文
《绿毛水怪》是王小波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作品,摆脱了历史悲情叙事和宏大说教的束缚,而展现出不兼容的新时期文学的自由与浪漫。本文从创作背景、行文线索及其思想主题入手,分析其所构建的“爱情乌托邦”。《绿毛水怪》既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传统之外,又在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新时期叙事之外,形成了反对道德化感伤情绪和青春无悔虚假态度的别样价值。
《绿毛水怪》主要以王小波的童年和少年在牟平的生活体验作为背景,发表却迟至1998年,王小波去世之后。该小说虽不是王小波的处女作,却是他最早表现出文学才华,受到关注的作品,也是他与爱人李银河的定情之作。作为王小波的早期作品,这篇小说粗看起来,从对话到细节描写,还透露着稚嫩,但是王氏幽默已初见端倪,并在当时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的喜爱。但很遗憾,这篇小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未能发表。更苛刻一点而言,这篇小说也不兼容于整个新时期文学,甚至有别于20世纪90年代流行文学的审美趣味。但对于王小波而言,恰是这个时期,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他的这种个人主义文学气质才得以取得“历史性间隙”的生存空间。
《绿毛水怪》所表现出的文学气象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可绝非无迹可寻。这也与王小波偏爱西方文化,同时受到西方文化中“自由主义”的创作风格影响有关。与同时代作家相比,王小波的作品没有历史悲情叙事,也没有宏大说教,而是通过对美和自由的极致追求和向往来展现伤痕。房伟曾提出中国现代文学自起源就呈现出一种“后发现代”特质,即中国现代文学总表现出杰姆逊说的“民族寓言”特定模式,甚至是那些力比多的文本,也难逃宏大叙事的束缚。这也使得中国文学呈现出被动性、情感压抑性、自卑情绪,并且充满了通过道德性塑造,超越西方他者的内在焦虑。而《绿毛水怪》则是在这一奇怪的逻辑悖论下,产生的具有反抗气质的“非主流”作品。
《绿毛水怪》展现了王小波基本的美学风格和主题,和王小波成熟期的作品相比,该小说很少涉及人情世故,对世相的洞察,更多的是飞扬的青春基调、瑰丽的浪漫想象、单纯的童话色彩、反传统的科幻意味,以及奇趣可爱的想象力。当然,这其中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小说中陈辉和妖妖(杨素瑶)二人跨越“物种”的真挚感情。
小說采用第三人称视角“嵌套”第一人称展开叙述。“我”王二作为一个旁听者,听老陈给我讲他和妖妖之间的往事。从小学时期的亲密,到中学时期的懵懂暧昧,再到后来的错过与后悔,一段乌托邦式的理想爱情呈现在我们面前,而细细考察,王小波作品中“传统”与爱情的对抗思路早已隐含其中,爱情本是私有性质,但20世纪70年代的爱情,似乎已经沦陷为传统禁忌中的抽象表征,其悲剧性色彩不可避免。
首先,让我们先来谈一下这篇小说的创作背景,以及其所反映的当时的社会基调。
众所周知,一部诞生于某个时代的作品,大多是要来抨击或反思这个时代的,这篇小说也不例外。故事创作于1977年,这一时期的小说大多都具有对英雄的崇拜心理,有史诗的创造情节,肯定歌颂现实和片面的追求风格。
在这篇小说中,王小波则突破了新时期文学的桎梏。他对男主人公陈辉软弱性格的描写并非对女性的崇拜,而是借此机会建立起一种个体崇高感的形象,曲折地反映了男性对自由的思考以及自我精神的解放。小说直接采取一种“叙事间离”的效果,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古灵精怪的男孩。他热爱高尔基,热爱文学,当老师诋毁他看的是不良书籍时,他哭着反驳老师高尔基和列宁是好朋友,也可以看出那时的他文学启蒙之深。陈辉这个怪物男孩,类似《皇帝的新装》那个揭示成人世界的虚伪的小孩,又很像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中能洞察人们心思,拒绝长大的小奥斯卡。这样的人物设置,不仅形成了主题学上反抗庸俗、反抗成人,赞美童真世界的作用,而且也起到了“非常有魅力”的叙事特效性功能。这种将“教育”置换并隐喻“启蒙”的创作,在同时期刘心武的《班主任》中也有体现。但是不同于刘心武笔下愚昧顽劣的坏孩子,陈辉和妖妖,与孙主任和刘老师的斗法,充满了叛逆精神和童趣,为新时期文学提供了别样的审美风采和文学途径。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陈辉、杨素瑶二人的故事脉络。其实这个故事的情节很简单,篇章划分也很有趣。第一部分名叫“人妖”,第二部分名叫“绿毛水怪”。前者被排除于男女性别之外,而后者则是具有克苏鲁神话色彩的虚构形象,这两种可以称得上是“怪异”的东西用来形容一个女孩子,也使之带有一种强烈的反差。陈辉和妖妖是小学同学中的异类,一个被称为“怪物”,一个被称为“人妖”,甚至老师也给他们贴上“复杂”的标签。两个人就这样在一种无形的孤立中成为好友,也因为读书找到了情感的共鸣,认为彼此是自己永远的朋友。
小学毕业之后,二人再一次于中学同一个班级重逢,曾经单纯的友情也在少年青春期中孕育出了懵懂爱意。那天晚上,陈辉送妖妖回家,在路上,二人不由自主谈论起曾经的时光,那时的他们是那么单纯天真,回到此刻,好像什么都没变,但又好像有什么已经变了。王小波并没有直接对这种朦胧情感进行描写,而是介入了二人小学时最爱的卡加与涅朵奇卡,小说中是这样写的:
我突然在她的眼神里看出了制止的神色,就把话吞了下去,噎了个半死。不能再提起那本书了。我再也不是涅朵奇卡,她也不是卡加郡主了。那是孩子时候的事情。
“吞”了下去,“噎”了个半死,把陈辉在明白了妖妖心思后那种刻意掩饰的感觉描写得准确又形象。紧接着便是说,“我再也不是涅朵奇卡,她也不是卡加郡主了”。反复地读几遍,你会读到一种充满了遗憾的距离感。一条像是无法逾越的河流横亘在陈辉和妖妖之间,这条河流是性别,是时间。
但好在这种隔阂并没有阻止两个人继续交往,此后的两年里不管刮风下雨,陈辉总会踏上那条放学路,送妖妖到车站。二人又开始无话不谈,从文学、理想到诗歌,王小波将最真挚的感情注入到两位少年的对话中,隐藏于最平凡的生活和文字里。二人没有轰轰烈烈、爱得死去活来,也没有“我爱你”“我也爱你”这样如此浓烈而深情的告白,《绿毛水怪》却让我们处处感受到彼此的爱意。
就像陈辉对妖妖说的那句:“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妖妖惊叹陈辉是一个诗人,我也惊叹于王小波的天马行空。这也让我无端想到了欧文·亚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一句话:“在浪漫的爱情中,最美妙的事情就是困惑寂寞的‘我’,消失在‘我们’之中。”不是陈辉与杨素瑶,不是怪物与妖妖,不是我和你,而是我们,我们行走在似水流年里,我们在奔向月亮,这是何等的浪漫!
故事继续讲下去,就开始走向了悲剧。此后,陈辉和妖妖被迫辍学,三年之后,陈辉在《雾海孤帆》中找到妖妖留给他的纸条,但寻址而去,却得知了妖妖在山东时出海游泳而意外溺亡的消息,这也是二人错过的开始。陈辉准备离开时,收到了妖妖留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平淡得出奇,但内容中翻涌的至深至诚的感情,足以让人动容。
陈辉:
你好!我在北京等了你一年,可是你没有来。你现在好吗?你还记得你童年的朋友吗?如果你有更亲密的朋友,我也没有理由埋怨你。你和我好好地说一声再见吧。我感谢你曾经送过我两千五百里路,就是你从学校到汽车站再回家的六百二十四个来回中走过的路。如果你还没有,请你到山东来找我吧。
我是你永远不变的忠实的朋友杨素瑶。
我要去的地方是山东海阳县葫芦公社地瓜蛋子大队。
王小波在这篇故事中喜欢使用数字来描写情感,让这摸不到触不得的感情也有了它的重量和刻度。除了妖妖在信中写的“我感谢你曾经送过我两千五百里路,就是你从学校到汽车站再回家的六百二十四个来回中走过的路”,她曾经还对陈辉说过:“陈辉,记得我们一起买了多少书吗?二百五十八本!现在都存在我那儿呢。我算了算总价钱,一百二十一块七毛五。我们整整攒了一年半!”不需要复杂的修辞,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淡淡地、平静地将普通而又不能再普通的事情表达出来。因为在乎你,所以有关你的一切我都铭记于心,“两千五百里”路是“我爱你”的佐证。
小说写到这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断裂,既是故事断裂,也是时空转型。小说一下子中断了前半部分对现实生活的描述,为我们展现了想象的“绿种人”的海洋生活。陈辉回到山东老家后,在一次出海中碰到了化身成绿毛水怪的妖妖,并毫不犹豫地愿意跟随她前往大海深处生活。成为绿毛水怪的妖妖与美丽明艳的形象大相径庭,甚至有些恐怖和吓人,可她依然保留着善良、天真、美好的天性,变成“绿种人”的妖妖与陈辉相约明天再見,陈辉吃了药,也要加入“绿种人”的队列。但陈辉因为得了肺炎,错过了约会时机,与妖妖天各一方,不再相见。故事最终以妖妖刻留在礁石上的字迹结束。字迹的内容是:
陈辉,祝你在岸上过得好,永别了。但是你不该骗我的。
杨素瑶
我们无从知晓被陈辉“骗”了这么多次的妖妖最后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写下这行字,我们也无法责备陈辉从始至终的错过,时间仿佛一把剪刀,无情地剪断了陈辉与妖妖之间的联络。至此,老陈才将《绿毛水怪》的故事讲述完毕,可是“我”作为故事的旁听者,却对这个故事持怀疑态度。陈辉对故事“赌咒发誓”的肯定,与“我”对故事的否定,也形成某种结构性张力,引导读者进行深入的理性的思考。进而言之,这种旁支性功能角色,有效地缓解了《绿毛水怪》奇幻色彩带来的不真实性、虚构性,进而制造了一种“真假掩映”“真真假假”的艺术效果。
小说结尾,第一人称“我”(老王)和故事的讲述人陈辉,终于回到了无奈的现实。公园的长椅上,二人为了故事是否真实可信,争执了起来。第一人称叙事的“我”,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叙事者。他语言粗鄙,内心冷漠。他对绿毛水怪故事的嘲弄与全文洋溢的美丽激情,形成了鲜明对比,更深刻地寄寓了对庸常世界的批判。
世界上真的存在“绿种人”的妖妖吗?其实“我”的倾向是并没有,妖妖变成水怪只是陈辉的臆想和杜撰。其实从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窥知一二,比如“我”被癫狂的老陈吓坏了,咬着牙跟他说你想进安定医院吗?还有后面即将赴约时,陈辉被送进了医院而与妖妖永别。而王小波自己在《沉默的大多数》中也提到:“人绝望到一定程度以后会编出一个故事来骗自己,好让自己有活下去的动力。”我们无法否认陈辉或许是在绝望中编造出这样一个奇幻的故事来回避妖妖已经去世了的事实。
也正如《巴别塔之犬》表达的那样:大家都以为自己和爱人共有一个巴别塔,但人与人之间的鸿沟谁也不能跨越。
王小波用《绿毛水怪》表达了自己的爱情观,人一生的所爱或许有很多,可是真正难忘的挚爱却只有那一个,可是挚爱难觅,或许一生都在错过。
这个幻想中的“绿种人”的故事,特别强烈地传达着生活在物质极度贫困和精神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对自由和光明未来的向往。有论者称之为“知青的乌托邦”,认为绿种人受着并又超越了西方美人鱼的影响,展现了独属于王小波的想象与浪漫。“绿种人”不受国界的限制,也不受水域的限制,他们可以任意到海洋和内陆湖河去游览,还可以乘风起飞,到城市的屋顶和火山口……这个海洋世界中所拥有的一切,正是陆上人们渴望却又无法得到的。如果理想成真,或许王小波与其他人也会同“绿种人”一般躲进海里不回来了。
《绿毛水怪》既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传统之外,也在新时期叙事之外。它的出现,有着浪漫主义与欧洲早期启蒙主义的双重色彩,摆脱了感伤的道德化情绪和青春无悔的虚假态度,运用浪漫的想象力冲淡悲剧色彩,给读者留下水一般静静的悲伤。
似水流年是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只有这个东西才真正归你所有。其余的一切,都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转眼间就已跑到似水流年里去了。
—王小波《似水流年》
陈辉和妖妖的故事总是围绕着水展开,无论是他们一起熟读的《雾海孤帆》,还是“我们行走在海底”,或是变成了海怪的妖妖,你会发现总是有水的出现。当然,还有他们故事发生的似水流年,对陈辉来说遇见妖妖仿佛已经是他一生所有的经历了,而对于妖妖来说更是如此。只是生活终究还要继续,每个人在时代的洪流中身不由己,所以陈辉也只能带着悲伤与懊悔,流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