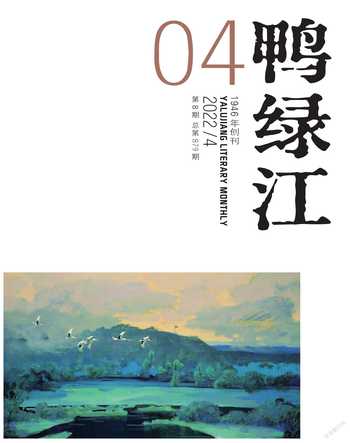唤醒(组诗)
空房子
把脚步移出来,把心装进去
黄泥墙,黑土瓦,木制门
算是最好的朋友了
剩下的还有四壁,站在原地
风掠过,尚存的气息
是先父咳嗽的回音
母亲虚脱的汗渍
不约而同地涌出来
给旧时光握手道别
一个下了地,一个进了城
如同被季节错过的稻田
渐渐荒芜。情感的负罪
套牢了余生的悟性和寄托
房子空了,村庄空了,心空了
在浇筑钢筋水泥的日子里
一个转身,记忆里的空房子
不经意间就显山露水
稻香
体内的脂肪越积越厚
盘中餐,我们更加熟稔
香米、贡米、御贡米、珍珠米
陈列在超市货架上的差价
却很少关注,乡下稻草长高的方式
这些在我生命里繁复的浆果
如何历经扬花、下弯、散籽的阵痛
又怎样喂养过我们残缺的童年
那些年的稻香,是一个村庄的根须
被血色和汗水喂养
是父亲和母亲常年的焦虑
时光的营养馈赠我们太多
搁浅在农事之外,从稻香里走出的足迹
不忍拒绝城市的霓虹
村庄的孤独漫成了生活外的眺望
只有那些困守的父老乡亲
还在一年四季背着太阳,用雨水和节令
培育稻香,却无法医治
城市的忙碌和健忘
咀嚼稻香,就是
咀嚼一个时代的沉浮
唤醒
寒光,一次次划开负重的日子
老祖宗告诉我“刀不磨要生锈”
我又一次,目睹水和陽光
碾过岁月的疼。那么锋利的刀
在时光面前撑不起腰,锈迹斑斑
故事的结尾,总会逆向而行
看似终点,又是开端
在石头上霍霍几下
锁眉之后,重见天日
消失
说消失就消失,措手不及
那些走乡串户的挑担
生长在记忆深处的呼声
被推土机钢筋水泥侵占
被慌乱的杂草挤推
隐隐约约的炊烟被风吹散
飘到了河的另一岸
熟悉的影子呢,不再属于我
一群鸟从上空飞过去
连鸟屎也没留下一粒
有车经过村庄,一个急刹
满满的乡愁溢了出来
没能惊醒柴门里的犬吠
也许,它正躲在苍凉的气氛中
黯然神伤
提及旧事
那时候我们都还小
赤着脚,在枯槁的阳光下
泥鳅一样滑溜
高举棍棒咿咿呀呀
嘴边缠绕着英雄的名字
拖着清鼻涕越跑越快
丈量,整个村庄四季的风
喘息声还未平息
眉目之间,翻越一年又一年
今天,我们是自己的英雄
在酒杯间豪气干云
突然就炸开了关于旧事的记忆
年幼时的那些棍棒
就像卡在喉咙里的刺
一吐为快
草
背“草背篼”的年龄
奢望漫山遍野都是草
手里的刀轻轻一挥
就能填饱耕牛简单的欲望
事实上,是要踏遍沟沟壑壑
占领遥远的地方
从遥远的地方回来
厌恶极了眼前漫山遍野的草
只是一个转身,就淹没了
父亲那本已荒芜的坟头
赶马人
路过村庄,一条响马鞭
孤独的鞭梢直指晨曦
转眼间就到了黄昏
青草和枯叶的颜色没有区别
心无旁骛地走路,赶马,吆喝
使唤整个村庄的柴米油盐
东家长西家短之外游动的影子
一辈子都没停下
反刍数十年的光阴
生活是一条走不完的路
远方在延伸,那里有两座坟墓
一座属于自己
一座留给驱赶的马匹
宿缘
无须四处寻觅,到了季节
去安放我疲惫的乡村
就近种下大豆、高粱、稻谷、红薯
生活的边角地带
花花草草天生素颜,没有上锁
任凭装进两眼的仓库
不做仗剑的侠客
用锄头敲打土地的背脊
庄稼和花草醒过来
像是天生慧根,与我结下一世宿缘
味道
我的身上总带有泥土味
时而夹杂着汗味
偶尔还有牛屎马尿味
因此,我与这座光鲜的城市
在某些细节上格格不入
我曾用城市的自来水
涂抹香皂,高档的洗发水、沐浴液
一次,两次,无数次
冲刷掉那些味道
偶有事实在短期内幻化成假象
眼睛骗不了感同身受
我总能嗅到存留在我身上的味
恍若相依为命的爱情
谁也离不开谁
扔不掉的就留下吧
这个城市里,与我味道相同的
还是大有人在。忽略那些味道
我们就不再是我们了
那就等同于没有根的浮萍
一切都是虚的
两棵桃树
老桃树上掉下一个桃子
入土,生根。小桃树
从果实里获取生命密码
坐在摇篮一样,晃悠晃悠
长高了,挂果了
风吹过来,愈发沧桑的老桃树
柔声对小桃树说
好啊,你也当母亲了
游戏
找个同龄人,一起回到十来岁
席地而坐,用剪刀石头布玩游戏
一笔一画,就像一砖一瓦
多么富有啊,有城堡,有枪炮
一段历史复活在面红耳赤的争论之间
互相攻打
你轰了我的炮,我夺了你的旗
最后剩下的,只有那么多横竖交织的线条
一段厘不清的记忆
消失在岁月的游戏中
作者简介:
兰采勇,刊物编辑,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偶有诗文发表,已出版个人作品集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