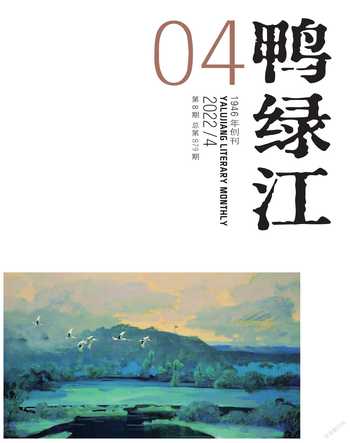滇行散记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本是王勃《滕王阁序》中描写滕王阁盛美之景象的语句,它化用了庾信《马射赋》中“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这句我走过中国的多处山水,我以为我热爱旅行,可是但凡我仔细回忆,不过是些模糊的浮光掠影与嘈杂无章的嬉笑打骂。
直至一日,我匆匆忙忙地跟随着我几个好友来到这宁静的云南,它剥夺我随口便能说出对景色赞美话语的能力,脑海中只是蹦出了这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住在大理环海公路旁,我们便萌发了一个奇妙大胆的想法——从双廊边上的红山庙绕着环海公路游遍洱海的山河湖海、人间草木,游那海舌公园,领略万人向往的挖色水路的民俗风采。大家兴致勃发,纷纷收拾背包,打算从早上一直游玩到夜晚。我们想象在那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寻那红嘴鸥与海边礁石,想在那阳光下看清传说中躺在水中的树。从诗中的意境挣脱出来,我们回到现实,却发现窗外竟私自下起了雨。
雨在村庄上空紊乱地倾斜着,它像一个笨拙的小孩拨弄着一种失灵的乐器,而这沉闷怪异的雨浇灭了我们集体出游的梦想。一心想要拍出好照片的女士们否定了雨景的构图元素,而男士们则更情愿在民宿中休整片刻。但我和另外一位少年看着民宿里波希米亚风格的装修,脑中依旧惦记着那个奇妙大胆的想法,墙壁之外想必有更多不循章法的风格所在吧。此刻我脑中有了更疯狂的想法,如果不能集体出游,那便独自“出走”吧。
我们稍作商量,约上了一位同样极其爱好探索的叔叔,租车前往喜洲古镇。路上透过车窗去看,无论晴雨,那终究是我们向往的充满奇妙之景的云南,让人捉摸不透,不管不顾地下着雨。
车轮在潮湿的道路上飞驰,司机先生是这里的本地人,他对我们因为下雨而放弃出游的想法十分费解。我不好意思地苦笑了一声,我们这群人果真不适合当走天涯的侠客。习惯了完美主义的人们将计划做得天衣无缝,我们重视纠正计划,求得天时地利人和之时再出游,但很少为“游玩”这一活动牺牲自己的完美主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好像可以为了一切被称为重要的事情而克服困难,面对无法改变的现状咬紧牙关去完成,我们有时美其名曰“英雄主义”。若有的人为了游玩这件事去耗费面对生活的勇气,他们会被人们称为“自找苦吃”“不懂变通”。
但世间那么多奇妙景致都不是在人们精心准备之下出现的,它们往往出其不意,只留给那些执意前往的人看。于是那些奇妙的景观因为很少有人遇到,被称为“奇迹”。同样,越来越多的人用“千篇一律”来形容所见之景。
里尔克曾经给年轻的诗人写信告诫:“以深深的谦虚与耐性去期待一个豁然开朗的时刻,这才是艺术的生活,无论是理解还是创造,都一样。”自然之境固有,本无美丑之分。而人类固化的思维总是让其失望而归。我们怯懦胆小、斤斤计较,而能以谦虚和耐性去期待自然之妙趣时刻的人,我们称之为“冒险家”。殊不知这才是人类真正走出“村落”、踏过人与自然分界的第一步。
飘逸的思绪牵引着我迈向一个高台,一座跃下去便是洱海、环绕着山石的高台。这样远望,我便与天面对面地欣赏,它望向我少年的面庞,我望向它。它是金光闪闪的,云疏密有致地排列着,背后的霞光不慌不忙地穿过云洞,打通了传往人间的通道。它又如同一面华丽的刺绣,用天然的光与影绣出了平铺着的繁杂花纹。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此话不假。它无须耗费心力便可创造出人们可以惊叹一辈子的美景。天上的神仙一挥手,便向人间洒下良辰美景。我知道关于神仙的传说都是古人无法探寻关于宇宙与万物的真理创造出来的,但在美妙的此刻,在这儿,真理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
雨中的海舌公园蕴含着一种宁静的勃勃生机。我们一行三人走在水坑遍布的小泥路上,绿柳蒙上了雨雾,变得慵懒。柳随风动,在茂盛的树林中,风声却微不可闻,我们像是走进了影影绰绰的迷宫。海西与海东风景各异,海西的水中生长着树木丛林,湿地众多。湖上茂密的草海怕是藏匿住了无数少女的心思,她们与情郎约定乘上小船穿梭其中,求得一份同舟共渡的佳缘。纳西族女孩不屑藏匿自己的爱意,在她们年少的目光中早已有了某种对世事的了然。枯木静静地卧在水中,它们是不是已经在这儿定格了数千年,让生命的最后一刻显得优雅而庄严。但此刻的它们看起来依旧充满平静的智慧,或许它们也同样期盼着远方的海鸟,海鸟会带来种子,种子能孕育出新的生命。
些许穿越云层的阳光在雨中慢慢地洒下,洒向那墨蓝黑沉得像斜谷一样的夜。“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他披蓑衣踏草鞋,走进我的眼中。内心突然激起的澎湃涌遍全身,我望着眼前空无一人、只有蒿草遍布的道路,潜眠在内心最深处的感知霎时顿悟。人类的喜乐怠惰,若不趋自然,则不再自然。
云南的天气反复无常,此时的雨让天气阴冷起来,坐在暖和的车内,困意也突然袭来。我们的汽车在镇子上的小路上随意穿梭,人们不慌不忙地避让着车子,与其说他们是对汽车习以为常,不如说是他们对外界变化自有一种淡然与包容。我带着一身清新久违的泥土气息,望着那散植于民居墙下的粉红色铃状小花,一下子竟无法回过神来。刹那间,我便听到了风声、雨声、落叶声、山川声、水流声,似乎是所有的声音被天衣无缝地裁剪在一起,慢慢的,它们变成了一种声音。我扭过头去,问那些窝在房子里一下午的人:“你們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他们不解地望着我,木愣地摇着头。那是一种轻微得几乎要被忽略掉的声音,但却是排山倒海的、势不可挡的万物生长的声音。它好像还在说:“你是这世界上又一个能听到我们气息的人。”
作者简介:
麦子珩,女,华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