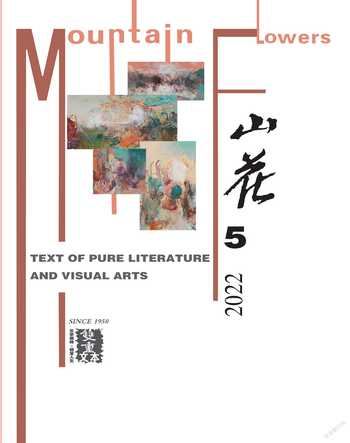戏鲸俱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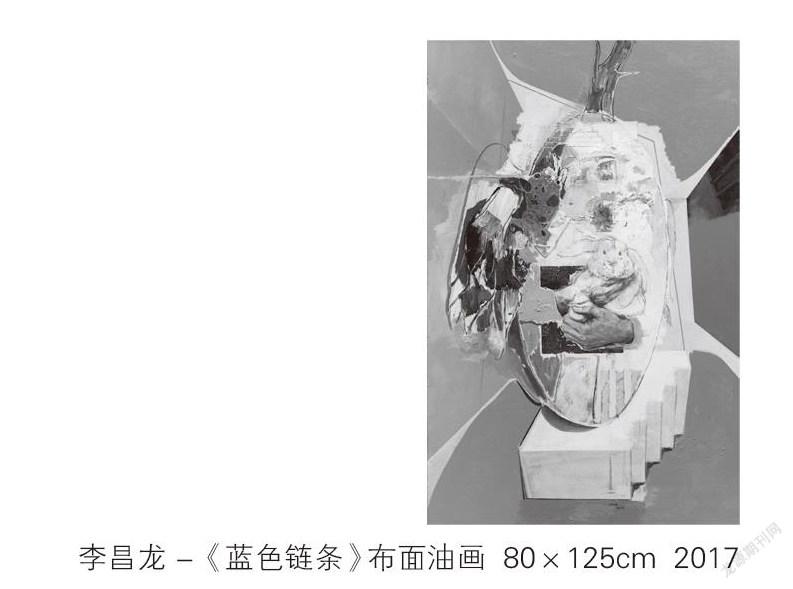
1.拼车
最新拼车消息,以下每一车都需要救命:
12月5日(周六)14:00《小姐姐你好》3=3……
戏鲸俱乐部的群里跳出消息。3=3,那就是这车已经有3人了,还缺3人。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条救命的消息。我正恐惧于不知如何度过这个周末,或者说该如何度过接下来的每个周末。我的意思是,体面些,克制好随时想蹲地上哭的冲动。
戏鲸俱乐部距我的住处有点距离。地铁要坐六个站,再加十五分钟单车。现在是锦都的12月,又是黄昏时分。冷风将我的皮肉、骨头都吹得簌簌作响。我才意识到,路上行人稀少,骑单车的似乎只有我一个。人们都知道如何正常地活着。
原来,我是和整座城的人都分开了。
“您已偏离路线,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眼看快要接近目的地,不论我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地图导航都在用机械的电子音重复这句话,语调冷漠,以至于我都听出了一些讽刺的意味。我好讨厌“您”这个字,“您”有时意味着对话的两个人毫无关系。我把单车锁好,然后站在风中,不动了。我不动还不行吗?厚重羽绒服里的这个肉体,是多么累赘呀,连我自己都想拒绝呢。——若是他看见此刻站在大街上的我,一定会庆幸自己的英明果决。我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出门。就在这时,我抬头看见了“佳期公寓”四个字。
戏鲸俱乐部在佳期公寓C6楼。这是一个住宅区。我穿过绿化带和健身器材区,摁了门铃。在等开门的时候,恍惚以为是来朋友家玩,男朋友或女朋友都可以,反正应该是认识我、在意我的人。
“哈喽!”老板一开门就和我打招呼,一个矮胖的戴眼镜的年轻人。我才清醒过来,这是一个陌生人。
我打起精神,也用热情随意的口气回答他:“哈喽!”
进屋,看见客厅里每个角落都坐着人。橱柜里摆着一盒盒剧本,还有好多蓝色小鲸鱼的毛绒玩具。这就是戏鲸俱乐部了。
“嗨!”
“来啦!”
“你玩什么本?”
“《小姐姐你好》。”
“噢,是七点的。这边先坐下。”
好几个人和我打招呼,但我们都没有问对方姓名。只有老板被称呼为胖哥,显然是一个贴切的绰号。他行动迟缓,眼神飘忽,一眼看过去就是那种大多时间活在游戏里的人。但他皮肤尚未松弛,大概也和我们一样,二十来岁。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用俱乐部这个略显老派的词。
我回应着人们的招呼,心里还是觉得拘谨。他们穿得比我时髦,女生们全都化了眼妆,我却还戴着眼镜。还有人带小狗,小狗和它的主人穿一样的岩灰色毛线衫。人们努力为我在沙发上腾出了一个位置。我看着那个可怜的小空位,把我的包放上去,说道,抱歉,我先去洗个手。
我迫不及待想去洗手間照镜子。没人关心你的姓名,但是所有人都会注意你的外貌,或者,没人注意。网上有同城活动小组,组长直接宣称长相不好的就不要申请入群了。老实说,我还私下给这个小组长发过我的照片。那张照片是我留长发时的自拍。此刻的我,已经是短发了,或者说一言难尽的发型。我是昨天刚换的新发型。剪完之后我就时时留心街上、地铁上人们的发型,结果总是沮丧地发现,再没有人比我的发型更失败的了。在洗手间的镜子里,我缓缓地把鸭舌帽戴回去,将几绺在那该死的发型师手下幸存的碎发别到耳后。我的脸型不适合戴任何帽子,只是现在这样境地,戴帽子似乎还是更好些。
进入《小姐姐你好》的房间里,主持人给每个人发了一个角色的本。大家开始读本。二十分钟后,我先作自我介绍:
我是王韦雨,今年26岁。出生在农村,但刻苦读书,大学毕业后留在了锦都。我深爱着一个人,但是我不会说他的名字。
和我一起坐在沙发上的长发高个男生接着说:
我是张海,今年27岁,我是一名工程师,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可以看到王韦雨,阿雨……
他一边说,一边指了下我,还深情地朝我望。我愣了一下,内心居然涌起一股真实的感动。该死,我好久没有这种感动的感觉了。
梁子鑫、林玲、刘巧梦、夏毅……我在瞬间就拥有了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还有闺蜜、姐姐、侄女等。等大家介绍完毕,房间里的一只柯基叫了起来,就是刚才我一进俱乐部就看见的那只时髦狗。它朝着主持人不停地汪汪叫。
“奶奶不高兴了,它还没介绍呢。”
大家轰然笑开。我的邻居林奶奶居然是一只狗,不过,有什么不可以呢?
介绍完毕,主持人又让我们接着往下读本。对于经常看小说的我而言,剧情未免幼稚。爱不能、恨别离,最后因为阿尔茨海默症和肺癌晚期再彻底失去记忆和爱人,内容接近于我妈看的晚八点档电视剧。
编剧非常有心地设计了小剧场部分。
“你怎么忍心抛下我一个人?”房间里的灯光此刻被调为暖黄色,钢琴声若有似无。我带着哭腔,说阿雨的台词。很奇怪的是,情绪的开关就在这一刹那被打开了。
“我可不可以最后再问你一句,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是吗?”念完这一句,我就转身到我自己包里找我的纸巾。那是一种上面有小帆船、小茶杯图案的可爱纸巾,就算是浸了很多水也不会有纸屑。我伸手在自己的包里摸索好久,眼泪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干脆停下来,让泪水流淌一会儿。
就是这么滥俗的台词。就在前几天,我问过他一模一样的话。我不得不惊讶地发现,像我这样一个业余也写小说,常常给人物设计对话的人,在崩溃时,说出来的也无非是这么滥俗的话。我必须对晚八点档的电视剧怀有更多敬意了。
结束的时候,我发现垃圾桶里都是刚刚扔进去的纸巾。我的“侄女”刘巧梦正抱着她的狗,还在意犹未尽地擤鼻涕。可是一旦恢复游戏之外的聊天,她基本说每句话的时候都杀气腾腾。
“射手座男生都是渣。”
“老娘谈得少。”
“每个月花一万五还多呀,那买东西的时候怎么着也得四万块呢。”
我也迅速恢复常态,披着羊绒大围巾,挺直了腰,交叉着腿,津津有味地听她说话。我们继续闲聊着,还挺像刚刚拍完戏的演员。话最多的是梁子鑫,一个1990年生的男生,他年纪最大。他饶有兴致地带动全场聊天。你们都哪一年的呀,你们都做什么工作的呀,你们每个月花多少钱呀,你们谈过几次恋爱呀……刚开始我还认真回答,渐渐我发现,他其实并不是太在意其他人说什么。
我们当中有一个服装学院模特专业的女生,大一,2002年出生的,耀眼夺目,像是从国贸商城的橱窗里走出来的。梁子鑫每次问到她的时候,就会前倾着身子。
“我们下次一起去密室玩吧。”
“我加你微信吧!”
我清楚这些对话里其实并不包括我,于是拿上包,先推门出来了。也不知道那个男生最后有没有加到她的微信。我又拐进洗手间,感觉自己想蹲下来哭,就给我远在老家的发型师阿承发微信。
“剪了刘海,人生跌落谷底。多久才能长回来呢?而且全头都剪得支离破碎的。”
“那么明显?刘海怎么样?”
“眉毛那。”
“你被忽悠了。”
“半年才能恢复?”
“要。至少。”
“快疯了我。”
“空的时候发张照片我看下你刘海。”
“不要看了,惨不忍睹,就是要多丑有多土,要多土有多丑。”
“等回来的时候我帮你改过。”
“还有改的余地?”
“有我在,别怕。”
看到阿承发的这句话,我差一点又要情绪崩溃了。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我会需要靠发型师来支撑我的人生。更没想到的是,我会在失去爱情的同时还给自己剪了一个失败的发型。美和好需要日复一日地经营,而毁坏与堕落只需要一瞬间。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唉,接下来的半年可真是漫长艰辛呀。若单单只是失恋,恐怕都不需要熬这么久吧。
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我在走廊里和一个长发高大的男生撞了个满怀,抬头一看,正是张海。
他望着我,笑眯眯地说:“再见阿雨。”
空气里有一种甜蜜的味道,仿若还在戏中。我慌慌张张地挥了下手,走出了佳期公寓。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不需要介绍自己的名字。
我们再也没有见过。
2.魔石
魔石真的存在,宛兰,这次你要作出正确的选择,否则你一辈子都要在懊悔中度过……
我在公布自己被触发记忆后的一段自言自语。
这是我第六次来戏鲸俱乐部了。虽然我住得离这里有点远,但我喜欢“佳期公寓”这个名字,给人一种未来值得期待的感觉。地铁坐六个站,到站后我会打车过来,大约十五块钱就好。我也可以正常地在这个城市活下去。
这次我上的车是惊情本。我是秦宛兰,和安在溪在白鹿宫中从小一起长大。白鹿宫周围是一片原始森林,人迹罕至。传说森林深处有一个石碑。只要用自己的鲜血染红石碑,就可以触动时间机器,回到过去的某个时间点。
十六岁那年,白鹿宫遭仇杀,我和安在溪在一片混乱中分散了。此后,我们开启了漫长的寻找对方的岁月。五年时间过去了,我仍然对安在溪念念不忘,一边习武练功,一边等待和安在溪的重逢。
这个剧本最大的疑点是,在我的记忆中,总有两个时间段的记忆:在A时间段中,我不堪逼迫,选择和蒙面黑衣人一起跳下悬崖,此生也永远错过了安在溪;在B时间段里,我选择死守,直到安在溪来拯救我。
大家推断认为,A时间段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因我当初作出错误选择,后来我找到魔石,不惜划伤自己,用鲜血触发时间机器,再次回到悬崖边。这一次,我无论如何都苦苦等待安在溪的到来,这样才有了B时间段的记忆。
这时,胖哥推门进来,嘿嘿一笑,说道,提醒一下,这是一个纯本格推理,没有穿越,没有分裂。我们都大声质问,原来你听得到我们说话呀。
胖哥说,那是,我都在隔壁听着呢。他还在角落的黑板上写字:“五个死者。”
五个死者呀?我们只发现了三个死者。这下全错了,还以为到可以复盘了呢。几个玩家全都颓然地坐回椅子上。
过了一会,大家又开始推理,或双手撑着,分析铺满桌面的线索卡片,或咬着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反复读自己的剧本,或是在角落里画事件草图。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了。坐我旁边的一个男生嚷道,不行了,得来点咖啡提神。他问我要喝什么,我犹豫了一下,说,卡布奇诺,热的,半糖。咖啡我一向只喝热卡布。我犹豫的是,该不该让他帮我点。
咖啡来了。我们端着咖啡,继续研究,乍一看,大家站在一起分析案情的阵势还挺像那么回事的。我知道,屋里的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很享受这样的扮演。
“你的发色需要经常补吧?”咖啡喝掉一大半,推理还是毫无进展,我开始注意别人的发型。另外一个玩家,一个年轻女孩,林允墨,看起来比我小两三岁,二十岁左右吧。她有一头烟灰色的长发。
“是的。差不多每個礼拜就要补一次。”
“真好看,羡慕你!我的人生基本被一个蹩脚的发型师毁了!”我今天没有戴帽子,我还是不习惯戴帽子。和她说话的时候,我眨巴着眼睛,想尽量提醒对方多注意我的五官。其实这女孩五官挺好的,除了那可怕的发型——我希望给她留下这样的印象。如此我才能取得继续和她聊天的资格。
“你可以买一个假发片,或是染一下颜色,也会好些。”林允墨说。我心里感激不尽,频频点头。我当然不会去把头发染色,那样的话,刘海就长得更慢了。我现在唯一的指望是刘海夜以继日地凶猛地生长回来。假发片又嫌麻烦,就跟隐形眼镜或美瞳一样。我感激她和我聊天。我现在一点都不喜欢我自己。我以为也没有人会喜欢我了。
令我惊喜的是,林允墨看着手机说,哇,原来外面下雪了,我要去看雪。
我也去。留下安在溪和其他两个男的在屋里,我们走到公寓门口,看着雪花一片一片地飘落下来。一时间,没有人说话。我完全呆住了。
“下雪的时候,我们去吃牛肉火锅。”他熟悉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我似乎看见他正站在我面前,一脸灿烂地对我笑。
我慢慢蹲了下来,捏起一小团雪,冰冰凉凉的。我喜欢雪。在锦都,可以体面地随时蹲下来,大概就只有这样的下雪天吧。我蹲着,又努力仰起头看雪,不让眼泪流出来。
林允墨没有注意我,她在用手机拍视频。过了一会,她就进屋了,没有等我。这很正常,我却还是感到了一些失落。自从发现永失我爱后,我就开始渴望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爱。事情就是这样,有时候你失去一个人,就需要用整个世界来填补。
我到底是如何失去他的呢?雪下得很大。我不得不回忆起自己作出过的一个愚蠢的选择。我多么希望魔石真的存在,时间回到过去,回到我作出那个愚蠢选择前。
当然,这只是幻想。我还能分得清现实和剧本。现实是,我的爱情消失了,就像雪落于地,一场空。我改变不了过去,我一生都要生活在懊悔之中。
我慢慢站立起来。房间里,还有青梅竹马的安在溪等着我呢。他会用余生来寻找我和原谅我。
房间里,大家已经一致同意复盘了。全本所有悬疑细节被一一解答。原来这是一个同时存在的平行世界,秦宛兰和安在溪都有一个双胞胎,还都取一样的名字。一个秦宛兰选择了和蒙面人一起跳下悬崖,另一个秦宛兰则选择在悬崖边苦守,终于等来她的安在溪。
也就是说,在另一个真实的平行世界里,秦宛兰和安在溪终于在五年后找到了对方。他们回到了白鹿宫,从此幸福甜蜜。
因为玩本的时间太长了,结束后,大家都没有力气聊天,径自离开了戏鲸俱乐部。
外面雪已经停了,在绿化带、人行道上都留下一层薄薄的白。街边停着的一溜汽车上也全都落满了雪。有人在汽车上写了英文的“我爱你”;还有人写“2020”,旁边画了一个爱心。
安在溪和他的两个朋友出公寓门,我也出公寓门。安在溪和他的两个朋友右拐,我也右拐。安在溪和他的两个朋友站在路口等红绿灯,我也站在路口等红绿灯。我把手从暖和的口袋里抽出来,朝安在溪挥了挥手。
安在溪愣了一下,略带惊讶地说道:“你也往这里走呀!”
是呀,我也往这里走,我也要去吃饭。我一个人。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吃饭呢?我在心里这样回复道。可是,实际上,我没有说话了,我只是朝他点了点头。但是安在溪恐怕连这个点头都没有看见。绿灯亮了,他和他的两个朋友迅速地过街了。
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吃饭呢?我一个人没办法吃牛肉火锅。下雪了要吃牛肉火锅。还有,今天是我的生日耶。我心里想着这些,并不过街。我想着刚才戏鲸俱乐部里,安在溪明明知道我就是那个凶手,却为我百般辩护。他还说他总亲手为我做二锦馅。他用肉嵌油面筋一只,豆腐皮包肉五只,香菇一朵,置于陶罐,加鸡汤、火腿片、冬笋、糖、酒等佐料,用棉纸封罐,上蒸笼蒸煮而成。当然,我并没有真的见到什么二锦馅。这一切都是想象和表演。
唯一真实的感觉是,我饿了。
我拐进路边的一家火锅店。我别无选择。我感到再不给自己喂点东西,我那臃肿累赘的身体可能不是蹲在地上,而是瘫倒在地了。
一盘牛肉、一盘土豆、一盘白菜、一盘面条……一个人吃牛肉火锅一点问题都没有,只要你付钱。等待火锅的汤烧开的时候,有一个微信视频通话进来。是我妈。远在千里之外的她,祝我生日快乐,并且问我今晚怎么过的。我给她看我点的一大堆食材,然后我妈就在微信里看着我吃。
我忽然问道:“妈,我是你唯一的女儿吗?我有没有一个双胞胎姐姐还是妹妹什么的?”
我妈看我的眼神里到底还是流露出了同情。
在锦都,我当然也有一两个朋友,但我不想见任何朋友。我害怕见朋友,我只想见陌生人。在陌生人面前,我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没有令我懊悔的过去。我不需要怜悯,我能处理好一切问题。我愿意用我所有的鲜血,触发时间机器。——我必须终止这样的想法了。
从火锅店出来,看见街边停着一整排落满雪的车辆。我选了其中一辆,在车前盖上,用手指缓慢地,担心写完似的,一笔一划地写了他的名字。写完之后,我看着那个熟悉的名字,又一笔一划,轻轻地将那个名字擦去。每擦去一笔,我都感觉到一种刀尖划过心口的无声的疼。
我不能留在幻想的悬崖边。我其实很清醒,现实世界中,没有时间机器,没有双胞胎,没有平行世界,没有我的爱情,只有白花花冰凉凉的雪。一碰即化。了无痕迹。
我不能再来戏鲸俱乐部了。
3.绝杀
你是那个说真话的精灵吗?
青婆是海妖的仆人吗?
绿精灵是说真话的精灵吗?
主持人说:你们乘坐的轮船触礁,昏迷后醒来时发现已经在海岛上。你们必须杀死海妖,救出你们的爱人。三只精灵可以提供帮助,但它们一只说真话,一只说假话,一只随机说真话或假话。现在,你们可以问三个问题,来区分它们。
我们一群人坐在房间里,背景音乐是海浪的翻滚声,灯光昏暗,似乎真的躺在海岛沙滩上。这个问题不难。我们很快就提出了正确的方案,然后顺利拿到了火把、迷魂草、毒蝎、匕首、龙鳞等。我们要去杀死海妖。我们有一个小时的行动时间。
行动组人员包括:长卷发穿皮草的宫姐、航天司高层的儿子阿磊、花衬衫娘炮男、银链刺青肌肉男,還有抱笔记本电脑一边工作一边和我们玩的十三姨和一头乌黑长发穿唐装的茶叶店主……还有我,在事业单位上班却没有编制、业余喜欢写小说的工作人员。
一年多过去,我每个周末还在玩剧本杀,本格、变格、古风、情感、欢乐、沉浸类型都玩过。我不仅继续去戏鲸俱乐部玩,还加入了很多玩狼人杀剧本杀的群。不同于戏鲸俱乐部这样的店家,狼友群聚会还多了一个自我介绍的环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从这一刻开始,每个人都会一脸诚恳地隐瞒自己的真实信息,基本每次都会为自己创造一个身世。得益于大家浩瀚的想象力,我听到了各种职业:机场工作人员、河流环境管理、标准化设计、投资人、种茶人、奶昔营养师、在读硕士、火锅店老板……就算你不在乎对方的任何真实信息,单单把眼前这个活人和他的网名、朋友圈照片对接上,也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后来我大致知道了一个规律:越是在网上活泼俏皮鬼灵精怪慷慨豪迈的,在现实中基本貌丑内向肉多话少目光下垂。我的朋友圈里经常有各种美食的照片,天知道,我从来都不会做饭,我那小得可怜的出租屋里,甚至没有厨房。
我想见人。我想见陌生人。我又不能像过去年代的人们那样,聚集到村口的大树下,我只能去酒吧和桌游馆。玩狼人杀剧本杀阿瓦隆这样的发言游戏,至少还有人认真听我说瞎话。
那天下午我们齐心协力杀死海妖后,氛围还不错,有人提议一起吃饭,一桌的人就真的都来了。反正我们回去,也是一个人回到出租屋里点外卖嘛。十三个人,坐在那里等上菜的时候,又开启了自我介绍环节。
“我是米加,可能是这里比较老的,1992年的。我是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的,学的是河流环境管理。现在在一家化工厂上班,基本上一半时间跑现场,一半时间在办公室看材料。”
全部人自我介绍结束后,空气突然安静了下来。实在无话可说,又有人提议,那我们线上玩狼人杀吧。刚好一个法官,十二个玩家。法官在狼人杀英雄榜上开了一个房间,大家进入,线上摸牌。玩的是“预女猎守”。
“狼人请睁眼,选择你要击杀的对象……”
“女巫请睁眼,你有一瓶解药,一瓶毒药,你选择用解药还是毒药?”
“预言家请睁眼,平民是这个手势,狼人是这个手势,你查验的玩家是这个。”
天亮了,玩家发言。
“我是预言家牌,我验过了,3号是金水。这轮我们先归一下票,把5号投出去。”
“这轮我是神牌。警上的有五个玩家。12号刚才的发言我觉得有问题,他的逻辑是混乱的。我不觉得他是个好人。”
“你盘我是倒钩被打脸还少吗?那个狼坑我觉得就下2吧。”
“你们凭啥说女巫开毒开早了?我是一个好人。我觉得女巫开得挺好的。6号你不愿意跟我讲话,我发言你都不愿意听,那把这6先出了吧。那至少11号还愿意哄哄我……”
“8号已经失心疯了,9爆是为了要保1……”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一次在餐厅玩这个游戏的缘故,我觉得很不舒服。想到过去一年来,我每个周末都是和这样的陌生人共同度过,心里涌起一阵难过。我才意识到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们。他们在我眼中一律面目模糊,没有一句真话,丝毫都不值得信任,不管是在游戏里,还是游戏外。他们甚至会在朋友圈发布自家待租房屋的信息,或是晒别墅豪车的照片。可是,看看我们这一群人的吃相!
菜上来了。一切归于平静。我没有走。再想想,回到出租屋里一个人吃外卖的感觉!
饭吃得差不多的时候,我走出餐厅,想到外面抽根烟。坐我旁边的男生也跟了出来。他为我点火,我说谢谢,他说,不客气。他也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后,又说,我上次见过你,上次我记得你说你是一家出版社编辑。他还得意地朝我一笑,说,我不会认错人的。
我镇定地继续吐了好几个烟圈。我能怎么办呢?我总不能把所有见过我的人通通灭口吧?也许将来会流行和机器人聚会,只要它们会陪我说话就好。
“我一见你就喜欢上你了。”
“谢谢。”我说谢谢的口气和刚才谢谢他为我点烟的口气基本一致。毕竟一年多过去了,我的发型早已恢复了正常。我留着完美的发型,化着精致的妆容。我早就不会轻易相信人们说的话了。这让我成为了一个狼人杀剧本杀的顶尖高手,也让我很有安全感。
“我想和你约会。”他说。
我被烟呛了两口。说实话,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看过他的脸。
“外面风好大,我们进去吧。”我礼貌地说。一定要保持做人的礼貌。记得有次我觉得和一个女生聊得来,剧本散了以后我们还手挽手一起逛锦都国贸商城。还有一次,是认识了一个男生,他彬彬有礼地送我到地铁里,看着我上车,还和我挥手。这两个人,我和他们分开以后才想起连微信都没有加呢。想到以后大家再也不会见面了,所以要尽可能地礼貌。
这个男生却见了我两次。但也不是什么问题。锦都可以玩狼人杀剧本杀的群太多了。我换个头像和网名又可以重新亮相。这个月是朝阳米加,下个月是西三环苏晓,再下个月是国贸妮妮,景恒街白薇……我是海妖,每个月要吃十个人类的灵魂。我是生物学教授,致力于研发治疗AS疾病的药物却卷入了一场阴谋。我今年二十五岁,偷了时空罗盘,穿越回十年前,却被时空司判为闯入者,灵魂被关在黑镜中。只有爱我的人日夜不停地喊我的名,才能将我的魂魄召回……
我每个周末都给自己一个虚假的身世。我玩狼人杀玩剧本杀玩阿瓦隆,玩的是孤独,杀的是寂寞。也许我只是不敢面对现实。可是我为什么要面对现实?我在剧本中给自己造了一个桃花源。在这里面,爱到死去活来,爱到穿越时空,爱到互换灵魂,只要一百多块钱。
有次玩完剧本杀,坐地铁回去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特别的年轻女孩。她那乌黑亮丽的一大束长发柔顺地垂在胸前。她的膝盖上摊开着一本书。她静静地低着头,在看书,仿佛与人群完全隔離开了,但或许是感觉到了我在盯着她看,她忽然抬头也看了我一眼,甚至还笑了一下。她这一笑的时候,顺便还把书立起来了,我看清了书名:表演的艺术。
我仓皇地下了地铁。或许女孩并没有真的笑。她到底是女巫、平民、预言家、守卫还是狼人呢?我已经有点分不清现实和幻觉了。
4.表演
我看见镜子里的自己笑了。
访谈时间:2020年2月2日
访谈方式:面谈
访谈人:陈美者
被访谈人:米加
访谈内容:
陈美者:玩剧本杀多久了?
米加:一年多吧。
陈美者:多久玩一次?
米加:每个周末呀。就周六和周天两天。
陈美者:为什么喜欢玩?
米加:刚开始玩是因为那时候刚失恋,玩本的时候可以尽情哭。后来玩多了就喜欢在本里谈恋爱了。我都快三十了。其实也没有很开心。玩剧本杀呢,至少在那四五个小时里,我是被人爱的,也是爱着别人的。有次玩的一个本,是说宁愿用自己的灵魂换爱人的灵魂复活。一屋子的人都哭了。太感人了。
陈美者:都是和陌生人玩?
米加:只想和陌生人玩。见一面以后基本就不会再见了。
陈美者:玩这么多的本,有没有遇到还想再见的人?
米加:有呀,有次坐在我身边的小哥哥我很喜欢。我主动加了他微信。
陈美者:那次不是剧本杀,是狼人杀吧?穿灰色毛衫那个吗?确实是长得好看。
米加:对呀。而且他说话很温柔。每次都跟我说他不是狼,每次我都相信了。我真的有一年多时间没有过对现实生活中的男生有心动的感觉了。
陈美者:但那天他拿了一个下午的狼牌呀。后来和那个男生怎么样了?
米加:没有后来了。他都不回我微信。我觉得算了吧。其实我现在也挺害怕真的爱上一个人。你明白的。(笑)
5.日记
我的小床上摆满了小鲸鱼的毛绒玩具。那是戏鲸俱乐部的胖哥送给我的,准确说,是积分兑换的,在俱乐部每消费满500元就送一只小鲸鱼毛绒玩具。
我在一群小鲸鱼中,沉沉地坠入深海般的梦境。现在,谁来杀死海妖,唤醒我的灵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