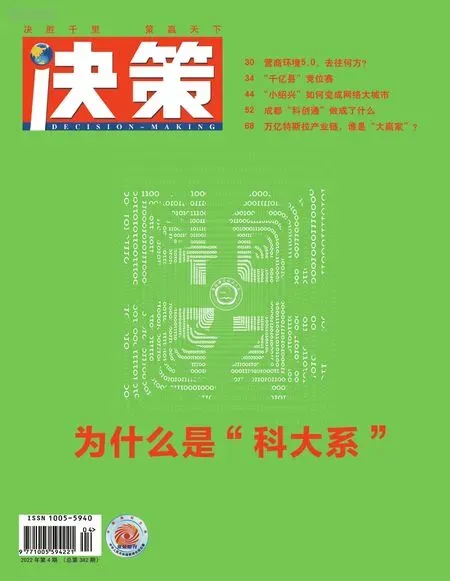科创向产业的跳跃需要“三家”共振
转什么、谁来转、怎么转?
四口井分别为S1、S2、S3、S4,K49+818 段降水井布置示意图见图2。(注:G1、G2为水位观测孔,不在本方案设计范围内。)
如图4所示,假设伸杆已伸出但尚未与任何伸杆支撑组件相接触,该段伸杆质量被其根部和滑车共同承担。相应的平衡方程为:
没得转、不敢转、不好转。
这是科技成果转化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原始创新成果没有产业化,就好比捧着金饭碗讨饭吃”,对于任何一个科创资源丰富的省市来说,“墙内开花墙外香”现象尤为值得关注,因为科技研发成果不会自动变为经济优势。
其次,“源”有了,怎样才能流长?答案是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贯通起来,以市场导向、企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让科学家研判技术前景、让企业家发现市场需求,才能提升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效能。
首先,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是策源地。正如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一直疾呼的,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研究成果的强大,基础研究创新能产生颠覆性技术。这也是破解转什么、没得转的难题。
第三,破解怎么转,离不开一个关键因素——资本的力量。让市场验证技术价值的最敏锐体现,就是风险投资家是不是敢投、愿投,最好是能一投再投。不管是在美国硅谷还是在北京中关村、深圳南山、杭州滨江和合肥高新区,现实中无数的转化成功和失败案例都表明,只有资本助力,才能实现“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的有机联动。
但怎样才能实现有效转化?这就是大家熟知的“惊险的一跃”,而要实现从科创向产业的跳跃,需要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的同频共振,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正向推动。
如何才能将丰富的科创成果变成发展的胜势?经济发达地区的实践证明,必须在转化上做文章。
一般说来,语音成分(元音、辅音)的借用,往往是从借词开始的,而借词是语言接触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现象。按照语言学家说的,如果出现语法成分的借用,那就是“深度影响”。至于这个说法是否合理,我们暂不讨论,但在青海汉话中出现的非现代汉语所有的一些语法现象,和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土族语、撒拉族语有很多一致的地方,特别是和蒙古语更加接近。
李建军[1]认为,农业研究与开发体系大致包括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私人公司和其他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以及各个国际化农业中心等,而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以农业科研院所为主体,以农业大学为主干的农业研究与开发体系和独特的农业自助体系,这些体系的职责是实现农业技术创新。农业技术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了农业技术推广在内的多个环节。本研究的农业科研人员指的是农业科研院所、农业大学内从事农业技术创新的人员,其工作职责包括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农业推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
要实现这个联动,体制机制创新是根本。只有加快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体系,构建转化生态,建设新型研发机构,才能有效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谁来转、怎么转、往哪转,以及不敢转、不好转等一系列难题,真正将科技创新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
安徽之所以连续多年在区域创新能力上排名全国前十位,一是科技成果产出的支撑,二是在成果转化上创新招数,大力培育新型研发机构,设立了中科大先研院、中科院创新院、合工大智能制造院、清华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打通了科技创新到产业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同时,创新“以投带引”的新打法,健全前沿科技“沿途下蛋”机制,构建孵化载体,上演了被业界称为“神操作”的转化案例——人工智能、新型显示、存储芯片、集成电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兴产业,以及量子通讯等未来产业的“传奇”故事,让安徽在先发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图谱上,占有一席之地。
更重要的是,这些现象级产业又催生出相对应的微电子学院、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研究院、AI研究院等,特别是规划建设“科大硅谷”,整合政产学研金服用资源,形成创新链赋能产业链、资金链助推产业链的互动循环。
科技创新是“栽树工程”,栽大树和育丛林共同构成生态体系,而金融投资就是“浇水施肥”,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的同频共振,是建造从科创到产业的“桥”与“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