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禁足期的保健药
[法]辛西娅·弗勒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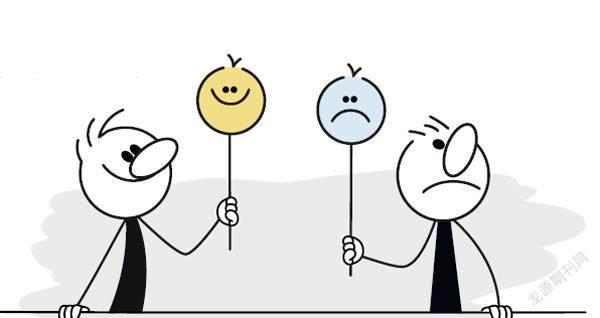
隔离有它严肃的地方,但隔离3.0(隐喻互联网3.0时代)也有滑稽和荒诞的时候。它秉承了即兴喜剧的伟大传统,而数字工具又为它增添了技术感、画面感和互动感。幽默的“调节”作用并不新鲜,近年来,幽默已经成为社会、文化和女性主義宣传中的重要元素。仅举一例,200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蒂莫西·亨特——他绝不是为了搞笑——曾针对女性发表过一番荒唐言论:“当她们在实验室里时,会发生三件事:你爱上她们;她们爱上你;你批评她们时,她们就对你哭。”女科学家们随即在社交网络上发起了以“性感得让人分心”为标签的“呼应”,纷纷晒出她们在显微镜前哭泣,或者自责跟男同事又谈起恋爱来的照片。
在这个标签下,每隔一个小时,就会有逗人发笑的推文让我们一展愁眉。这就是幽默的作用:它在产生禁锢感、阻滞感、屈从感的地方产生自由;它行使解构的权利:这样或那样看似——甚至就是——悲剧的事件被解构了、被颠覆了、被易容了,不是被否定,而是被超越、被升华;转瞬之间,悲剧不再坐庄,去悲剧化开启了,它是正向心理投射的产物。这可以算作逃避,但也可被视为简单的中心偏移,向旁边挪一步,脱离现实,腾出距离,渡往彼岸,切换视角。
当然,幽默还有其社会作用:它在社会分裂之时组织社会,在纽带断裂之时维系纽带,甚至在绝望人间塑造人性;总之,幽默以自发的方式生产,却无决心和信心带来的负重感。它不咄咄逼人、不激昂陈词,只留欢声笑语,让我们这些船骸继续漂流。其实,幽默是能产生运动的,因而在禁足期间,幽默是一剂促进身心运动的保健药。“所以,反讽就是意识的流动本身,头脑不断废黜自己的造物,以保持劲头并继续主宰符号、文化与仪式”,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在其1964年的作品《反讽》中如是说。
这剂传统良药可消解因过失而涌上心头的怨恨、气恼和愤怒。扬科列维奇再次告诉我们,幽默做到了“对整个现实的尊重”,尽管它要经历自身的微渺、微末、琐屑和无谓。它的“无谓”是为了更好地接受。最先尝到这滋味的是我们的医护人员,他们借此稍做休整,以恢复体力、抓住眼前的生命。
(摘自《世界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