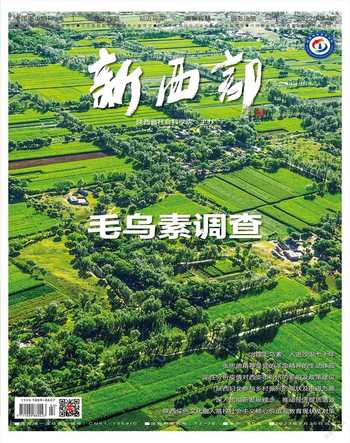张应龙:一个人和他的二十年
呼东方



2020年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公映后,邓超扮演的角色乔树林原型人物之一的张应龙半跪着扬沙的照片,出现在了电影中那所学校的大屏幕上。二十年里,张应龙与毛乌素的关系,是一个从盲目植树造林到尽力地通过科学、信息、科技力量架构起一种近自然恢复原有生态系统的过程。他说,“如果有一天,毛乌素生态系统能够自我循环了,才能说明沙漠真的消失了。”
沿包茂高速一路向北,从榆林进入神木境内,公路两边的灌木或者樟子松林后面,会时不时闪出大块大块枯黄色的草地。
车从红碱淖高速口驶出,一抬眼就能看到棕色旅游牌上标识——毛乌素治沙造林基地。车速降下来,路两边已经完全是平整的草原,草地上大片的羊群、还结着冰的湖泊(当地人称之为“海子”)、湖岸边半人高未割的黄草、公路中间站着的牛和羊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过往的车和人……如果不是3月初陕北大风吹得人站不稳,天空有扬起的沙尘,这些景象还真让人觉得行驶在澳洲、欧洲平原或者安纳托利亚高原上。
棕色旅游标识牌指引着车子驶入草地深处,从天然海子到草甸,再逐渐过渡到大片的樟子松与红松混交的林带。此前张应龙从微信发过来基地位置,百度地图显示是锦界镇乌沟路北300米。按着导航,车在这片林带行驶了10多公里后,左边林带里有了几个连接的海子,海子后面的植被中,出现一个有三幢建筑的院落。
在稀少人烟的地方,突然出现如此人工精心规划的建筑群,尽管导航显示距离终点还有1000多米,但凭直觉这里应该就是毛乌素治沙造林基地(以下简称“基地”)。虽然基地与想象中的不大一样,但仔细想想,又觉得符合资料里介绍的样子。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二十年前,第一次听说有人要来我们村治沙的时候,村里的人都觉得这人一定神经有问题,放下那么好的工作不干,来这里治沙。”基地林场场长王占林说道。王占林乍一看像是位敦实的蒙古族人,他这样的长相在这陕蒙交界的地方并不少见。
王占林初遇张应龙时,他还是沟掌村的村民。那时候的沟掌村是神木有名的贫困村,陷在沙窝深处。2003年春天,听说有人要在村子招人植树造林,王占林想也没想就应下了这个事。“当时主要是听到给钱挣呀。”在这个鲜有打工挣钱机会的沙窝子里,这才是最初吸引人的原因。
但王占林没想到,这一干就是二十年。他跟着张应龙从打网格固定流沙开始,到撒紫穗槐等各种草籽,等地上有了草,就开始种树。他亲眼目睹自己住的沙窝子,从星星点点的绿到大片大片的绿色覆盖黄沙。二十年间,他也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农民逐渐变成能识别各种草和树的林场场长,也成了很多人眼中的沙漠植物学家。沟掌村的村民们在张应龙和基地帮助下,每年通过林业产业和务工收入有2000多万元,从而摆脱了贫困。
王占林说:“现在不管来我们这儿的教授、院士,还是参观学习的人,都说应龙的治沙造林应当是国内最讲科学、最先進的方法。”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邵明安院士也这样评价:“张应龙最大的特点就是讲科学。”如今张应龙是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治沙委员会的委员,他认为自己是用最科学方法造林的,但他也感觉到有不足的地方,“我在治沙过程中还有很多盲目性,和自然、社会还有不相统一的地方。”
若二十年的时光可以塑造成一面镜子,试想一下现在的张应龙站在镜子面前,面对2002年的自己会想到什么呢?庆幸、懊悔、醒悟还是反思?此种滋味只有他自己清楚。
“2000年左右,我去了趟德国,见识到了德国的人工造林,真让人羡慕啊,我就联想到了自己的家乡神木。”张应龙回到神木了解到,“神木和德国一样,年平均降雨量为400毫米,当时我就想,神木能不能和德国一样,多栽树变成森林。”其实,这时候的张应龙离开神木已经数年,他当时主要在天津和北京搞卫星模拟信号技术,有三四百万元的积蓄,“穿着定制西装,踏着进口皮鞋,手提大哥大,走到哪里都得意洋洋。”张应龙笑着描述自己当时的样子。
2002年,张应龙之所以回到神木,是因为朋友介绍的一个房地产项目。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当地朋友拉到毛乌素腹地的沟掌村,晚饭的时候,沟掌村支书王二流不停地给在座的酒友讲起在这里植树造林的各种好处。这种诱惑或许正好暗合了张应龙内心深处隐藏的那个“乌托邦”之念,酒到醺酣处,他就应下了此事。
几天后,王二流带着承包合同找上门,张应龙才知道自己“还弄下这么一出事”。重口头信誉是陕北人的特性,他签了这份七十年期限的土地承包合同,承包了沟掌村19.2万亩的毛乌素荒沙地。
这片荒沙地所在的位置是秃尾河源头的圪丑沟。吃饭那晚一行六个人,张应龙带头出资100万元,其他每人出5万元,总共125万元,成为第一笔治沙的经费。
“当时我以为出钱请了人代管种树就行了,没想到电话一个接一个,都是琐碎的事情,今天是基地盖宿舍需要砖头,一块砖拉进沙漠需要两毛钱;明天又说要通车就得先修路;又说花了1.2万元买了20多万株树苗,栽了十几天,半米深,不到半个月全都没影了。”张应龙在北京待不住了,反复权衡之后,辞掉年薪20多万元的工作回到了神木。
“回来以后,我才发现想雇人都雇不到几个,自己不干就没人干了。”身临其境了张应龙这才发现理想与现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别看我现在是全国劳模了、治沙英雄,可没人知道我这个英雄当年都是逼出来的。”
张应龙还弄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林业与气候的关系。神木与德国的气候完全不一样,他原以为两个地方的年降雨量都是400毫米,却没考虑德国的海拔只有200多米。而且德国的气候是雨热同季,雨水集中在了春夏两季,秋冬无雨。而黄土高原雨热不同季,春季无雨,夏季只有雷雨,秋季阴雨绵绵,冬季只有一点雪,与德国的气候刚好相反。
最困难的一次,张应龙被连续困在基地四十八天。秋季的暴雨让基地变成了孤岛,张应龙只有两条狗和四匹马陪着。门不用关,狗就睡在床底下,裤子松紧带坏了,就用绳子勒着,也不洗脸,身上都起了皮。
“我很郁闷,很失望,但我要为我应承下的事情负责。”张应龙说,经历几番挫折后,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想要治沙,得靠科学。
是沙漠改变了我
初春的毛乌素沙地在凌晨六点三十分的时候,地平线就开始出现了大段蓝调的晨光,七点十分左右开始日出。基地院子里旁边几个连接在一起的海子里还结着冰,地表与地下的温差让湖面不断地涌出大量的水蒸汽。日出的光芒打在湖面上,湖边的树林被湖光反射成金黄色,笼罩在了雾气中。湖面与芦苇丛中的水鸟似乎被日出突然的强光惊到了,一群群地飞上了天空。
基地负责综合事务的老王每日早起晨练,他对湖里栖息的鸟类大体有所了解。据他介绍,基地距离红碱淖直线距离只有10多公里,基本屬于一个水系,这些年随着生态系统逐渐恢复,鸟类也在不断回归,现在除了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遗鸥,常见的还有大天鹅、赤麻鸭、鸬鹚、灰雁、豆雁等等。随着季节的不同,迁徙来的鸟类也不同。
基地还从澳大利亚引进了鸸鹋。张应龙听沟掌村一带的老百姓说过,在1960年代,这一带的沙地里曾生活着一种类似鸵鸟的动物,比鸸鹋的个头还小,张应龙和有关专家讨论了后,从澳大利亚引进了200多只鸸鹋,作为生物多样性实验的样本,每只花费上万元。
此时已经是2010年,张应龙的治沙造林事业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治沙面积已经扩大到了42.8万亩。但想起治沙之初自己面临的危机,张应龙依然心有余悸。“最痛苦最混乱的时候,我被周围人看成了疯子,在沙海中投入以前所赚的300多万元,却连紫穗槐都没有种活!”但张应龙不服气,没钱了他就开始卖自己开发的楼盘。
危机也引出了自省。“问题就在于我自己不懂,既然不懂,就找懂的人啊。治沙单靠一个人力量不行,而当时神木的治沙造林状况就是政府出资金都没有人愿意出力,居然出现了一个自己掏出了所有积蓄来治沙造林的人,政府能不支持?”
至此,张应龙开始做了一些“杂事”。2004年3月,张应龙倡导成立神木市生态保护建设协会,这是一个民间公益团体组织。用他的话来讲:“这样就有渠道接受政府的治沙资金,让我摆脱了困境。”他还与沟掌村村民合作,成立了“神木市秃尾河源林业生产合作社”。
早年有过文字编辑经历的张应龙也注意到了媒体宣传对自己治沙事业的重要性。2005年,他创办了“神木生态网”,2006年又办起了《神木生态》简报。他还和陕西省音乐家协会创办了“生态音乐版”杂志《音乐天地》。
从2005年开始,张应龙和他的协会与日本“每日放送”、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陕西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华商报等60多家新闻媒体以及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陕西省林学会、陕西省森林文化协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作家协会等单位合作,在电视、报纸、新闻媒体等平台录制纪录片《毛乌素沙漠寻宝记》《大地寻梦》《陕北启示录》等,还举办了系列采风活动、生态文化研讨活动,这些活动带动了一批中外自愿者参与其中。
除了这些“杂事”,张应龙当然还是将更多精力放在“正事”上。从2004年开始,张应龙走访了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最早让他豁然开朗的是一位中科院的专家,“他告诉我治理毛乌素一定要顺应当地的自然条件,不能盲目,要先把水保住,这样土壤中的养分才不会流失,种树成活率才能高。还要种混交林,乔灌草相结合。”
以前做事太随性的张应龙,这时起开始老老实实到处拜师学习,还拉着专家到他的基地现场指导。“我是自己有什么需求就找什么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合作。最近和我合作的就是中科院水保所。”
张应龙先后与中科院、中国林科院、西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省治沙所等科研院所合作开展科研活动。与德国、日本完成了一些国际科研合作项目。还主持承担了国家科技部总投资9600万元的陕北能源化工基地生态修复惠民工程项目,完成了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项目、林业公益林行业专项、国家行业标准项目、陕西省科技计划专项等23个项目。主持起草了国家行业标准三项,陕西省省级地方综合体标准一项。
在基地二楼上,挂着一块省级院士站的牌子,这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邵明安院士的工作站。楼道里挂满了协会合作引进土壤环境、水文、微生物、植物、动物昆虫等社会科技工作者的照片。老王介绍说,这些科技工作者包括1名院士、1名长江学者、2名杰出青年科学家、其他教授研究员12人。全国各地高校、科研机构累计与协会合作的有200多人。
“我经常对人讲,不是我改变了沙漠,而是沙漠改变了我啊!”只要是见过张应龙的人,都能听到这一句发自他内心深处的感慨。
张应龙像一块海绵,贪婪地学习着他以前根本没有接触过的地理学、气候学、植物学、动物学、环保学、微生物等知识。他说自己在沙漠中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杂学家”,这些知识让他明白了治沙更多的是要搞近自然的植被恢复,“治沙造林的关键点不在林上,关键是讲风水,尽可能关注风保住水,植被就能自然恢复起来。”
张应龙通过自己的多年的实践,提出了毛乌素沙地治理的三个阶段,从防沙治沙开始,到护沙用沙,再到现在的生态循环模式的建立。也就是从初期的沙漠固沙到中期的有效保护与产业形成,最终实现生态与人居产业循环利用。他的这一理念得到了国家林草局的高度认可并向全国推广。
作为中国沙业学会委员,张应龙最近正与国家林草局三北局准备做一个新的研究项目,内容就是明确三北防护林典型林种、树种衰退程度的分布格局及衰退驱动因素,研发典型林种衰退林近自然修复与重建技术。
通过与科研、高校的合作,如今这个治沙基地不仅是“陕西省公众科学素质与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发展研究中心”“陕西省省级院士工作站”“陕西省科技厅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长柄扁桃国家创新联盟”“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榆林生态文明示范基地示范点”,更是“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毛乌素生态试验站”和“中科协全国科普兴村示范基地”。
“老不死”引发的科研课题
张应龙有个生活习惯,不管是去神木还是榆林办事或开会,只要是能当天回来,不管多晚他都要赶回基地。老王为此嘲笑他是“葛朗台”不舍得住酒店。老王对住在基地的邵明安院士的做法更是感慨不已,“他春节都没回家,待在基地搞研究没停一下!”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张应龙和邵明安院士是毛乌素治沙人的典型代表。
张应龙觉得,自己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治沙成果,自身勤奋是次要的,重要是顺应了地球气候变化这个大环境。“现在经常说榆林治沙让沙带向北推了300公里,可是我们还要知道是这个时期地球的西风带也向北移了300公里,其实是自然帮了很大的忙。1970年代是中国的气候开始从極度干冷期向暖湿期过渡的时期,到了1990年代就特别明显了,这个时期特别有利于植物的生长,我们这群治沙人正好赶上这么一个好时期,气候帮了大忙。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开始重视治沙,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我是赶上了这个时代洪流。所以不能过于放大个人的力量,不讲大环境的因素,单纯放大我们这些治沙英雄和精神,会让内行人看了笑话的。”
但是从纵向对比来看,张应龙的治沙与毛乌素第一代治沙人及第二代治沙人都是有明显区别的。他的科学治沙是在众多专家指导下反复实践才摸索出来的方法,而且最难得的是,他将自己的治沙方法总结成了一套理论体系。这套体系最核心的地方就在于,毛乌素治沙要先掌握风的规律,让沙子静下来;然后是减少蒸发量,按降水量与降水规律维持人工林地水承载能力;有了林地后增加新造林地有机质,保障林木的营养质需求;新的人工生态系统,要适应微生物、昆虫、动物的生存环境。按着这些科学步骤,张应龙探索创新出混交造林、生态经济林、种九留一,十年龄樟子松林下绵羊轮牧、林业秸秆与林区有机废弃物回收资源化利用、林下食用菌天然生长等六种模式。
张应龙先后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理工等高校聘为研究生导师和客座教授。特别是在发现、推广种植到研发长柄扁桃等方面,张应龙取得的成就是他人无法能及的。
2020年10月16日0时23分,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作为搭载物品,神木市生态保护建设协会提供了20克长柄扁桃种子随三名航天员进入太空,开启为期六个月的太空之旅。
据张应龙介绍,从2004年在基地发现长柄扁桃,到现在向全国推广种植,效果非常不错。内蒙古乌兰布和、延安吴起、青海海西州,以及宁夏、黑龙江、甘肃等地的长柄扁桃,基本上都是从张应龙的基地引进的。
2004年,张应龙在和基地种树的农民一起吃饭时,一位放羊老人讲起,这沙地里有一个叫“老不死”的植物,怎么也死不了。他随这位老人找到了这种沙地植物。请教了邵明安院士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学方面的教授后才知道,这种植物学名叫长柄扁桃。“在这以前,这个物种只在文献里有记载,都以为它早已灭绝。”
经专家检测鉴定,长柄扁桃野生三百多年还挂果,生命力极强。沙漠里种树,存活都困难,想要开花结果,更是难上加难。长柄扁桃的发现,让张应龙看到了希望,这种植物太适合在毛乌素沙地里用于绿化成林了!
张应龙进一步发现,长柄扁桃果实含油量很高,可做生物采油。恰好当时日本有个项目落地到了他这里,于是,经过日本的科学家联合西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起合作研发,制出了食用油、化妆品等。研发中发现长柄扁桃产量低,科研人员就又通过杂交实验,新研发出四个品种,使产量大幅度提高。
现在基地栽植生态经济林长柄扁桃10万亩,实验苗圃200亩,无性扦插大棚10个,种质资源收集圃150亩,组培实验室1个。开发出了长柄扁桃食用油、活性炭、蛋白粉、苦杏仁苷、生物柴油、化妆品等产品。张应龙的基地也成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长柄扁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经是教授身份的张应龙与诸多科研人员在《西北植物学报》等学术报刊发表了若干有关长柄扁桃研发的论文,编辑出版两本专著《长柄扁桃》与《长柄扁桃资源开发利用》,并获得国家专利12项。
按张应龙的说法,此次长柄扁桃种子搭载神舟十三号开展太空育种,具有诱发变异频率高、幅度大、多数性状遗传稳定快等特点,是创造新种质的一种有效可行的方法,为作物育种开辟了一条新途径。“通过外太空育种技术,有望使长柄扁桃的性状、抗药性和它的产量稳定性有一个大的突破。我们会逐步把长柄扁桃作为毛乌素沙地主要的木本经济树种来培养,所以经过太空育种的长柄扁桃,将来会成为一个林业产业上的科研突破。”
最终理想是生态循环模式的建立
2015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赵春雷第一次来到基地工作的时候,这里的生态植被覆盖程度已经非常好,但林下还不能长蘑菇。仅仅过了三四年,他突然发现林下长出好多蘑菇,特别是牛肝菌。
张应龙和农民们发现樟子松林下的野生蘑菇时,并不认识这是什么菌,还是邵明安院士告诉他们这是牛肝菌,而且此前国内只有云南有这种菌。牛肝菌对环境要求非常高,首先必须是在高原地带,而且土质要非常肥沃,地表必须有足够的水分支持。还有一个必须具备的重要指标,即植被的遮光率达到75%。显然,牛肝菌能在毛乌素沙地大量生长,足以体现出这里生态的巨大变化。
据张应龙介绍,牛肝菌没办法人工养殖,邵明安院士现在正攻克的一个课题,就是想复制基地这个模式,把面积放大,逐步实现人工种植。
记者了解到,经过二十年治沙造林,基地种植人工林已达40万亩,管护面积达50万亩,整个植被覆盖程度由20年前不到3%提高到现在的65%。从2013年开始,林地里长出了榆树,到现在已有几万株,成为这里生态环境向好的又一佐证。邵明安院士还发现,基地的土壤有了可喜的“固碳”现象,这种现象是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土地肥力提升的重要标志。邵明安院士认为,把碳固定下来,土壤的肥力提升了,就能带出林下经济。如果这个目标能实现,老百姓就能受益,那就真应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
从基地瞭望台望下去,可以看到丛林中有一些黄色的昆虫捕捉网。据老王介绍,这样的网在基地布了60个。另外,基地还布了若干台远红外摄像机,捕捉到了很多回归的野生动物,特别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我们有几个标本室。昆虫室是将毛乌素沙地里所有的昆虫做一个收集,然后找到昆虫生活的习性。另外还有植物、动物以及文物标本室。野外还有土壤、水份、光照的观测点三十多个,采集相关的数据,包括地下水资源的变化和土壤养分、每年光照的变化,通过互联网,直接传送到邵院士的办公室。”
老王说,基地以公路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区,南区主要是农场,开辟出了一万亩的标准化机械化耕地,目前开展一个草粮轮作为主的大课题。“这些耕地也曾经是裸露的沙丘,人工把沙丘推平后,在上面覆盖20-30公分的黄土,然后才可以搞农业种植。”另外,这个农场还建成了年产1000吨微生物菌种厂、年产1万吨生物有机肥料厂和林下食草禽类养殖示范厂、鸸鹋繁殖繁育场、欧洲雁种苗繁育场等。
现在基地提供职工的餐食,包括小麦、大米,都是基地种植出来的。这两年,张应龙在基地试种了30亩水稻和2600亩谷子,东北长粒香和宁夏的珍珠米都试种成功。
张应龙心中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他说。协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生态文化,第二是生态科研,第三是生态示范,第四是生态惠民。去年,基地搬迁到新大楼的时候,他将这里命名为“科研文化培训中心”。这个培训中心是与陕西省科协合作,主要针对公民进行科技素质教育。
与大众认为的科普教育要以青少年人群为主不同,张应龙将他的科普教育主要面向以政府機关行政人员为主的群体。“真正需要科普的是决策者。我在榆林推了很多年的混交林,但很多领导觉得太麻烦,觉得把树栽活就行了。在培训中心,科学家们就是先给决策者讲清科学理念和方法,再带他们到实验室里现场学习,这样或许就能让很多领导干部在决策时考虑到科学性与适用性。”
这些年,张应龙也一直在给所有来参观考察的人厘清一个理念:所谓治理沙漠是不对的,沙漠是不能治理的。一定要分清楚沙地和沙漠是两个概念。沙漠是地球的季风气候变化导致形成,在沙漠中是无法建立一个生态系统的。只能做一些的工程措施,锁住沙漠,防止扩大危害人居环境。
“我的这一套治理方法,只适用毛乌素沙地。沙地在历史上曾经是有森林和草地的,所以现在是要让它重新恢复原有的生态系统。中国四大沙地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沙化,恢复生态系统是一种正向治理的态度。”针对毛乌素沙地这些年治理取得的效果,张应龙说:“不能说毛乌素沙地消失了,毛乌素是消失不了的,它退化用了一千年,现在是得病了,去病如抽丝,要恢复至少也得三千至五万年。只能这样讲:毛乌素沙地得到了彻底的遏制。”
经过二十年的治理,毛乌素治沙造林基地已被国家林业局评为“中国七大最美沙漠”,被诸多媒体称赞为“毛乌素中的马尔代夫”“毛乌素中的塞罕坝”。可是,即将进入耳顺之年的张应龙却没有成功的喜悦,反而却越来越惴惴不安。很多时候,他问自己,栽种的这些人工林未来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他回答不上来。“我能想到大的方面就是,现在的生物多样性不足,土壤的承载力也不够,只能和邵明安院士一起想办法找到突破,想办法维护,保障这片人工林长期的安全。”
张应龙最终的理想,是能让生态循环模式在毛乌素建立起来。其核心是在人为不管护的时候,树林也能自我生息繁衍。简单地说,就是唤醒沙地自然生态循环与自我生命发展繁衍的力量。所以,现在林地里树木如果不是大面积死亡,偶尔一两棵死亡,人工就不干预,让它自我更新。“当然,这是一个长远过程。尽管实现这个目标很遥远,但我们至少可以从现在起,把握好这个正确的方向。”张应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