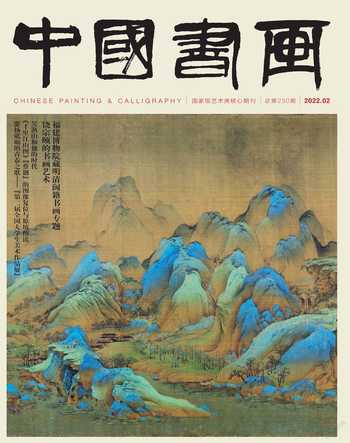《三十六法》的作者及年代
寇克让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般人只知这句话出《论语》,不知孔子此言,实为引语。另有一事,据《史记·管晏列传》,孔子称愿为“执鞭”,也就是甘愿做管子的御仆。如此崇拜,那么孔子引管子名言顺理成章。
乾嘉学派之吴派代表人物惠栋,在《九经古义》中特别指出了这个问题。惠氏六世传经,惠栋及其父惠士奇声名更为显赫,《九经古义》积其家学,钩稽九经隐微,借此可略见一斑。
《论语》是儒家经典,为何这样的问题会放任两千年呢?那是因为标点符号的问题。如果古代文献像后来一样,将直接引文施以双引号,就不会有这一桩误会。
在书法文献中,没有标点,或者误施标点引起的问题很多。比如,赵壹《非草书》中“云适迫遽,故不及草”,当作“云:‘适迫遽,故不及草’”。也就是说,赵壹这句话是引文,引谁的?看上下文应该就是张芝,或者当时其他的草书家梁孔达、姜孟颖诸辈的话。这句话以及紧随其后的“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和张芝的名言“匆匆不暇草书”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即草书书写在迟速之间,迟的价值已经备受瞩目,这就是“匆匆,不暇草书”的语义。
一个标点致文义南辕北辙,古代文献中此类情况为何屡见?主要是因为不施标点,加以古人语促,年代久远,误会就产生了。因为一个逗号,差点误读“草圣”张芝的事情还有一次,只是远不如“匆匆不暇草书”影响深远。因为张芝一生不仕,在正史列传中说得很清楚,所以下面的这个标点事件虽然混淆事实,却并未产生恶劣影响。王僧虔《又论书》有一句“索靖字幼安敦煌人散骑常侍张芝姊之孙也”,当代有点校本误作“索靖,字幼安,敦煌人,散骑常侍张芝姊之孙也”。殊不知索靖在晋仕为散骑常侍,而张芝终其一生并未入仕。
标点虽小,稍有不慎却能窜乱旧章,厚诬古人。问题的关键是点校必须明事实。标点之误,看似语文之失,实则多由史实不明。
有一篇古代书论《欧阳询三十六法》,长期以来被误会为欧阳询《三十六法》,这样一来,其作者及年代始终无从考定。《佩文斋书画谱》说“诸本都附欧阳询后”,可见误会之深远!当然,因其中“高宗书法”“东坡先生”“学欧者”云云,《佩文斋书画谱》质疑非唐人所为,“故附于宋代之末”。问题是发现了,甚至断代也大体不错,但仍是眉睫之失。
更遗憾的是,当代人对于三百多年前的这个有价值的怀疑置若罔闻,仍将《三十六法》置于欧阳询名下,尽管也注意到欧阳询《八诀》和《三十六法》有時候合称为《欧阳率更书三十六法八诀》。众所周知,《八诀》是欧阳询论书名作,既然与《三十六法》合刊,必有缘由。这让我想起南宋以来,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原来单行的《经》《传》《疏》往往合为一册,而徒经本从此淡出,传疏本成为潮流。《欧阳率更书三十六法八诀》显然是这个时代背景的产物,《八诀》相当于“经”,《三十六法》为传,这样问题便涣然冰释。
按验原文发现,《三十六法》言必称《八诀》,兹胪列如下:“《八诀》所谓‘分间布白’,又曰‘调匀点画’是也;《八诀》所谓‘斜正如人,上称下载’,又谓‘不可头轻尾重’是也;《八诀》所谓‘四面停匀,八边具备’是也;《八诀》又谓‘勿令偏侧’亦是也;《八诀》所谓‘迎相顾揖’是也(只此一条未见于今本《八诀》);《八诀》所谓‘勿令左短右长’是也。”
除援引《八诀》诸条外,今本《三十六法》举例欧阳询名作《九成宫醴泉铭》两次:如《醴泉铭》“建”字是也;如《醴泉铭》“秘”字。于其他书家则只字无关。
从《三十六法》引文、举例两个方面都可以看出,它就是解释欧体书法的,可视为《八诀》的传。除此之外,《三十六法》两次引《书法》,一次引《书谱》:《书法》所谓“意在笔先,文向思后”是也;《书法》曰“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自然宽猛得宜”;《书谱》所谓“密为老气”。这个《书法》是赵构所作,《书谱》是姜夔《续书谱》的省称,那么《三十六法》是南宋的文献可成定谳。如此一来,其中所谓“高宗书法”“东坡先生”“学欧者”等,不仅毫无扞格,反而是其时代特征。
类似《欧阳询三十六法》这样的问题,文献校读常常会遇到。
《后汉书》章怀太子《注》多次引裴松之《宋武北征记》,有时简称,如《孝献帝纪》,《注》作裴松之《北征记》,无误;有时全称“宋武北征记”,点校就出了问题,如《刘焉袁术吕布列传》,点校本误作宋武《北征记》。仅因标点不当,直接造成文献作者的讹误。有时候书名号当用不用,虽不至于错讹严重,却使文意难安。
《杨震列传》附《杨秉传》说杨秉“博通书传”,这个“书传”究竟指什么?因为点校本“博通书传”四个字没有施标点,所指十分宽泛。实际上,前文《杨震传》说“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此处说杨秉“少传父业”,那么,杨秉显然从父杨震受《欧阳尚书》,下文果然说到,“桓帝即位,以明《尚书》征入劝讲”,所以“博通书传”应当做“博通《书》《传》”,就是《尚书》及《大传》。汉人“经有家法”,此亦一例。
责任编辑: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