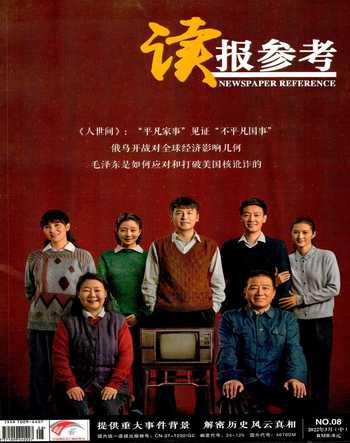毛泽东是如何应对和打破美国核讹诈的
赵丛浩
新中国成立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艰苦奋斗,自立自强,始终与威胁我国国家利益的风险挑战作斗争,有力维护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来自美国的核讹诈曾严重威胁了我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主权。对此,毛泽东沉着冷静,多措并举,领导我国应对和打破了美国的核讹诈,维护了我国国防安全和主权完整,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
恰如其时地作出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原子能及其利用等问题的汇报,讨论并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毛泽东指出,原子能事业“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毛泽东之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作出发展原子能、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是结合我国面临的风险挑战、自身发展条件等一系列因素后,慎重作出的。
当时我国的国内外局势颇不平静。国际方面,美国对刚刚建立只有数年的新中国频繁施加核讹诈。如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初,美军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打击下节节败退,为了挽回败局,美国政府就扬言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进行,尽管美国在常规武器装备上拥有绝对优势,却未能打赢战争,也就促使其将最后希望寄托在核武器上。如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美国为了攫取对自身有利的谈判结果,就威胁对朝鲜战场和我国大陆地区使用核武器。国内方面,盘踞在台湾等东南岛屿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国内其他地区的残余反革命势力,与境外反华势力频繁勾结,妄图凭借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与“核优势”死灰复燃。
为了保卫人民政权,维护来之不易的主权独立和人民自由,我国不能任人宰割,帝国主义者也决不会自动放下武器。因此,要实现和平、维护和平,就必须具备消灭敌人、打赢战争的能力。这就要求新中国必须掌握自己的核武器,增强保卫自己的底气与威慑侵略者的能力。正是在这种局面下,毛泽东指出,“原子弹、氢弹、导弹,我们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此外,毛泽东还有更加深远的战略考量,那就是通过研制核武器,推动我国的科学技术大发展,助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尚在医治多年的战争创伤时,一些世界大国就已经迈入了“原子时代”“喷气时代”的门槛,我国迫切需要在科学技术领域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对全党提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研制核武器这类高精尖武器,无疑正是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大力带动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向前发展,从而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奠定深厚基础,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十分有益。
实事求是地根据国情提出应对核讹诈的多层次准备
在打破核讹诈方面,研制并掌握核武器无疑是极为有效的方式,但不管手中有无核武器,新中国都决不屈服于核讹诈,而是从国家整体战略出发,制定符合国情特点、能够发挥自身优势的对策措施。这就是毛泽东指出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新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战略。从这一前提出发,要应对和打破核讹诈以及打赢核战争,就意味着我国必须在面对侵略战争时,以防御承受住敌人的第一击。关于进攻和防御的关系,毛泽东以辩证的观点明确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也就是说,有进攻就有防御,进攻和防御各有长短,在一定条件下,二者还可以相互转化。毛泽东结合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从战略角度作出论证,两次战争“都是防御者胜利,进攻者失败”。以进攻实施侵略,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以积极的防御实施自卫战争,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之举,必然胜利。但是,胜利不是自然而然或轻易就能取得的,只有积极行动,提前部署,才能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对于核打击,如果预先做好防御,是可以大大减轻其造成的损害的。因此,毛泽东指出,“战争历来都需要攻防两手”,既然在进攻武器方面,“比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那么必须“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
核武器的特点是适于打击高价值目标集中的区域。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工业设施大都集中于东北、沿海等少数地区,毛泽东曾担心敌人用10颗原子弹就可以摧毁我国的工业中心,严重破坏我国工业骨干力量,大幅破坏我国现代化建设成果。因此,利用我国大纵深国土空间和自然地理特点,分散布置工业设施和人力资源,是应对核战争的必要手段。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着眼以战略防御应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布局,提出实施三线建设的设想,力求建设巩固的战争大后方。党中央据此作出了开展三线建设、加强备战的重大战略部署。毛泽东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通过三线建设,“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基地和铁路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后来,他在听取制定“三五”计划情况时,专门指出要重视防御核打击的问题。
拥有核武器、做好防御等反侵略准备,是应对和打破核讹诈的有效方式,但敌人不会等待我们一切准备就绪才发动进攻。事实上,正是由于我国没有掌握核武器,缺乏抗打击能力,美國才会有恃无恐地频频对我国施以核讹诈。毛泽东就这种情况指出,“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蛋。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就用常规武器跟他们打”。也就是说,即便没有核武器,面对侵略,中国人民也决不会束手投降,而是会根据自身实际,在反侵略战争中扬长避短,将手榴弹等手中可用的常规武器的最大效能发挥出来。当然也要看到,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一样,都不能包打天下,二者各有优缺点。但总体上看,以常规武器应对核武器是以弱敌强的不对称举措。如1957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就指出:“我们军队现有的这些武器,对付原子弹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要提高武器的质量,减少人数。”此外,毛泽东一直认为核武器的主要作用是“吓吓人,壮壮胆”,判断未来发生的战争依然是常规战争。他引用时任美国三军参谋长泰勒所写的《音调不定的号角》一书,指出,美国虽然作了核战争和常规战争两手准备,但他们的方针还是打常规战争,以此强调我国为打好反侵略的常规战争作好充分准备,不仅仅是未掌握核武器条件下以弱敌强的无奈之举,也是针锋相对地遏制美国发动常规战争,进而遏制其发动核战争的必然之举。
广交朋友,在全世界筑起反对核讹诈之“墙”
核武器诞生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仅掌握在美国等少数几个大国手中,成为它们干涉他国内政、破坏世界和平的工具。因此,反对核讹诈和核战争,不仅是我国维护主权完整和国防安全的迫切需要,而且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和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自身独立与自由的必然要求。如时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的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就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的核讹诈政策。
约里奥·居里于1951年6月的一天,约见即将回国的中国科学家杨承宗时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不仅如此,他还帮助新中国的科学家在欧洲购买开展核武器研制所需的器材和图书,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起步作出了贡献。
对此,毛泽东抓住要害,阐明了全世界最大多数人民追求和平的共同愿望,深刻地指出:“世界人民是反对用原子弹杀人的。”他主张团结世界上一切可能的力量共同反对核讹诈和核战争,把这项工作比喻成“筑墙”,提出努力团结更多力量、争取更多支持,“把墙筑高筑厚”。1954年10月,毛泽东就指出,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应对和打破核讹诈方面,这一问题同样十分重要。那么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团结的对象?毛泽东认为,美国人民和中间地带国家都是我们可以争取、团结和联合的对象。他强调,“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要把美国人民和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区分开来,“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他还指出,亚非拉国家要“普遍地保卫和平,反对战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集团,反对使用原子弹和氢弹”。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也认为有团结其力量的可能。比如,尽管日本是美国的盟友,但“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对核战争”。毛泽东多次指出,由于美国与中国等国不直接接壤,因而美国若发动战争,必将首先针对“中间地带”,目标是占领中间地带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到了1960年代,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中间地带”的范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
这一系列论断是毛泽东科学研判各国力量消长、世界战略形势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后,针对美国战略政策及其影响作出的,已被历史证明是符合实际的正确判断。与我国具有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尤其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政治立场的中间地带国家,毛泽东都认为有团结的可能。他结合世界形势的变化指出,“几个大国要控制小国是不行的”,西方国家所谓的团结也只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弹下面要求它的大小伙伴们向美国靠拢,交纳贡物,磕响头称臣”,这“势必走向所谓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由于美国的扩张政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愿参与美国挑起的冲突,但作为美国的盟友,也很可能因美国的军事冒险而被动卷入战争,甚至全面核战争。如195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北约军队的作战计划完全是“建立在使用原子和热核武器”上,但根据模拟计算,“即便是在最好的设想情况下,看来也将会有200万至2000万欧洲人死亡”,这使得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意识到战术核武器的使用“将不能防卫欧洲,而是要毁掉它”。新中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但是,美国以应对苏联为理由,在双方战略核力量趋于平衡后,仍然大量扩充核武库,大大增加了对中间地带国家的军事优势,逼迫其向自己靠拢,必然引发包括其盟友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的反對。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中国在1960年代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并成功完成空投核试验、导弹核试验等相关任务,具备了核武器实战能力,从而彻底打破了美国的核讹诈。但这一过程是艰难的。毛泽东用全面、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在对我国国情和世界战略格局的精准分析、把握与预判中,着眼应对和打破美国的核讹诈,不仅高瞻远瞩地作出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坚持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积极主动作为,把核讹诈这一外部风险挑战,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次历史机遇,团结教育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调整了全国产业布局,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和人才队伍培养,促进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均衡发展,扩大了国际影响力,彰显出毛泽东巨大的勇气和智慧。
(摘自《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