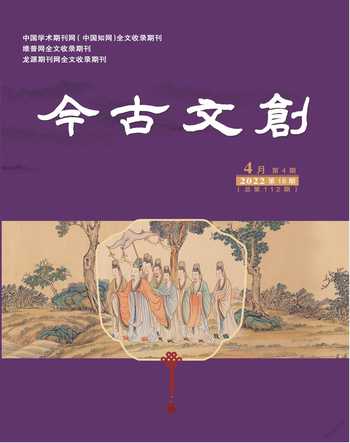《南诏图传》考述
【摘要】 《南诏图传》又名《中兴二年画卷》《南诏中兴国史画卷》,原本为中兴二年南诏官员王奉宗和张顺绘制,是云南流传至今历史最为悠久的纸本史料,极具文物价值、史料价值。本文通过文献、图像资料对比,再辅之以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试图对《中兴二年画卷》的年代问题以及“西洱河记”图像内容进行探讨,对其文化艺术、宗教、地理等多方面内涵进行探析。
【关键词】 《南诏图传》;《中兴二年画卷》;西洱河记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6-005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6.017
《南诏图传》又名《中兴二年画卷》《南诏中兴国史画卷》,为南诏忍爽张顺和王奉宗在公元899年即中兴二年绘成,图传原藏南诏宫廷,宋、元、眀期间不见著录收藏,不知散佚何方,清代曾辗转收藏于琳光松园老人丈室,后又传入清宫,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被掳掠国外,今藏于日本京都有邻馆。
《南诏图传》共彩绘画卷和文字卷两卷,均为横卷式。画卷长5.73米,宽约0.3米。从右自左,画卷可分为十个片段(十三张画幅),其中九个片段按文字卷的内容又可分为四个部分。
文字卷的第一部分为画卷的一到六段,讲述了“巍山起因”“梵僧七化”的故事。这一部分的画卷出现了梵僧、神兵、浔弥脚、梦讳、细奴逻、逻盛等丰富的人物形象,叙述了南诏王室的起源,即第一代蒙舍诏领袖奇王细奴逻避难巍山,并得到观音化为的梵僧点化的故事。第二部分为第七段,主题是“铁柱记”,夹于“第六化”和“第七化”的图像之间,文字卷中此部分内容则在第一部分的“巍山起因”之前。第三部分为第八段,所绘中兴皇帝及其侍从礼佛图。第四部分为第十段,主题为“西洱河记”,夹着“西洱河记”的来自王奉宗和张顺两人的颂词,位于画卷最末尾。三四部分之间为文武皇帝礼佛图,这一部分的绘画未在文字卷中找到相关说明。
此图传是云南流传至今历史最为悠久的纸本史料。图传所展示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引人瞩目。南诏时期历史信息少见文字记载,目前仅在《唐书》《新唐书》《蛮书》《南诏野史》等文献及出土文物中可窥部分面貌,故而作为南诏大理国时期最古的画卷,《南诏图传》有着非凡的研究价值。迄今为止,学界对图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版本和年代、文字卷、服饰器物、艺术特征、图像考释、宗教学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成果体现。然而对于一些问题至今尚未有定论,仍有讨论的空间。本文将就《南诏图传》的版本问题及“西洱河记”的含义争议试做一探讨。
一、现流传《南诏图传》考述
《南诏图傳》别名《中兴二年画卷》,此称来源于画卷末“谨画图样,并载所闻……中兴二年三月十四日……等谨。”据此,可知此图传原作应当于中兴二年期间。然而,在中兴皇帝礼阿嵯耶观音图之后文字内容①明显提示画卷的故事内容已经到此完毕,其后又出现了文武皇帝礼佛图(第十个片段)。这一部分的内容明显后来加入“西洱河记”的双蛇鱼螺图之前的。因而更多学者对本画卷是否是中兴二年之作存在争议,是否为摹本还是再摹本的讨论不休。
清代人张照的《跋五代无名氏画卷》中提及其纸色古朴,推断为唐末五代作品。也有研究者通过分析观音像特征,判断图像性质属于十二十三世纪摹本②。甚至有国外的学者用碳十四手段测定图传年代为距今1500±250年,即很有可能是公元705年③。这些结论是否可靠呢?仅以纸色断定年代并不算充分的论证。而碳十四测年的时间范围动辄数百年,此方法在历史时期断代的可靠程度尚且存疑。同时查平以今证古,她以崇圣寺大观音像与图传内造像类比,倒推图卷里的形象应当是晚期造像取代早期造像的结果,并进一步确定其为十二十三世纪的摹本,这一论证过程实际上显得有些粗糙。实际上公元899年以前的南诏国观音造像世所罕见,又如何能确定图传里的造型不是后世观音形象的来源?
文武皇帝的身份是判断此图传完成年代的关键。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文武皇帝应为中兴二年之后补绘。至于文武皇帝的身份,有杨干贞说、郑氏说、段思平说等。汪宁生认为“文武皇帝”为郑买嗣谥号,画卷为郑死后绘制,王张二人可能改投郑氏,即画卷也许仍出于原作者之手④。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文武皇帝”更有可能是尊号而非谥号,并且认为文武皇帝其后随从“赐姓杨”应为国姓,“西洱河记”为后加的内容,所以文武皇帝应该为杨干贞⑤,然而笔者以为,文字卷的“西洱河记”与杨干贞“彰显自己为西洱河金龙之裔”似乎并无联系。
李霖灿在《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中以“文武皇帝圣真”和“文经元年”字样为依据推断文武皇帝应为段思平⑥。在《跋五代无名氏画卷》内提及篇首有“文经元年”,此为段思英年号,据此他认为画卷的图和仪注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⑦。但笔者因为材料限制未能在图卷中找到“文经元年”字样,不知道此四字于何处出现或者以何种形式出现。如若“文经元年”几字确实存在于卷首,李霖灿之观点则显得更为可信。
二、“西洱河记”相关内容及其内涵试探
《南诏图传》末尾为双蛇鱼螺图。图卷旁有文字记载:“北”字样下方“弥苴佉江”,“东”“南”之间“矣辅江”,“西”字样旁有“西洱河者西河如耳,即大海之耳也。河神有金螺金鱼也。金鱼白头头上有轮爰。毒蛇绕之,居之左右。分为两河也……”
学界对于此“双蛇鱼螺图”由于可供对照的资料实在太少,至今仍然没有定论。诸家观点可以总结为鱼螺为善蛇为恶与鱼螺蛇均为善神两类。多数学者归结为祖先崇拜,如杨跃雄等人将图中交尾红蛇辨认为今天白族人崇拜的“祖先蛇”,进一步将其辨认为祖先崇拜⑧。也有不同观点,如侯冲认为根据文字卷内容,祭祀鱼螺两河神是为了“息灾难”,甚至与汉文化的“阴阳历数”可能有关系⑨。
如要了解这幅画的来龙去脉,需重回图与文字的语境之中。《文字卷·西洱河记》则有记载:“……记云:西耳河者,西河如耳,卽大海之耳也。主风声、扶桑影照其中,以种瑞木,遵行五常,乃压耳声也。二者,河神有金螺金鱼也。金鱼白头,额上有轮。蒙毒蛇绕之,居之左右,分为二耳也。而祭奠之,谓息灾难也。乃于保和昭德皇帝绍兴三宝,广济四生,乃舍双南之鱼金,仍铸三部之声众……”
金螺金鱼为河神,蛇有“毒”字。两“毒”蛇相互缠绕,河神金螺金鱼在“毒”蛇围成的圈中,即其应该为祥瑞压制不吉的象征。关于金螺金鱼象征及组合的问题,在《云南古佚书钞》中找到这样的记载,“点苍山脚插入洱河,其最深长者。惟城东一支与喜洲一支。南支之神,其形金鱼戴金钱;北支之神,其形玉螺。二物见则为祥。” ⑩而在今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附近村庄也仍有在人死后于其墓中放置一个装有鱼螺和洱海水陶罐的习俗,当地人称这样的罐子为风水罐。风水罐是有灵性的,它能安息亡灵,也能庇佑子孙。
可见,鱼螺在当地被一直视为神物。鱼螺为洱海物产中最丰富也最具代表性的,其品类数量直接能影响到沿海人民的生产生活,所以在当地,鱼螺成为天然的神物是自然而然的。在如今大理喜洲河矣城的“洱河灵帝”本主庙里,有这样的对联“洱河灵帝祐名乡九隆后裔,神祗鱼螺利吾境三邑庶民”,河矣城是白族绕三灵活动的重要场所,其地所奉本主即段赤城。
在当今大理白族地区,本主信仰十分常见。“本主”为汉语意译,在白语中发音作“武增”,可理解为“我的主人”?。白族本主崇拜脱胎于不同地区的村社文化之中,携带有自身的特质。本主崇拜主要有农耕文化和村社文化两重特征,前者是由本主文化产生的渊源,即原始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决定,后者侧重于本主崇拜在白族崇拜体系中所处地位,即其托体于本主庙成为村社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一般一个村有自己的本主,或者几个村共享本主庙信奉同一本主?。即使是在现在的白族社会,本主崇拜在白族生活中仍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许多白族人遇到诸如出生、成人、婚葬、建房、出行、学业等要事,仍会到本主庙祭拜。在一些重要节日之时,村民也会齐聚本主庙。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主庙可谓是村社文化的祭祀、教育中心。本主庙承载了村民对历史民俗的记忆,在一代又一代的祭祀和相关活动中,一些文化因素流传至今。
再看《南诏野史》中讲到劝利在元和十五年(820)时改元大丰,“重修崇圣寺,五月大雨霖,龙首龙尾二关倾,除洱海河怪,建龙屋塔高十二丈。”按《白古记》记载:“唐时洱河有妖蛇,名薄劫,兴大水淹城。蒙国王出示有能灭之者赏半官库,子孙世系免差徭,部民有段赤城者,愿灭蛇缚刃入水,蛇吞之,人与蛇皆死。水患息。王令人剖蛇腹,取赤城骨葬之,建塔其上,燬蛇骨灰塔名为灵塔,每年有蛇党起风来,剥塔灰时有谣曰:赤城卖硬土。今龙王庙碑云,河龙王段赤城云永昌生两头牛……” ?
野史中又按《白古记》,提及其中洱海河怪为蛇妖薄劫。联系这个故事可知,《文字卷》中息的灾难应是水患,更进一步说是蛇妖引起的水难。而庙宇对联“神祗鱼螺”之语,以及庙内本主侍从所持鱼螺神物,鱼螺双神在河矣城本主信仰体系中的非凡地位得以显现。
至于蛇交尾的表现形式,在云南青铜文化遗存中,有双蛇相交或相互缠绕的图案的诸多青铜器,于青铜杖首、青铜兵器、青铜扣饰、铜鼓等器物上,均可看到与蛇相关的圆雕或浮雕、透雕等遗物。如石寨山可见这一图案表现形式的来源之早,有学者将其指向生殖崇拜。而冯汉骥先生则认为一些蛇的表达代表土地?,由于滇地出土带蛇纹青铜器最多,也有人认为蛇是滇人的图腾。?此类说法甚至将滇王蛇形钮作为判定依据,认为汉王朝承认滇以信仰蛇为核心的文化特征。杨勇认为这一型扣饰“底部设计蛇的图形可能还有整体构图上的考虑,这些蛇既是扣饰场景的参与者,又在无形中将扣饰的底部闭合起来,避免了因形制的不规则带来的凌乱感。” ?
显而易见的是,蛇这一形象在西南地区青铜文化中占据著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探讨青铜文化中的蛇形象是如何影响到后世艺术品的形态时,我们应当意识到鱼螺蛇为各地特产,是天然的观察对象,当材料之间时代间隔过于久远,判断必须十分谨慎。
通过资料搜集,在大理国时期的《张胜温梵像卷》中发现了相似图案。然而奇怪的是,鱼螺和蛇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南诏图传》中鱼螺在双蛇之内,而《张胜温梵像卷》鱼螺已在双蛇之外自由游动。毋庸置疑,前者的双蛇鱼螺是后者创作之母本。画卷里的不同形象表达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内涵,如《南诏图传》卷偏后的位置,一尊铜鼓歪倒于观音像之内,说明此图有意表达佛教信仰的深远,以至于压倒了代表原始土著文化的铜鼓。故而双蛇鱼螺图的表达并非偶然。
在创作《张胜温梵像卷》的时代,“西洱河记”被认为象征了国运将衰,《梵像卷》里的双蛇有“救苦观世音”压制,所以世间太平,鱼螺便没有被禁锢在蛇环之内。
与此同时,双蛇鱼螺图也应是一个洱海地区的古地图,“西耳河者,西河如耳,卽大海之耳也”“蒙毒蛇绕之,居之左右,分为二耳也”等语则说明双蛇则表示洱海,鱼螺分别指示南北。
三、总结
唐宋之际,在中国西南边疆出现了一个影响甚广的少数民俗政权,即南诏国。由于一些历史原因,许多史书记载的南诏国内容少且不详细,明代学者杨慎先生的《南诏野史》弥补了一般所编纪类阙遗部分,有关蒙氏政权的始末尤为详细。其中谈到蒙氏细奴逻于公元649年在蒙舍川(即今大理巍山地区)建国,细奴逻的后代皮逻阁自公元728年起,开始吞并周边其余五诏,称王南诏。并至于舜化真公元902年亡国。在数代南诏王的经营下,逐渐成了一个大国,其势力范围主要在当今的云南地区。而南诏国势力的坐大与唐王朝的支持密不可分。
在此背景之下,南诏与中原唐王朝交往甚密,文化交流尤为密切。李灿霖先生评述藏于纽约都会博物馆中的《维摩诘经》的字体书法与扉页维摩诘会图,认为其唐风俨然,甚至难与汉地书画相区分。《南诏图传》也是古大理地区与中原密切交往的一个见证,无论画卷安排还是人物服饰,都可以见到汉地文化的影子。
从考古材料看,与佛教有关的文物集中出现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南诏图传》解释了佛教在南诏流行的前因后果,《张胜温梵像卷》则是南诏大理国宗教绘画的集大成之作。在这些绘画中,也能见到中原佛教对南诏文化的影响,《大理行记》中记载:“所诵经律,一如中国。”到了元代两地宗教已经到了很相似的地步了。通过分析《南诏图传》的绘画细节以及“西洱河记”在两幅画卷中的表达转变,可以一窥当时社会的宗教面貌,了解佛教在大理地区流传之初始,可谓意义深远。
注释:
①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台湾民族学研究所1967年版,第90-120页。
②Chapin,Helen B:“Yünnanese Images of Avalokite?var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8,no.2(1944):131-86.https://doi.org/10.2307/2717954。
③Wenley,A.G:“A Radiocarbon Dating of a Yünnanese Image of Avalokite?vara.”Ars Orientalis 2(1957):508.http://www.jstor.org/stable/4629060。
④汪宁生:《〈南诏中兴二年画卷〉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80年第00期,第136-148页。
⑤杜成辉:《〈南诏图传〉中补绘的“文武皇帝”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4期,第144-147页。
⑥李灿霖:《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台湾民族学研究所1967年版,第90-120页。
⑦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20页。
⑧杨跃雄、王笛:《〈南诏图传·洱海图〉与白族的“祖先蛇”崇拜》,《昆明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8页。
⑨侯沖:《白族心史》,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2年版,第310页。
⑩王叔武辑著:《云南古佚书钞》,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杨仕:《试论白族本主崇拜的性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第58-63页。
?杨政业:《白族本主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15页。
?(明)倪辂辑,(清)王崧校理,(清)胡蔚增订,木芹会证:《南诏野史会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像试释》,《考古》1963年第6期,第12页。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
?杨勇:《云贵高原出土青铜扣饰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3期,第26页。
作者简介;
杨硕,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西南考古、史前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