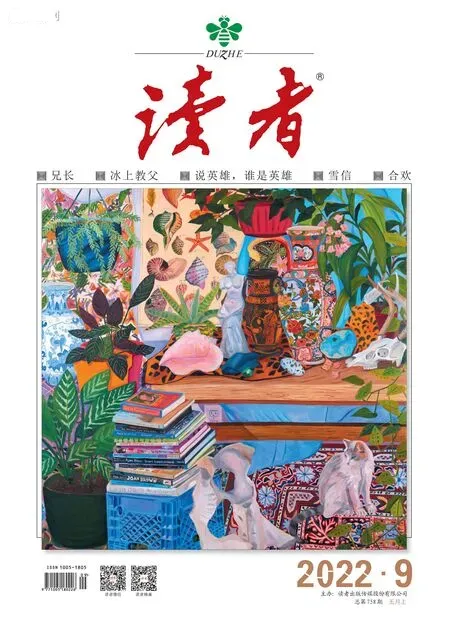兄长
☉梁晓声

如果谁面对自己的哥哥,心底油然冒出“兄长”二字的话,那么大抵他已经老了,并且他的兄长肯定更老了。
几天前,在精神病院的院子里,我面对我唯一的哥哥,心底忽然冒出了“兄长”二字。
我的兄长大我6岁,今年已经68周岁了。从20岁起,他一大半的岁月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在我的记忆中,我与兄长之间的亲情只体现在一件事上:我三四岁时,大病了一场,某天傍晚我躺在床上,对坐在床边心疼地看着我的母亲说,我想吃蛋糕。之前我在过春节时吃过一块,觉得那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外边下着瓢泼暴雨,母亲保证雨一停,就让我哥去为我买两块。我却哭了起来,闹着说立刻要吃到。当年十来岁的哥哥,脱了鞋、上衣和裤子,只穿着裤衩,戴上一顶破草帽,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冒着暴雨去为我买回来。
外边又是闪电又是惊雷的,母亲表现得很不安,不时起身走到窗前往外望。我觉得似乎过了挺长时间哥哥才回来,他进家门时的样子特别滑稽,一手将破草帽紧拢胸前,一手拽着裤衩的腰边。母亲问他买到没有,他哭了,说第一家铺子没有蛋糕,只有长白糕,第二家铺子也是,跑到第三家铺子才买到。说着,哭着,弯下腰,使草帽与胸口分开,原来两块用纸包着的蛋糕在帽兜里。那一刻他不像什么落汤鸡,而像一条刚脱离了河水的娃娃鱼;他有点儿像在变戏法,尽管终于变出了两块,但委实变得太不容易,所以哭了。
其实对于我,长白糕和蛋糕是一样好吃的东西。我已经几顿没吃饭了,转眼就将蛋糕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母亲却发现,哥哥的胳膊肘、膝盖破皮了,正滴着血。
后来,每每我恨他时,当年他那种像娃娃鱼又像变戏法的少年的样子,就会逐渐清楚地浮现在我眼前。于是,我心里的恨意也就逐渐地软化了,像北方人家从前的冻干粮,上锅一蒸,就暄腾了。只不过在我心里,热气是回忆产生的。
是的——此前我许多次地恨过哥哥。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哥哥已经在读初三了,而我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的这3年,正是哥哥从高一到高三的阶段。那时,我身下又添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们平时是不太见得到哥哥的,我们能见到母亲的时候,并不比能见到哥哥的时候多。作为建筑工人的父亲,则远在大西南工作,每隔两三年才得以与全家团聚一次,每次12天的假期。当年父亲的工资每月只有64元,他每月寄回家40元,自己花10余元,再攒10余元。如果不攒钱,他探家时就得借路费了。父亲的工友到我家里来时,曾同情地对母亲说:“梁师傅太仔细了,舍不得买食堂的菜吃,自己买点儿酱、买几块豆腐乳下饭。两分钱买一块豆腐乳,他往往能吃3天!”
那话,我是亲耳听到的。
父亲寄回家的钱,十之八九是我去邮局取的。从那以后,每次看着邮局的人点钱给我,我的心情不是高兴,而是特别的难受。正是那种难受,使我暗下决心,初中毕业后,但凡能找到一份工作,我就一定不读书了,早日为家里挣钱才更要紧!
父亲的工友一走,哥哥就哭了。母亲已经当着来人的面落过泪了,见哥哥一哭,便这么劝:“儿子别哭,你一定要考上大学,好不好?家里的日子再难,妈也要想方设法供你到大学毕业!等你大学毕业了,家里的日子不就有缓了吗?”
从那以后,我们见到哥哥的时候就更少了,学校几乎成了他的家。从初中起,他就是全校的尖子生,也是校团委和学生会的干部,多项荣誉加于一身。
每月40元的生活费,是不够母亲和我们5个儿女度日的。母亲四处央求人为自己找工作。
我从小学二三年级起就开始做饭、担水、收拾屋子,做几乎一切家务了。我对哥哥是很恼火的。我认为挑水这一项家务,不管怎么说也应该是哥哥的事,但哥哥几乎将全部心思都扑在学习上了。
1962年,我们搬了一次家。那一年我该考中学了,哥哥将要考大学。
6月,父亲回来探家,他明显老了,而且特别瘦,两腮都塌陷了。
一天,屋里只有父亲、母亲和哥哥在的时候,父亲忧郁地说:“我快干不动了,孩子们一个个全都上学了,花销比以前大多了,我的工资十几年来却一分钱没涨,往后怎么办呢?”
母亲说:“你也别太犯愁,那么多年的苦日子都熬过来了,再熬几年就熬出头了。”
父亲说:“你这么说是怪容易的,实际上你不是也熬得太难了吗?我看,千万别鼓励老大考大学了,让他高中一毕业就找工作吧!”
父亲又对哥哥说:“老大,你要为家庭也为弟弟妹妹们做出牺牲!”
哥哥却说:“爸,我想过了,将来上大学的几年,争取做到不让您给我寄钱。”
父亲火了,大声嚷嚷:“你究竟还是不是我儿子?!难道我在这件事上就一点儿也做不了主吗?”
在父亲的压力之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复习,托邻居的关系到菜市场帮着卖菜。
有一天傍晚,哥哥回到家里,将他一整天卖菜挣到的两角几分钱交给母亲后,哭了。
他的同学和老师都认为,他似乎天生可以考上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
哥哥没再去卖菜,也没重新开始备考。他病了,嗓子肿得说不出话来,躺了3天。同学来了,老师来了,邻居来了,甚至街道干部也来了,所有的人都认为父亲目光短浅,让哥哥不要听父亲的。
哥哥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他是为母亲考那所学院的。哈尔滨当年有不少漂亮的铁路员工房,母亲认为,只要哥哥以后成了铁道工程师,我家也会住上那种漂亮的铁路房。
父亲给家里写了一封有一半错字的亲笔信,以严厉到不能再严厉的词句责骂哥哥。
哥哥带着对父亲、对家庭、对弟弟妹妹的深深的内疚,踏上了开往唐山的列车。
哥哥上大学之后的第一个假期没探家,来信说要带头留在学校勤工俭学。第二个假期也没探家,说是等父亲有了假期,与父亲同时探家。而实际上,他是因为没钱买车票才不回家的。
哥哥上大学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不久,家里收到了一封学校发来的电报:“梁绍先患有精神病,近日将由老师护送回家。”电文是我念给母亲听的。
母亲一直拿着电报发呆,一会儿看一眼,坐到了天明。我虽然躺下了,却也彻夜未眠。
第二天我正上最后一堂课时,班主任将我叫出了教室——在一间教研室里,我见到了分别一年的哥哥,还有护送他回来的两名男老师。那时天已黑了,北方迎来了第一场雪。护送哥哥的老师说,哥哥不记得回家的路了,但对中学母校的路熟稔于心。
哥哥回来了,全家人都变得神经衰弱。因为哥哥几乎不分白天黑夜,终日喃喃自语。
两个月后,精神病院通知我们,医院有床位了。一辆精神病院的专车开来,哥哥被几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强制性地推上了车。家人的精神终于得以松弛。
而我的学习成绩一塌糊涂。
哥哥在医院住了3个月,在家中休养了一年后,精神似乎基本恢复正常了。一年后,他的高中老师将他推荐到一所中学去代课,他每月能领35元的代课工资。据说,那所中学的老师们对他上课的水平评价挺高,学生们也挺喜欢上他的课。
那时母亲已没工作可干了,家里的生活仅靠父亲每月寄回的40元勉强维持。每个月一下子多了35元,生活改善的程度简直接近幸福了。
那是我家生活的黄金时期。家里买了鱼缸,养了金鱼,也买了网球拍、象棋、军棋、扑克。母亲是为了使哥哥愉快。我和弟弟妹妹们都知道这一点至关重要,都愿意陪哥哥玩。
如今想来,那也是哥哥人生中的黄金时期。他指导我和弟弟妹妹们的学习十分得法,我们的学习成绩都快速地进步了。我和弟弟妹妹们都特别尊敬他,他也经常表现出对我们的关心。母亲脸上又有了笑容。甚至有媒人到家里来,希望能为哥哥做成大媒。
半年后,哥哥的代课生涯结束了。他想他的大学了。
精神病院出具了“完全恢复正常”的诊断书,于是他又接着去圆他的大学梦了。那一年,哥哥所读的桥梁设计专业迁到四川去了,而父亲仍在四川。父亲的工资涨了几元,他也转变态度,开始支持哥哥上大学了。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那一年是1965年。然而哥哥的大三没读完——有人“大串联”去了,有人赴京请愿告状,有人留在学校打“派仗”。
哥哥又被送回了家——他又疯了。
这下,全家人都看管不住哥哥了,经常是,一没留意,哥哥就失踪了。母亲东借西借,为哥哥再次住院凑钱。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毫不犹豫地第一批就报了名——每月能挣40多元钱啊!我要无怨无悔地去挣!那么,家里就交得起住院费,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就能获得拯救了。
我下乡的第二年,三弟也下乡了。我和三弟省吃俭用寄回家的钱,几乎全都用来支付哥哥的住院费了。后来四弟工作了,再后来小妹也工作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支付不起哥哥常年住院的费用,因为每月要80多元。幸而街道办事处挺体恤我家,经常给开半费住院的证明。而半费的住院者,院方是比较排斥的,故每年有半年时间,哥哥是住在家里的。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发现家里的窗上安装了铁条,玻璃所剩无几,代之以木板,镜子、相框甚至暖壶等易碎的东西一件也没有了,连菜刀、碗和盘子都被锁进了箱子。
我发现,母亲额上有一处可怕的疤,很深。四弟和小妹谈起哥哥简直都谈虎色变了,而母亲含着泪说,她额上的伤疤是自己不小心撞在门框上而导致的。
那时,我的内心产生了憎恨。我认为哥哥已经不是哥哥,而是魔鬼的化身。我暗自祈祷:“老天啊,为了我的母亲、四弟和小妹的安全,我乞求你,让他早点儿死吧!”
那次探亲假期里,我一次也没去看他。临行前我对四弟斩钉截铁地嘱咐道:“能不让他回家就不让他回家!住院费你们别操心,我要让他永远住在精神病院里!”
我托了关系,哥哥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半费常住患者。
我在回到兵团的次年,成为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在复旦的3年,我只回过一次家,为了省钱。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我又承担了替哥哥付医药费的义务。为了将这项义务可持续地承担下去,我曾打算将独身主义坚持到底。两个弟弟和小妹先后成家,在父母的一再劝说和催促之下,我也只好成家了。接着,我有了儿子,将父母接到北京来住,埋头于创作,在北京“送走了”父亲,攒钱帮助弟弟妹妹改善住房条件……
各种责任纷至沓来,使我除了支付住院费一事,简直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对于我,似乎只成了“一笔支出”的符号。
1997年,母亲去世时,我坐在病床边,握着她的手,问她还有什么嘱咐。
母亲望着我,眼角淌下泪来。母亲说:“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块儿死,这样他就不会拖累你了……”
我心大恸,内疚极了,俯身对母亲耳语:“妈妈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哥哥,绝不会让他永远待在精神病院里……”
办完母亲丧事的第二天,我住进一家宾馆,让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来。哥哥一见到我,就高兴得傻小孩似的笑了,说:“二弟,我好想你。”
算来,我竟20余年没见过哥哥了,而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我不禁拥抱他,一时泪如泉涌,心里连说:“哥哥,哥哥,实在是对不起!对不起……”
我帮哥哥洗了澡,陪他吃了饭,与他在宾馆住了一夜。哥哥以为他从此自由了。而我只能实话实说:“现在还不行,但我一定尽快将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回北京,我就动用轻易不敢用的存款,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简易装修,添置家具。半年后,我将哥哥接到了北京,并动员邻家的弟弟二小一块儿来了。二小也是返城知青,常年无稳定工作、稳定住处。由他来照顾哥哥,我给他开一份工资,可谓一举两得。他对哥哥很有感情,由他来替我照顾哥哥,我放心。
于是哥哥的人生,终于是一种正常的人生了。
那3年里,哥哥生活得挺幸福,二小也挺知足,他们居然都渐渐胖了。我每星期去看他们,和他们一块儿做饭、吃饭、散步、下棋,有时还一块儿唱歌……
好景却不长,二小回哈尔滨探望他的哥哥妹妹,不慎从高处跌下,不幸身亡。这个噩耗使我伤心了好多天,我只好向单位请了假,亲自照看哥哥。
我对哥哥说:“哥,二小不能回来照顾你了,他成家了……”
哥哥怔愣良久,竟说:“好事。他也该成家了,咱们应该祝贺他,你寄一份礼给他吧。”
我说:“照办。但是,看来你又得住院了。”
哥哥说:“我明白。”
那年,哥哥快60岁了。他的头脑、话语和行动都变得迟钝,其实没有任何可能具有暴力倾向的表现。相反,倒是每每流露出低人一等的自卑来。
我说:“哥,你放心,等我退休了,咱们俩一块儿生活。”
哥哥说:“我听你的。”
前几天,我又去医院看他。天气晴好,我们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我一边看着他喝酸奶,一边和他聊天。
我问哥哥:“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
哥哥说:“那是一个童话。”
我又问:“为什么是童话?”
哥哥说:“妈妈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更好地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妈妈编那个童话,我努力实现那个童话。当年我曾下决心,不看着你们几个弟弟妹妹都成家立业了,我是绝不会结婚的……”
他看着我苦笑。
原来哥哥也有过和我一样的想法!我心一疼,黯然无语,呆望着他,像呆望着另一个自己。
哥哥起身将塑料盒扔入垃圾桶,坐下后,看着一只猫反问:“你跟我说的那件事,也是童话吧?”
“什么事?”我的心还在疼着。
“就是,你保证过的,退休后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
(鬼 鱼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人间清醒》一书,本刊节选,宋德禄图)
——被大自然接管的精神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