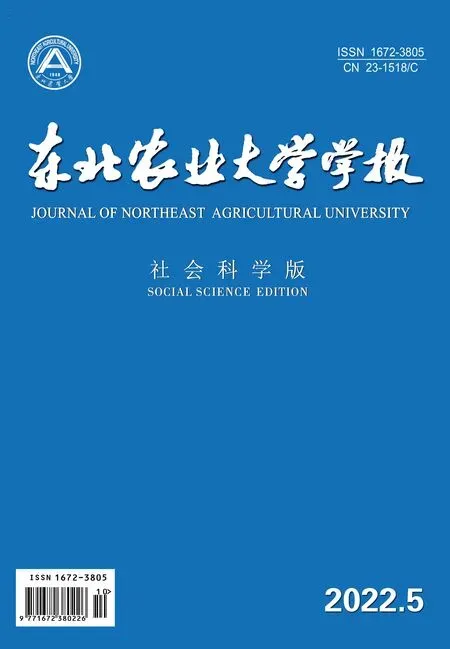我国社会企业信息披露制度构建
——基于美英立法启示
方祖鹏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企业是一种融合社会公益目的和商业经济目的的社会组织形式,兼具公益与营利双重性质。虽然基于不同背景,学者对社会企业的定义略有不同,但具有两个公认的本质特征:一是具备公益目的,且公益目的不得居于次要地位;二是通过市场化交易获得利润。因此,无论是营利组织还是非营利组织,一个企业只要具备这两个本质特征,理论上就可以被称为社会企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机关还为社会企业创设了法定组织形式,典型者如美国的共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和英国的社区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自20世纪80、90年代初露萌芽以来,社会企业在全球蓬勃发展,并被称为“小企业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1]。目前,美国非营利组织B Lab已认证4 649家社会企业,遍布78个国家和155个不同行业①B Lab网站,https://www.bcorporation.net/en-us/?_ga=2.51674345.1592138004.1645415997-1739829984.1645415997,2022年6月29日访问。。英国现有超过10万家社会企业,市值约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为英国经济贡献了超过600亿英镑,并雇佣了200万名员工②英国社会企业联盟(SEUK)网站,https://www.socialenterprise.org.uk/policy-and-research-reports/the-hidden-revolution/,2022年6月29日访问。。社会企业实践发展也促进了相关学术研究升温。社会企业目前已成为国外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顶尖大学均已开设专门研究社会企业的课程[1]。
我国社会企业正在获得快速发展动能,并在普惠性教育、养老事业、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特定群体就业、创新社区治理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经济与社会价值。民政部指导下成立的非营利组织——中国慈展会自2015年起联合多家公益研究机构开展社会企业认证,目前已认证314家社会企业③社会企业认定平台网站,https://csecc.csedaily.com/,2022年6月29日访问。。根据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的估算,我国有自觉意识的社会企业数量接近1 700家④相关数据参见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扫描——调研报告2019(简版)。。为更好地引导、孵化、培育和管理社会企业,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北京市政府在第十二个、第十三个和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中都明确提出促进社会企业发展,并于2018发布《北京市社会企业认证办法(试行)》;佛山市顺德区、深圳市福田区、成都市等也出台了一系列培育和认证社会企业的政策⑤参见2014年《顺德区社会企业培育孵化支援计划》、2014年《顺德区深化综合改革规划纲要》、2018年《福田区关于打造社会影响力投资高地的意见》、2018年《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然而,正如2022年1月12日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社会企业蓝皮书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研究报告(No.1)》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企业面临合法性不足的难题[2]。一些企业夸大或虚假宣传其公益绩效从而将自己“漂绿”为社会企业;一些社会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逐渐偏离初衷,转而以营利为主要目的;部分社会企业融资困难,发展乏力。
社会企业在我国的长足发展,离不开配套的法律制度保障。与营利性企业不同,社会企业以公益为首要或主要目的。公司目的差异决定了社会企业在董事的信义义务、利润分配、资产锁定、信息披露等方面必须有较营利性企业更严格的要求。此外,社会企业发展也需要法律给予合法身份,以对外彰显和证明他们对社会目标的独特贡献,从而形成社会企业的品牌效应[3]。因此,我国应构建包括信息披露制度在内的社会企业法律制度,以推动社会企业良性发展。
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美、英社会企业的信息披露制度,分析其优劣、得失,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回答我国社会企业信息披露制度构建问题。
二、社会企业信息披露内容
(一)美、英社会企业的法定组织形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意大利、比利时、美国以及韩国等均为社会企业设立了法定组织形式。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其各州社会企业信息披露制度不尽相同,多样化立法为对比分析不同信息披露制度的实践效果提供了丰富的案例资源;英国悠久的社会企业发展史和立法史为社会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因此,本文以美、英社会企业信息披露制度为比较考察对象。
作为联邦制国家,美国各州享有广泛立法权,社会企业立法亦属于各州立法机关的权限范围。自2008年以来,各州政府在商业公司法律框架基础上创设了四种社会企业法定组织形式,其中共益公司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⑥这四种社会企业法定组织形式分别是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littl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简称L3C)、弹性目的公司(flexible purpose company,简称FPC)、社会目的公司(social purpose company,简称SPC)以及共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简称BC)。。因此下文对美国社会企业的讨论均以共益公司为代表。自2010年马里兰州率先通过共益公司立法以来,截至2022年6月,美国已有37个州通过共益公司立法,4个州正在立法进程中⑦B Lab网站,https://benefitcorp.net/policymakers/state-by-state-status,2022年6月29日访问。。美国共益公司立法采用了示范法的立法技术。即由官方或民间组织拟订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示范法,各州在示范法基础上制定相同或类似的法律,以避免各州法律冲突,减少交易成本。在共益公司立法领域,非营利组织B Lab制定了《共益公司示范法》(Model Benefit Corporation Legislation,以下简称《示范法》)。目前各州共益公司立法均参照《示范法》完成。因此,通过《示范法》可以大体窥见美国共益公司立法全貌。英国政府在2004年和2005年分别通过《2004年公司法》(Companies Act 2004)和《2005年社区利益公司条例》(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Regulations 2005,以下简称《2005年条例》),为本国社会企业打造了“社区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这一法定组织形式⑧下文对英国社会企业的讨论均指英国社区利益公司。。
(二)美、英社会企业立法规定的信息披露内容
美国《示范法》要求共益公司制作共益报告(benefit report)以披露其完成社会使命的情况。《示范法》第401条将共益报告披露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叙述性说明(narrative description)。在这部分共益公司需要对实现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定性说明,包括四方面:一是共益公司在该年度内追求一般公共利益的方式及成果;二是共益公司在该年度内追求特定公共利益的方式及成果;三是阻碍共益公司实现一般公共利益的任何情况;四是共益公司选择第三方标准(third party standard)用于编制共益报告的过程和理由。第二部分是绩效评估(assessment of performance),即根据第三方标准对共益公司在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表现所做的评估。第三部分是其他信息,包括共益董事(benefit director)名称、住址、报酬等内容。目前已制定共益公司立法的各州均参照《示范法》将披露内容分为以上三部分。英国《2005年条例》第26至28条对信息披露的内容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即披露信息应包括公益目的和财务资讯两方面内容。社区利益公司监管机构制作的社区利益报告模板,则将这一原则性规定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披露要求。具体而言,报告模板要求披露信息包括七部分:一是公司活动与其影响。社区利益公司应陈述在本年度从事的活动及其如何为社区带来利益。二是与利益相关者的协商。公司应陈述利益相关者范围及如何与其进行协商。三是董事薪酬。公司应披露该财务年度董事薪酬总额以及向离职董事支付的离职补偿金。四是关于非完全对价的资产转让。公司应陈述以非完全对价转让资产的情况,例如公司对外捐赠等。五是本会计年度股息分派情况。六是与公司运营相关的债务偿还情况。七是公司董事或秘书签名⑨社区利益公司监管人网站,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office-of-the-regulator-of-community-interestcompanies,2022年6月29日访问。。
(三)社会企业信息披露内容评析
1.法律只要求抽象的定性披露,给予社会企业粉饰成绩的空间。无论是美国共益公司立法,还是英国社区利益公司立法,均只要求公司定性说明履行社会公益的情况,没有纳入任何量化指标。这导致目前可获取的社会企业披露报告中,相当一部分是在自我宣传,这对希望全面、客观地了解社会企业的阅读者而言没有价值[4]。
定性披露虽然具有较为全面、简洁易懂等优势,但社会企业对自身价值理念、已取得成就、未来展望等信息的抽象说明不仅不能为披露报告的阅读者带来足够参考,反而可能会让其失去对社会企业的信任和投资兴趣。如果在保留定性披露的同时,引入定量披露,则可进一步展示企业特定指标在不同时间的变化及趋势。阅读者借此可更清楚地了解某一社会企业在本行业的水平,披露报告的价值可得到总体提升。
2.定性披露要求导致信息量匮乏。单纯的定性披露要求,使社会企业可以简单地对企业活动进行说明,导致披露报告中信息量极为有限[5]。Alex Nicholls以789份社区利益报告为样本所做的一项调查清楚地反映了这一问题。该调查显示,51%的社区利益公司仅使用四个或以下句子来阐述公司活动。显然,概括式说明难以向社会公众呈现一个社会企业的真实社会绩效,更难以让潜在投资者和消费者横向比较不同的社会企业。其实质只是对监管框架的象征性回应(symbolic response),充其量是在制造一种可靠的假象[6]。
三、社会企业信息披露标准
(一)美、英社会企业立法规定的信息披露标准
对于是否应在立法中要求社会企业遵循披露标准的问题,美、英立法显示出极大分歧。英国立法遵循轻触式(light touch)监管逻辑,未要求社区利益公司遵循一定的披露标准。轻触式监管逻辑倾向于采用辅导、协助以及预防的方式对待社区利益公司,其源于新公共管理改革学说。该学说反对基于规则的管理(rule-based management),认为严格的分级化管理是低效的[7]。美国内部对此也不统一,目前全美32个州的立法与《示范法》保持一致,均要求共益公司遵循第三方标准进行披露。特拉华州、肯塔基州、得克萨斯州和田纳西州的共益公司立法则体现出低度管制倾向,允许共益公司自行选择是否遵循第三方标准进行披露。
美国《示范法》第401(a)(2)条规定,共益公司须在每年制作的共益报告中纳入绩效评估。绩效评估是对共益公司社会和环境方面表现和影响力的说明,由共益公司自行制作。《示范法》要求绩效评估须根据监管者和共益公司以外的第三方机构制作的披露标准做出。目前,社会企业可以采用的第三方披露标准中极具影响力,并被广泛采纳的分别是非营利组织B Lab设计的BIA(B Impact Assessment)标准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设计的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标准。
(二)社会企业信息披露标准评析
1.是否应在社会企业立法中纳入信息披露标准。美、英立法对社会企业立法是否纳入信息披露标准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英国立法之所以不将遵循一定的披露标准纳入社会企业义务,意在给予社会企业更多灵活性。然而,除非社会企业具有高度披露自觉和卓越的披露水准,否则缺乏披露标准可能导致披露内容的无序性。社会企业披露报告价值在于真实地向外界披露企业相关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包括正面的、有利的信息,也包括负面的、不利的信息。如果任由社会企业自行决定披露内容,甚至将披露报告作为宣传工具,那么披露报告便失去了存在价值。因此,美国《示范法》要求社会企业遵循披露标准的规定,较英国相关立法更为可取。
2.是否应设置统一的披露标准。对于是否应在社会企业立法中设置统一披露标准的问题,美国立法做出了否定答复。目前美国相关立法都允许社会企业自行选择披露标准。然而,这一做法同样依赖于社会企业高度自律,一旦失去自律精神,无异于为社会企业趋利避害的选择性披露打开方便之门。
目前市场上供社会企业选择的披露标准较多,其中既有如BIA、GRI、社会责任8000这样声誉卓著、广受采纳的披露标准,也有一些粗制滥造的披露标准。第三方标准的质量几乎得不到任何监督或保证[8]。如果允许社会企业自行选择披露标准,其可能选择评估效能最弱或对自己最有利的披露标准,导致社会企业的披露报告流于形式,也会产生评估效能最弱的第三方标准反而成为最流行标准的竞次(race to the bottom)现象。
允许社会企业自行选择披露标准还会带来另一个严重的问题——社会企业披露报告的阅读者无法对比根据不同披露标准做出的披露报告。以目前最具影响力的BIA标准和GRI标准为例,根据BIA标准做出的报告以成绩单形式呈现,内容为公司在环境、劳动者、客户、社区和治理五个方面获得的分项分数和总分;根据GRI标准做出的绩效评估是以文字形式表述的详细说明,内容为公司在环境影响、经济影响及社会影响方面的具体信息。若两个社会企业分别选择BIA标准和GRI标准,并分别以成绩单和文字表述的形式做出披露时,根据两种标准做出的披露报告之间缺乏比较维度,社会企业报告的阅读者无法分辨哪一家公司的社会绩效更为优秀。可见,出于对披露质量和披露效果考量,应要求社会企业遵循统一的披露标准。
四、社会企业信息披露方式
(一)美、英社会企业立法规定的四种披露方式
披露方式是指社会企业通过何种途径将披露报告呈现给社会公众,目前美、英社会企业相关立法规定的披露方式可归纳为四种。一是网站披露制,即要求社会企业在其网站上披露报告,其见于新泽西州和纽约州的共益公司立法之中,如《纽约州商业公司法》第1078(c)条规定:“共益公司必须将共益报告公布在其网站的公共部分。”二是美国《示范法》规定的披露方式,其为共益公司提供了更多选择。这种方式区分已建立和尚未建立网站的共益公司,前者需要在网站上披露共益报告;后者不需要建立网站,只需在任何人向共益公司索要共益报告时,免费向其提供一份复印件即可。《示范法》的引领作用使这种方式广受采纳,目前27个州的共益公司立法采用这种披露方式。第三种披露方式与第二种类似,但给予了共益公司更大的灵活性,目前仅有俄勒冈州采用这种方式,如《俄勒冈州法》第50.758条规定:“共益公司需将共益报告公开在其网站上或向任何索要共益报告复印件的人免费提供该份报告。”在这种方式下,即使共益公司已建立网站,也不必将共益报告披露在网站上,只要提供共益报告给任何向其索要的人即可。四是集中披露制,即社会企业将报告提交给相关主管机关后,由该主管机关集中对外披露。英国采取这种披露方式。英国《2004年公司法》规定,社区利益公司需在每一财政年度将社区利益报告提交给公司登记处,公司登记处需将该报告转交给社区利益公司管理人,由其负责对外披露。与英国立法类似,《明尼苏达州法》第304A.301条要求共益公司将共益报告提交给州务卿,由州务卿统一将收集的共益报告披露在州网站上,共益公司无需自行以其他方式披露共益报告。
(二)社会企业信息披露方式评析
对社会企业信息披露方式的考量,应从三个相关主体视角出发。首先是社会企业本身。作为信息披露主体,社会企业的披露负担因不同的信息披露方式而异。其次是披露报告的阅读者。阅读者是信息披露的对象,不同的信息披露方式影响阅读者获取披露报告并加以对比的难易程度。第三是监管者,收集并核查披露报告是对信息披露情况进行监管的前提,披露方式决定收集披露报告的难易,进而影响监管成本。
1.从社会企业视角分析。从作为披露主体的社会企业视角出发,网站披露制预设了一个前提——所有社会企业均有自己的网站,却没有衡量前提的有效性。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共益公司没有建立自己的网站[8]。原因在于一些规模较小或创建时间较短的社会企业缺乏足够的技术人员和资金来建立和维护网站,或者尚无建立网站进行宣传的需要。对未建立网站的社会企业而言,网站披露制将给其带来额外负担。至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披露方式所包含的向索取者提供报告复印件的做法,也给社会企业带来了一定负担,因为无论索取者的数量多寡,社会企业都必须逐一回应。相比之下,集中披露制大大减轻了社会企业负担,其只需将制作完成的社会企业报告一次性上交给主管人员即可。
2.从阅读者视角分析。前三种披露方式的最大问题是披露方式的零散化,给需要横向对比不同社会企业报告的阅读者带来不便。社会企业报告的潜在阅读者,如投资者和消费者,往往需要综合查看并对比某个行业或地区的报告,从而做出投资或消费决策。若社会企业只在各自网站上做出披露,那么阅读者需逐一登入各社会企业网站,分别在网站查找并下载社会企业报告。若社会企业只向索取者提供复印件,那么阅读者需要联系各家社会企业,这一过程显然过于繁琐。而集中披露制则使阅读者可以一次性下载并比较不同的社会企业报告。
3.从监管者视角分析。网站披露制意味着对社会企业披露情况进行监管需像普通阅读者一样逐一登入各社会企业网站,增加了监管成本。而“向索取者提供复印件”的披露方式虽然在表面上给予社会企业更多灵活性,但事实上可能只是制造了一种公众可以获得社会企业报告的假象。2017年一项调查显示,在收到调查者索取共益报告的信函后,119家共益公司中只有5家依法提供[9]。可见,被动的披露方式难以保证社会企业依法披露。对这一披露方式的监管同样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在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相比之下,集中披露制则便于监管。该披露方式要求社会企业直接向监管者提交报告,而无需采用登入网站等手段核实社会企业披露情况,节省了时间成本,提高了监管效率。
五、社会企业违规披露的处罚
(一)美国社会企业相关立法规定的违规披露处罚
目前美国少数几个州走在了《示范法》前,根据本州情况制定了对违规披露的处罚,可分为三种:一是罚款。如《罗德岛州法》第7-5.3-13(f)条规定:“在本章规定的(提交共益报告的)时间后三十天内,任何一家未能或拒绝提交其年度报告的共益公司,每年将被罚款25美元。”二是撤销资格(revocation of status)。如《明尼苏达州法》第304A.301条规定:“若一公共共益公司没有在任何日历年的4月1日前按照本章要求提交社会共益报告,则州务卿应撤销其社会公共共益公司资格。”相比明尼苏达州,新泽西州则给予共益公司一段补正行为的宽限期,《新泽西州法》第14A:18-11(d)(2)条规定:“如果共益公司在两年内未向州财务部门提交共益报告,则财务部门可以准备并提交一份声明,声明该公司已丧失其作为共益公司的资格,且不再受本法约束。”三是行政解散(administrative dissolution),目前只有新罕布什州规定这种处罚措施。相较于撤销资格,行政解散更为严苛。撤销资格只是使一家企业丧失共益公司资格,企业还可以其他公司形式存续并经营;行政解散则直接宣告共益公司主体消灭,企业不得再从事任何经营活动。
(二)社会企业违规披露的处罚评析
罚款的优势在于执行简单,但其缺陷也显而易见。首先,罚款的数额难以把握,若数额过低,例如罗德岛州规定25美元罚款,惩罚力度不足以震慑违规披露的社会企业;若数额过高,又会给社会企业带来过重负担。其次,在没有其他配套措施的情况下,社会企业在缴纳罚款后,即使仍不进行合规披露,也不会受到进一步处罚。因此,单采罚款无法对社会企业进一步施加压力,督促其矫正违法行为。
撤销资格的优势在于能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促使社会企业进行合规披露。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采用撤销资格作为处罚措施的明尼苏达州,共益公司的合规披露情况远胜于其他州[9]。但撤销资格也存在问题——其可能成为某些社会企业投机取巧的工具。一般来说,社会企业转换为普通营利公司属于公司性质的重大转变,需经多数股东同意。而单以撤销资格作为违规披露的处罚,则使社会企业的管理者可以通过故意不披露合规报告使公司被撤销社会企业的资格,自动转为一般商业公司,从而规避多数同意条款的限制,且无需受到任何其他处罚,最终侵害股东权利[8]。
行政解散作为违规披露的处罚措施则过于严苛。行政行为应遵循比例原则,即行政权力所采取的措施必须与能达致的目的相称。一些小公司和初创公司的违规披露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囿于财务资源和学习成本等问题,立法应为其留下纠正错误的空间,一概行政解散有责罚过当之嫌。此外,从整体来看,社会企业目前仍处于成长阶段,过于严厉的法律责任将阻碍创业者成立社会企业,不利于社会企业整体发展。
综上,单采任何一种处罚措施效果都不尽理想。因此,应将不同的违规披露处罚措施相结合,首先采用较轻的处罚,以督促社会企业尽快进行合规披露;对仍违规披露的社会企业采用更重的处罚方法。通过不同处罚方法的搭配使用,达到促进社会企业合规披露的目的。
六、我国社会企业信息披露制度构建
我国虽尚未建立社会企业信息披露制度,但一些营利性企业已自发地在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和市场交易所等机构要求下进行社会责任信息的定期披露⑩关于我国要求企业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规定,参见《清洁生产促进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据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企业共发布2 097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10]。除以美、英经验为借鉴外,还可以参考我国营利性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实践,以实现国外经验与本土实践的有机结合。
在参考我国营利性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实践时,需厘清营利性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社会企业信息披露的异同。二者相同之处在于,披露内容均为履行社会责任的相关信息;相异之处在于,首先,作为披露基础的企业目的不同。营利性企业目的是营利,其实现社会共益仅属于被倡导的行为,而非强制性义务;而社会企业兼具营利与社会目的,实现社会公益是社会企业的根本任务。其次,企业目的决定营利性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并无法律和行政法规要求;而社会企业对其实现社会公益的情况进行披露则为法定义务。最后,除非部门规章和行业规范另有要求,营利性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标准和方式都可自行决定,且往往较为宽松;而社会企业信息披露的内容、标准和方式均应由法律规定,且要求均高于营利性企业。本文在参考美、英经验和我国实践基础上,提出以下构建社会企业信息披露制度建议。
(一)在披露内容中同时纳入定性和定量说明要求
定性说明是对事物“质”的说明方法,优点在于简洁易懂、制作成本低,缺点在于较为抽象、模糊,且缺乏权威性和可信赖度。定量说明是指对事物和现象从“量”的角度切入,以数字化符号为基础进行分析的说明方法,优点在于准确、清晰、客观,缺点在于统计和制作成本较高。美、英社会企业信息披露制度显示,只要求对履行公益情况进行定性说明,会导致披露质量差、信息量少等问题。因此,我国应吸取国外社会企业披露实践及国内营利性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实践经验,在披露内容方面赋予社会企业较高要求。具体而言,应要求社会企业定量说明社会责任信息,如能源消耗总量、能源构成比率、温室气体排放量、废弃产品回收量等。同时,对一些需要长期观察收集的数据以及难以量度的绩效,如社会企业环境理念、内部环境规章制度等,允许社会企业定性说明。通过定量与定性说明有机结合,使披露内容准确清晰,为社会企业的社会业绩评价提供更全面、立体的信息依据。
(二)遵循统一披露标准
《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评价报告》显示,多家上市公司由于环保问题被有关部门通报和处罚,但这些公司却未将该类信息披露在企业网站、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其他相关环境报告中。原因在于,营利性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往往是自发的、非强制的,法律难以为其特别设置披露标准。然而,对社会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要求显然应高于营利性企业。我国应为社会企业设置披露标准,要求其遵循一定披露标准,以规避社会企业选择性披露的问题。
关于我国是否应为社会企业设置统一披露标准的问题,美、英社会企业的披露实践已显示,披露标准不统一将使依据不同标准做出的社会企业报告之间不具有可比性,阅读者难以进行横向评估。《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评价报告》也指出,我国营利性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一大问题是部分企业缺乏统一规范的撰写框架和体系,披露指标不成体系,明显无法满足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比较、分析企业环境信息的诉求。为此,该报告推荐更多企业采用统一标准发布环境信息,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信息指标的完整性、实质性和可比性。可见,未来我国应为社会企业设置统一的披露标准,以增强社会企业报告的可读性、可比性。同时,还应将披露标准分为通用标准和行业专项标准,要求所有社会企业遵循通用标准,并根据自己所处的行业遵循行业专项标准。
关于我国社会企业披露标准制定主体的问题,需要结合国情具体分析。根据我国《标准化法》第5条规定,依制定主体而分,可分为国家、行业、地方与企业标准四类。由政府制作披露标准可能出现专业性不足、资源损耗大和制定周期长等问题,由企业制作披露标准存在披露标准不统一、未充分听取利益相关者意见、难以横向比较和大型企业把持标准制定话语权等问题。因此,我国应避免完全放权于企业制作披露标准,而是在立足本土实践基础上尝试结合公私主体优势。具体而言,应将建立本土化社会企业披露标准体系的任务交由同时具备公私主体因素的行业协会。其一,行业协会具有专业经验和技术优势。其二,已制定的披露标准需要根据社会情况变化及时修订,行业协会在社会情境变化时可以快速反应,进行迅速、有针对性的增补。其三,可以避免由企业制定标准导致的行业内不同标准泛滥、无法进行横向比较的问题。其四,披露标准不仅对社会企业的品牌声誉具有直接影响,指标选定、指标口径决定着社会企业的披露成本,因此,披露标准的制定需要广泛和有效的沟通。行业协会作为行业内各方利益的代表者,对于减少冲突与摩擦、实现多方利益平衡、降低遵从成本(compliance cost)具有重要作用。
由行业协会制定披露标准,也可能存在大型企业把持披露标准制定权,进而根据自己经营特点量身定做披露标准的风险。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充分贯彻合作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理念,发挥企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首先,在披露标准制定过程中,要求行业内社会企业广泛参与,以促进各方利益相关者形成共识,在规则制定中反映出共同价值。其次,在披露标准制定后,应由政府机关批准。通过政府机关的严格审查,防止偏袒特定社会企业的披露标准的出现。
(三)建立统一信息披露平台
目前我国营利性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式大体上可归纳为三种。一是在统一的信息平台上披露,如证券交易所网站、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这种披露方式对应美、英社会企业立法的集中披露制。二是在公司网站披露,并将报告置备于公司经营场所。三是通过信息专刊、新闻媒体等公开方式对外披露[11]参见《证券法》第85条、《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第10条和《清洁生产审核办法》第25条的规定。。这三种披露方式对我国社会企业信息披露方式的设计有重要参考价值。
未来我国社会企业的披露方式应包括作为“硬法”的强制披露和作为“软法”的鼓励披露。关于前者,我国应构建社会企业信息披露统一平台,并要求所有社会企业将信息披露报告集中上传至该平台。首先,可以减轻社会企业另建网站的经济负担。其次,可以方便阅读者获得并横向比较。最后,节省了监管者的时间成本,提高了监管效率。
至于在公司网站披露、通过新闻媒体对外披露等方式,虽有助于扩大社会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力,但成本较高,可能会给一些经济实力较弱的社会企业造成较大财务压力。因此,可以将这些方式列为鼓励披露方式,即在社会企业信息披露制度中鼓励采用网站披露、新闻媒体披露等方式,使得有余力、有意向的社会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披露方式向社会公众宣传自己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
(四)采取多层次违规披露处罚措施
我国《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中对违规披露信息企业的处罚规定可为借鉴。该条例规定,违规披露信息的企业应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罚。企业若纠正违规披露行为,则可被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满3年未纠正,则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并向社会公示。被列入该名单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3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我国应避免美、英等国处罚措施单一的做法,建立多层次的处罚措施。具体而言,第一层次处罚措施可以效仿《排污许可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公告”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中规定的“黑名单制度”,即当社会企业未如期公示社会企业报告或公示信息不实时,在社会企业信息披露统一平台上公示这些企业名录。由于“黑名单”可以给违规披露的社会企业的商誉带来显著负面影响,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督促社会企业尽快纠正违规披露行为。若社会企业在接受第一层次处罚后6个月内仍未纠正,则采用第二层次处罚措施。第二层次,可以参考我国《环境保护法》《证券法》及美国罗德岛州的相关规定,对违规社会企业及负责信息披露的自然人施加罚款。除罚款外,还可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中,对违规披露的社会企业予以限制或禁入。若社会企业在接受第二层次处罚后6个月内仍未纠正,则采用第三层次处罚。进入第三层次意味着社会企业违规披露时限已达一年以上,此种行为不仅使社会公众无从了解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相关信息,更让监管者无法根据其社会企业报告实施有效监管。我国可以借鉴美国明尼苏达州和新泽西州《共益公司法》的规定,采用撤销社会企业资格措施,以实现对严重违规行为的精确打击。
多层次处罚措施既给予了社会企业充分的纠正错误的弹性空间,允许社会企业在及时纠正违规披露行为时从“黑名单”中被除名,不至于给社会企业带来过重负担,有效地利用法律效力和市场作用的双向压力促进披露合规化;又在社会企业拒不改正时以更高层次的处罚进一步施加压力,以促使其合规披露,体现了“引导为主、惩戒为辅”的处罚精神,有助于规范我国社会企业的信息披露行为。
七、结语
社会企业体现了当代各国在复杂多变、充满挑战的新社会形势下对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追求与尝试。目前我国社会企业正在获得快速发展动能,建立信息披露制度有助于扫清发展道路上的“漂绿”“使命漂移”和融资困难等阻碍。美、英等国的社会企业信息披露制度为我国相应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我国社会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具体构建中,应同时纳入定性和定量说明要求,从而为社会企业的评价提供准确和直观的信息依据;并要求社会企业遵循统一披露标准,以确保信息披露的全面性和可对比性;同时,应建立供社会企业进行信息披露的统一平台,从而为社会企业、阅读者和监管者提供便利;还应依据“引导为主、惩戒为辅”的处罚精神,采取多层次处罚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