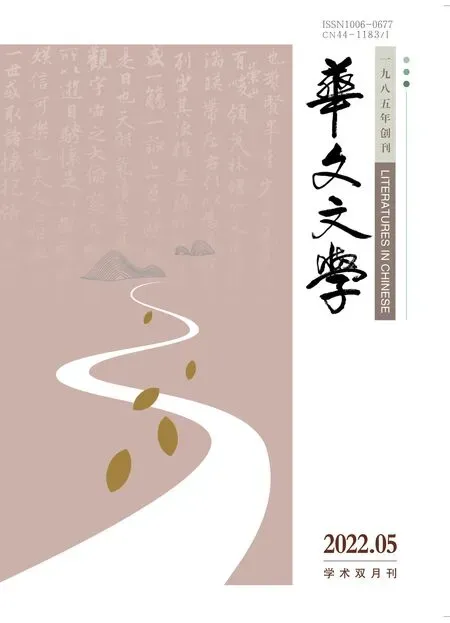南洋爱与死:黎紫书小说的在地经验与景观书写
蒋成浩
1990年代以来,黎紫书的小说多次获得“花踪文学奖”、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等奖项,并在文坛取得良好的口碑,她以瞩目的文学实绩成为马华文学亮丽的风景。无论是早期的短篇小说《蛆魇》《出走的乐园》《野菩萨》,还是近年来的长篇力作《告别的年代》《流俗地》,黎紫书的小说始终彰显出独特的身份标识。她以“南洋”的在地经验为依托,细腻且深入地呈现出个体命运在本土风景、历史空间中的丰富性。蕉风椰雨的南洋景观、五方杂处的文化图景,在黎紫书的小说中不只是纯然客观的“在地”生态,更是她精心营构的艺术空间的基石。黎紫书凭借敏锐的艺术直觉,将南洋的本土风景与在地经验熔于一炉,成为小说的独特性之所在,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一、历史的背影:新老华人的经验错位
黎紫书的小说始终延续着一贯的主题,她擅长营造恐怖、阴暗、压抑、梦魇般的氛围。她笔下的小人物生存在历史低矮的天空之下,蜷缩于城市阴暗的一隅,瑟缩在潮湿的阁楼之上。黎紫书“总在自己的阴暗空间中,过滤着社会人生中的毒汁,用那阴冷浓稠的毒汁告诉世人,在这个污浊世间中有着那让人透不过气的郁闷、沉闷、阴暗和无奈”①。在她的小说里,南洋的白蚁摧枯拉朽般蚕食着木质建筑,家族秘史如同神秘的热带雨林,等待主人公只身入林前去探索。不独黎紫书,在新生代的马华作家中,黄锦树、李永平等作家的小说都营造出一种低沉、阴暗的氛围,黄锦树的小说集《死在南方》《雨》中,每一则故事都与寻找、暴力、死亡息息相关,在他的笔下,死亡成为生命的常态,历史与暴力总是同一副面孔。而李永平的《大河上下》《雨雪霏霏》则将本土想象发挥到极致,他笔下的主人公溯流而上,深入雨林,寻找的是生命、国族的寓言,是鲜血凝聚的历史。他们的写作都与自身所获取的在地经验密切相关,都是作家自我意识、学识、情感、洞见的投射。
所谓“在地经验”,是后现代地理学观照下的一整套“人地关系”的经验体系与知识范畴,它更强调个体与地方的情感的动态联结,地方是广义上“空间”的一部分,“当我们感到对空间完全熟悉时,它就变成了地方”②。地方之为地方最显著的特点是区隔,是地域上的边界性,它通过清晰的边界划分将群体规约在特定的地域,“地方”天然的具有“排他性”,并形成区域内独特的文化经验。晚清以来,中国内乱频频,粤东南地区的中国人迫于生计,大量移民马来西亚,并形成了“在地性”的华人文化。移民社会的文化形态是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从华人离开故土、枝叶飘零到逐渐在马来西亚本土定居、落地生根,其间不只是身体从流徙到安定的转变,更衍生出复杂的在地经验和身份认同,因此,华人的生存境遇构成了马华作家最关切的命题。细读马华作家的文学书写,文本给人的整体感受总是偏向于低沉、阴暗,他们笔下的人物小心翼翼的生存在历史的夹缝之中,承受着残酷的历史暴力。个体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生与死都像极了南洋的植物,寂寞的生长、委顿。
黎紫书的文学创作深受大马在地经验的影响,并鲜明地标识出了自己的文学风格。身为新生代华人,黎紫书始终从本土经验中汲取营养,将其转化为文学经验,华人特殊的生存境遇与多元的文化场域,又为黎紫书提供了观察与思考的多维视角,使其不断探索人生世相的丰富性。黎紫书成名于1990年代,她是土生土长的大马新生华人,“经验是由感受和思想结合而成的”“经验意味着一个人从已经经历的事情中学习的能力”③。在她的作品里,时常能够窥探到华人早期移民在大马的生存境遇。对黎紫书而言,华人“落地生根”不只是一种生存选择,她更关注这一过程中,个体如何面对历史的负重,以及不同代际的华人之间,如何处理逐渐分化的“中国记忆”与身份认同。
黎紫书以女性细腻的笔触试图重返早期华人移民的生存现场,在《告别的年代》中,新、老华人以不同的姿态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苏记”是老一代华人女性的代表,“杜丽安”则是土生土长的新生代华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小说中,杜丽安的母亲“苏记”没有确切的姓名,只通过寥寥数笔得知“苏记”的老家在广西桂林,年轻时移民南洋。苏记同马来西亚历史上大多数华人女性一样,她们没有姓名,没有历史,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她们是移民者,又是移民者中的女性,承受着时代与性别摊派的双重苦难。苏记长期经营着流动的炒粉档,在这片陌生之地,她唯一无法忘却的是家乡的饮食风味,在“吃”上清晰的标识出错置时空中隐藏的身份。黎紫书的小说里,“饮食”是新、老华人之间最坚固的纽带,杜丽安深得母亲的真传,做得一手好菜,在婚后,她曾以“美食”为手段抓住男人的胃、俘获他们的心,从而试图扭转自己作为女性在婚姻中的劣势地位。
黎紫书并非只聚焦于新/老华人之间的差异性,他们的差异性往往存在于相似的苦难命运中。他们成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背负着不同的历史伤痕,遭遇着不同的爱恨情仇,却都铭刻着相似的苦难。苦难最终成为一种符号,既是命运的,又是文化的标识。不独黎紫书,在马华作家笔下,老一代华人成为某种文化观念的象征,更加具有符号性、抽象性。他们有时是历史暴力的受害者,有时又是历史暴力本身,他们是垂垂老矣的“中国性”符号,是新生力量破土而出的阻碍,又是历史的记忆者、见证者。“这一段父辈奋斗、漂流和挫败的‘史前史’却要成为黎紫书和她同代作家的负担。”④黎紫书在处理新、老华人关系时相对温和,她关注到新/老华人之间因各种历史的、政治的因素而导致的失语现象。“对于土生华人而言,新的多元分化凸显出他们处境的尴尬:面对当下兴起的华人性,他们自身的华人认同究竟该置于何方?”⑤代际之间有关身份认同的困境,并不会随着多元文化的形成而消失,相反,庞大的移民群体在南洋逐渐形构了自身的文化形态,这一形态又以流变着的“中国性”为依托,但对于新生代华人而言,“中国性”反而成为身份认同的阻碍。《告别的年代》中,杜丽安是土生土长的新华人,在杜丽安身上,她已经习惯了本土的生存策略,游刃有余的在“故乡”生活。而作为老一代华人代表——苏记,她始终言语不多、老态龙钟,一辈子坚守着一个微不足道的岗位,她的历史只能凭借他人的记忆才能拼凑成模糊的剪影。苏记是“失根”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显现出失根的怅惘,因此她隐忍、退却、神秘。而对于杜丽安而言,她要凭借自己的双手创造新的生活,因此,在她身上更多的是“女性力量”的显现,她要努力开拓出属于自己的社会空间,冲破禁锢、因循的罗网。如果说老一辈华人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只能在历史的夹缝中苟延残喘,那么“当下”则是属于新生华人的时代,她们不再甘心做历史的被动接受者,而要以强势的姿态夺取创造历史的主导权。但是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正是老一辈华人筚路蓝缕、走过苦难岁月打下的历史根基。
此外,新老华人之间的经验错位不仅反映在“失语”与“言说”的矛盾结构中,还体现为始终挥之不去的充满暴力的历史记忆中。老一代华人的南洋漂泊史,始终烙印着历史的创伤,并代代相因。在黎紫书笔下,这段惨痛的华人记忆以“父辈”的形象表征了出来。黎紫书有意颠覆以往小说叙事中有关父辈的神话,在她笔下,父辈们竟成为“纵恶”的根源。《蛆魇》是黎紫书的成名之作,小说以亡灵为视角,营造了一个封闭、阴暗、散发着腐烂气息的叙事空间。在这篇小说里,老一代华人即是历史罪恶本身,当“我”以“亡灵”的身份重返“家园”时,却意外地揭开了家族肮脏的秘史。爷爷是暴虐、情欲的化身,“我”始终无法忘却在暴雨的夜晚,他拎着把冷刀砍我房门的情形。“我家”始终处在阴雨的环境里,被四周茂密的丛林所包围,这似乎是一片被历史遗忘的角落,仅剩下“我们”一家在垂死挣扎。“我”在雨夜看到爷爷强迫“我”有智力缺陷的弟弟为其口交,那卑琐的面孔、腐朽的身体在弟弟看来则是不可抗拒的神圣力量。而母亲常沉浸在情欲中不能自拔,正是因为她偷情才导致“我”亲生父亲的自杀。黎紫书的这篇小说压抑到极致,“我”的每一个发现都是致命的,“家”早就不再是避风的港湾,而是各种梦魇的集合地,爷爷和母亲摧残着“我”与弟弟,他们以暴力和情欲的强力来毁灭一切。
艺术的风格来源于对历史记忆的处理,马华作家“钟情于”阴沉、压抑的小说氛围,正是始终萦绕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大马华人无言的历史记忆所决定的。时间并不会弥合原有的裂痕,当两代华人驻足回首的时候,照见的是更深广的沟壑。“人长大了情分渐渐不再,尤其是上一辈人陆续走了以后,现在就只剩下一个点头了。”⑥在黎紫书笔下,老一辈华人最终定格成一张泛黄的照片,他们有着“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历史沧桑,同时,他们也因所遭受的历史暴力、战争创伤而变得与当下社会格格不入,甚至于心理扭曲。无论是《告别的年代》还是《蛆魇》,老一代华人成为新一代华人成长道路上必须直面的“历史遗留物”,他们要么对生活、对子女沉默无声,要么成为暴戾、罪恶的化身。新一代的“主人公”必须要摆脱“老一辈”的“势力范围”,才能最终走上自己的道路。
二、地方经验:族群混杂与多元文化
“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⑦黎紫书小说中呈现出多元的文化状态,一是她将多元文化作为小说故事情节生发的背景,以多彩的幕布为小说人物的活动提供舞台空间。二是隐含在文本深处的多元文化思维,作者对人生世相的观察与思考并不是单一的向度。黎紫书对族群与文化的认知始终处于变动的状态,经历了由偏见到包容的过程。黎紫书的小说聚焦于大马华人的生存境遇,同时也建构了多元的文化空间,但不同的文化空间有着不同的功能作用。在其早期的篇章里,不同族群的人物共置于同一故事时空体中,但他们并非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华人之外的族群往往充当故事的点缀。黎紫书小说里常出现的印度人、马来人,他们不是能动的主体,而是华人生活中另类的风景。华人以外的其他族群人物,对于情节发展、主人公的命运交集并无重要关联。
《夜行》是黎紫书颇具意识流色彩的小说,“男人”置身在拥挤的火车里,在漫长的旅途中找寻故去的记忆,伴随着“男人”的目光,作者对火车车厢中的人进行了聚焦式的特写,在“男人”的眼中,“有一个印度妇女抱着大眼睛长睫毛的孩子凝望他的那一格车窗,看得他怪不自在的,那么大那么清澈的眼睛,他别过脸去望向远处静态的人影”⑧。印度女孩的凝视导致了“男人”坐立不安,拥挤的空间使人无法遁形,印度人的存在引起了“男人”负面的情绪。此刻,作为主体的“男人”将自我情绪投注到他所关注的对象上,其它族群只有借助“男人”的眼睛才有了“被呈现”的可能。在这篇小说里,“男人”对周遭的压抑环境异常敏感,他人的一举一动都能引发他内心的波动,在他眼中“对面的锡克男人双手交叠胸前,挺直腰背,巍峨地坐在座位上。他讨厌锡克男人的眼睛,是因为长须蒙面吗,那一双眼睛特别显得贼气又狡黠”,“不动声色的锡克男人闭上眼睛,仍然可以看到眼皮底下的骚动,果然是一双充满诡计的,果狸一般的眼睛”⑨。作者营造出“火车”空间,火车集合了各种各样的旅客,他们无法自由的活动,人与人在狭小的空间里不得不产生交集。借助“男人”的眼睛,作者勾勒出不同族群的人给主人公带来的印象,锡克人令他讨厌,那双“狡黠的眼睛”让他产生不适感。在这段描写背后,隐藏着作者某种无意识的种族认知,锡克人的形象穿过历史的迷阵,并没有任何变化,依旧穿着一成不变的服饰、满脸惨灰色的胡须。不同族群在狭小的空间里被压缩成标本似的符号,每个族人对应着一种刻板的印象,被挂在疾驰而去的列车内部。火车奔袭而去,车轮滚滚,不变的是种族之间的偏见、历史因袭的沟壑和难以弥合的裂痕。
黎紫书早期的小说,华族之外的族群只是华人生活中的陪衬,他们可有可无却又处处存在,少了他们故事依然完整,但在现实的生存空间中,他们不可或缺的构成华人生存环境的一部分。族群问题始终隐藏在黎紫书小说的文本缝隙之中,随着创作的成熟,她对族群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多元文化不只是马华作家可以炫耀的写作资源,而且内化成小说的骨血,它与华人的生命、生活息息相关。在黎紫书的长篇处女作《告别的年代》中,印度人、马来人的形象更具丰富的意蕴,他们不再是华人生活的陪衬。《告别的年代》分三个线索进行,主线是杜丽安的生活史,第二线索是“你”在“五月花号”旅馆中寻找母亲遗失的秘密,第三线索是作家“韶子”对自己小说创作历程的心路剖析。在第二条故事线索中,“你”自幼“父亲”缺席,与母亲相依为命,四处辗转流徙,寄居在旅馆,母亲去世之前向“你”透漏了父亲的消息,“你”开始拼命的寻找。“五月花号”旅馆像一座巨大的坟墓,这座年久失修,即将被遗忘的旅馆,令“你”既熟悉又陌生,试图找寻其中不可告人的秘密。在寻觅中“你”遇到神秘的印度女子“玛纳”,小说里玛纳以引导者的身份呈现在读者面前,她身材曼妙,面容姣好。玛纳悄无声息的隐居在五月花旅馆中,“你”逐渐感应着她神秘的气息,在玛纳的指引下,“你”渐渐走出虚幻的秘密空间,找寻出家族遗落的秘史。玛纳的印度人形象在《告别的年代》里扭转了大马华人对印度裔的刻板印象,反而成为女神般的“指引者”。小说中,玛纳不能说话,她的失语宣告了语言的无效性,“你”寻找的途径不是靠语言指引,而是内心的感应。黎紫书用很大的篇幅塑造了印度人玛纳的形象,先验的刻板的族群认知在这部小说中大为淡化,种族身份不再是人与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在小说里,对人性的探索才是恒久不变的命题。
黎紫书小说中呈现的多元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充满日常生活性的,文化的多样性嵌入个体生存的始终。《流俗地》是黎紫书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相较于《告别的年代》,《流俗地》有了较大的转向,足够令人惊艳。黎紫书小说的“变”与“不变”都能在《流俗地》中找到痕迹。黎紫书的变化之处在于,她的以往的某些小说,常给人一种叙事上的焦虑感,如何组织架构,如何讲述故事,这些形式上的探索成为其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难免会有“匠气”的痕迹。如果说《告别的年代》里,黎紫书还在苦心经营如何架构长篇小说的叙事框架,那么到了《流俗地》,叙事在技巧层面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流俗地》展开了一副大马华人的日常生活画卷,黎紫书熟稔的切割时空,在“时间”的腾转挪移中织成一张日常生活的“流俗”之网,共时性与历时性交织在一起,不同族群的人物五方杂处,盲女银霞、拉祖、细辉、蕙兰等人物的命运就这样铺展开来。叙事的方式、技巧在《流俗地》中完全不留任何“匠气”,一切都那么自然舒卷,臻于化境。
黎紫书小说的不变之处在于她对日常生活领域的关注,大马华人个体的日常生活在她笔下是故事的集散地,是想象与价值的边界。有关日常生活的美学,西方不少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来洞悉透视,从波德莱尔、齐美尔、本雅明,再到集大成者的列斐伏尔,集中阐释了社会学、美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齐美尔认为,对现代生活空间的把握“植根于其关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性的分析性见解中,即根植于对这些看似不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城市现代性的货币经济空间被决定、被体验、被表述的社会交往形式的重视”⑩。不同于张贵兴、黄锦树等马华作家,他们将沉重、宏大的国族叙事负载于文学之中,那是风风火火,爱欲蓬勃,杀伐决断的生命之歌。相较而言,黎紫书更钟情于细水长流、悲欣交集的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书写不太关乎现代主义或写实主义,而更关乎作家对日常生活的生命体验,以及如何艺术性的处理、呈现这一世界,日常生活就是“常”与“变”的交织。在黎紫书的关照下,不同族群同生共长,大马是他们的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每个人都彼此依存,而无任何文化与价值上的高低优劣之分。
黎紫书对日常生活的洞见体现在对人物命运、心理的把握上,《流俗地》以盲女银霞为故事的主线,一个双目失明的女性终日与黑暗为伴,如何找寻并赋予自我以价值,这是银霞所要直面的问题。日常生活于是就成了人物命运的演绎场,“盲女不盲”“眼盲心不盲”的文学心理学解读已成陈词滥调,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千篇一律,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关键在于如何将银霞置放于她所处的日常生活的背景当中,以铺就自我的救赎之路。小说中,银霞的生命经验就是在一次次遭遇与突围中不断成长,日常生活不再只是制造痛苦的根源,而有了更为丰富可信的内容。小说有一段写银霞去印度裔好友拉祖家,拉祖家供奉着“迦尼萨”神像,迦尼萨断了一根右牙,象征着为人类做的牺牲。拉祖的母亲对银霞说:
你看啊银霞,迦尼萨断一根象牙象征牺牲呢,所以那些人生下来便少了条腿啊胳膊啊,或有别的什么残缺的,必然也曾经在前世为别人牺牲过了。
这一番话让银霞大为震惊,如雷贯耳,又像头顶上忽然张开了一个卷着漩涡的黑洞,猛力把她摄了进去,将她带到一个前所未闻的,用另一种全新的秩序在运行的世界。[11]
黎紫书小说里总是充满这些平静而“惊心动魄”的时刻,这一细节极大地考验了作家的思想境界与艺术水准,银霞因为一句话所遭受的生命震颤,是日常生活中“存而不显”的真实情境,黎紫书却能敏锐的洞悉人心,将它做艺术的呈现。在这里,其他族裔的文化已不再如黎紫书早期作品那样,只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成为银霞自我救赎之路的指引。《流俗地》中,银霞不甘于枯老于家中,也数次有挣脱枷锁的机会,但现实迅速又给她痛击,就是在不断地感受“细微的喜悦”与“沉重的打击”之间,生活的丰富性与生命的韧性就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日常生活处处具有破碎的崇高感、仪式感,但也是藏污纳垢的黑暗之所,既可以拯救一个人,也可以使其坠入深渊。它不是密不透风的铁板一块,也不只是琐琐碎碎的柴米油盐。《流俗地》中的人物群像置身于多元的文化空间中,似乎找不到固定的主角,又好似没有一个是配角,他们都浸淫在日常生活之中,肩负着自己的命运,在真实中超越了真实,每个人都兼具世俗与超拔的两个向度。
从《告别的年代》到《流俗地》,黎紫书始终聚焦于多元文化背景中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经验,逐渐建构起属于作家自己的日常生活诗学。《流俗地》令人惊艳的不仅是黎紫书在叙事上的已臻化境的能力,她“任性”地截断时间众流,腾转挪移、引譬连类、穿插自如。更在于她对日常生活敏锐而富有洞见的把握,小说里许多现实生活中“存而不显”的细节,黎紫书都能精准的予以艺术的呈现,诸多神来之笔,令人惊叹。黎紫书小说中的厚度与深度,究其原因,不得不在历史的脉络中寻找。马来西亚作为长期的移民地,形成了族群混杂的格局并造就了独特的本土文化。种族之间的分离聚合,或融合或对抗的状态时有发生。无论是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在特定的大马空间内,都不可能不受他族的影响,因此多元文化的融合、共存亦成为大马文化的特色。与个体在地经验最密切相关的是族群经验,族群关系的演变始终影响着大马华人的身份认同,亦成为马华文学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
三、蕉风椰雨中的南洋景观
“南洋”是黎紫书小说主要的故事发生地,在她的小说里,南洋是一块神秘之地,象征着财富的橡胶林、幽深的热带雨林、蕉风椰雨的景观共同构筑了“南洋想象”。大马对黎紫书而言就是她魂牵梦系的乡土,是她出生、成长的地方,是记忆的物理容器。她的小说反映了深刻的人、地关系,“人”与“地”不仅仅是主客之间的关系,作为地方经验的“乡土”渗入了主体的情感想象。其中,自然景观与社会景观在乡土中对个体带来深刻的影响,它们共同构成了黎紫书小说鲜明的地域文化标识。“南洋”作为地方,当它以文本的形式面向读者的时候,先验的阅读期待会形构一个理想的“南洋空间”。但在黎紫书的小说中,与其说是“建构”南洋,不如说“敞开”南洋,在他笔下,南洋是公共性的,又是独一无二的,主要表征在黎紫书的雨林书写与日常景观的细致描摹中。
黎紫书并不以雨林书写著称,相较于黄锦树钟爱雨林中个体命运的书写,黎紫书更侧重书写小镇、城市的众生相,但在她经典的短篇小说中,对雨林的书写亦充满隐喻和象征,成为人物生存活动的重要场所。“相信天使、魔鬼与灵魂,是人类固有的一种心理。古往今来,不论哪里的人都会有一种超自然的感知,不论它有多么微弱、多么少见。”[12]面对广袤的热带雨林,超自然的力量更接近于神力,在它面前,个体察觉到自己的渺小而对自然产生敬畏。黎紫书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大马本土是她的故乡,大马独特的热带环境影响着她的艺术感受。大马的热带环境、丰沛的降水资源哺育了广袤的热带雨林。在黎紫书笔下,雨林不仅仅是自然景观,更是生命之所、神秘之地、母性之源,一切的生命都诞生自雨林,一棵棵茂密蓬勃的树木,破土而出的蕨类植物都洋溢着生命的张力。马华作家习惯将雨林比作母亲,雨林自成一套生态系统,降雨、吸收、生长、循环、分解,生命的诞生、成长、死亡、消失不必外显,一切都隐匿在雨林中。黄锦树、李永平擅写雨林,正如乡土作家将土地视作母亲,马华作家将“探索雨林”作为重返母亲怀抱的途径。张贵兴深情地说:“进入雨林,仿佛婴儿回到母亲子宫,殷殷吮吸,不再苦恼。”[13]个体在苍茫的雨林中显得无限渺小与微茫。此外,马共是大马华人心照不宣的历史创伤,雨林的隐秘性为各种政治活动提供了避难所,马共长期以来遁入丛林,在丛林中指挥武装斗争。然而隐匿并不意味着消失,世人有关马共的想象从未断绝,一支队伍遁入雨林后如何生活?如何组织?又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这些疑问对作家而言充满诱惑,他们深入雨林,意欲探求历史遗留的蛛丝马迹,雨林中不仅残存着动物、植物的尸体,还掩埋着人的尸骨,他们被潮湿丛林的微生物迅速的分解、吞噬,被枯枝残叶所遮盖,对雨林的探险更像是对历史的开掘。
《州府纪略》是黎紫书在形式上别具一格的小说,这篇小说叙述主人公谭燕梅的人生际遇,作者并没有按照平铺直叙的方式来写,而是借助主人公身边同代人的“口述”,来勾勒出谭燕梅的人生遭际,形式上与罗生门的样式相仿。不同人物的口述相互补充,视角、动机各不相同,却引人入胜,补全了谭燕梅完整的一生。谭燕梅与金兰姊妹黄彩莲之间从熟识到产生间隙,其间穿插着不同的历史事件,马共的地下活动、残暴的日军侵略,赋予了小说以深厚的历史感。作为戏子的谭燕梅在父母双亡后嫁给了恩人之子——疾病缠身的文弱书生,她最终成为风华绝代的名角,受人爱慕。在表面的风光背后,谭燕梅长期与马共保持联系,成为马共地下党的一员,在日本入侵马来西亚后与金兰姊妹黄彩莲一起隐遁丛林。小说的精彩部分正是借助众人之口试图还原谭燕梅、黄彩莲马共身份下的雨林生活,长期以来的马共想象在黎紫书笔下有了具体可感的细节。
《州府纪略》中,雨林成为爱欲、暴力角逐的场所,黎紫书有意将雨林生活世俗化、情欲化,隐秘的生存空间造就了压抑性的心理。黄彩莲的丈夫——马共党员刘远闻周旋于黄彩莲与谭燕梅之间,在一个雨天强暴谭燕梅,面对两个女人之间的矛盾,他想要逃避却再无从逃避,雨林是他能够躲避的最后避难所。面对日军的疯狂袭击,雨林充斥着暴力与鲜血,最后黄彩莲为了拯救丈夫中弹身亡,而新生的婴儿则被谭燕梅领养。原本以为丛林是安全的场地,它能隔绝外界暴力的侵害,谭燕梅最终才明白,革命似乎只是幻想,血污的权力争夺才是革命背后残忍的真相,而雨林并不保护任何人,它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它能吸收雨水,同样能吸收鲜血,它能分解植物,同样能分解尸体,它无法铭记什么,也无力保护什么。谭燕梅带着黄彩林的孩子走出雨林,重新回到小镇上,回到痨病丈夫的身边,把姊妹的孩子抚养成人。小说在最后有高深的一笔,谭燕梅的养子赵苏吓自述,母亲在去世之前曾带领自己去雨林边观看马共投降仪式,她深情的望着丛林,望着逝去的青春记忆。母亲谭燕梅去世时,“我”自述道:“阿妈的死我才真伤心,那个共产党阿爸阿妈,就和隐入深山的共产党一样,还没有在我的生命里出现过,就烟消云散了。”[14]雨林吸收了一切历史惊心动魄的事件,最后归于沉寂,仿佛不曾发生,逝去的人,逝去的青春都融进每一颗参天的树里,变成枝叶,随风招摇。雨林在黎紫书笔下是人性的角逐场,历史幽暗的一面在这里展开,在这里消亡。
不独雨林,南洋的植物在黎紫书的小说中有着独特的意味,它彰显着南洋风情,又融入到故事情节当中去,成为人物命运变换的布景。蕨类植物、旺盛的草丛、高大的木瓜树、菠萝蜜树成为小说中常见的自然景观,它们是作者精心营造的空间场景,鲜明的昭示出人物的生存境遇。在《蛆魇》一文中,黎紫书反复渲染“我”生存环境的阴暗、潮湿,处处散发着腐朽的气息。小说一开场,呈现了阴暗的月夜下“我”坠湖的场景,这是一个茂密丛林中的湖,四周长满了杂草,蛙声四起。即将溺亡的“我”一把抓住岸上的马齿苋,它牵引不住“我”的重量,被连根拔起。黎紫书善于从微小的事物中营构艺术感,小说中“我”在生死存亡之间,“右手把初生的草茎连根拔起,带起一把褐黄的泥沙,以及扑鼻的草根与泥香”[15]。植物在此作为生命的隐喻,它等同于“我”的处境,柔嫩的马齿苋无法作为拯救我的工具,它被我连根拔起,而我最终也要坠入湖底,肉身消亡。在“我”的灵魂浮出水面之后,我一路惊恐狂奔着朝向回家的路,穿过丛林、踏着草丛,我如惊慌失措的鸟,每一片草丛在我眼中都潜伏着危机。植物在《蛆魇》中不再象征着欣欣向荣的生命,它包围着我的家,在无休止的漫长雨季中散发着腐朽之气。草丛、树木被营造出鬼魅的气息,白蚁蛰伏在丛林中,阳光不来,雨季不去,从草地间散发着致命的瘴气。“我”的家建造在荒野之上,自然的气息充盈着荒芜之感,安静的夜晚,雨水打在院落的芭蕉叶上,一滴滴敲打着叶片,汇聚之后又顺着叶子滑落下来,如此静谧,如此荒凉。黎紫书将植物当做生命的一种独特样式,他们与人一样,以土地为母,吸收养分,毫无节制的蔓延,悄无声息的“繁衍”、生长、死亡,最后枯萎零落,被分解后又复归土地,了无痕迹,植物的生灭应和着人的生灭。
除了雨林书写标识出“南洋”的特色外,更重要的是,黎紫书聚焦于对日常人文景观的描摹,她为每一个故事的演绎都搭建了规模庞大、布局合理、道具精致的舞台。如孤绝的华校、衰颓的小巷、古旧的牌楼,甚至于长满铜锈的门环、歪斜着贴在门上的春联,都建构着独具一格的“南洋”风景。黎紫书的小说基本都以大马华人为主角,有很多篇章描写华人少女、青年的隐秘心事,他们都生活在封闭的空间里,沉浸在自己的天地中。《某个四月天的下午》《流年》中的主人公都是处在青春期的少女,她们往返于华校与家庭之间,校园里的生活总是充满压抑的氛围,高高的围墙、枯燥的作文课、令人讨厌的同学,在漫长的夏日里躁动的情绪充斥在少女心头。华校在黎紫书的小说中是类似孤岛的存在,外界的社会环境对华校内部产生消极的影响,少女敏感的内心捕捉着孤独与怅惘。这样的隐喻是有现实依据的,在马来西亚,华校被官方教育体制所边缘化,颇有自生自灭的难堪境地。华校本身作为人文景观即是华人教育的骄傲,又显现出孤绝的抵抗姿态。
1) 从泵进口到出口,压力逐渐增大;随着泵进口压力降低,流道内低压区范围增大,高压区范围减少以至消失。
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人文景观,一种文化必定能以具体的形式呈现出来,能够形成可视性的景观为人观看、捕捉。南洋风情不仅体现在对雨林和植物的描写上,还体现在小说中对人文景观的呈现。建筑、宗教、街景、广场都成为日常空间的一部分,在文学作品中成为一种文化的标识。“大多数城市,甚至是所有的城市,都会用一些公共建筑来提现对‘超凡’的信仰。”[16]人文景观的可视性某种程度上起到凝聚族群的作用,标志性的建筑往往成为区域之内群体的共同精神符号。我们强调“地标性建筑”只是由于它能够被大多数人所观看,所熟知,他在区域群体内召唤出共同的文化想象。这种景观小到街景,大到国家标志,一提到天安门,令人瞬间联想到的并非实体性的天安门广场建筑,而是这一建筑空间隐喻的“首都”“中国”等符号化了的概念,它无形中唤醒群体的民族感,并形成文化上的凝聚力。此外,人文景观是文化存续的一种手段,它“矗立”在个体朝夕生存的环境之中,成为一种亲密的符号,成为历史、想象之物,不断被书写、被解读。
日常生活在黎紫书笔下具有丰富的意味,她把细致的笔触伸向生活中的具体场景,她在小说中对街道、房屋、商场进行仿真似的描写,以此凸显人物日常生活的琐屑感、真实感。“把城市一点点拆开,再将碎片调换、移动、倒置,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组合。”[17]黎紫书小说里的城市经过历史的冲刷,以沧桑的面孔示人,它们像是一块化石,或者说它们就是历史本身,她笔下的人物穿行其间,注视着斑驳的墙壁,仿佛走进了时光的幽暗隧道里,过去、现在、未来相互交叠在一起,每一寸砖墙、每一处风景,细细看来,都是不堪的回忆。在黎紫书的小说代表作《野菩萨》中,她构筑了“月份牌巷”“七月街”的道路空间。街道正如一个城市蠕动的肠道,凭借它城市才能保持畅通,城市的生活空间才得以保障,街道的风景最鲜活的呈现出市镇生活的日常样貌。“城市借助于街道,既展开了它的理性逻辑,也展开了它的神秘想象。”[18]小说里,月份牌巷是一条狭长的小巷子,它显然不同于繁华的大街道,它更像是历史的遗迹。主角阿蛮只有穿过狭长的巷子才能由压抑变得舒适,她感叹道:
那巷子几乎像一条神秘的,逆行的时光单行道,又像历史这堵老墙上深深的裂缝,会把人的三魂七魄吸进去。巷子里两排双层屋都已成古迹,墙像长癣似的,青苔斑斑,绿的发黑;墙体的裂缝崩出长羊齿叶的蕨类植物,感觉像骷髅头上长毛发。铁门上锈迹斑驳,门牌脱落,咿呀咿呀。门楣上或有蜘蛛一代一代织下的天罗地网,或有年代不详的,旧时燕子的弃巢。[19]
这条覆盖着历史尘埃的巷子处处彰显着岁月的痕迹,巷子两边分布着老旧的民居,一阵风吹过,铁门上贴着的春联被吹落,在空中飘荡。小说中的小巷空间成为历史符号,它充满丰富的隐喻,那是华人散居的场所,在历史的侵蚀下,如今尽显老态,只有门前风中摇动的春联才可窥见居住者华人的身份。狭小的空间通道、暮气沉沉的小巷令阿蛮感到压抑,只有穿行到更开阔的空间中去,才稍稍感到舒适,这条小巷似乎暗示着华人在大马的生存境遇——狭窄、压抑、逼仄。
当我们再读到作者对“七月街”的描写时,又是另外一种风景,七月街是商业街道,两边布满大大小小的店铺。不同于都市商业中心,七月街仅仅是老旧破败的市镇街道,它对于阿蛮的魅力在于儿时的记忆,七月街是他们小时候瞒着大人能够去到的极限之地了。穿过七月街,过了一座桥,可以抵达人民公园,小小的街道却是阿蛮儿时惊心动魄的旅程。无论是月份牌巷还是七月街,在黎紫书笔下都是历史本身,建筑空间承载着芸芸众生生活中的哀乐,是铭刻着华人生存的地标。黎紫书敏锐的从老旧的街道中读取了历史的况味,历经岁月的淘洗,街道并没有得到更新,它们像自然生长的人一样,从当年辉煌的时代不可避免地步入衰老。“有一种建筑一直被认为能激起鲜活的历史感,那就是废墟。”[20]老城、老街的人文景观本身就极具故事性,它们激起人们内心的废墟感。老旧的建筑被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所边缘化,但它们还保留着的社会记忆功能。被遗忘的“废墟”只能越来越古旧,在旧人看来那是昔日荣耀和记忆的情感空间,在新人看来那些老旧、凌乱的街景无时无刻不再彰显着衰落与颓败,是历史苍凉的言说。
四、结语
黎紫书用她的一系列作品,建构了极具艺术想象力的“南洋”空间,她所有的文学书写,都立足于对本土风景与在地经验的不懈探索。“地方”之所以重要,在于“‘地方’并不是从一个更大的地理空间里“分划”出来的区域,而是以认识者(或感知者)为中心,去看待、感知、认识世界而形成的一个‘地方性空间’”。“南洋”作为地方,正是黎紫书情感附着的焦点,是一处充满价值与意义的所在,更是她洞察人性、观察人生的坐标。此外,大马多族群五方杂处的现实环境为黎紫书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她以敏锐的艺术直觉将这些独特的文学经验转化成艺术实践。当然,黎紫书念兹在兹的并非只是建构“南洋”,而是指向人性、爱欲、记忆、身份等生命的终极命题。黎紫书的小说即温柔又暴烈,她常把自我情感隐匿于文本的细微之处,她将芸芸众生的爱与死,尤其是蜷缩在城市阴暗角落的个体的命运演绎成一段传奇。在黎紫书看来,“呈现”比“批判”更重要,在日常生活的褶皱里,潜藏着熠熠生辉的诗意。于是,黎紫书试图呈现在历史跌宕中的大马华人的生存境遇,他们因袭着历史的包袱,承受着历史暴力遗留的心理创伤,在俗世的舞台上往返穿梭。黎紫书也为读者呈现出历史夹缝中人性的幽微难明,那阴暗潮湿、梦境迷幻、百虫狂舞、万物腐朽的夜晚,潜藏着“丰腴”的故事。黎紫书以本土风景与在地经验作为自身文学写作的源动力,凭一己之洞见,在马华文学中建构起了独具风格的个人标识。
①金进:《马华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页。
②③[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页,第7页。
⑤[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页。
⑥[19][马来西亚]黎紫书:《野菩萨》,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第156页。
⑦[美]保罗·唐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⑧⑨[马来西亚]黎紫书:《出走的乐园》,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第119页。
⑩[英]安杰伊·齐埃利涅茨:《空间和社会理论》,邢冬梅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6页。
[11][马来西亚]黎紫书:《流俗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75页。
[12][美]段义孚:《无边的恐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
[13][马来西亚]张贵兴:《猴杯》,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3页。
[14][15][马来西亚]黎紫书:《出走的乐园》,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第59页。
[16][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74页。
[17][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18]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页。
[20][英]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历史及其图像:艺术及对往昔的阐释》,孔令伟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6页。
[21]鲁西奇:《空间的历史与历史的空间》,《澳门理工学报》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