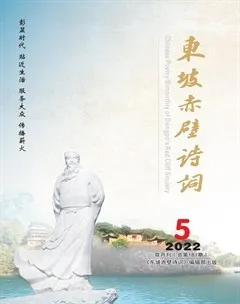论新田园诗词创作的价值取向(一)
王琼
诗,作为文学作品的样式之一,自古迄今,在人们阅读的视野里,一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特有的审美特征。而田园诗,作为其中一枝奇葩,更不例外。若作为一个流派的形成,当溯源于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归隐后所产生的大量作品,进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得以诞生。从此,人们便将描写乡村风貌、田园生活等系列题材的诗词作品,冠以“田园诗”之名,正式纳入了中国文学的审美视野。其代表人物,且为世所公认的,晋有陶渊明,唐有王维、孟浩然。至宋诗人渐多,如范成大、杨万里等等。他们的笔下,同样产生了不少描写宋代农村田园生活场景的优秀作品。自宋以降,田园诗词似未再现高潮。
那么,身处21世纪的今天,我们如何创作出更多的新田园诗词佳作呢?笔者以为,创作田园诗词的价值取向,这个重要因素,是无法避开的。这个价值取向,对于一位新田园诗词创作者来说,那就是在其创作过程中,一定要用艺术形象的语言,表达自己创作意图;用独特的视角,描写农村、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环境的变化;用自己的真实情感,观照他们的喜怒哀乐。从而,为“三农”发声,为人民代言。笔者欲从三方面试述之。
一、“新”字新解
说到新田园诗词,一直以来,心中总存一“结”。为何要在田园诗词前加一“新”字呢?笔者以为,当代人说当代的事,当代人写当代的诗,而对于前世人来说,我们是后来人。所以,写出来的诗词,当然是与他们不同时代的内容,可以说是新的;而对后世人来说,我们也将被称为前人。那么,再说我们的田园诗词,是新田园诗词,似乎令人费解,有点站不住脚了。况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新旧更替,是一个永无休止的铁定规律。所以,之前,我很少提到“新田园诗”这个概念。
对于这个问题,在我担任《东坡赤壁诗词》执编后,方才逐步得以理解。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大地掀起了滚滚诗潮。黄冈东坡赤壁诗社,应时而生。《东坡赤壁诗词》杂志也创刊于此。20世纪末,东坡赤壁诗社在全国率先开辟了21世纪新田园诗词创作之风。在《东坡赤壁诗词》杂志里,开创了《田园诗赛》和新田园诗《诗人看台》两个栏目。并且,对新田园诗词赋予了新的意义,即定位于“三农”:新时代的农村、农业和农民。于是我想,之所以要加上一个新字,是因为第一要点,必须是面向农村广阔的田野,观照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以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容,据此来定位新田园诗词。
当我们理解了田园诗词被冠以“新”的意义后,回过头来看,就会明白我们在学习前人的优秀作品时,不但要学习其艺术表现方法,重视诗词的文本质量,而且还必须了解其创作背景和意义所在。如陶渊明《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翁捕捉了农村极为普通的场景,用白描手法,简笔勾勒,虚实相间,声色相调,浓淡相宜,描出一幅朴拙而自然、宁静又不失生机的乡村美景图。陶渊明的田园诗,皆以其真实的生活为背景,真切写出了躬耕的苦乐。他本为入仕的士人,因官场不达,而又看不惯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故而归隐。他将自己的思想情感与他眼中的田园景物,始终巧妙融为一体。其诗风清雅,语言淳朴、自然,从而使其田园诗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作为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不妨再看看唐代的王维和孟浩然。因其皆处同一时代山水田园诗人,故后人并称“王孟”。
较之陶渊明的主动归隐,王维早年同样有过积极的政治抱负,后因安禄山攻陷长安,被迫受以伪职,长安收复后,因平乱有功的弟弟王缙,请求削官为王维赎罪,这才保住了官职,开始了半官半隐的生涯。而孟浩然呢?早年虽有志用世,然入仕无望后,不媚世俗,以隐士而终身。
清大学者纪昀称:“王、孟诗大段相近,而体格又自微别。王清而远,孟清而切”(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道出王、孟二人的田园诗,虽同样受陶影响,但却各有特性。由此,对于我们今人而言,要想了解他们的山水田园诗,则须在学习这些作品时,不仅只是看到表面的文字,还要对他们的创作背景,加以分析和理解。
回溯历史,众所周知,先贤们因其各种原因,寄身山水田园,亦寄情其间,通过自己的作品,寄寓人生感慨和人格理想。我想,这或许就是他们田园诗的重要意义所在吧。然而,从文学艺术发展史角度看,他们树起了山水田园诗的丰碑。所以,他们的作品,仍是后人学习的重要范本。
那么,我们当代诗人在自己的创作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确定自己的创作意图呢?这就必然涉及作者创作“这个作品”的目的了。新田园诗词创作尤其如此。通过前面对新田园诗词的探讨,大家应该知道,在创作新田园诗词的时候,除了要学习和借鉴先贤们传统的艺术创作手法外,更重要的是,要创作出具有新气息、新面目的田园诗词佳作。这才富“新”的意义。
二、价值内涵
2022年6月10日,周文彰同志在中华诗词学术论坛上的讲话《端正诗词价值观》中提到:“所谓诗词价值观,就是关于诗词有没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对诗词的价值判断,人们通常从两个维度来进行:一是看诗词本身的品质,一是看诗词对社会生活的意义。”对此,笔者欲从田园诗词的价值入手,对田园诗词的品质,也谈点看法。
周文彰会长在讲话中还谈到:“判断诗词的品质,就是看诗词好不好。这是关于诗词文本价值的判断。”那么,这个判断的依据,是因何而定呢?我想,除了该作品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外,至少还有一个条件,是无以可避的。即评判者的诗学素养。《周易·系辞上》:“仁者见之谓之仁,知(智)者见之谓之知(智)。”这句话用在这里,借其含义,言评论一首诗词的高下,其实也是见仁见智吧。现今是自媒体时代,有个手机号,便可在许多网站注册公众号。于是,山头林立,各种信息满天飞,可见人心之浮躁。真正能静得下来读书,沉得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在这样的环境下,想追求诗词作品的高品质,虽有难度,然而,作为一名自觉诗人,我想大致还是会把握一个尺度,不会为了哗众取宠而自降诗品,去玩文字游戏,以博取人情赞赏的吧。
众皆知之,于今,随意打开手机微信,即可看到许多“著名诗人”“诗词名家”的链接,诗词大赛的消息,也随处可见。获奖作品大致平仄合规就行,缺少声韵美,缺少形象艺术美,一些概念性语言拼凑起来的“诗词”,居然可获某某诗词大赛一等奖,据说拿钱便可以买到获奖证书。有的大奖赛,实为不良网商谋利的工具,赛事通过网络拉票赚取流量、购买虚拟礼品的多少来评选奖项,获奖者比比皆是。更有甚者,此间还有不少人,竟大言不惭说自己是在“玩诗”。时空果真能穿越的话,相信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们,如能穿越到今天,定然也会被气死过去。诗词不是文字游戏,作为一名诗者,应时时提醒自己,不必沉醉眼前浮名,应追求诗词品质的提升,以臻诗词艺术美的完善。对于自己创作的每首诗词,都应力求有其存在的价值。要倾注自己的真情实感,用诗词歌颂真善美;对人物或事物的褒贬,要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对于农村田园,力求形象客观地描绘。此外,新田园诗词依旧还要语言清新,气脉连贯,逻辑思维清晰。不能让读者读完了,只感觉一堆词语的堆砌,甚至为了所谓的“创新”而生造词语,却失去诗词艺术美的本真。
笔者认为,对于诗词艺术美的追求,应是诗词创作者的共同目标,没有时空间隔,没有地域界限。田园诗词,亦自当如是。
试问,今天读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谁不会由衷地心生向往?读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时,谁不会心生喜爱呢?我想,大凡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基本都会背诵了吧。我们再读到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时,又有谁不是情不自禁被带入诗中的画境里呢?这些优美诗句,每读每新,这就是好诗的价值所在,相信再过千年,这些好诗句,依然还会在世间传诵。
在田园诗词的发展史上,北宋大文豪苏轼,绝对是一位无法绕开的高地。苏轼任徐州太守的那年春天,徐州发生了严重旱灾,身为地方官的苏轼,曾率众到城东二十里的石潭求雨,得雨后,作《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场景纷呈,别开生面。其一,从黄童白叟喜悦聚观谢雨盛会,看到“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情景,发出“归家说与采桑姑”的想象。其二,更是形象生动描写出村姑们听说使君谢雨,要路过门前,便赶紧梳妆,三五成群,挤在棘篱门首,往远探望。你推我挤时,居然还有人尖叫:是谁踏破了我的裙子?场景鲜活,让人读来不觉莞尔,恍若这一切就发生眼前。读苏轼这组《浣溪沙》,从中可见,北宋时的女子,是不能随便走出门户的。五首词依次读来,就是五幅鲜活的农村生活场景,若是细细展开,俨然就是一部电视连续剧。他用形象生动的笔触,描写农村风光,反映农民的情绪,为农民的喜悦而感到欣慰。同时,从“问言豆叶几时黄”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苏轼对农民生活的真切关怀。其爱民之意,跃然纸上。这组词,文风朴实,格调清新。既无艳词,亦无僻典,语言清丽自然,可谓真正的清词范例。苏轼通过这五首词,将农村题材,带入北宋词坛,给词坛注入了朴素清新的乡土气息,为农村田园词的发展,开创了良好的文风,可与其豪放词并举,共同弥补北宋词题材狭窄之弊,且完全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
尔后,再看南宋辛弃疾。辛词继承了苏轼豪放词风,进一步开拓了词的境界,扩大了词的题材。是以,后人将其与豪放派词宗苏轼,合称“苏辛”。他还善于吸收民间口语入词。他描写农村景物和反映农家生活的词,多是清丽而明快,极富生活气息。如《清平乐·村居》: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该词选取了农村一户五口之家的一个生活画面,用一首小令,以白描的手法,朴实的口语,将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形态,都刻画得惟妙惟肖,极具生活情趣。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尚如《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时越近千年,今天会有人不能读懂这两阕辛词么?在我们今天的田园里,是不是同样可以看到“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景象呢?这是一个肯定的答案。甚至现今仍有许多人,在写田园诗词时,还在不知不觉借用这个意象。所以说,好的田园诗词,是能走进人们心灵深处的,是能在人的心里产生共鸣的,而且是没有今古之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