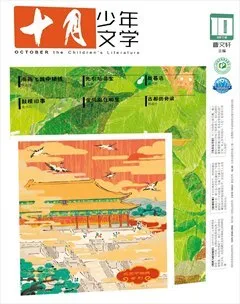古都的脊梁


一、象天法地
当他望着琼华岛上刚刚筑成的广寒殿,是否曾在脑中构想,古往今来世界上占据最大疆域的王朝之都将在此建立,一条气势恢宏的中轴线将奏响由高低错落的屋檐组成的最庄严、华美的文明乐章……
或许野心勃勃的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派遣他来此相地时,也无法料想一座伟大的都城将在他的手中诞生;或许回族建筑学家亦黑迭尔丁在与他合作时,都捉摸不透他施展着怎样的才华使祖先几千年的智慧被那样巧妙地诠释。
他,就是元大都的总规划师刘秉忠。
话说忽必烈登基后,为增强对中原的控制,将都城由元上都南迁至燕京地区的金中都古城。但这座城市的供水来源莲花河水系已经水量不足,不适合再作为都城。于是在1267年,忽必烈开始推动新都城的选址、规划与新宫殿的设计、营建工作。就这样,身为中书省官员的刘秉忠成为了总规划师,亦黑迭尔丁成为总建筑师。
游牧民族刻在基因里的天性自由,如何与积淀数千年的礼乐教化相融。刘秉忠费尽心思,从古籍中寻找灵感,给出了一个极为精巧的构思布局。
蒙古人有“逐水草而居”的习惯,因此刘秉忠在选址考虑上,将大宁宫所在的琼华岛周围的天然湖泊尽可能地揽入城内。琼华岛位于太液池南部,对应到今天为北海的白塔山所在位置,这里是漕运的终点,是将要建成的新都城的大动脉。因此,刘秉忠将琼华岛确定为新都城的中心,元大都也成为中国历史上首座中心出现大面积水域的城市。
元朝泱泱大国,一片水光潋滟的秀美风景不能符合都城应当体现出的皇权威严。因此,刘秉忠想到诉诸《周礼·考工记》中的都城营建思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是历代都城的建设“指南”,但据说,历代都城中只有元大都最符合《周礼》的思想。就这样,华北平原上出现了一座规划整齐、方正纵横的城市,成为了一个“完整的、有计划的整体”。
“九经九纬”,是说城市里有横向、纵向各九条道路分列。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线当数中轴线——也是这篇文章的“主角”。刘秉忠是如何画下的这条最重要的线呢?他经过缜密的思考,将海子最东边湖岸(对应如今鼓楼南后门桥所在位置)作为中轴线基点,并以接近子午线的方向作为大都城中轴线延伸方向,北京中轴线就此形成。
刘秉忠意识到,这条中轴线太重要了,它可是世界上疆域最大的王朝之都的中轴线。因此,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被永远记入了中国古代城市营建的史册。
他做了一件令人不解的事情:派人实际测量出了全城的几何中心点。难道修建那么多宫殿、道路还不够兴师动众,竟又要耗费人力物力去测量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点?但他就是要测量出这个点,并在上面竖起一座高高的台子,在上面刻下无关痛痒的“中心之台”四个大字。
可这四个字,其实包含了太多意义,使这座中心台远比它本身更加崇高。
在那时,元朝的疆域是以燕山为南北分界,因此元大都所在的位置居于中心。从地理位置来说,元大都还是华北平原、蒙古高原和东北松辽平原的交会之处,是太行山东部华北平原与西部黄土高原的交会之处,这多个自然条件的中心,叠加成自古以来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牧业经济文化区和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的交会之处,南北东西民族文化的碰撞、融会之处。元朝还是世界上商贸最繁华的国家,无数船舶通过太液池进入元大都,让这里成为了世界的商业中心……
无论从各个维度,它都称得上是中心中的中心。
然而,刘秉忠还是留下了一个谜题,这条中轴线其实并不是指向正北,而是偏移了微妙的两度。这样的偏转不仅难以被人察觉,动摇其作为中轴线的权威性与庄严性,同时还有着更为重要的指向意义。他等待着后人发现这个秘密,发现这条中轴线的真正源头……
二、江山社稷
“禀告皇上,前日在库中寻得一卷图册,附有注释,记录了刘秉忠当时设计中轴线的想法。”
“善哉!讲来听听。”
明太祖朱棣面对着铺开的泛黄图纸,听着大臣的讲述,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感慨于在一片空白上建立如此的秩序,需要怎样的胆识与魄力。
“……今天,您看到的中心阁和中心台,就是元大都中轴线的北端,而南端则是丽正门,全长大约七里有余,蔚为壮观。”
的确,刘秉忠画下的这条长长的轴线,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当所有人都对中轴线赞不绝口时,朱棣却思索着中轴线该向何处延伸。元大都中轴线的长度突破了当时的纪录,但它绝不应止步于此,因为这条线诞生于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国度,诞生于一片有着最悠久历史的土地。
他在想,这中轴线就像一棵树干,扎根于千年文化积淀的土壤中,而他一定要让这棵树枝繁叶茂。
朱棣在位的二十二年里,便推动了两次中轴线的延长。这不仅仅是一条作为概念而存在的线的延长,更是整座都城的一次次扩张与蜕变。
向北!元大都时,钟鼓楼并不在中轴线上,且距离过远。因此,朱棣下令重建新的钟鼓楼。鼓楼建在原本中心阁所在之处,而在其北侧一百九十米处又兴建钟楼,中轴线得以向北延长。不仅如此,中轴线上的内容也因此更加丰富起来。原本那个刻着“中心之台”的大石柱,变成了钟声阵阵、鼓声隆隆的声音之源,仿佛一座都城的脉搏。
向南!明永乐十七年,朱棣为抵御伺机南侵的蒙军,下令放弃北部的荒凉地带,全力开拓南城,将北京南城墙向南迁移近两里。中轴线由此延长近四点八公里。一座都城在战争的阵痛中,挣脱原本框架,化蛹成蝶。
难道中轴线只能在一维的空间上拓展?
朱棣却不这样认为,早在迁都以前,他就已经开始谋划在中轴线添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据说,那时他就决定在中轴线上营建新的宫殿。他十分重视这座宫殿,在破土动工以前,仅派遣众人到各地广泛搜寻珍贵的石材木材,就耗费了十一年之久。
在他的指挥之下,一座最庞大的宫殿群就此成为中轴线上具有统治力与震慑力的政治中心。因为都城边界的屡次迁移,中心之台早已失去了作为都城几何中心的意义。这名为紫禁城的宫殿群,取而代之成为了中轴线上无可争议的绝对核心。紫禁城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几何中心,它不像中心之台——大地上稍不留神就会错过的一个点,从空中俯瞰,紫禁城如同红墙黄瓦组成的巨浪,涌向每一个人的内心。明清两代的皇帝在此指点江山,一道道政令如不可违抗的天命从这里发出……
如果仅仅是二维平面上的拓展,那未免也太小瞧了这位明成祖朱棣的想象力与野心。中轴线,也可以向上生长,不是层叠的砖石、错落的屋檐,而是将大地掀起一阵波峰!
如今,无数的旅者、市民,在黄昏时分簇拥着景山之巅,举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器材记录下紫禁城默然矗立的每一寸光阴。而景山在朱棣迁都前尚不存在,那里原本是元故宫的遗存。
在那象天法地的时代,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这“天之四灵”在每一片大地上见证着历代都城的诞生。根据风水,紫禁城的北面是“玄武”之位,应当有山。朱棣毫不犹豫下令将元故宫拆除,挖掘太液池、南海和紫禁城中筒子河的泥土,将其堆砌成万岁山,这座山也成为了中轴线上的制高点。
朱棣所做的一切,只是开始。明朝人根据《周礼》,在都城的四周建设了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如众星拱月,环绕着辽阔江山的核心,强调着“居中为尊”的皇权象征。中轴线也一次次延长,最终形成了从永定门至钟楼,全长七点八公里的北京中轴线。
三、家族传承
在样式房里,雷发达监督着几位工匠制作太和殿烫样的屋顶。工匠们按照繁复的工艺流程,先是在黄泥胎模上粘贴一层高丽纸,然后把用于增加强度的两层麻呈文纸和涂上水胶的两层东昌纸依次贴在表面。几个小时过去,工匠们不觉已汗如雨下。就在这时,雷发达看到屋顶做的有一丝偏斜,应当是坯模出现了问题。
于是,他下令从坯模开始重新制作。工匠们感到不满,捧着屋顶烫样反复地查看,都觉得不至于重新制作。毕竟,那么大一个建筑群的烫样,谁会注意到这么精细的一点儿偏差呢?雷发达见状,就让工匠们放下手中的工具和材料,为他们讲述了朱棣兴建紫禁城的故事。
“……就这样,朱棣画下了中轴线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大家一定要牢记,紫禁城的诞生离不开这条中轴线,而它本身就是依照着最严谨的对称布局展开的。可能有人觉得那一点儿偏斜并不严重,但请想一想,现在将要建立的三座大殿,都坐落在中轴线上,更何况咱们正在制作的太和殿,更是紫禁城最重要的一座建筑。这点儿偏斜真的不严重吗?”
工匠们这时候终于明白了雷发达为什么这么重视太和殿的烫样,为什么严苛到容不下丝毫的偏差与疏漏。因为这是一条已经绵延数百年的中轴线,不能在他们手里被“碰歪”。
样式房是清代宫廷建筑的设计单位,类似于今天的建筑事务所。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建筑设计,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制作“画样”和“烫样”——画样就是建筑设计图纸,烫样则是要给皇帝过目的建筑模型。这个太和殿的烫样,只是样式房里不计其数无比精准而精致的建筑烫样中的一个。
雷发达对于中轴线的坚守,也是雷氏家族数百年传承的序章。
1683年,为翻修重建紫禁城,工部营造所在全国范围内招贤纳士。年逾花甲的雷发达不远千里从南京来到北京应募,竟从上千工匠中脱颖而出。后面发生的一切都在证明,历史,把接力棒交给了正确的人。
雷发达成为了紫禁城的总设计师,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当属指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座大殿的设计建造。三座形态各异、对称端庄的大殿,彼此前呼后应、层层递进,丰富了紫禁城的层次,更丰富了中轴线的层次。特别是六百年间未被地震损毁的太和殿,似乎要凭借那三万多个斗拱部件的严密组合,将中轴线永远地捍卫下去。
而最令人惊喜的是,他在设计过程中,不仅追求严谨,还兼具开放的思路。在重新规划清朝紫禁城时,他一方面不断强调着中轴线,另一方面也在轴线两侧的建筑布局上采用基本对称但偶有变化的灵活方式。这个做法不仅没有破坏,反而突出了中轴线,进一步强调了“居中为尊”,以建筑语言昭示着中轴线的意义。
雷氏家族一掌管样式房就是几百年,子子孙孙都在京畿大地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记。从中轴线上的紫禁城出发,圆明园、颐和园、避暑山庄、清东陵、清西陵……时至今日,中国近五分之一世界遗产的建筑设计,都出自这个被人们尊称为“样式雷”的家族。
四、梁陈方案
随着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紫禁城从此不再是天下的政治中心。1925年,故宫蜕变为故宫博物院,珍藏并向公众展出前朝文物。
此时,梁思成正在展厅中踱步,在故宫的烫样前久久驻足,仔细端详研究。他惊叹于样式雷烫样,将建筑的各个部件那般精准地展现,就连层叠生长的斗拱都基本按照真实的搭建逻辑制成,十分精美细致。这些精巧的模型形成有秩序的建筑群,烘托出一条鲜明而壮观的中轴线。
就连模型都如此令人爱不释手,这真实的紫禁城,这真实的中轴线,这由皇城、宫城、内城、外城四重嵌套井然有序的真实的北京城,又怎能令人忍痛割爱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呢?
然而,一座着重工业、科技发展的新北京城即将兴起。在文化古城中建立工业新城,这怎么可能不发生矛盾?
绝对不行!梁思成下定决心,要尽全力捍卫这座有着无可估量的历史文化价值的老北京城——这座有着独一无二的中轴线、独一无二的布局的最恢宏的古城。
他和参与讨论新城建设的另一位专家陈占祥两人,经过考察、分析和讨论,主张在旧城以西约一点五公里的三里河地区建设新城。在新城中,行政机关同样采取紫禁城的对称布局,意在打造北京的“第二条中轴线”。如此,便可以完整地保留老北京城,保护古建筑和城墙,让新北京城有更加广阔的发展余地,同时还能够让新旧北京城的两条中轴线遥相呼应,达到“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目标。这便是著名的“梁陈方案”。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已经知晓,基于当时的发展考虑,老北京的城墙还是被拆除了,另有许多城楼、古建筑消失在历史的烟波中。几百年形成的城市肌理,也随着城墙的坍圮被打碎。每一个懂得老北京城历史文化的人,想来都不免为之叹息。
北京城里的每一条道路、每一段城墙、每一座城楼都围绕着中轴线、烘托着中轴线,“九经九纬”的城市脉络,围绕着中轴线生长蔓延。任何一分损失,都是对中轴线的伤害,这也是“梁陈方案”力求完整保留老北京城的原因。
可是历史的选择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任何一个选择都有其利弊。经历了那一场大拆大建,北京城的中轴线,却顽强地留存了下来,继续对我们倾诉着历史的沧桑……
五、故宫掌门人
“……北京中轴线是全世界最长,也是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一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读到了建筑系创始人梁思成对北京中轴线的论述。他仿佛看到梁思成正站在讲台上,生动地讲述着中轴线的传奇;他仿佛看到梁思成面对着老北京城墙被拆毁后留下的空地泣不成声,他的内心也被深深地刺痛。从那时起,他便在内心埋下了一颗种子,希冀有朝一日能够为传承中轴线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几十年后,他成为了故宫博物院院长,他总戏称自己是故宫的“看门人”。
刚刚出任院长时,单霁翔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摸清家底”。他踏破了二十多双布鞋,用双脚丈量故宫里的每一寸土地,他是第一个数清楚故宫里的建筑总共有9371间的人。有一句话他总是挂在嘴边:把壮美紫禁城完整交给下一个六百年。这故宫里的每一座建筑、珍藏的每一件文物,都是这完整的紫禁城里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他时刻铭记着遍体鳞伤的老北京城,所以他尽自己的努力不让故宫遭受同样的命运。
刘秉忠画下了中轴线,朱棣下令兴建了中轴线上最重要的建筑群,雷发达延续轴线并设计了紫禁城中最重要的三座宫殿,梁思成提出了保护旧城与轴线的方案……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使命,而他逐渐认识到当代使命,从此成为了故宫文化的传播人。
在单霁翔院长的努力下,故宫当中更多扇门向游客敞开,将更加完整的故宫展示在世人面前;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推出,将更加有故事的故宫展示在世人面前;灯光秀、VR虚拟现实展览,各种极具现代感又不失特色的展览,将更加多元的故宫展示在世人面前……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故宫在诞生六百年后再度焕发生机,使故宫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成为让人们放缓脚步的历史长卷。
北京中轴线,又长出了新的枝叶,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未来。
六、仰山之瞥
我曾在去年十月,有幸亲耳聆听单霁翔院长讲述中轴线的前世今生。当他讲述到中轴线的今天时,显得尤为激动。似乎与那条无处不在昭示着皇权威严的轴线相比,今天这条中轴线更令他感到自豪:这条全长七点八公里的中轴线;这条正在申遗、将要走向世界的中轴线;这条由南至北串联着祭祀、政治、商业、文化与社会五个不同主题,展示着北京城众生百态的中轴线……
他说,中轴线的全长早已不再只是七点八公里,它向北可以延伸至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中轴线还在生长,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北京城今天的发展。
于是,我在一个碧空如洗的日子,寻到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中的“北京中轴线仰山坐标点”。我骤然间回想起那个登上景山之巅,望见金光璀璨的紫禁城的黄昏。虽然在仰山看不见北京中轴线上那些标志性建筑物,但我能感受到中轴线如一道“磁力线”正从我身体中穿过,如一条河流注入血液,如一棵参天大树扎根于心。
当单霁翔院长在故宫博物院中来回踱步,当梁思成盯着北京城的图纸陷入沉思,当雷发达欣赏着样式房里陈列的故宫烫样,当朱棣登临万岁山之巅俯瞰着壮阔江山,当刘秉忠在白纸上画下一条微妙地偏移两度、指向元上都遗址的中轴线为后人留下千古谜题,他们是否也感受到了那道“磁力线”?
七点八公里的中轴线,指向历史深处的元上都遗址,指向拥抱未来的“双奥之城”,我们不知道它还将指向哪里。但我们知道,它将永远一端系着历史,一端朝向未来。
是啊,中轴线还在生长,永远生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