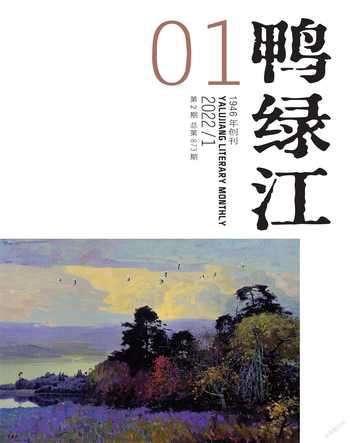苍鹰图(组诗)
乌鸦
乌鸦一只。在我家的背后
打破竹林侧面的阴影
呱的一声
飞过对面梨树林头顶的光秃
吓掉树枝上最后一条皱纹
过一遍田野时
飘下两片擦伤的羽毛
再一百八十度——转回
目中无鸦地站在
一尊有想法,而无行动的石狮背上
洗自己的羽毛
娘举起竹竿,追打
邪恶的象征,已滑过石狮的脊梁
呵,呵,大自然的清道夫
娘不知道,乌鸦自己也不知道
苍鹰图
凝视你,从故乡飞来
两只长翅在蓝天写字
一对利爪不失时机地打标点
你写了什么,我还没钻透一个字眼儿
天空下。还是故乡的那对绝壁
已无语千年
绝壁上的苔藓,在证明还活得自在
那小溪自深山而出
叮咚流水又光滑了石头
那些椭圆。要么,有一个是我父亲
要么,有一个是我母亲
旁边最小的一个,想来是我的童年
可没有谁举起手。向我打招呼
而你的投影
也将小潭变成了另一片天空
可是谁呀,已将你和我的故乡
永久地囚困于我的墙壁上
你以不屑一顾的眼光
与我对视。你已把时间凝固在画上
你的姿态。一个永不落地的梦想
请问你,我能以
什么方式把时间装在永恒里
为一颗夜明珠。即使月光回归了大海
也不会心慌意乱
你想了许多年,也没有回答
如果你飞出我的房间,会飞向何方
小母燕
你张开一把剪刀,从南方
一路裁剪风雨而来
你开始马不停蹄,含泥滴滴
垒你贴在墙壁上的小居
竣工剪彩的那天,终于来临
那个孩子,却抻起一根竹竿
那个应当记入史册的家
粉碎成沙。瞬间里目睹这
惨烈的一幕
你站在不远处的电线上
只轻叫了一声
你又从田垄里
含来清新的泥土气息
滴滴地垒,垒出一朵向日葵
用汗,用血
再次完成你的作品
你凝望那个家,构思你的儿女
欢天喜地的场景……
那个孩子,仿佛从另一个邪恶的世界
冒出。又抻起那一根竹竿
再一次演绎:孩子与燕子的悲剧
你却站在不远处的电线上
只轻叫了一声
那只小母燕,就有我娘的气质
鸟祭
谁知道哩
我们是鸟的遗产继承人
响亮黑夜,鸟的鸣啭
可我们一石二鸟
一直以来,视鸟为敌
而天空,留下鸟的许多
传世之作
鳥儿飞过的路,也有棱角
我们的手可轻轻触摸
那种感觉
只有在,已遥远而去的故乡
那时的家
被时间装进了虚无
鸟路
在天空里,没有画地为牢
每一步没有尘埃。每一段路的旁边
没有警示牌,没有村规民约
没有骗人的广告,没有明星的鬼笑
没有叫卖的虚假,每一段路上
没有因为车祸家破人亡
没有打架斗殴。没有小偷
没有张家短、李家长
哪怕你是一只普通的小鸟
也不会因为缴水电气费而发愁
自有鸟以来。鸟的路一直没有产权
属于大雁,属于青鸢,属于麻雀
只要你能飞,都是鸟们的共同财产
也不会发生
鸟儿分家大打出手。头破血流
那些路。属于人间没有文字的最美诗歌
诗行之间的空白,掠过鸟的影子
我以一生去抓那影子
仅仅抓住了一片羽毛:我唯一的所有
我唯一的忧伤
我只能在地上,摇摇晃晃
不是在鸟路上。飞翔
家
鸟的家挂在树枝上
并不漂亮,像一只小土碗
像一尊小酒壶,像一个小茶杯
既不是别墅,也不是高楼
鸟可以随随便便地
扔掉。不像你和我
扔掉一个家,十分悲伤
鸟,时常落在另一棵树上
迎接阳光。走向它的家
让它的孩子
在阳光里睁大眼睛
一阵呢喃,一串露珠似的
它的生活,远离烟火
天空裸露
蓝蓝的,婴儿在啼哭
你莫飞
想过没有,你一旦飞了
将是一个什么状态
我仍以从春到冬,守住那个小窝
不让雪压瘪
不让风吹到树尖上去
不让一阵惊雷,破碎
而你,在没有界限的天空
飞去飞来。把人间的轮廓
一点一画,记在心里
当你某一天
飞回小窝。发现
我翅膀上的羽毛,一片也没少
而我在你心中的轮廓。面目全非
我的夜
再一次酒醉,但我一直不承认
重复一句:甭管
那几个酒肉朋友走了
我追随,那只带路的夜莺
(也许是一只乌鸦)
摇摇摆摆,走到明月山下
那些石头在石头的眼里
不是兄弟。而我在大山的眼里
也只不过是一个能行动的物体
比偷窥的一只兔子好不到哪里
比我装在肚子里的斑鸠
好不到哪里
比在林间哼小调的昆虫
好不到哪里
这是我的夜
作者简介:
老山,本名付平,重庆垫江县人,
就职于垫江县水利局,水电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