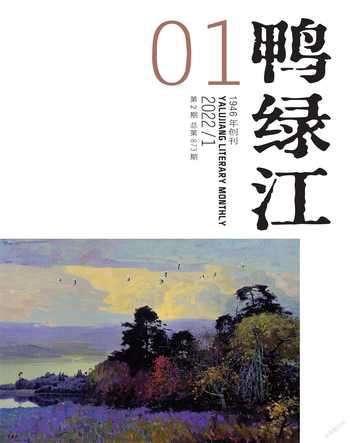劫持(短篇)
男人从家里出来,走在街上很长时间,似乎还能闻到自己身上的那股味道。所以,他确定味道是一种记忆。他在与人群擦肩而过的时候,害怕别人闻到那股味道而刻意躲闪。
男人沿着城市主干道那条长街的门市开始寻找,与其说在寻找一个保姆,不如说是在向一个未知的方向逃跑。那个味道会在突然的某一刻,像一道暗器从不明的方向射向正常呼吸的鼻孔,使身体瞬间窘迫、倾斜起来。他像狗一样四处寻嗅,或窗帘、沙发上,或牙缸、被子里,母亲的屎尿以胜利者的姿态冷静地看着他。
他拿出剪刀把窗帘剪短,剪到母亲够不到的长短,剪着剪着,索性一把扯了下来。牙缸也不用清洗了,直接扔掉,想以后用嘴直接对着水龙头刷牙。他把家里所有能收起来的东西通通塞进柜子里,或者跟谁置气一样,毫不心疼地丢弃。原本像模像样的家很快变得空空荡荡,一览无余。他突然发现,原来,百分之九十的东西都是可有可无的。
他搂着母亲的肩膀说:“妈,你看怎么样?”
母亲傻傻地笑,又恐惧地哭起来。
他用了好大的劲儿才把母亲安顿好,看她睡得香沉,才放心地出去找保姆。在此之前,他给母亲找过24个保姆,每一个都不超过两个月,就说什么也不干了。母亲四处屎尿,人家也忍了,但给她清洗太难,母亲会使出全身的蛮力抗争。保姆说:“最后的结果是,我不但没有给你母亲洗上澡,还把我身上蹭得到处都是,这个活儿实在干不下去了。”
男人从没动过把母亲送到养老院去的想法,当初母亲把自己的双室房子留给他,对他的两个哥哥挑明:“我老了就跟三儿。”现在母亲到了这个份上,他只能挺着。两个哥哥过年过节带着媳妇孩子过来看看,算是仁至义尽,其实是心生怨恨的,以为他占尽了便宜。男人从兄弟媳妇的脸上已然明了一切,但大家谁也没说,没说就意味着这个家还是和谐的。
每次兄弟们要过来,男人一大早就把母亲身上的味儿清理干净,要打无数遍的浴液,把她按到澡盆里反复地冲洗。有一回过春节,母亲突然狂躁,怎么劝哄甚至来硬的都不让碰。眼看兄弟们就要来了,他无奈地把一个床单撕成绳子捆住母亲放到浴盆里。那么多年,那套双室房子就像一双巨瞳,时刻提醒着他是占了兄弟的,欠了兄弟的。所以,再难他都得忍,也得承受。
三个兄弟,大哥在工厂三班倒,三口住一室半。二哥在街边游走式贩卖水果,有一次跟城管起了冲突,还被关进了拘留所。出来的时候男人去看他,二哥没给开门,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在家。
只有他一个人,45岁了还没有结婚,从小酷爱画画,但没念什么正规院校。以前去广告工艺美术公司打工,后来开始自学油画,疯魔一样,十几年过去,他的画可以卖点钱了,可以不用母亲的养老金糊口了。
男人本来已经断了念想,反正自己也是在家画,跟母亲一人一个屋,只要母亲不自伤,随她一个人折腾去。他一天出屋两次做饭用餐,母亲也不打扰他,自己一边看电视一边乱涂乱抹。
但最近有一个南方的画商找到他,要大批量地收购他的画,不是按幅买,而是按批收,一卷画多少钱。他同意了。他笑自己,还没到按斤算的地步,但这次机会对他来说如同沉闷许久的罐子里打开一点儿缝。他兴奋得睡不着,他要抓住这次机会。这样,找一个保姆给母亲做饭洗澡就迫在眉睫了。
那个叫管家婆的家政公司开在临街的一家麻辣烫旁边,他没抱什么希望,或者说抱了全部希望。老板把本子拿出来,按照男人的要求查看档案,那个叫月珍的女人在众多应聘者中跳脱出来,是因为她是农村的,还是单身。这样的条件让男人觉得踏实一些,没有什么牵挂,会全心全意地做眼前的事。
月珍比男人大三岁,已经48岁了,身材粗壮肥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月珍租的小房子离男人家不太远,两三站路,有时母亲太闹,时间晚了没有车回家,月珍就走回去。男人给她打车的钱,她每次都婉拒。这让男人心里过意不去,又对她另眼相看。
有时画画累了,男人会邀请月珍去他屋里坐坐,聊聊天喝喝茶。其实两人也没什么可说的,无外乎老家的孩子、以前家暴的爱人,还有让她受气的公婆和阴阳怪气、指桑骂槐的小姑子。这种话题就是死胡同,走到头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男人发现,月珍称得上完美保姆。她仿佛有一种魔力,母亲在她的照顾下,情绪越来越稳定,不到处涂抹了,脸色也渐渐红润起来。这让男人惊叹她的聪慧。她一定是细心琢磨过母亲的起居和心理,才能准确地把握她的节奏和需求,达成一种内在的承转。母亲睡觉的时候,月珍不停地擦灰洗尘,还会适时地给画画的男人递上一杯清茶,或是一条毛巾。她像一个诊断者,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把家里的两个人照顾得得心应手。这哪里像一个村妇,简直温润如玉。
男人有时想,一个如此适合这个家的女人从天而降,就是一个天使。他终于成了一个自由人,能出去会朋友、喝酒、找女人。月珍会在晚上五点半的时候准时给男人打电话,问他回不回来吃饭,男人每次跟她说不回去了,都有一种老公向老婆请假的心虚,好像不回去就亏欠了她什么似的。因为他知道,她在等。
男人的画很顺利,偶尔还会蓬勃,画商主动加价,虽然很少,但对男人来说就是无价。男人终于过上了甘之如饴的饱满生活,晚上喝完小酒,洗完桑拿,离了歪斜地打开门,月珍还在,这让他有点意外。平时,月珍把母亲哄睡了,打个电话跟他说“我走了”,他就开车回来,前后时间不长,但几乎都是错过。但那天,他是太高兴了,喝多了酒,在大厅里睡着了,回去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十二点多了。月珍还没走,他就知道母亲有麻烦了。
果然,不知什么原因,母親突然拉肚子,月珍把她的衣裤足足洗了一晚上。男人进屋的时候,月珍的手通红而冰凉,额头的发丝散乱。他莫名有点心疼,他太了解了,母亲的麻烦会把一个人弄疯。
男人借着酒劲从皮夹里拿钱要给月珍,他对月珍说:“我今天回来太晚了,你拿着。”
月珍躲闪不要。
男人上前一步往月珍的手里塞。
月珍往后退。男人本就有些趔趄的脚步一下子扑进了月珍的怀里。月珍扶住了男人,把男人送进房间,男人躺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那晚月珍没有走,在厅里的沙发上睡了一宿。男人第二天中午才醒,看到眼前的月珍已经光荣上岗,把香喷喷的饭菜煮好了。
男人问月珍:“昨晚我喝多了?”
月珍笑而不语。
男人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月珍一边盛饭一边说:“不知道。”
男人听出月珍在跟他开玩笑,他再想问下去,月珍说:“吃饭吧。”
男人是在画画的时候把昨晚的事情想超来的。他从屋子里取出500块钱给月珍,说:“你来了这两个月,我妈的状态越来越好,昨天你洗了那么多脏衣服,我又回来得太晚,你拿着。”
月珍当然不会要,转身给母亲煮清肠解毒又润肺的小米蔬菜粥去了。
男人的画在南方卖得不错,手头宽裕了些,女朋友也是接二连三地换,当然都是在钟点房。男人一直在等一个跟他谈感情的女人。自从离婚之后,他穷困潦倒,成日隔宿地画画,就是希望有钱了找个女人,成个家。但那些女人完事了之后就一边冲洗一边要衣服、化妆品或首饰。他想:“等我把衣服穿好,出去吃饭的时候再说都等不及吗?”
女人还在那儿高喊,把钱放床头柜上,好像不早说出来,他会溜掉一样。让他感觉很不好,感觉自己是个嫖客,但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嫖客。他把钱放下,独自走出钟点房,感觉天是灰的,再看自己洗不净油彩的手,突然鄙视自己。
回到家,月珍刚刚走。饭在锅里热着,屋子里仿佛还弥漫着一个女人的气息。他从钟点房出来就给月珍打电话说:“今晚回家吃饭。”就像一个老公对他的老婆说一样。
月珍说:“好的,饭都在锅里了,我先走了。”
他其实想听到的是,她会等他一会儿。
他说:“你今天有事?”
月珍迟疑了一下,说:“嗯。”
他特别想问是什么事,但话到嘴边又觉得越界了。
第二天一早,月珍大包小裹地带菜上来,他还是看似漫不经心地问月珍:“昨天家里有什么事了?”
月珍说:“有人给我介绍个对象。”
男人正在画画,画笔顺着松节油拧到了一边,扭头问她:“谁?”
月珍说:“一个退休的老干部。”
男人说:“多大年纪?”
月珍说:“67岁。”
男人放下画笔说:“我觉得不合适,你去了就是给人家当保姆。你在我这里干,你挣的是工资,自己有支配权。你跟他是侍候人家,还没有钱,给你点零花钱还像施舍一样,我觉得你受不了。”
月珍说:“你怎么知道?”
男人说:“这还看不出来吗?你能把咱们家弄得这么好,说明你是一个要强的女人。”
月珍说:“我觉得他人还行。”说完转身做饭去了。男人画不进去了。男人想,如果月珍相亲成功,他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男人感觉一种莫名的恐惧笼罩下来,他不想再过一次从前那种手足无措的生活。他把月珍叫进屋,把自己多年去开各种会议送的床单被罩、手套钥匙包和出去旅游买的手镯项链等好玩的小东西统统拿出来,对月珍说:“这些都是小玩意儿,不值钱,送给你。”
月珍看着眼前琳琅满目的东西,咯咯笑起来说:“我可不懂这些。”
男人急了,拿过杭州蚕丝被说:“这个总用得上吧?”
月珍一摸,觸感湿滑如水,猛地缩手。
男人说:“这个你一定喜欢。”
月珍还是婉拒了。
男人不再出去玩了,又开始成天在家画画的日子,窗外的阳光打在他的画板上,母亲的状态时好时坏。男人知道,这跟月珍内心的变化有关。母亲仿佛已经住进了月珍的身体,月珍明朗母亲就舒展,月珍焦虑母亲就疯癫。
晚上,母亲早早睡下了,男人第一次请求月珍晚一些走。月珍说:“我家里有点事。”
男人知道,一定又是那个老男人。在这个城市里,月珍没有亲戚朋友,为了躲避乡下家暴的前夫,她化名逃了出来。家里能有什么事呢?有一次男人问月珍:“你原名叫什么?”
月珍笑而不答。
“那这个名是谁给你起的?”
“我自己。”
“挺配你的。”男人赞许地说。
月珍离开之后,男人也无心画画,看到母亲已经熟睡,他想应该没什么事。母亲从不起夜,睡觉的时候仰面朝天,面容肃穆,身体也不弯曲打折,僵直如死去一般。这个样子倒是令人安心。
他忍不住好奇,给月珍打电话,没接。
他约了几个画友出去喝酒,又是一番醉态辗转,回来时翻遍衣兜才发现,走得匆忙,钥匙忘记带了。
那天晚上,他不停地给月珍打电话。在这个城市,只有月珍能打开他家的门,但月珍一直关机。
他只能擂门,他幻想母亲突然灵光一闪,起夜听到敲门声,又灵光一闪把门拧开,但事实证明那只是幻觉。
男人只好报警,叫来开锁的。但那天不知为什么,开锁的也打不开家里的防盗门,也许是动静太大,终于惊动了熟睡中的母亲。母亲没有把门打开,而是受到了惊吓,一声又一声的惨叫从屋子里面传出来。男人不知母亲在屋子里发生了什么事,开锁的人说这样太危险了,必须尽快把门撬开。男人只好向消防队求救。消防队和警察一起把防盗门彻底破坏了,周围的墙壁全都损坏脱落,才把门打开。大家看到母亲坐在地板上手里举着菜刀,一下一下地砍着桌子腿。
每砍一下惨叫一声,好像砍到了自己一样。
那天晚上,屋里的门就那么悬着立在那里,风呼呼地刮进来,他搂着母亲躲在画室里,裹着大棉被瑟瑟发抖了半宿。
月珍第二天一早看到他们的样子,手捂在嘴上,瞪着眼睛看他们娘儿俩。
男人说:“你昨晚为什么关机?”
月珍说:“我回家之后没什么事就关机了。”
男人说:“你是不是跟老男人在一起才关机的?”
月珍不理男人,埋头开始干活儿。男人加入月珍的行动,母亲安静下来,孩子一样看着,他们拍手说:“好,好,真好。”
男人去家具市场买门,又找瓦匠弄水泥抹石灰。月珍在家照看母亲、做饭、打扫卫生,一直忙活到晚上十点多钟还没干完。男人对月珍说:“今晚你别走了。”
月珍说:“我想回去。”
男人呼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你又不是没在这儿住过。今天这么晚,你怎么就必须回去呢?家里是不是有人在等着你?”
月珍说:“我捡了一条流浪狗,我怕它饿着。”
男人说:“你别骗我了。”
月珍执意要走。男人说:“那我送你。”
月珍说:“你还敢走吗?”
男人看了看母亲的屋子,坐了回去。
男人给月珍打出租车的钱,月珍刚要说不用,男人一下把月珍拉到自己眼前,不由分说把钱揣进月珍的上衣口袋里。月珍去玄关穿鞋,男人到门口送她,等到月珍转身下楼,男人关门时才发现,那50块钱夹在鞋柜的隔板里。男人感到一种莫名的愤怒,他给月珍打电话,还是关机。男人着了魔一样地给月珍打电话,气得失眠。
月珍第二天来上班,男人对月珍说:“你把电话打开,看看有多少未接来电。”
月珍拿出自己的老年手机,说:“我不会看。”
男人回屋取一个三星手机送给月珍,那是他一起交了三年的网费,联通赠送十年未换手机号码的老客户的礼物。月珍笑着说:“我可不会用那么高级的东西。”
“我教你。”男人不容置疑地站到月珍的身边,挨着她的身体告诉她怎么开机。
月珍躲到一边去说:“我可学不会,我现在这个挺好。”
男人说:“不行,我教你怎么拍照上微信,今天回去你就把捡的那只小狗给我拍下来,我要看看。”
月珍说:“我不能要你的东西。”
男人说:“你为什么永远都在拒绝我?”
月珍还是摇头逃了。
男人恨恨不平,心想,真是小地方的人,没见过世面。
男人很长时间不出去玩了,画也画不进去,因为母亲又跟以前一样到处涂抹了。月珍辞职那天,男人正在画一幅肖像画,是一个有钱人给他的情人订的生日礼物,8000块钱。男人爽快地答应了,但画得并不顺利.月珍有几次给男人送茶水,看到男人一副沮丧的样子。
男人看着月珍说:“我给你加钱,你别走了。”
月珍说:“不是钱的事。”
男人说:“是不是那个老男人?”
月珍说:“不是。”
男人说:“我知道是。”
月珍不吱声了,回屋收拾自己零零碎碎的东西。
男人从身后一把搂住月珍,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就在他和月珍的胸前散成了花。月珍惊恐地看着男人,男人把月珍拉到弥漫着松节油味的屋子里,把她按到了床上。月珍好久没有碰男人了,她渾身颤抖,男人开始猛烈地撕扯她的衣服,她挣扎,男人的手仿佛在跟一个老男人比体力。事后,男人想,他怎么就堕落到跟一个48岁的农村女人上了床,还那么勉强。
现在,月珍躺在男人的被窝里进退不得,她想起来,又害怕男人注视自己的一身赘肉。他们还没熟到翻身穿衣不觉得难堪的份儿。她就只能在被子里藏着,像藏着一块粗拉拉的石头。男人只好先起来,他起身拿过一件衬衫披上,进了卫生间,他想等自己出去的时候,月珍已经开始做饭了吧。
月珍什么时候走的,男人并不知道。等到洗漱好了出来,只看到母亲正蹲在地中间。不知道又是什么事触到了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神经。她来去都如鬼魅,男人的第一个举动不是去拉住母亲,而是去抓手机给月珍打电话。
男人感觉自己的心跳得厉害,他说了一辈子都没说过的那么多的好话,如情人一般温柔乞求的话,月珍终于答应过来。
母亲看到月珍,像孩子看到久不朝面离家出走的妈,哭得毫无遮拦,撕心裂肺。月珍说:“我到楼下买菜去。”
男人松了一口气。他说:“你什么也别买了,今天我叫外卖,咱们好好庆祝一下。”月珍说:“花那个冤枉钱干啥?”说完转身下楼。
月珍刚走一会儿,母亲就犯病了,用手狠狠地挠墙。男人忙给月珍打电话说:“你赶快回来吧。”那一刻,他感觉自己也像一个怕黑的、无助的孩子乞求妈妈早归。
月珍和男人一起把母亲弄进浴室洗干净哄睡了,两个人都觉得精疲力竭。男人对月珍说:“我想跟你谈谈。”月珍抬起苍老的脸看着男人。
男人说:“这个家不能没有你。”月珍说:“是你母亲不能没有我,还是你不能没有我?”男人说都是。月珍等男人继续往下说,但男人住了口。月珍起身说:“刚才的菜还没买完,我出去买明天一早吃的菜。”男人说:“你不会不回来了吧?”月珍开玩笑说:“那可不一定。”男人说:“那个老男人还去找你吗?”月珍说:“我也不知道。”男人说:“我跟你回去把东西搬过来,一起住吧。”月珍说:“我住哪儿啊?”男人说:“当然是我的屋。”
月珍说:“那我是你什么人啊?”
作者简介:
聂与,原名聂芳,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钟山》《上海文学》《山花》等刊物发表小说若干,有小说入选年度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