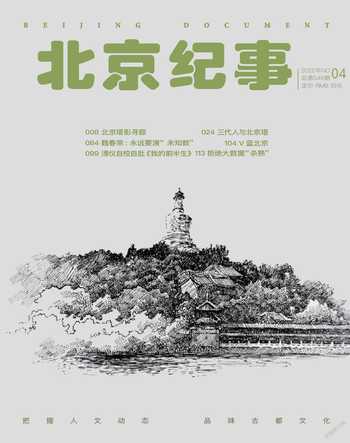芝麻酱的江湖地位
端木东舸

铜锅涮肉就得蘸麻酱
北京人喜欢芝麻酱,一年四季离不了。苦日子里,它是百姓口味寡淡没有食欲的“续命神丹”;在现今,又成了好多人走遍四海最舍不下的味道牵挂。
芝麻酱,这种京外并非主角的调料,北京人究竟爱到了什么程度?这么说吧,在北京城有吃食的地方,但凡听见有人高声吆喝“多来点儿芝麻酱”,嘹亮的嗓音后面,基本都会坐着一个稳稳当当的北京土著。
过水面,是北京人春夏最喜欢的主食。筋道的面条煮熟后,用凉水反复淘洗到不再滚烫,芝麻酱用水澥开,加点盐或是生抽,让它有了老北京嘴里常说的“盐津味儿”,直接兜頭浇在过好水的面条上,一口面条一口黄瓜,吃起来凉丝儿丝儿咸滋儿滋儿,既入味又解暑,是热天儿吃食当中的不二之选。
离开京城,还真是很少见到有直接把芝麻酱不加任何修饰直接用来拌面的,多少都会有一些味浓性烈的口味掺杂其中,吃起来芝麻酱的那股醇厚香味若隐若现,不免少了几番风韵。
寒冬腊月,北风烟雪。三五好友围坐在一口铜锅旁边,烧红的木炭支撑起热烈的气氛,翻滚的肉片抹杀掉身心的疲累,一顿涮羊肉,北京人认为最恰如其分属于这个特定的季节。
涮羊肉口味高低,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肉的质量,只有上佳的新鲜羊肉,才能保证鲜嫩的口感并且肥而不腻,浓淡适中。而另一个决定性因素,便是少不了的蘸料。
全国各地都有火锅,而只有老北京的传统铜锅涮肉,才会用芝麻酱作为主要调料,配合上酱豆腐、韭菜花和一勺现炸的辣椒油,用它们紧紧包裹住刚刚变白的肉片,入口的瞬间,一股咸香醇厚激烈迸发,让每一个挑剔的食客都能在肉与蘸料的纠缠中获得最大满足。
这是老北京吃惯了的味道,尽管各式火锅的蘸料繁花似锦,可放眼去看涮肉馆里的北京土著们,谁不是捧着一碗芝麻酱调料在大快朵颐?就连雄霸天下的川渝火锅里最为标志的油碟,在北京城也同样要悄悄败下阵来。
北京人,敢用芝麻酱去蘸一切涮熟的吃食。羊肉、爆肚、蔬菜、豆制品、海鲜,无一“幸免”被北京人夹进碗里旋转翻飞麻酱密布,继而入口大嚼,高兴至山呼海啸,往往看惊了一众外来之客。
涮羊肉时候,一般少不了芝麻烧饼。外表焦酥覆满芝麻的烧饼,掰开来那绵软的饼芯里还冒着丝丝热气,一股花椒和芝麻酱的浓香烘托出它不一样的品位。这是北京人所热爱的主食之一,早点铺、小吃摊、清真馆,屡屡见其抛头露面。
说起烧饼,就想起北京人喜欢的早点里另外几样吃食。
杂碎汤,一碗散发着大料味的清汤里,泡着不少切碎的牛羊杂碎。
本来腥膻味重的杂碎,在几勺芝麻酱和韭菜花、香菜末的调教下,神奇转身,没了所谓的邪味,多了几许清香。以致令这一碗器官,在老北京的早点桌上,成为了撼不动的娇宠。
现在的人们,说起早点往往是十年如一日的煎饼、油条、豆腐脑,油饼、豆浆、小笼包。比之从前,真得少了很多品种。
杨米人在《都门竹枝词》里写过:“三大钱儿卖好花,切糕鬼腿闹喳喳。清晨一碗甜浆粥,才吃茶汤又面茶。”
面茶,不同于茶汤,虽然二者都是用糜子面熬成糊再加入调料拌匀来吃,但里面拌的东西可谓天壤之别。茶汤大部分人都知道,基本都是甜口,里面放了不少白糖,有的还配了青丝红丝,看起来漂亮,喝着甜蜜。
而面茶却是标配咸口,主要灵魂就是芝麻酱。面茶出锅盛在碗里,浇上几大勺用香油澥开的芝麻酱,再撒上一把芝麻盐,不管你是举起碗转圈吸溜着喝,还是用勺从上至下㧟着喝,要的就是那股芝麻酱和芝麻盐带来的浓香和咸淡。
看似过于朴素的一碗面茶,可用料却非稀松平常。糜子面、芝麻酱、熟芝麻,哪个也不便宜。所以现在规模小一点的早点铺根本没的买,一是可能真也不会做,二是成本稍高,定价太贵了也没人吃,不值当的。
但面茶这东西,早年间确实很招北京人喜欢,就算在当下,稍微有点年纪的北京人,遇着了它,一般也不能视而不见,主要还是放不下那一缕芝麻酱的香。
爱吃芝麻酱,就把它揣进食材里,也是一项不错的选择。
身为北京人,好多都是从小开始喜欢上了芝麻酱糖饼。浓厚的芝麻酱和绵甜的红糖拌好,抹在饼内烙熟,趁热吃在嘴里,那种焦香灼热,糖汁和芝麻酱糊满嘴的快感,拒绝不得。
对于北京人来讲,“芝麻酱可以配一切”,决非危言耸听。
拌个凉菜,不管是白菜、黄瓜、茄子、豇豆、凉粉、水萝卜,只要是你能想出来的菜品,哪个不是和芝麻酱那么囫囵一搞,就显得无以复加得可口入味?
做个主食,烙饼、馒头、花卷、揪片、面条、煮尜尜儿,有咱们北京人不敢往里面加芝麻酱的吗?主要是有了芝麻酱,那吃食确实显得更香啊。要不怎么说,芝麻酱是味道寡淡时代的“续命神丹”呐。
这些正规套路的吃法,多少还有那么些保守。而把芝麻酱拿过来直接怼进嘴里,对于很多正宗北京人来说,也是不在话下。这就显示出了京城人的飘忽和不羁。
芝麻酱和白糖,那是小时候物资紧俏,家长用来哄孩子的利器。虽然现在日子是宽松了,可一茬一茬人们吃下来,芝麻酱和白糖这道佳肴,倒真成了一辈甚至几辈人化不开的情思。
小时候能用来当零食的东西少,家里大人时不时会从瓶子里㧟出几勺芝麻酱放在碗里,和白糖一起和匀,给孩子们解馋。醇厚和甜蜜交融在一起的味道,而今想起来,似乎串联起了整个童年回忆。我总觉得那里面有一种情分,是那些捧着碗吃过它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不论年迈几许,都挥之不去的。
前几天忽然心血来潮,烤了几片剩馒头,抹满了芝麻酱和白糖,酥脆上包裹的厚重甘甜,一口咬下,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
汪曾祺老人家在其文章《老舍先生》中曾记述到:“老舍先生是历届北京市人民代表……有一年老舍先生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那一年北京芝麻酱缺货。老舍先生说:‘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不久,北京的油盐店里有芝麻酱卖了,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喷喷的麻酱面。”
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因为老舍先生那股从里至外的北京味儿,以及先生本身也是喜欢芝麻酱的人,他当然了解芝麻酱对于北京人的重要。
汪曾祺老人家曾经在同一篇文章里回忆过,去老舍先生家做客,吃过他亲自掂配的“芝麻酱炖黄花鱼”。一个连炖黄花鱼都要放芝麻酱的人,算是把北京口味发挥到极致了吧?他一定会明白,芝麻酱已然成为了京城百姓日常生活的“刚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