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满仓桃花雨
1
钱娘娘这几天总往我家里跑,而且还总是找爹下了班的时候来,来了便一腚坐在那个宽板凳上,陪着爹一起喝大茶,娘就在天井院里烧水煮茶,一连几个阴雨天,灶里的柴禾有些湿,弄得小院里一时间狼烟滚滚。
爹和钱娘娘就在这狼烟滚滚里,忽隐忽现,不时有开怀的大笑声,穿过狼烟跑到娘跟前去。娘就会合着狼烟剧烈地咳嗽几下。
然而,那柴禾终究是烧得旺起来了,火苗跃跃,照着娘枯瘦的脸庞,一会儿明,一会儿暗。
爹那年才四十二岁,钱娘娘三十九岁,钱娘娘本就是桑园子的闺女,都说一等闺女不出庄,二等闺女邻村相,三等闺女下四乡。这一等闺女的钱娘娘就嫁给了本村的钱宝生。那时爹还没有去矿上上班,还在队里挣工分,在农闲时唱唱戏。
钱宝生是孙村大矿的正式工。
大矿上福利待遇好,开的工资多,让人家羡慕,但整个桑园子村就只有钱宝生是大矿正式工,他是接了他爹钱顺昌的班,那时候时兴工人退休后,由他的直系亲属能直接接替名额一个。钱宝生就兄弟自己,姐姐七八个,自然这名额到不了别人去,所以也因为这工人的名額,钱宝生才说上了媳妇,钱宝生天生大脑袋,却不见得多聪明,反倒为人处事上有些分寸,村里人在私底喊他钱二青。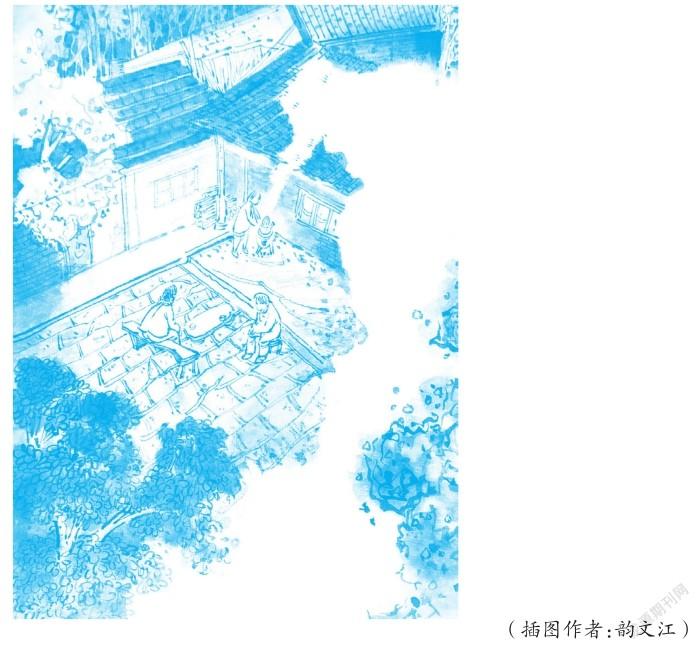
钱娘娘小字桃花,二十岁前在庄里的庄户剧团里与爹唱搭档,青衣花旦老旦摔花旦样样拿手。
我爷爷年轻时成立了剧团,那时候流行唱拉魂腔,唱十八里相送、唱大出观、唱樊梨花点兵、唱三蜷寒桥、唱走娘家、唱拾棉花、唱喝面叶。到了我爹时,爹自然也就成了团长,这时候已经改唱豫剧了,唱大哭殿、唱断桥、唱对花枪、唱武凤岭、唱刘公案一本、二本、三本,金牌搭档桃花和满仓唱遍了四邻八乡。
娘也是当庄的闺女,不过娘比不得桃花,娘可能三等闺女也算不上,娘先天有病,要不是当初因为穷,爹还不一定会娶娘。
桃花原是有意于爹的,但桃花的大哥李玉道当家作主,他不看好六个儿子的于家,看中了钱家独苗钱宝生。
桃花拗不过命运,她嫁给钱宝生那天,我爹失踪了一天。
钱宝生有一股子蛮劲,桃花嫁过来两年,就生了仨孩子,儿子刚子,双胞胎女儿红玉紫玉,钱宝生干活有了定性,年年是掘进工区优秀一线职工。桃花成了钱娘娘,成了钱娘娘的桃花喜欢去东沟的红岩岗去挖红土。东沟那里还留着曾经的戏台,一块高出四周平地的土台子,土台西面正对着废弃了的深挖洞广积粮时期的防空洞。
爹秋天的时候把剧团解散了,把七口装了服装道具的大箱子抬进防空洞里,并把防空洞的门用火药给炸塌了,防空洞被我爹掩埋了个结结实实。于家庄户剧团在爹的手里断了生机。
那个火药的动静太大了,响在桑园子的上空久久不去,桃花眼神迷离,她听到有人问,这是谁给放的结婚大礼炮?
从防空洞回来的那天傍晚,爹和李玉道狠狠地打了一架,原因是李玉道不小心撞了爹新栽下的小树苗。
爹在大哥五岁那年,才有机会也去了煤矿,只是去的是镇上的松河煤矿,属于合同制工人。比不得钱宝生,但比一般农民就强出了一大截。
钱娘娘与爹都没有离开过桑园子,还是那样子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距离,但爹确实是许久许久不曾与桃花说过话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话有些心思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各人有各人的日子,日子是活的,人也是活的,活着就得循着前面的路走。
钱娘娘踏进我家的门,是因为她受她姨奶奶家表姑所托,要来给表姑的女儿豆花提一门亲。
那年大哥刚刚满了十五岁,刚刚考上了镇里的联中。大哥在联中是住校生,两个星期回来一次,回来拿娘滚好的地瓜干煎饼和酱油麸子炒鸡蛋。
钱娘娘说的豆花是前村里的,前村在桑园子南边,赶岔河大集第一个要途经的村子。
娘的脸色多少有了些欢喜,她给钱娘娘递了一袋烟,钱娘娘有时候是吸烟袋的,但她当着爹的面却从来没有吸过,她总是能把自己收拾得清清爽爽利利索索,说实话比娘会打扮多了,娘常年穿一身灰褐色的衣衫,头发因为有点自来卷的缘故,总是鸡窝一样乱糟糟的,整个人显得有些邋遢和窝囊。
钱娘娘与娘不一样,她有着一张银盆大脸,头发细长被挽成纂儿固定别在后脑勺上。脸上白净净的,衣服是藏蓝色的偏多,又素净又干练。最特别最好看的是钱娘娘的眉眼,那眉眼里永远有淡淡的忧伤和幽幽的清愁。
爹觉得钱娘娘的提议很合心意,夜里就与娘商量说等下次大哥回家拿饭时,就让他们见上一面。
2
大哥回家拿干粮时,娘破天荒地给他留了五个白面馒头,是爹从矿上食堂里领的饭,没舍得吃,拿回家来的。
大哥很吃惊,他对于白面馒头的向往,曾在学校里一度到过高峰值,那些城里的孩子,顿顿都有白面馍吃,还顿顿有菜。
大哥拿到馒头后,小心翼翼地放进书包夹层里,鼓鼓的书包,一下子不枯燥了,变得那么诱人。看在馒头的份上,执拗的大哥也因此答应了娘的要求,陪她去南边池塘那洗衣服、挑水。
嫂子豆花就是那时候给大哥定下的媳妇。
15岁的豆花就在大哥最不留神的时候,相看了大哥,起初豆花并没有看上大哥,她撇着嘴,这么点个儿,还不如我高,又黑又瘦。
钱娘娘就说,吓,还嫌人家不高,人家还是个学生娃娃,哪像你,卖豆腐大王,大字不识一个。有骨头不愁肉,桑园子全庄就只有三家煤矿工人家庭,钱家于家赵家,赵家光闺女,我家刚子浑,要不是你娘天天找我托我,我还真不想操这个心。
钱娘娘说完白了豆花一眼,豆花红了脸,她从九岁就在庄里卖豆腐,算钱进账倒是门儿清,就是不识字,逢人家有赊账的,就得找别人来帮忙记账。
豆花又偷偷看了一眼大哥,大哥正弯腰给娘从水井里往外拔水,井绳在他手里歪歪扭扭地拉扯着,半天也没弄上半桶水来,看得豆花不禁又想撇嘴。
钱娘娘说,人你也看了,话我也和你说了,你先回家去吧,好好考虑一下,等过几天我就去你家,问问我表姑去。
豆花觉得自己第一次相亲有点仓促,只是看了看人,也没有说上一句话,“也不知他说话声音好不好听,如果好听我就愿意。”豆花心里是这样想的,她没有与钱娘娘说话,自己走到井沿边上,把大哥的井绳拽过来,呼哧呼哧就拔上来两桶水,两只水桶从井里拉上来,灌了满满的水,看到两只水桶四平八稳地排放在井沿边,大哥一阵惊奇。
大哥说,“谢谢你。”
豆花本来是想来问问大哥名字的,大哥的名字她原是知道的,老早就听钱娘娘说过了的,于大江,知道归知道,不是他亲口说的呢。
豆花没想到从大哥嘴里听到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谢谢你”,她有些发呆,怔怔地看着大哥。
大哥笑了,他嘴角弯弯,毕竟15岁还是个容易害羞的年纪,他头一低,就想去提水桶,把水桶提开,前边一个后边一个,中间够扁担长儿,这样就能用扁担把两桶水挑在肩上了。
大哥趔趄着把两桶水提开,把扁担搁在肩膀上,没敢再说什么话,连跟娘说一声“先走了”也忘了,他着急忙慌地挑起水,在豆花目不转睛的注视下,落荒而逃。
豆花看着于大江的背影,眉眼上落了一份粉红。
3
没过两天,钱娘娘就又来我们家了,爹这个月是夜班,每天上午9点准能回到家中,爹的班与宝生叔的班都是三八制的,正好错开,宝生叔上早班的时候,爹下夜班,爹上早班的时候,宝生叔上中班。
因为这个三八制的排班,宝生叔总是受村里陈小手的挤兑。陈小手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医术不太行,全靠能忽悠,这么多年了,在桑园子谁不知道谁呢?
陈小手见到宝生叔说会问:“钱宝生,你今天上的什么班?”
钱宝生就会答:“今天我上的二班。”
陈小手笑嘻嘻地说:“哎呦,我知道了,原来是上的儿班呀。”
钱宝生就只嘿嘿笑。
后来陈小手又说了一次,当时钱娘娘在场,钱宝生又嘿嘿地笑,钱娘娘就有些不高兴,她不紧不慢地问陈小手,“我说你要解大手吗?要手纸吗?我说你宝生叔上夜(爷)班时你怎么不问,非得解小便时问。”
陈小手天生左手比右手小,娘胎里带的,后天矫正不了,他平日里最忌讳别人拿他的手说事,这会儿对钱娘娘怼了几句,他仔细咂摸了半天,惹了一肚子火气。
钱娘娘算着我爹应该下班到家了,我爹跟她说过,8小时钻井下挖煤,下班就是重生,做着猴车升井后,第一时间是去洗澡,洗澡后在食堂里吃饭,然后就能骑自行车回家了,回家当然是先补觉。
钱娘娘来我家有些早,这个点爹有可能才刚从猴车上下来,往澡堂里跑,可能是想到我爹跑去澡堂后的情景了,钱娘娘的眼睛闪闪亮,脸颊忽然红了一下又红了一下。
我的娘趿拉着双宽口旧布鞋,因为鞋子穿得有点久了,有点不挂脚,一走一趿拉,一走一趿拉,就像一个人老是擤鼻涕又擤不干净一样。
我娘起床就是三件事,喂猪喂鸡喂小白,然后就是扫院子,把院子扫得尘土飞扬,扫完院子后,会在新扫的院子里洒上点水,这样满院子就有了一种水润润的清香。
我娘有时候也会在这满院子的清香里出一会儿神。
錢娘娘来得确实是有点早,她好像也喜欢被娘收拾过的小院里的清香,她坐在晨曦里逆光的样子很美,娘没有理她,径直去了后院里摘黄瓜,后院有块空地,被爹用下班在家的时间,开垦了两畦菜田,种了爬架的黄瓜和老来少芸豆。
娘摘黄瓜摘得并不认真,小黄花小嫩刺,娘统统没看进眼里去,她耳朵里听着小白的声音,只要小白撒着欢儿转圈圈一样地叫,那才是爹回家来了。
小白没一会儿就叫了,娘从后院里挎着竹篮子出来,钱娘娘笑盈盈地坐在那里看着我爹笑,我爹边放车子,边对着钱娘娘笑,大金鹿自行车已经被爹骑了快十年,一对车镫子都掉了,光剩一根独横轴了,支架也歪歪着,除了车铃铛不响外,全车都响,连车轮上的轴条也响,这不,爹还没停好自行车呐,他就朝钱娘娘转过头去,后边的自行车哗啦一下子就倒了,把跟在他身后的小白,吓得一溜烟跑了。
爹回身把大金鹿给扶起来,钱娘娘说,“豆花那边回信了,同意呢。”
我爹大喜,他对着娘大声地嚷:“还不快泡茶,大江这事能成,多亏他钱娘娘。”
我娘放下竹篮,看了我爹一眼,她的眼睛里有些内容,爹却忽略了。
后来,娘私下对我说,其实她是不喜欢大哥找豆花的,豆花那女子她见过啊,很精明的样子,但没有文化,保不齐你大哥以后会不舒心。
可耐不住爹愿意呀,爹兄弟六个,他是老三,兄弟六个差点没全打了光棍,穷,说媳妇难啊。爹这是想先下手为强。
爹给了娘三十块钱,去小卖铺买酒买菜,他说中午的时候,请钱娘娘一定要过来吃饭,是不是商量一下定亲见亲家的事。
4
我哥于大江,在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就这样被我爹娘给稀里糊涂地定了亲下了礼,那时候给豆花下的彩礼是人民币60元钱,两件褂子三条裤子,两个棉袄,当然都是布料,还有两床被子面、两床褥子面,最后买了个手提包,咖啡色的,有些洋气。
我家下彩礼给的布料和被子面都是爹在矿上发的,国营厂家的货,同样很叫面。而且爹那年冬天还特意给豆花家送去了一车乌黑油亮的大煤块,豆花家向家里运碳的时候,前村人的眼睛都羡慕得发了红。
我因为跟在娘身后还格外得到了一把染了红色绿色的花红果子和几颗糖块,这些定亲吃饭会亲家的事,大哥一样也没参加,好像他才是个局外人。
定亲的事,爹并没有征求大哥的意见,这也是后来大哥对爹最有成见的事。
爹让娘等大哥回家拿饭时,给大哥称点肉,补补身子。大哥是周日下午回家的,他在家住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就得赶回学校,不能耽误周一的课,他回家来第一件事是来找我,他抓住我的手,紧张兮兮地问:“咋,大河,爹娘真给我定了亲了?”
我刚割了猪草回来,小白在蹭大哥的裤脚。
我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是啊,哥,我们还和豆花嫂子一起吃饭了呢。”
大哥问哪个豆花?
我说:“就是给你说的那个媳妇呀,前村卖豆腐的,个子高,身体壮,说话大嗓门,脖子上有一块青记。”
大哥拉着我的手,忽然一下子落下来,他颓废地低下头,丢下我和小白,一个人走到院子外面去了。
吃晚饭的时候,大哥还没有回来,爹这次上的是打连勤,就是月底了中班上完接着上夜班,爹没在家,娘让我去找大哥回来。
我家在西山脚下,出大门就是西山,我常常去西山上摘酸枣儿,摘了放在空酒瓶子里,灌上白开水,拿到学校里去喝,太阳一落山,西山上就和平时不一样了,风吹着,有各种声音的鸟儿在叫,叫着叫着,就把西山叫黑了,黑了的山,鬼魅魅的,有些吓人,我喊了几声大哥,大哥没有回我,只有山谷里的布谷应和了几声,我真想拔腿就跑呀。
再往前走,拐过山路,左面小丘陵上的那棵大梨树下,梨花已经败了,青涩的小梨子不时掉落下来,打到大哥的头发上,大哥的影子,在风中有些摇晃,又有些远。
“哥,于大江。”我大声地喊。
大哥从夜风中走了出来,紧闭着嘴巴,脸色肃然,他并不应声,只是跟在我后面,慢慢地向家里走,大哥知道我怕黑,走了一会儿,他追上前来,牵住我一只手,我的鼻子一酸,眼睛一热,差点掉下泪来。
第二天,天不亮的时候,大哥就背上干粮去学校了,桌子上留下了娘特意给他炒的辣椒咸菜肉丝酱,还有爹用粮票给他换回来的五个馒头。
又过了半年,大哥中考失利,没考上重点中学,但是考上了职高,爹愿意让大哥下学找个工作,但因为大哥个子矮,走哪里人家都不要,大哥才能继续上了两年职高,在职高里大哥学习了养蘑菇的技术。
5
钱宝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事的。
孙村矿塌方,最前面的掘进工人钱宝生被埋。
两天后,事故结果就出来了,工人违规操作,导致煤层塌方,三人受伤,一人死亡。
钱宝生没有被抬回家,他被直接送进了医院的太平间里,在冰冷的柜子里躺了七天,七天后,钱宝生被拉走火化,矿上也给出了赔偿方案。等钱刚子明年满十八岁后可以被招為矿工,再就是钱宝生两个姑娘的抚养和钱娘娘的生活问题,矿上给了一部分钱,具体多少钱,谁也不知道。
娘去安慰钱娘娘,娘说:“人死不能复生,他娘娘,你可要挺住。”
钱娘娘看了娘一眼,又看了看身边站着的三个孩子,钱娘娘长长叹了口气,她把三个孩子揽进怀里,把头深深地埋了进去。
爹拿出了100块钱,又去村里找村书记,说让村书记下通知搞个捐钱的箱子放村委门口,让全村人都多少帮衬帮衬点,众人拾柴火焰高,能帮多少帮多少。
桑园子给钱娘娘捐了不到200块钱,当然这里面有我爹的100元。
钱宝生说没就没了。这很让人唏嘘。
钱娘娘从那以后,一次也没再来我们家,这让娘很是诧异,倒是豆花从钱娘娘出事后,竟比平时来得勤了,平时也就是过年的时候,年初三,我去叫她,她来我们家住上两三天,这叫过婆家。但现在她已经不等着过年我去叫她了,前村离桑园子又不远,半小时就能打个来回,她不分节日不分早晚,只要卖完了豆腐,就会来我们家呆一会儿,有时帮娘喂喂猪喂喂鸡,有时也帮我割筐猪草,还偷偷给大哥织了件毛衣,她是真不会织呢,手指头都被织针戳破了,后来我等了好久好久,也没见她把毛衣送给大哥。
豆花来我家时,也去钱娘娘家,钱娘娘不常在家,她还是总去东沟挖红岩土。
钱娘娘不来的时候,爹也没有啥不中意的,本来我还以为爹会因为钱娘娘不来,而有些微微的生气,可是什么也没有,爹表现正常着呢。
爹好像真的不喜欢唱戏了,他把家里保存的唯一一张他们剧团1972年的演出照也给弄丢了。
6
大哥终于职高毕业了,18岁的大哥足足又长高了一头,正儿八经一个男子汉了。大哥毕业那天,头一回在外喝了酒,三个同学把他送回来时,他拉着同学的手不让同学们走,三个同学中有一个娇小的女生,女生的脸蛋儿红红的,她不劝痛哭流涕的大哥,她只是转过头,看着屋外的天空。
大哥拉着那两个男同学哭,最后又过来想拉一拉那个女同学。豆花从钱娘娘家听到动静了,她跑进院里来,看到有同学在,她停了停脚,一眼就看到那个女同学的脸了。
“大江。”豆花从容走进屋里来。大哥放下了手,女同学眼睛顿时暗了下去。
“我们回去吧。”女同学低低地说。
同学们走后,大哥就吐了,吐了一床单,豆花把大哥揽起来,喂了水又给他擦了嘴巴,把褂子给拽下来,从上衣口袋里掉出一张一寸照片来,豆花从地上捡起来这一寸小照,有些晃眼,照片中的女子正是刚才见过的那个女同学。
大哥第二天才彻底醒了酒,头疼让他又躺床上半天,他听着豆花在院子里同娘说话拉呱还帮娘干活,他只把头转向墙,像是要把面前的墙看出朵花来,他透过窗子,看到院子里晒衣绳上晾着他的上衣,他下意识地去摸一摸胸口,胸口的秋衣上可没有放那张一寸小照的口袋。
爹的消息是下半夜捎来的。
大伯二伯四叔五叔六叔都被叫到我家院子里来。
四叔是村里的会计,他说:“我们去矿上找矿领导,这事,最后结果都得是工人违规操作,所以我们得先想好与矿上怎么谈,谈个什么条件。”
大伯说:“是,不过,松河矿矿长不是别人,是咱村里任家的外甥,多少也该有些照顾。再说这个矿不是大矿,也好说话。”
二伯五叔六叔都点了点头。
五叔回头来找我娘,我娘在得到消息后就跑出家门了。娘不识字,也不知她跑哪里去了,我被安排在家里等着,大伯叔叔们带着大哥去矿上交涉。
大哥出门时,我在后面扯住他的衣角,悄悄问过他了,问爹怎么样了?
大哥低低地说:“断了一条腿。”
我吓了一跳,如果没有了一条腿,那以后爹还怎么走路呢?我听爹原来对钱娘娘说过,说等从矿上退休了,他就再把桑园子剧团给组织起来,重新把以前的老戏给排一排。我发现爹说这话时,钱娘娘和爹的眼神都是亮亮发光的。如果爹没有了一条腿,还能不能登上戏台呢?
夜真黑呀,娘还没回来,大伯叔叔大哥也没回来,没有人来,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不敢动,西山上的风怎么又吹起来了,还吹来了各种各样的声响,屋子里又不敢开灯,怕无尽的黑把这唯一的光亮吞噬得更快,脑海里奶奶曾经给讲过的鬼故事,张牙舞爪地爬了出来,我嘤嘤地哭了起来。
“大河,你在哪?”豆花的大嗓门从大门外响起来。
“豆花嫂子,你快来。”大哥在的时候,不让我叫豆花嫂子,可是现在,我多么希望豆花在我身边呀。
“大河。”豆花绕过我,进屋里把灯绳拽了下,“啪”一声灯花绽放,屋子里顿时温暖起来。
“给,吃吧。我从钱娘娘家拿来的。”豆花把手里的大米饭递给我。她本来喊钱娘娘是表姐,可是自从与我大哥定亲了后,她就随我们改了口,也喊钱娘娘了。
豆花陪着我一直到了早晨,娘还是没有回来,大哥回来了,他耷拉着脑袋,一副很困很累的样子。
娘跑着去了矿医院,十里路她用了半个小时,到医院就一个病房一个病房找,她眼前不断涌现那年她陪钱娘娘去医院找钱宝生时的情景,现在的情景和那时的情景一度折叠在一起,让她分不清东西南北,她一路找一路哭,爹那时已经做完手术了,手术的麻药还没下去,他正迷迷糊糊地向前走,忽然听到娘一声接一声地喊他,喊得撕心裂肺,他努力转头去找,却怎么也看不到娘,只是娘的声音更急切了,罢了,任务还没完成呢。爹悠悠醒来,他睁眼就看到娘的肿眼泡,他想咧咧嘴对娘笑笑,有什么大不了的嘛,他人还活着呢。可是爹没有笑成功,倒是他一咧嘴,扯到了嘴角伤口疼,他的嘴巴从里面缝了十一针。
娘看到爹醒了过来,就笑了,她抹了一把泪说:“你活着就好,你还活着就好。”
7
爹在家病休了十个月,十个月照常开工资,但是没有全勤和年终奖,其他福利都有,还额外答应了多补一车福利煤给我家,给娘和我还有大哥争取来了三件棉大衣和三双雨靴,多分了一车白菜和两袋面粉二十斤大米,大伯可能是想着让我多穿几年吧,给我争取来的大衣和雨靴又长又大,下雨的时候,我忍不住穿着雨靴出门,因为雨大风大雨靴大,我摔了好几跤,可是摔了也快乐,我歪在水里,哈哈大笑。
爹右脚植皮是用的他大腿根那里的肉,但爹的右脚还是有点跛,万一走巧了正踩上硬硬的石头子儿,会疼得一咧嘴。
在家休十个月,爹哪里能休得了呢?爹决定同邻居陈冬子一起去贩鱼。
爹是十月底出的事,是三月份去的日照。为什么选择去日照呢,因为日照涛雒镇四门子村有爹年轻时认识的一个朋友。
陈冬子是陈小手的大哥,他有一台拖拉机,他在车斗里放了被子和塑料布和马扎子,让爹在车斗里呆着,他们一路往东,带着雄赳赳气昂昂的雄心壮志,要去贩海鲜,当然也不能空着车去,爹让娘把村里的油核桃收了百十斤,放在车上,到日照后看看能不能卖了,一来一回捎带着赚点油钱也好。
拖拉机上还备了煎饼咸菜和白酒,白天他们上路,晚上就找个避风的地方在车斗里吃喝休息,当然晚上躺在车斗里睡觉的时候不免要拉起女人,陈冬子拉的最多的是钱娘娘,他拉钱娘娘的媚眼和丰满,爹就有些不樂意,但爹以大局为主,也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但他对陈冬子从心里有了些厌恶和反感。
去的时候,核桃倒是好卖,一转手就赚了二百块,这二百块钱把爹和陈冬子的脸都照亮了,让他们也因此失了小心。
爹找到四门子村的老朋友刘显恒,刘显恒很热情,他带爹和陈冬子去了海边,看了行情,对于长途贩卖鲜鱼,他表示够呛,人家都用带冷藏的物流车,你一台拖拉机拉半路不臭了。
爹和陈冬子很是发愁,他们在涛雒镇呆了三天,没办法,总不能空车回来吧,爹和陈冬子商量后进了一批小咸鱼和海蜇头,进了一小部分活鱼,想着一路走一路卖,也多少能卖了。
爹和陈冬子错误地预估了天气,从爹他们装好车开出涛雒镇后,天就开始蒙星下起了小雨,出了日照界,雨越下越大,拖拉机开不了,只能找地方避雨,避来避去,就把活着的鱼都给避没了气,爹和陈冬子晚上趁夜黑,向小河沟里倒死鱼时,被巡逻的村民逮了个正着,为此被罚款200元,商量到最后,求情到最后,爹都快给人家跪下来了,对方才松了口罚了100元。
爹和陈冬子七天后回到桑园子,回到家也不敢歇息,车上还有小百斤咸鱼和海蜇头呢,摆摊卖鱼,生意并不好做,到后来,爹和陈冬子平分了剩下的咸鱼和海蜇头,也因此每人分了500元债务,这凭空多出来的500元债务让本就不富裕的家,更不富裕了,爹娘在夜里有多愁,我是不知道的,只知道那一年,我们家几乎天天煎鱼吃煎饼,还吃那些嚼起来咯吱咯吱作响的海蜇头。
爹看起来轰轰烈烈的下海活动至此宣告失败。
还有五个月呢,矿上只发基本工资,那还是还不上又新添的新账呀,爹便去了村里的石料厂,爹年轻时就会起石头,在高高的山体悬崖上,能用炸药起下来方正的青石头,那时候村周边的村子都在,靠山吃山,也相应有了磕石机,砖厂,砌块厂,灰膏厂。
爹用余下的近五个月的时间,起了172车青石头,一车25元。
爹拿出来1300元还清了家里所有的外债,其他3000元存在了村里的信用社储蓄点,这是爹娘存得最多的一次钱,爹盘算过了,大哥18岁了,也该张罗着给他盖房子了,人这一辈子房子很重要呀,要娶媳妇要生孩子呐,爹让娘给他打下手,他凭一己之力前前后后用了5年终于给大哥盖了双挂耳的三间新房。
爹被通知回去矿上上班的前一天,他与陈冬子打了一架。
原因是爹把大金鹿推大门外,擦拭修整时,陈冬子打门前经过,他凑到爹耳边跟爹开了个低俗的玩笑,又是关于钱娘娘的。
爹一拳头就揍上了陈冬子的鼻梁,陈冬子的鼻子接着就破了,流了不少的血,爹才不管他出不出血呢,三下五除二,用他起石头抡洋镐的劲头,把陈冬子打了个落花流水。
陈冬子趴在地上狼嚎,村里的人都跑过来看热闹。
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过钱娘娘了。
8
26岁的大哥用小麦秸玉米芯、花生壳、棉籽壳、锯木屑等,在爹给他盖好的三间屋的新家里,搭了低矮的大棚,竟然养出了一茬一茬的蘑菇,粉嘟噜的平菇,很有市场,让周边村里的人很是吃惊,便不时有人前来学习观摩,这让我爹和我娘觉得面子上倍有光彩。
那年五一,我爹决定让于大江和豆花结婚。
大哥其实不愿意与豆花结婚。他为此也采取过措施。
每年春节,我们大家族聚一起的时候,豆花都会来,大哥都会不在,有次人多嘴杂,把豆花说臊了,豆花就觉得很丢面子,她哭着跑回了前村,大哥趁机住到他种蘑菇的新家里去,锁上门不让人进,自己也不回家里住了。
爹叫四叔五叔六叔出马,跳进院墙把大哥给押了回来,这个晚上给大哥开了个盛大批斗会,也不知是爹和叔叔们厉害,还是大哥厉害,反正这以后到爹决定给大哥娶媳妇,大哥都没有提任何异议。
五一到了,大哥被安排着穿新衣戴新帽,试新鞋,又是背媳妇,又是吃脆生饭,忙得大哥没心思去想其他的,倒是豆花一个人坐在婚床上,看看这个布置一新的新房、全新的被子褥子、全新锅碗瓢盆,心里突然地涌上来一阵哀愁,她低下头,咬紧了嘴唇,吧嗒吧嗒地掉起了眼泪。
钱娘娘作为大客,被娘派了五婶六婶去请,去请了两趟,也没请来,五婶说,“没见到人,钱刚子媳妇那个嘴厉害着呐。”
六婶也说,“看那媳妇的样子就知道钱娘娘这几年的日子指定不好过。”
娘就有些没主意,她问爹要主意:“要不我拿两包糖去?”
爹看了娘一眼,没说话,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娘一下子又没了主意。
早上的一桌主宴席又过来催了,说让快入席,就等媒人这大客呢。
爹冲娘伸了伸手,他从娘手里接过两包糖,他说,“我去,我去叫。”
爹走出家门时,娘的眼睛慢慢枯萎又徐徐绽放,她听到大哥婚礼上燃放了礼炮,这是桑园子村第一家娶媳妇放礼炮的人家,娘听见头上的喜鹊叽叽喳喳叫了起来。
爹没有去钱娘娘家,他去了东沟,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东沟,原来的东沟是一面大土坡,现在土坡已经被推平了,修成了一条柏油路,成了桑园子南北主街的一条大路,那沟底的土台还在,土台上的两根木头柱子还在,柱子下的大青石板还在,那石板下的青苔还在,那些经年的风雨还在,爹摸着青石板慢慢地坐下来,他的耳边隐隐响起锣鼓家什声,隨着锣鼓声起伏荡漾着抑扬的唱腔,是拉魂一样的腔调,是摄魄一样的婉转,彩衣长裙衣袂飘飘,丹凤眼柳叶眉兰花指飞跃眼前,爹张大了嘴巴,他的身形已经旋开,在土台当中,蟒袍玉带,威风凛凛的黑脸包拯,亮开了一嗓。
爹被自己吓了一跳,他转头去找,土台上除了有风吹过什么也不再有。
爹听到窸窸窣窣的声响是从防空洞那里传来的,那被结实堵住的洞口旁被挖开了一个小洞,缩紧身子趴下来才能钻进去。
爹从小洞里爬了进去。
爹的眼前豁然开朗。
偌大的防空洞里,放着三个煤油灯,灯罩里面的棉芯上开着盈盈一豆烛火,防空洞里七口大木箱全部被打开着,里面的戏衣,蟒、袍、乌纱帽、髯口、刀枪剑戟、凤冠霞帔都一一被拿了出来,整理得整整齐齐挂在防空洞的坡壁上,锣鼓板二胡长笛,也安静入了座,坡壁正面端端正正地挂着剧团的那张演出照片……那箱子盖上,那些四周隔置的青石板上,排了一排排用红土捏就的各式泥人,这些泥人或是威武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或是情深至坚的白素贞,或是温柔的桃花庵里的妙善,或是骁勇善战的穆桂英,或是风流倜傥的罗成,或是两情相悦的李凤姐与乾隆……
爹一个一个把泥人拿在手里,一个一个看下去,看到了自己从十二岁上台演出时,那些流年不再的情景,爹看得情不自禁,爹一会儿老生一会儿花旦一会儿青衣一会儿小生,爹把手中泥人的角色都去了一遍,爹的声音沙哑,他看到了墙角那缩成一团的桃花。
爹把怀里的喜糖扬上半空,那糖块噗噗噗纷纷掉落在土中。
爹听见桑园子的上空又响起了礼炮,那是中午的吉时已到,觥筹交错的宴席就要开始了吧。
爹慢慢跪下身子。
爹泪如雨下。
……
这许多年后,我爹和桃花的故事还在桑园子流传,而我的娘也已入土多年了。
【作者简介】青梅,原名刘清梅,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高研班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