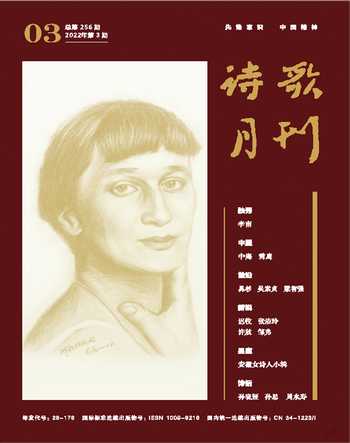新景观、旧情感与焦虑症
周水寿
如何为新诗之“新”作证?毛子为我们搭建了三幅诗歌景观图(阅读景观、现代景观和科学景观),并在其中灌注了情感,使得诗作可读可感可思。在现代社会的境遇中,毛子致力于为诗歌垦辟新地,却又困身在“存在性焦虑”这片无解之地。纵观毛子诗歌,称其为当今中国诗坛肩负“现代性的后果”(吉登斯语)写作的旗手,也并无不妥。急促的语词和摩擦感的显露,是他内心无法掩盖之焦虑的外化,他游走在精神与现实的巨大罅隙,尝试缝补又恨不能举刀将之割裂;他企图躲进书堆乞灵于精神先贤们的富矿,偏又在某种生命的负罪感和新闻碎片中沉陷。或许最终围困他,使他不能轻易说出的,只是他那颗真诚的诗人之心,他那“灵魂一直在鞭打肉身”(《寄居之诗,兼给邢昊》)的踟蹰。
新景观的呈现
毛子有着磅礴的思索与阅读海洋。在写作中,他毫不避讳自己的精神出处,甚至直接拿它们来写诗,说透彻一点——毛子拿自己的阅读材料、阅读体验作诗。喜爱列举的毛子,甚至直接列举(或曰嵌入)人名来唤出诗意,似乎人名及其背后的隐含就是诗意。幸好,毛子是一位优秀的“砌砖人”,凭借扎实的手艺和诗人气质,驾驭住了这些突兀的方块字译名,为我们构筑起一道别样的“阅读景观”。如《矛盾律》从“近日读《惶然录》,一段文字跳入眼帘”开始叙述,其间列举了佩索阿、卡夫卡、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梵高、荷尔德林,这些“我精神家族的庞大成员”,一共7个人名。
毛子的诗歌不单是对信息的接收,也是低沉的回响。他为我们展开了一幕幕日常生活的场景,发出了一声声咏叹。但这还不够,“具有活力的诗人必须寻找新的话语,对新的场景进行更为开阔的诗学述说”(杨克、温远辉:《在一千种鸣声中梳理诗的羽毛》)。与继续坚守,写作农耕时代意象的诗人们不同,毛子打入现实生活的内部,与塑料、钢铁结媒,蠕动着强劲而疲惫的消化器官,在满眼科技感的生存下打量着“未开封”的对象物,为新诗的“新”作证。毛子以非诗的东西入诗,在语言的擦拭中攫取诗意为现代景观赋能。毛子打捞着现代性的场景“碎片”,并为它们赋予了精神的光亮。
相比于之前所说的“阅读景观”和“现代景观”,科学与诗歌的化合反应令毛子的诗歌熠熠生辉。在《星空》《水瓶星座》《祖父》《安排之诗》《在沪蓉高速公路》《塞车记》《永动机患者》等诗作中,我们都不难见到宇宙(知识)的神秘面纱在晃动。除写关于宇宙和生物知识的诗歌外,毛子还借用其他科学知识,如时区概念(《酒店入住》),视网膜成像原理(《片刻》),等等。相较于新诗创始之初,郭沫若写《天狗》时夹杂的科学新语,毛子做出了与时俱进的开拓。涉及黑色素(《生活书:婚姻》)、堰塞湖(《徒劳之诗》)、明矾(《夏午,在河边》)、测谎仪(《在石牌抗战遗址》)的这些诗作,即为佳证。
旧情感的双重含义
在上述三幅新景观下,毛子的诗歌藏有着“旧情感”。情感的“旧”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指诗人对前现代时期,人类与自然的亲密关系的怀念;二是指亲情、爱情这些人类亘古不变的情感。
毛子有多首诗歌写到月亮。这颗被古人称为“玉盘”“婵娟”的星球充满了传说,但在毛子笔下,它恢复了自己最真实的面孔——它是“我”眼中的一块石头:“当他聊起这些,云南的月亮/已升起在洱海/它微凉、淡黄/我指着它说:你能赌一赌/天上的这块石头吗?”(《赌石人》)这番话虽说是科学的本真揭露,却无异于一种冒犯。诗中那个黝黑的楚雄人(赌石人),离别时拍拍“我”的肩膀说:“朋友/我们彝族人/从不和天上的事物打赌。”在另一首题为《月亮》的诗歌中,诗人写道:“天空……它只养一个月亮/那时,它是野物,还不是家养/我们也在百兽之中/尚没有孤立。”“我们”(人类)的演进,从百兽之中那个抓骨头的人,慢慢成了直立的握笔的人。诗人感慨:“月亮一定还在那里,但我们看不见它了/我深深的孤独来源于此。”与其说,“我们”看不见月亮了,不如说“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月亮”(文化的、科学的月亮)。在远古时代,我们与月亮的关系自然、纯粹(含有人对月亮魅力的敬畏成分),可是现在不复以往了。
如何用生物知识表达亲情?父亲的去世,使毛子写了很多悼诗。《往生记》写道:“爸爸转世了/算命先生说:往东南方向走/你会遇到一个新生的生命/但他不能肯定/我的爸爸是兽类、水族类还是直立的灵长类//爸爸啊,我依然杀生,不吃素。”此诗交织着科学化的物种分类和老旧的转世之说,但显然,这些知识不过是寄托对天人两隔的父亲的极度思念。有关母爱的赞美,毛子虽声称“一直不想作声”(《保留之诗:给母亲》),但也留下了几处对朴素母爱的记录。在《母亲》一诗中,他更是将母爱延伸到大自然的各类“母亲们”,他酝酿了一场彻底的对母爱的赞誉。“我忘了它们也是母亲/——分娩的毛驴、孵蛋的海龟、护食的母鸡、哺乳的鲸/装着小家伙的袋鼠、发情的牝马、舔舐幼崽的母狮……/这些蹼趾的、鳞鳍的、盔甲的、皮毛的/翅羽的、蹄角的母亲/它们遍布在水底、空中、洞穴、丛林”。它们表达着“古老的哺育”,用气味和肢体,用被我们视为“飞禽”“走兽”的身躯。
焦虑的原因及表现
对现代性的反思,是毛子焦虑的一大源头。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种骄妄的人类中心主义逐渐生成,并以现代之名弥漫全世界。与现代性及其进步主义思维不同,毛子有一颗“失败之心”(《失败之心》)。他指示我们“每一个肉身,都在衰退”(《论进化》)这一事实。他审视人类的现时代(《审视之诗》),查看我们自以为前进的脚步是多么孱弱。毛子试图用诗歌为我们拉起警戒线,“而果戈理说得多好啊/——我怜悯你们/你们这些战无不胜的人……”(《深测度:致X》)
某种对生命的负罪感,是毛子焦虑的另一源头。“我们还在吃,还在消化/吃是一种债务啊,也是终身刑役”(《在我们都脏的时候……》)。在这里“吃”指向了人的生命形式,也即“吃的悖论”——我们生命的持续建立在其他生命消亡的基础上,故而“人类,杂食动物,道德模糊的动物,处于极需引导和自赎的境遇”(尤格拉《智慧天使:西蒙娜·薇依传》)。毛子写自己的忏悔词,“我穷。/说过谎。/八岁时偷过父亲的钱。/至于我拖欠的命,有青蛙、蚂蚁、麻雀/和跟随我多年的一条狗”(《忏悔》)……
那么焦虑在毛子的诗中,是如何体现的呢?除了语调的“急迫”外,焦虑还表现在对“摩擦”的感受上。如果说排列是互不相让的大型摩擦,以至于各个意象只能通过换行来实现润滑、实现转向、实现归结,那么在毛子诗歌中,小的摩擦随处可见。例如“舔”这个动作就是带有肉体感的摩擦,让我们看一首在意象排列下形成的舔舐之诗:“铁丝网/绷带/雨刮器/避雷针/望乡台/穷人的晚餐/敌人的女儿……//今夜,这些重的、疼痛的、没有声音的/它们像骆驼弯腰/慢慢舔我”(《咏叹调》)。又如《出埃及:致德东》所写,“昨天,我梦见都灵的那匹马/走过来舔我”。可以说一个温顺的动作在毛子这里获得了精神的痛觉,这种痛感连接着人类这一整体,如《匍匐之诗》尾句所示——“那一刻,摩挲‘People’这个单词/我的声音小到/只有嚅嗫……”。当然,“摩擦”还有更为广阔的含义,“我想摸摸身体里的水/它终日荡漾啊,荡漾/并不说话”(《我想……》),就可视为毛子焦虑的生动譬喻与展现。我们似乎可以想象,辗转反侧的难眠之夜与终日晃荡的水所扮有的亲密关系。
无疑,毛子收获了一枚焦虑的果实,也正是这份焦虑的铺展,使得诗“人”之形象得以确立;诗歌在语言之外抓获了可供给养的土壤。“既为头顶星空的浩瀚而鸣,也为自己体内的浩瀚而鳴”(陈先发语),毛子的写作行动擦亮着一再被遮蔽了的现代汉语,绘制出了新诗图谱上不容忽视的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