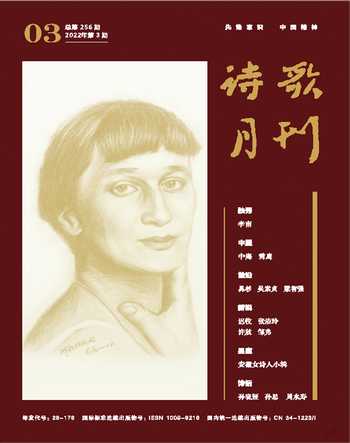以想象启示天地诗境
孙思
诗人赵丽宏始终遵循自己的本源之心,对诗歌葆有难得的素心与纯粹。他的诗集《变形》以想象的超越性,建构了生活与存在的诗意境地和精神深度。诗人将生活的表象作为切入口,向生活的纵深处探寻,让我们透过语言的显微镜,看到他蕴藏其中的生命智慧,他对人类命运的深切观照。
一
美是一种认识力的内心图像或内心视像。如何将这些图像或视像,放置到一个独特而奇异的视野中,需要诗人有超常的逸出现实的想象力。赵丽宏擅于将生活当成试金石,以此检验人存在的质感空间。如一堵普通的墙,通过诗人的“造境”,从原本的静态变成动态,就成了《墙的变体》。于是这堵墙因其不可复得,而呈现出更为深刻的意义。犹疑的视线/落在一堵墙上/墙,威严无声/坚定地挡住我的去路……
视线找到一个可叙述的载体“墙”后,随着镜头的推进,让读者的自我之门突然敞开,想象的画面在文字所描绘的空间里,不断向外伸展和扩充,直到抵达诗人所要表现的,微妙幽深的隐喻所在。
诗中的视线是时间中的个人式,墙是空间里的社会式,视线和墙作为一个整体活动,是个性与共性的结合。只有当视线与墙相遇,墙与人类情感发生联系,并象征着人类命运时,“墙”才具备了独创性。
想象活动是富有构成性的一种心理能力。借助想象构造出来的《倒立》一诗中,诗人想要表现的是人生的综合图景。在诗里,诗人把天地互相置换,形成对照,构成读者视觉上的反转。以“手脚倒错时/视野中/是一个翻转的世界”开始,充溢着现实事物的转化和新鲜感。接下来一种连续的虚幻而又可见的呈现,把读者引入到一个直观而又倒错的感觉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地成了天花板、行人变成了蝙蝠、天空变成了海洋、雨珠成了喷泉”。非此非彼而又亦此亦彼的有机交错状态,激活了读者的视角和运动觉;在充满情趣的同时,其肌质在自由不受限制的前提下,表现出富有意味的三维空间意境。让原本的一切在一种无界限的状态中,留下深长的回音。诗人以气使笔,独特的想象力和独创性在细节的画面结构里,获得科幻性效果,突破了原景的局限,给予我们的视觉冲击,如同一部3D电影。
二
赵丽宏的《牵线木偶》一诗,其审美知觉远比日常知觉更单纯。但正由于它的单纯性,也就更敏感,更具有意味。
诗人以绘画方式,采用各种不同线条来刻画这个“牵线木偶”。如齿状线“龇牙咧嘴、手舞足蹈、上蹿下跳”,细线条“想哭时被逼着笑、想躺时被牵着跳、想前行时被拉着倒退、想昂首时被迫磕头”,波状线“总想看看背后牵线人的模样、却怎么也无法回头”等等。这些线条交叉在一起,让这首诗的艺术感染力释放于我们对它的“看”之中。诗人是在情感的深刻性和普遍性中“看”,我们在诗人营造的语境里“看”。当诗人和读者的“看”重叠或相融时,它的悲剧式命运,使日常生活的种种,于瞬间呈现于我们知觉领域之内。
木偶和牵线人,前者的身不由己,后者的操控,通过诗人细致入微的描绘,两者的界限在诗中尖锐地呈现出来。一明一暗的并置,仿佛一个不调和的和弦,其隐喻空间表现到了极限,增强了命运感,又有一种强烈地迫使我们去看它的力量。
《母亲的书架》以故事形式开始,随着诗人的叙述和描绘,一个带着悬念和伏笔的书架,精致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接着诗人开始描述书架上书的种类。“第一本年轻的诗集、老气横秋的散文、让我返老还童的小说、那些疼痛变形的文字游戏”,这些在现今的诗人看来,已经是过去时,甚至还带着青涩的书,母亲却层层叠叠一本不少地放在书架上,尽管这些书中没有一本是诗人写给他母亲的:“我从没有想到为母亲而写/她却一本一本仔细地读/读得泪水涟涟/她从字里行间/知悉我心中所有的秘密/在她眼里,我依旧是/那个羞涩寡言的男孩/站在家门口/进退两难”。母亲无法走出对孩子的日牵夜挂,只能靠读儿子的书来解思念之渴。在母亲心里,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儿子说的话,她从这些话里仔细去辨别和了解儿子过得好不好。诗人让情感借助于书,让母爱占有一切时间的维度。诗的最后一节是第一节的重复,却是情感的叠加。或许诗人只有生活在别离中,才能让想象中的母爱衍生出无限。
把普通书架与母爱相勾连,其视角的独特显现,就像一部电影,抽离了时间,永不会枯萎和凋零地刻在我们的心壁上,使我们始终站在深沉地接纳和倾听的角度,一次次泪眼模糊。
三
赵丽宏的长诗《在天堂门口》设立了一个从天堂方向往尘世回望的视点,让一群哲人如同雕塑般,在诗中层层推进与展开,并引入越来越多的容量,直到进入一种更高的审视。
长诗一开始描述了哲人们在天堂门口,心领神会又各自寂寞的形态,由模糊渐显清晰。既设置了玄机,又蕴含了悬念。接下来以遐想展开画面,让原本存在于幽暗中的老聃,现身于光亮之中,并以反问的方式对老聃的“道”加以消解,“他俯下身子检视这一地宝石/竟然忘记了举手敲门/在他身后/蝴蝶正飞出庄子的梦境/在孔子的头顶翩跹/孔子在崎岖的路上颠簸/沿途留下气喘吁吁的叹息……”诗人以凝视式的想象,于当下穿越到庄子和孔子时代,将他们形成镜像后,到达深邃的层面。
第三节开始,诗人用一个“拽”字,戏剧性地引出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如同一部电影的开端,充满了动态感。紧接着师徒三人就 “觉醒和思考的能力”“人类的德行”“人世的‘理想国’”等,这些关乎人类的生存品格,进行了问和答。这些充满了忧患意识的问答,显示了诗人的智慧和洞识,也显示出其因痛而生的真切。
诗人让屈原在第四节现身。即便年代久远,他还是要扫除岁月沉沙,通过想象完成对屈原的再塑造与其对生命价值的求索,让屈原的精神不死,继续散发着恒久的光辉:“一个孤独的身影/在云岚雾气中踟蹰/屈原的登天之道/是一条不断的疑问之路/是一条无穷无尽的山水之路”。屈原的天问没有尽头,把他引出来,就是再续阔大时空中的叩问。
当“所有的天地之問/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时,屈原“仍带着一脸迷惘”来到天堂门口。人世间的痛在锥入屈原的灵魂时,也锥入到读者的心。
第五节开始,诗人接着往下追问但丁,这个时候诗人眼中的但丁与想象中的但丁发生对照,使反问产生了质疑、修正,直到自我的和解。结尾诗人将地狱和天堂互为转换后,剖开、弥合再剖开,直到在想象的空间里,完成对人类生命价值的求索,让所有的过去都重新生成为此刻。第六节紧接着对尼采进行了一系列的设问和反问,这些设问和反问是对人世、人心的考量,是一种关乎生命的根柢,关乎人的在世生存品格、人生幸福的古朴而高贵的智慧和洞识。
第七节从“吱呀一声微响/那扇紧锁的大门悄然开启/云雾缭绕/从门外涌入门内/又从门内飘向门外”到“为什么/在看似接近终极的时刻/你们进退两难/你们举步维艰”结束。瞬间想象形成的浪漫主义镜头,恰恰是重中之重,亦是点睛之笔。对他者的存在的反问,融进了更多的饱和度和渗透性。画面和意象的连缀,推动了最后的情节走向。
《在天堂门口》有着丰富的超现实意象和隐喻性。通过超越的想象,在彼岸性和此岸性之间的领域里,向人类启示了宇宙中的诗境。诗人赋予这首长诗的哲学深度以及思想构造力,让人间和虚设的天堂的二重性,变为存在的本质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