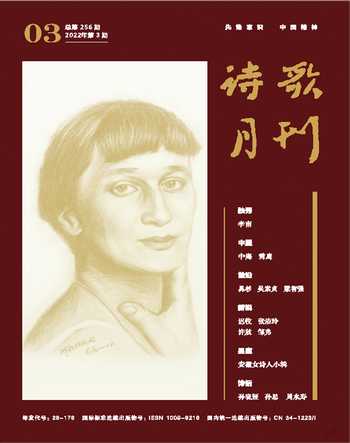访谈:给不安的灵魂一个满意的安放
中海 雪鹰
1.缘何写诗?
中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东北某地军校读书。学校大门口有一个邮局,里面摆满了各种报刊和书籍,在那里,我读到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埋下了诗歌的种子。几十年过去了,诗歌慢慢地成为自己身体一部分,如果不写,我就会感到焦虑。
雪鹰:如果说前半生爱诗、写诗,是我与诗结下的前世之缘,那么后半生的抒写与做诗歌传播,就是我的还愿之举。当诗歌在至暗中拯救了一个人的灵魂,并进而延长了肉体生存时间的时候,这种抒写便超越了它的普遍意义,就有了宗教般的对灵魂的统摄和抚慰作用。
2.你的诗观是什么?
中海:诗歌语言的炼金术,是给生活提炼出某种清新与生动的介质,也是给不安的灵魂一个满意的安放。诗歌并不一定要你产生共鸣,重要的是要冲破你的阅读屏障。
雪鹰:诗,必须是诗。写诗的人,一定要“把诗当诗”来写。
3.故乡和童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中海:我有多个故乡,但只有一个童年。童年即一个故乡,但每一首诗都是一个故乡。诗歌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可想而知。
雪鹰:就生命个体而言,一辈子不必离开故土谋生的人是幸福的,但也是不幸的。因为一个人一生身处故乡再看故乡,和远离故乡甚至永别故乡的人看故乡,体验与感悟的程度不可相提并论。事实上,故乡给予我的除了生命、亲情之外,苦难与痛感远比幸福与快乐要多。也许那是时代的因素,或者与自己的个性有关。但是,对于写作者来说,故乡与童年既是其创作的源头,更是取之不竭的源泉,它们会给我提供高純度、无须提炼的生命体验和情感记忆。
4.诗歌和时代有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与对应关系?
中海:清代画家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因此,诗歌也是与时俱进的,它一定具备时代特征。如果诗歌不能及时抵达现场,那诗歌本身价值就难以实现,这是诗歌的现代性之一。诗歌甚至可以超越时代,走在时代前面,预测未来。譬如后疫情时代的世界,诗歌该如何表达,这是卡林内斯库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特征。
雪鹰:诗歌来自于诗人的灵魂,诗人生存于时代之中,理论上说,没有完全脱离时代的诗。时代给予诗歌以素材甚至主题,诗歌回馈时代以美学承载和历史记录。我个人认为,诗与时代应该契合,诗人不该逃脱作为时代见证人的责任。同时,诗人还要对所处时代的诗艺探索、语言创新、理念提升付出努力,这也是诗人当仁不让的责任。
5.对于当下诗歌创作,你的困惑是什么?
中海:诗歌给世界的多样性以及事物的多义性提供了无限的可能,问题是这些可能的表达有几个人在读?有几个人读懂?
雪鹰:从当下汉语诗歌的现场,有人看到了繁荣,有人看到了浮躁,有人看到了希望,也有人一直悲观。有人把散文段子分行当作诗,有人钻进个人语言体系里喃喃自语,还有人毫无逻辑地堆砌词语。当下诗歌写作进入了貌似无序的农贸市场。诗歌的未来怎么走?方向在哪里?我个人认为,今天的汉语诗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浪淘沙的黄金时期,诗歌究竟有无标准,是否分行就是诗?不妨“让子弹飞一会”,时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是中年之后,如何写出自己满意的具有独特个性的新作?
6.经验和想象,哪一个更重要?
中海:经验的长度是一个个具象的累积,而经验的宽度才是想象力的延伸。诗歌需要一个长度和无限个宽度。没有经验和想象,诗歌将达不到某个高度。
雪鹰:只有经验的文字,往往因过实而降低诗性,而且会落入散文或记叙文的叙事套路。想象是诗的翅膀,但离开生命体验的想象,即使构成了诗,也必会轻飘无痕、缺少厚重。两者的结合最重要。
7.诗歌不能承受之轻,还是诗歌不能承受之重?
中海:诗歌小众与边缘化是一个事实,为什么?有人说诗歌之轻不能承受社会之重,这是对诗歌语言而言,既然诗歌语言有无限可能,为什么不能承受现实之重?是诗人出了问题,还是别的?很多诗人沉浸于“小我”,零度写作,在“大我”中写不出好诗歌,这是问题所在。但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这里的“轻”和“重”既对立又统一,一首关注现实的闪现人性光芒的好诗能在“轻”中承受“重”,能在“重”中携带“轻”。
雪鹰:诗歌的“无用之用”,决定了它“重”与“轻”的不同判断角度。
8.你心中好诗的标准是什么?
中海:诗歌很难用一把标尺衡量其好坏,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如上所述,我更倾向于诗歌语言的陌生化而营造出独特的意境。这个意境是回味于内心的一味中草药,它能调理肌体和内分泌。也就是说,一首诗短暂的停留,却留下永恒的痕迹。
雪鹰:诗,作为语言的艺术品,就像一个青花瓷,艺术的精美是全人类共同的感知。所以对当下追求“纯诗”写作的诗人,我是敬重的。但对于“道”的追求又是我一直放不下的。所以诗歌对现实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我对诗的个体评判。如果把宣传、教化与艺术性做为拔河的两个端点,我认为诗还应该往其纯艺术的一面努力靠近,或者说无限接近更好。诗就是诗,诗性第一,其他均可弃之。至于每首诗侧向于拔河中点的哪一面,将直接影响诗的品质与纯度。
9.从哪里可以找到崭新的汉语?
中海:砸碎一个散文化的词语,让其重新组合,就像桑塔格获得摄影艺术的前提是打碎世界并获得新的世界一样,这样获得的词语就是崭新的。当一个诗人接受了摧毁语言而创造另一种语言的诱惑,即便是无涵义,却体验了破镜重圆的魅力,诗人便沦陷于他创造的词语之中。
雪鹰:诗歌语言的新鲜、个性化,甚至陌生化的质地,不是因为诗人会生造一些词语,而是诗人用自己的天赋和语言技巧,打破语言常规,在想象、思考、词语的选择与对应,词序、语序、修辞的整合等过程中,旧词重构的结果。“崭新的汉语”靠诗人的手艺去打造,它原本是不存在的。
10.诗歌的功效是什么?
中海:诗歌不是用来疗伤的,有时候它甚至在你伤口上撒盐。对于诗人来说,诗歌是一个深渊,前方是什么不知道,唯有探索才能接近。对于读者来说,诗歌是近在眼前的诱惑,就是够不着。
雪鹰:诗歌既是精神产品,又有物质属性。它的功能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它在历史的长河里已经炼化为整个人类离不开的精神抚慰剂。对我个人而言,诗歌具有治愈和守望生命的功效。
11.你认为当下哪一类诗歌需要警惕或反对?
中海:诗歌的派系、类别、道路之争可能已经结束,用心写好每一首诗,维护诗歌的立场,这是当今诗人的首要任务。“渴望在措词和音韵上不断地花样翻新,与固执地恪守祖辈的语言同样是不健康的。”(艾略特语)我们要摒弃反复出现的某个词语在诗歌中充当主角,摒弃“抒情—表达—抒情”这样循环的伪诗文本。
雪鹰:当口语诗滑向了口水分行,当意象诗抛弃了逻辑关联,它们就都失去了诗性。两个极端写作都是我坚决反对的。而以散文、记叙文分行充诗的现象也很多,它们混在诗里隐蔽性最强、危害性最大,值得整个诗坛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