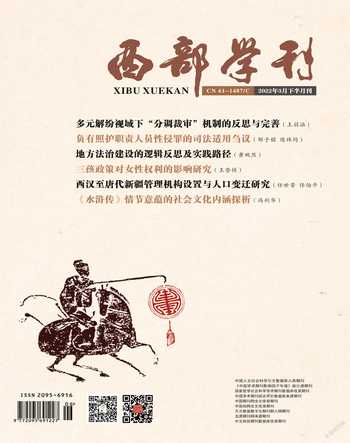《水浒传》情节意蕴的社会文化内涵探析
摘要:从逻辑层面看,《水浒传》情节分为“因”“果”两部分。佛教提出因果业报、积德赎罪、善恶转化等观念,影响小说创作思维与读者的文化心理。《水浒传》是在史料文献记载的基础上,结合“说话”、小说、杂剧等民间文艺发展而成,属世代累积型小说。故事叙述梁山好汉种下“恶因”却结出“善果”,情节看似矛盾对立,实则以“忠义”为纽带,演绎“恶业”的转化过程,统一于“因果相应”的内在逻辑,既体现佛文化对叙事思维的影响,又具劝善教化的深刻意蕴,契合民众普遍的文化心理。
关键词:《水浒传》;情节意蕴;因果;佛教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6-0169-04
《水浒传》的情节意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颇具影响力的有“农民起义”“诲盗”“为市井细民写心”等。不可否认,这些说法都注意到小说的部分内容,各有一定道理。但是,深究文本,无论哪种说法都很难通解全书,有以偏概全之嫌。文学批评必须立足于研究对象本身。我们应通过《水浒传》整体情节,结合社会文化,探析其深刻意蕴。
一、《水浒传》情节的“因”与“果”
《水浒传》洋洋洒洒百万字,情节波澜起伏,似乎千头万绪,但从逻辑层面看,可分为1—70回和71回至结尾两部分,前者为好汉们上梁山的过程,后者则是聚齐梁山后的发展与结局。
(一)因: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强盗
小说1—70回,写好汉们上梁山聚义的过程,是“前因”。108位好汉中,真正出身农民的,寥寥无几,谈得上“官逼民反”的也只有林冲那样的极少数,而真正行侠仗义的,似乎仅鲁达一人。杨雄、石秀、阮氏三兄弟、李逵等因犯罪而自愿上梁山,呼延灼、黄信、关胜等朝廷将领是被“赚上梁山”,而朱武、杨春、樊瑞等绿林强盗是合并到梁山,秦明、卢俊义、徐宁纯粹是被“害”上梁山。显然,这部分情节,既没有“官逼民反”的意旨,也并非歌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英雄。
不少好汉本身是山贼、江贼、盗贼、强贼,如朱武、陈达、杨春、邓龙、王英、燕顺、周通、李忠、吕方、郭盛、李俊、张顺、张横、孙二娘、张青、裴宣、樊瑞、穆春、穆弘、孔明、孔亮等。他们或在山林打家劫舍,“那伙客人抵当不住,转身便走,有那走得迟的,尽被搠死七八个,劫了车子财物,和着凯歌,慢慢地上山来”[1]53;或在江上谋财害命;或开黑店杀人越货。除了以盗的方式生存,他们还滥杀无辜,骚扰村庄,威胁百姓。例如,史进因王四酒后丢失书信,将其残杀;孔明、孔亮为争闲气,杀害上户一家;宋江为逼秦明上梁山,杀其一家及青州城大量百姓;石秀、杨雄将红杏出墙却罪不至死的潘巧云剥光衣服,挖出五脏六肺,又在祝家庄因偷鸡被发现而杀人放火。他们攻打高唐州、东平府、东昌府等,除了抢劫钱粮,还嗜血屠城,残忍得令人发指。即使被视作“官逼民反”典型的林冲,不仅欺软怕硬,殴打让他烘衣向火的庄客,还视人命如草芥,听朱贵说梁山盗贼杀人劫财的行径,表示认同,为交“投名状”①,毫不犹豫地在僻静路口伺机杀人。对此,刘再复感叹:“在他的潜意识里,也把普通人不当人,以无辜的人头作为自己的入门券也无妨。”[2]李逵、武松更是滥杀无辜的典型。李逵江州劫法场杀人无数,打祝家庄时杀害已投降的扈家,吃饭不给钱反而杀死店主韩伯当,为逼朱仝入伙,将四岁小孩头颅残忍劈成两半还能谈笑风生。武松杀潘金莲,为兄报仇,有孝悌之义,尚情有可原,但帮施恩打蒋门神,实乃“黑吃黑”,毫无正义可言,为报个人私仇,血溅鸳鸯楼,殺害张都监一家及玉兰,还可理解,但又残杀几位无辜妇女才心满意足,何其猥琐残忍。观其行径,他们嗜杀、虐杀、滥杀,绝非侠义英雄。有学者提出批评:“梁山‘好汉杀人讲的是千刀万剐,剥人皮,吃人肉,腕心肝做醒酒汤,还要讲究哪种吃法脆,哪种不脆,真是令人发指。”[3]细读小说,他们杀人放火,劫富但不济贫,更不是行侠仗义,伤害无数无辜生命,是为满足“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银”的物质欲望,可谓罪大恶极。
吴越《品水浒》认为:“‘好汉们绝不是英雄,而大都是灭绝人性的土匪强盗。”[4]林文山指出:“这本书‘诲盗,即教唆人们去当强盗。”[5]二者都肯定他们是“强盗”这一事实。王仕云《第五才子水浒序》云:“试问此百八人者,始而夺货,继而杀人,为王法所必诛,为天理所不贷,所谓‘忠义者如是,天下之人不尽为盗不止,岂作者之意哉!”[6]即作者本意就是视之为“盗”。小说开宗明义,写他们出自“伏魔之殿”,在回目中称“妖魔”,而洪太尉将其放出,是“惹灾”“酿祸胎”。从字里行间看,作者主观上也视其为“盗”。据冯汝常统计,作者“写水浒英雄‘落草的词语有35次,为‘盗的词语有30多次,称水浒好汉为‘贼人、‘贼首、‘强贼、‘反贼、‘贼寇等近300次”[7]。
毫不夸张地说,从1—70回情节看,他们就是罪孽深重的绿林强盗,走向聚义的路径,鲜血淋淋,令人发指。
(二)果:为国为民的忠义英雄
71回至结尾为《水浒传》的第二部分情节,乃“后果”。好汉们齐聚梁山,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以示愿为国建功。他们结交李师师、宿太尉,是为借助其力量促成招安,而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也只为扫除招安路上的障碍。
招安后,他们转变为遵纪守法、保卫国家之正规纪律队伍。梁山好汉为国前驱,奉诏破辽。在陈桥驿,小卒怒杀克扣酒肉的贪官,本情有可原,然擅自杀人违反法律,宋江只能挥泪令他自缢,“事不由我,当守法律。虽是你强气未灭,使不的旧时性格”[1]753。“强气”“旧时性格”指他们以前恣意妄为的强盗习气。宋江挥泪斩小卒,示痛改前非之决心。征辽中,好汉们英勇善战,兵打蓟州城,大战玉田县、智取文安县、攻打独鹿山,展示出强大的战斗力,一举杀入辽都幽州,使其国主请罪纳降,为国家安全做出巨大贡献。
其后,梁山队伍主动请求打击反贼,与方腊集团在润州城、毗陵郡、宁海军、乌龙岭、清溪涧等地大战。经过惨烈战斗,秦明、徐宁、董平等59名将领阵亡,林冲、杨志、张横等10名将领病故,鲁智深坐化,武松、公孙胜出家,燕青、李俊、童威、童猛辞官,除去安道全、皇甫端、金大坚等5名留京偏将,只剩下宋江、吴用、关胜等27员,损兵折将,代价十分沉重。好汉们十之七八战死沙场,班师回朝时,宋徽宗见了,也伤悼不已。他们出生入死,是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百姓生活安宁的忠义之举。朝廷降下圣旨,对殁于王事者,授予名爵,分别封为忠武郎、结义郎,而生还且愿为官的好汉,都授予官职,重金赏赐。gzslib202204042106毫无疑问,第二部分情节中,梁山好汉们聚义后,接受朝廷招安,征辽、征方腊,系为国为民的忠义英雄。
二、《水浒传》的情节因果与佛文化
表面上看,《水浒传》两部分情节意蕴,似乎是嗜血强盗与忠义英雄的价值对立,且前种“恶因”,后结“善果”,逻辑上似乎也不统一。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指出:“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那末,情节则是‘小说的逻辑面。它是显示生活、历史和自然的因果律的载体。”[8]87“因果”即小说事理逻辑的内在联系,乃“事之始终”,是情节的主宰。中国古代小说叙述感性生动的故事,通过情节的逻辑发展来揭示某种因果,意蕴理性深刻。我们应该透过“基本面”,结合社会文化,探析《水浒传》情节“因果”的深层意蕴。
(一)佛文化“因果”观念的影响
虽先秦儒道有因果思想萌芽,但明确的“因果”观源自佛文化。佛教提出,“因”指“因缘”,即产生结果的原因,“果”即前因之下的“果报”,因果之业,决定祸福贫贱、累劫轮回。《涅槃经游意》肯定因果在相应条件下的转化,形成因果业报、积德赎罪、善恶转化等观念。佛教源于印度,两汉时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時迅速传播。文人们阅读佛典几乎成了社会风气,多因果之谈。萧子显《南齐书》载有佛教思想的“灵应果报”。张煜指出:“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可以说已基本完成其中国化历程,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份。”[9]这说明,经过长期侵染,佛教融入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文化。
从创作的层面看,因果观对中国古代小说有极大影响。刘斌认为:“中国小说初具规模,究其渊源,一是先秦文化,第二就是佛学。”[10]确实如此。自魏晋南北朝,中国古代小说便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志怪小说的产生,便是有力的明证。孙昌武云:“长篇小说的兴盛,也都借鉴了佛传与大乘经等佛典叙事作品的写作方法。”[11]这揭示出佛文化对小说创作技巧的启发。因果观念深刻影响小说创作思维。刘书成指出,中国古代小说“结构上因果完整、内容上突出教化、情节上真幻交织,这些特点恰是在佛教影响下产生的”[12]。对此,吴士余云:“情节组合和叙述的因果序列,它是显示故事自身蕴含的内涵及其价值的审美化过程。”[8]87无论是“因果完整”,“因果序列”,都看到情节建构的因果逻辑。吴士余还认为:“自佛学因果说渗入小说思维始,特别是佛教的唱经故事和变文直接充实、丰富小说题材,小说家的叙事思维意识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层次。”[8]89可见,因果观渗透小说创作思维,使作家在叙事上转为借助情节来表达意蕴。
从接受的层面看,因果业报、善恶转化等观念在民间影响深远,民众普遍有善有善报、惩恶扬善、弃恶从善等“善恶昭彰”的心理,正如蒋述卓所言:“善恶报应成为民众的一种普遍心理时,它实际就是一种社会客观需求,深深掣肘着作品的创作。有时候作者不得不适应观众的这种悲剧补偿心理的需要。”[13]。因此,为迎合大众审美期待,明代白话小说往往有“因果昭彰”的故事模式。
(二)《水浒传》情节:因果相应
1.《水浒传》:世代累积型小说
《水浒传》绝非一人一时之独立原创作品,是在一定史实的基础上,结合“说话”、故事、杂剧等民间文艺发展而成,当属世代累积型小说。
就史实而言,《东都事略》载:“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14]《宋史》《泊宅编》《十朝纲要》的记载大致相同,称宋江为“盗”“贼”“寇”,描述其活动范围在北方一带,战斗能力极强,官军只能避其锋芒。这是《水浒传》前部分情节构建的源头,而所载其与官军对抗,被朝廷招降,最后受命征讨方腊以赎前罪的结局,则成为小说后部分情节的源头。
其后,宋江故事在街谈巷语中流传。“说话”、小说、杂剧等民间文艺对其情节不断増饰。罗烨《醉翁谈录》载,“说话”中有《戴嗣宗》《花和尚》《石头孙立》《青面兽》《武行者》等故事。话本小说《大宋宣和遗事》虚构出杨志卖刀、太行山落草、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张叔夜招降、征讨方腊等故事。它与龚开《三十六人赞》、陆友《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皆叙述有36名好汉,是《水浒传》天罡星的人物来源。元杂剧中出现大量水浒戏,涉及到宋江、黑旋风、燕青、鲁智深等。童天瓮《甕天脞语》载宋江为求招安,潜入京师名妓李师师家,提到山东烟水寨、108人,则是梁山泊与好汉总人数的来源。显然,民间文艺的虚构、敷演,使水浒故事情节日益丰富。
胡适指出:“《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到明朝中叶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15]所谓“结晶”,即该书是宋代至明朝传播的水浒故事的总汇与加工,无论作者对故事是进行“编次”还是“纂修”,都绝非完全独立原创。在其漫长的传承与成书过程中,既有民间说话艺人、戏剧艺人为了商业利润依根据接受者心理的不断虚饰,又有受众对故事的谈论、加工。因此,《水浒传》的故事情节,既借鉴了史料文献的记载,又整合了相关民间传说、话本、戏剧的内容,凝聚民间集体智慧,反映大众审美心理。
2.“因果相应”的内在逻辑
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汇总、加工世代累积的水浒故事,将因果观巧妙融入《水浒传》两部分情节,演绎好汉们由罪恶强盗转变为悲情英雄的过程,契合读者普遍的文化心理。综观全书,聚义之前,好汉们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犯下血腥大罪,是“因”;聚义后,归顺朝廷,为国捐躯,是洗刷罪孽、转为忠义英雄的历程,即“果”。两部分情节以“忠义”为纽带,叙述“恶业”的转化过程。
虽“忠义”源自儒家,但从小说情节的“因果律”看,好汉们的命运发展,最后都报应昭彰,明显是佛文化“因果相应”“积德赎罪”等观念的反映。聚义后,宋江意识到他们火烧水溺,杀害无数无辜生命,只有通过“忠义”来赎罪。他建罗天大醮,表达尽忠报国、禳谢前罪之意。好汉们亦有所醒悟,皆在醮坛下恳求上天,拜求报应。从此,他们痛改前非,不再滥杀无辜,只洗劫欺压良善、残害百姓的暴富户,是真正意义上的替天行道。从好汉们的结局看,为国为民,死而后已,是其对前罪的“自赎”。杀人放火、罪孽深重的好汉,结局几乎都是非死即伤,相当悲惨。例如,燕顺、周通、王英等战死沙场,宋江、李逵被毒死,吴用、花荣自尽而亡;而林冲风瘫,武松断臂老去,则是生不如死,无比凄凉。罪孽较少的好汉,得以全寿而终,如公孙胜辞官云游,阮小七打渔为生,还有燕青、柴进、宋清等十八人,或隐逸,或经商,或务农。没犯罪孽而上山的部分好汉,安道全、皇甫端、金大坚、肖让、乐和,仍在朝廷任职,结局相对较好。可见,善恶到头皆有报。gzslib202204042106虽然金圣叹盛赞前部分情节,将《水浒传》“腰斩”,但是,如果小说真就此结束,那么,毫无疑问,就是一部“诲盗”之书,思想意蕴极其低劣。后部分情节,他们通过征虏平寇、保境安民之“大善”,使人生价值得以升华。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将嗜血残忍、罪大恶极的强盗转化为可歌可泣的忠义英雄。两部分统一于“因果相应”的内在逻辑,寓有弃恶从善的教化意蕴。
结语
毋庸置疑,佛文化的因果观念影响《水浒传》情节构建的思维机制。小说通过波澜起伏的故事情節,叙述好汉们由绿林强盗转化为忠义英雄的惊心动魄过程,既体现叙事思维的深度,又具劝善教化的深刻意蕴,契合民众普遍的文化心理。因此,成书后,它受大众读者普遍喜好,获得良好接受效应,在社会掀起“水浒热”。注释:
①“投名状”:投名状在古代边缘群体用于增强团体内聚力,表达对个人、组织的忠心,有强烈的人生依附性和反社会倾向,通常意思是以非法行为做保证(投名状)而加入非法团体。投名状是加入非法团体的表示忠心的保证书。
参考文献:
[1]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刘再复.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M].上海:三联书店,2012:43.
[3]何等浩,宣杰.《水浒传》的思想性与逻辑性质疑[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2).
[4]吴越.品水浒[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2.
[5]林文山.水浒简评[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1.
[6]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7:40.
[7]冯汝常.强盗抑或忠义:一个无解的悖论——关于《水浒传》主题之争[J].北方论丛,2013(6).
[8]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M].上海:三联书店,2000.
[9]张煜.《水浒传》与佛教[J].明清小说研究,2006(4).
[10]刘斌.试论佛学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J].五台山研究,1991(1).
[11]孙昌武.文坛佛影[M].北京:中华书局,2001:8.
[12]刘书成.论佛教文化影响下古代小说的三大功能[J].社科纵横,2000(1).
[13]蒋述卓.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5).
[14]孔令境.中国小说史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1.
[15]张庆善.胡适、鲁迅解读《水浒传》[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7.
作者简介:冯利华(1976—),女,汉族,四川内江人,文学博士,内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