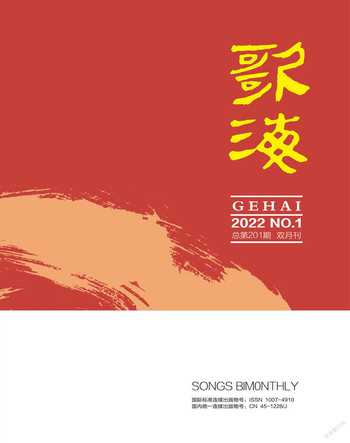乐舞为谁:从傣那“出洼”仪式看“嘎秧”在民俗展演中的属性意义
段蕴格 申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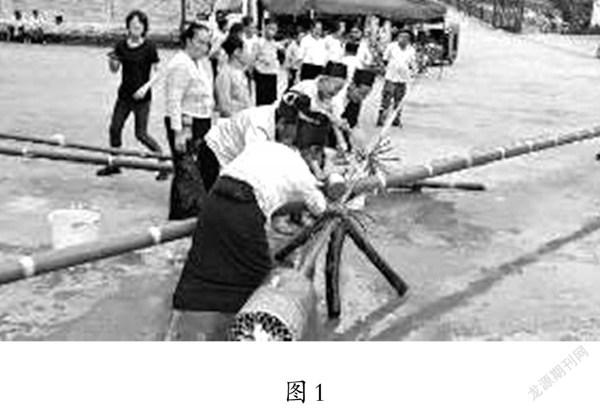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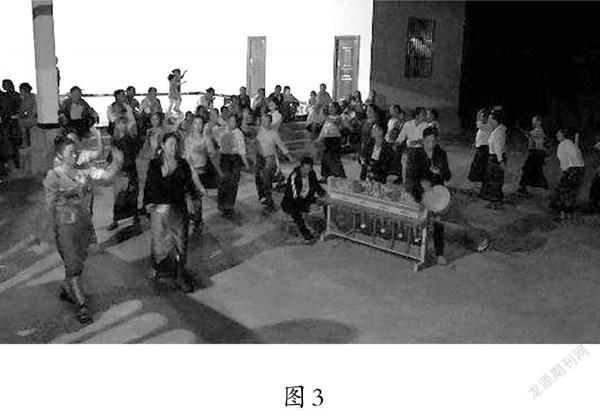
[摘 要]傣族有句俗语,“谷子黄,傣家狂”,揭示了傣家人重农耕的思想,“出洼”仪式正是存身于这种思想之中,根据自身表述风格与环境特征塑造出的具有民族特性的节庆仪式。“嘎秧”作为仪式中的活态传承,以其自身独特的肢体语汇,结合象脚鼓乐的声响,在双向交互中隐喻傣族群体深刻的情感内涵。
[关键词]傣那;出洼;嘎秧;民俗展演
傣族社区具有文本意义的“出洼”仪式,仪式空间中表情達意的知识系统承载着村民集体观念与情感表达的张力场。正如谢勒梅在《声音景观:探索变化中的世界音乐》中所表述,地方声音景观凝聚着一方人的意识形态,在包容与开放的时代观念当中,融入政治立场,使地方音乐文化的展演地点与民生观念逐渐发生改变,深藏于乡村社会的声音及肢体语言有了新的表意内容,引发我们思考如何跳出形态、行为和观念的具象限定以及潜入现象的深层提取,领悟主宰现象的核心本质,重建不同乐体文本间的逻辑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传统民俗得以恢复,承载着一代人悲欢离合的民俗音声逐渐走进百姓生活,由此引发局外人探知真实,解释民俗文化在不同人群当中营造的耳听感受,使具有“原生性”的风俗文化诉诸执文者最为深沉的心灵体悟,由此区别职业化耳听习惯。
一、“出洼”:关于民间信仰的当代解读
民间节庆仪式可以被看作国家建构中一项传统的发明,其意义在于通过汲取传统节日中符合国家话语的叙事表达,形成传统仪式的稳定体系,仪式中既反映着过去关系,还调节国家与当下社会礼仪建构。实际上,这种稳定性的框架并非固化文本,从个人和集体成就的叙述表达中往往体现出多义的解释。例如,傣族的泼水节在日常傣语中并没有“泼水节”的具体表达,对于傣族村民来说,这个节日是他们新年更始的节点,主要包括:拜寨神、堆沙、赕佛、浴佛、泼水、对舞等(各地有所出入),亦称“浴佛节”,傣语为“桑勘比迈”或“楞贺桑勘”(意为六月新年)。据村寨人表述,传统中的泼水节时间并非完全固定,而是按照科学的天文历法推算。这仅仅是节日的时间,我们所观测的仪式乐舞在仪式过程中、在现实中又有怎样的变迁,如何沟通研究对象成为解读民俗文本的重要环节?不可否认,在强调传统的年代,证实文化身份、与祖先保持连续性逐渐成为认知“在地性”的探究手段,但由于时间的流逝、空间的迁移,各区域间文化的传统与社会进程的话语表述有着一定出入,解读信仰往往还需要采集多种声音进行比较和引申,以符合民间文本化循序渐进的过程。
中国境内傣族音乐文化圈,主要以西双版纳傣泐方言区和德宏傣那方言区为主,二者虽然同属于傣族,但有着一定区别。彼此之间民族语言不同、文字不同、宗教教派不同,导致二者在音乐的表现形式以及思想内涵上有着相对的差异性。公元2世纪形成的南方丝绸之路,从永昌郡经德宏进入缅甸和印度,德宏地区在流入大量汉族商人的同时呈现出的新思想,较多地体现在德宏地区的文学创编当中,舞蹈音乐成为其思想的传播媒介。西双版纳傣泐族群更重佛教,由于与汉族接通较晚,其世俗音乐中大量暗含佛教信仰且趋于主要地位。以“章哈”为例,民族学调查资料显示,早期章哈歌手曾是傣族宗教仪式中的重要角色,由女章哈唱歌献神,村寨内凡有祭勐和祭寨仪式,按传统要求必须是由未婚女性章哈献唱,笔者认为或许浓厚的规约条件受到南传佛教和当地多神信仰影响。相比之下,德宏地区的傣族,早在汉代就与内地建立了密切的往来,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并由此产生大量世俗的音乐。在商品经济下逐渐衍生出不同于西双版纳傣泐族群的平民思想,大多呈现傣族人对于婚恋思想的意识觉醒并存在于大量叙事体裁当中,以当地著名叙事长诗《线秀》和《娥并与桑洛》为主,在此不做赘述,但它作为一种思想潮流使得傣那族群音乐形态趋于世俗化展现。
芒市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州府和潞西市市府所在地,当地傣语称之为“勐焕”(mónghuán),我们此次采访的艺人肖喊宝生活在德宏州府芒市丙茂村下八个自然村中的一个村小组,全乡辖丙茂、芒广、芒棒、筠竹园、芹菜塘5个村委会,下分有51个自然村66个村小组。芒市周边的傣族村寨多分布在河谷坝区。在这种地理环境下,傣族人形成社区管理,制度之下的体现是,村民不杂居,纯民族定居在一起,目的是维护寨子内的团结,在日常参加公共事务时,通常以群体划分出固定的集体组别。例如,部分资料显示,盈江地区村寨分老年组、中年组(包括妇女组)和青年组等。典型的是老年组,村寨中老年人的资历、地位较高,多负责管理传统祭祀和祭拜寨神的传承事务,在传统节日时传达流程要求,一定程度上起到对传统习俗的保护和管理作用。妇女组负责寨子里的生活风俗,每个寨子有自己的寨规,触犯寨规会受到一定处罚,妇女担任维护寨风的角色。实际上,傣族寨子通过这样一种划分进行社区内管理,来规约、稳定村民的日常行为,映射出傣族人对于族群认同下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理念:傣族全民信仰南传佛教,同时也有着自己的原始信仰和族群管理方式,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俗中艺术体裁的变迁。作为拥有共同信仰的民族,其集体活动与佛事活动在社区管理下分工时并非割裂,两者之间仍处于相辅相成的关系,村寨的意义逐渐延伸成社区文化的一部分。
人类学对于仪式研究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既不否认仪式的具体过程和具体情境,也不否认仪式的历史性进展或人与神圣力量的交流。尤其对于观测者而言,略显模糊的仪式过程给予更宽泛的解释,通过仪式与日常活动的两分镜像,从仪式与日常生产生活的相互映照中寻求解释,毕竟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仪式都一定要有与凡俗世界隔离开来的神圣场合和特殊时空建立联系,才可显示其存在的意义。因此,笔者在观测“出洼”仪式过程和“嘎秧”乐舞在仪式中的肢体语汇时,思考拥有族群独特历史文化背景下,观望社区群体是作为文化的传递者还是所属文化的受礼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思考局内人在进行民俗仪式时是否在向凡俗生活不断延伸和扩大,此时的乐舞律动发生怎样的变化。
二、“出洼”中的场景标识解读
芒茂佛寺至今还保留着古老榫卯结构的建筑,整个建筑一体建成,没有一颗钉子,距今有50多年历史。作为生活空间,它涵化寨内人于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寄托;而作为文化空间,奘房处于民俗仪式的核心位置,地处平坦,有些村寨的奘房旁可见粗大的神树,因此,奘房作为傣家人节日传统的凝练标识,在村民的心理空间上,任何建筑都难以企及。芒茂村的“出洼”仪式,主要由“竖寨桩”“出洼诵经”“对歌”“干朵”“绕奘房”“嘎秧”构成。
(一)“豎寨桩”释义
民间的每一类仪式都有自己的表达内涵和情感输出核心。正是这种“核心”的心理象征,“出洼”仪式的首要环节就是围绕“竖寨桩”完成的。制作过程中,村民将竹篾编成菠萝状并固定在竹竿的一端,“菠萝”往下有竹编而成的三层“叶子”(傣族人喜三),往上还有纸板做成的“镰刀”,黏有三色彩条。寨桩分两类,傣语称为“bohuan”,有团结幡、丰收幡、招魂幡等,一种是已入奘房修行的老人所供养,另一种是年轻人为了积功德而供养。无论哪种类型的寨桩都高高矗立,体现出村民对天地、自然、超自然力量所怀有的敬畏之情。或许“竖寨桩”可理解为汉族民间的“社树”,意味着由此通天接地,祈求神灵降福保安康。
晚上八点左右,在“helon”(傣那支系民众对社区拥有佛学知识的精神领袖的尊称)的率领下,妇女在佛寺内跪拜诵经,男人则坐在外面聊天休闲。诵经仪式结束后,“helon”作为村寨的权威人物,开始在象脚鼓的皮面上粘米团,村民把这样的过程叫作“喂鼓”。据村民介绍,从心理象征来看,只有鼓吃饱了,敲出的声音才好听、才能满足神灵。而作为现实功能,“喂鼓”的目的则是使象脚鼓的音色与铓锣的音色相和,与镲的声音高度匹配,回响声越大越好。
在喂鼓的同时,人们已将搭建寨桩的材料用清水洗净,当地人金小团说通过水的洁净表达虔诚。(见图1)此时人们簇拥在一起,准备合力完成“竖寨桩”的过程,夜空中伴着象脚鼓穿透力极强的声音,音响与静穆的佛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人群呼喊的热烈气氛下,妇女争先恐后地把各式供品拴在寨桩上,伴着鼓点、欢呼声与鞭炮声,寨桩缓缓地被村民齐心协力地竖立起来,也把人们祈求获得庇佑的心愿送往天际。紧接着,人们用无数蜡烛插在寨桩四周祷告,并不时将各式米花撒向火堆,鞭炮声响起,不停地敲奏象脚鼓。看到村里的妇女跪拜在寨桩前燃烛祷告,将上千根蜡烛在黑夜中铺成一条光路时,“竖寨桩”仪式已在往复循环的回响中完成。片刻之后,人们聚集在奘房大殿前的广场上进行娱乐性质的“嘎秧”,同时也构成“出洼”仪式中的首次集体性聚会,以此仪式完成与超自然对象的交流。在这样的空间,村民既是音响符号的表演者与传达者,也是音响符号的接受者与解释者。
(二)“干朵节”上的社会身份释义
“干朵节”是傣那支系的人们在庆祝丰收的仪式上,祈求得到佛祖庇佑的节日。它标志着傣家人的信仰和对于所属传统的眷恋,展现的是地方性文化“乐教”与“礼俗”的互动关系,再现乡村文化别样的声音景观。
据村民介绍,作为村寨重要的习俗,每当这样的日子来临,在外生活的人们都要专程回来求得佛祖的庇护。当日,身着节日盛装的年轻男女纷纷聚集在奘房的楼下,人们用母语交流各自的见闻。楼上传来老人祈福的诵唱,显现出独有的社区身份: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才能进入佛寺面对佛像进行祭拜。奘房的楼下,年轻男子身挎象脚鼓,通过正拍、闷拍、指拍等手法的变换,在铜钹音色的调整下奏出各种效果的鼓点,率领“嘎秧”的队伍不断变换着肢体语汇。现场的领舞者金小意介绍:当“嘎光”场景达到热烈时,鼓手还会加入拳、肘、脚的并用以掀起仪式情绪的高潮,此时,“嘎秧”的人群也会以吆喝与“嘎伴光”(象脚鼓舞)热烈的身体语汇构成呼应,使人们的情绪获得充分的释放。(见图2)
在这种特殊的民俗场景中,一切被赋予某种审美价值的音响或许都可以称为音乐。无论是简单的节拍敲击或是人们的吆喝声、笑声,无论是人们的诵经之声还是双脚踏地的音响,这种由他们自己创造的音响在群体的心灵中所产生的不同寻常的心理感召,是在城市中难以体验的。我们以人类学的立场去面对它们时,方才领会音乐人类学对音声作用做出的一个基本判断:声音的表达是人们形成群体认同的重要条件,是人们达成族群情感沟通的社会契约。许多年轻人表示,他们作为社会成员,都不会拒绝现代的物质消费,为了生存的需要,他们也要追求时尚的产品、用普通话甚至英语开展社交活动。但当他们回归家乡,身着民族服装,使用母语交流,咒声“嘎秧”的律动会使他们对族群的认同感油然而生。村里的女孩子说越来越喜欢身上的傣装,但是小时候很不喜欢。或许,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的当下,他们将是自己族群传统习俗最后的体验者与诀别者。
三、集体记忆与文化展示:岁时节日下的“嘎秧”
关注民间仪式的同时,下意识会反应表述对象的“民俗性”,继而寻找问题,在不确定的个案形态中寻找自我文化研究不断延展的可能性。从“嘎秧”的生存空间上看,其有着强大的族群认同惯性,人们从语言习俗、宗教信仰、民族服饰再到自己的鼓舞音声谱系,都形成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记忆。同其他地区一样,民俗下的信仰系统所仰视的神灵与生活息息相关。
(一)“嘎秧”的肢体表达与鼓语的心理接受
民间中的“嘎秧”以节日的方式传承,作为生活的重要载体,其肢体表达的身体内涵往往需要联系人们的心理感受和佛教信仰观念。据寨子里的老人说,傣族先民迁移到这里来,就已经有了“嘎秧”,源自生活和劳作过程。笔者认为德宏傣族的“嘎秧”,还必须追溯到古老的图腾祭祀礼仪及母系民族农耕文化。傣族属于百越族系,农耕文化继承和发展了母体民族以稻作为主的传统,继而形成典型的稻作文化模式。人们将对这种生存方式的期盼化作一种外在的仪式行为,以舞蹈和鼓声的形式与神灵对话,象脚鼓作为沟通人神的媒介,具有“使大地丰收”的功能,这种乐舞一体超自然的方式成为傣族村民延续至今用来祈福的手段。
佛教是傣族人民信仰的宗教,且对人们的生活起着支配作用。结婚、节日庆典、建房、进新房、祭祀、丧葬等仪式活动中,祭拜供奉时,全体族群在德高望重的老人或者“huoluo”的诵经持咒声中磕头祭拜,以祈祷村富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六畜兴旺,“嘎秧”作为佛事活动载体,营造着群体的心理认同和心理接受。
“嘎秧”一词为傣语,“嘎”是傣家最古老的语言,“嘎”在傣语中,意为围圈跳舞。在民间的几套组合中仍可看到,妇女基本保持上直立、下屈伸的动律方式,当地村民说,“倘若没有穿傣装很难跳”。实际上,缅甸掸族舞蹈下肢律动同样具有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在勾脚的脚型基础上,脚后跟用力向后向上踢,重手型和腿部膝盖的幅度。1笔者结合当地人的说法,傣族舞蹈服饰受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影响,傣族妇女多为直筒长裙,上衣包裹合身,男性也有穿直筒笼基的习俗,或可推认其舞姿与服饰的关联。笔者认为,民间“嘎秧”作为现代视域中的舞蹈形态,其共性特征与区域个性特点或可与鼓语指向和傣族自身的服饰特点有细微联系。
“干朵节”当日可观测到边舞蹈边击鼓的表演形式。不可否认,象脚鼓舞的声音对于肢体和人群气氛实在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在芒市和瑞丽一带,傣族象脚鼓极为突出,这一地区使用长象脚鼓,操作时不但可利用掌、拳、肘、膝、头击打鼓,又可运用舞蹈动作表达舞者的内心情感;同时配合“嘎秧”,给予舞蹈不同的鼓点声音,发出不同组合及情绪的信号。可以看出,人们通过象脚鼓与“嘎秧”之间的配合,往往可以宣泄情绪,抒发感情。根据当地人解释,这类活动在“干朵节”中往往寓意吉祥。村里人认为这种吉祥与雨水相关,如果当天下雨,人们会认为是得到庇护的象征。在民间故事里,傣家人认为金鹭鸶鸟是佛的化身,为傣族人铲除害虫,而“嘎秧”正是伴随长期农耕思想而逐步演变发展起来的,与百越母体农耕文化、原始信仰和佛教信仰、自然环境下的心理体感密不可分,这些因素为“嘎秧”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
(二)“嘎秧”的民俗历史意义
根据德宏历史沿革分析,将德宏傣族“嘎秧”文化生态变迁历程进行整理、归纳,其总体可分为古“勐达光”(哀牢国)雏形期、中华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现代繁荣发展时期。最初在宫廷活动上,庆祝傣历新年(大傣历)时,傣语为“比傣”,始于公元前95年“勐达光”王国时期,公元前94年为纪元元年。傣族宫廷舞表演的动作姿态,讲究形神兼备、柔中带刚、抑扬顿挫等,与后来出现的“嘎秧舞”动作姿态具有相似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时期是“嘎秧舞”的改革发展期。相关资料显示,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潞西(现芒市),德宏解放,經济逐渐发展。“嘎秧舞”活动更为凸显宗教仪式特征,同时与农耕文化相依附,体现于舞蹈的肢体动作当中。现如今的“嘎秧舞”以身体活动为基本手段,从动作的结构特征来看,男女互相交错,一般排成四列纵队,人数多则不限,少则数十人,手势与脚部的踢踏协调配合,动作变换要跟上鼓、铓、镲乐律的变化,动作节奏与乐律要保持一致。左右变化,进退逐序,个人动作与整体队伍要保持高度的整齐,打跳时间较久。
芒茂村“出洼”仪式中的“嘎秧”,与傣族所有户外展演的乐舞一样,作为一种在象脚鼓、镲、排铓三件套乐器伴奏下完成的风俗性乐舞,其乐队构成傣那语称为“guangmangguangxiang”,即敲锣打鼓之意,这样的构成几乎成为云南所有傣族地区民间乐舞表演的“标配”,成为傣族文化的共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是象脚鼓乐队节奏的文化内涵,构建了仪式心理的有效性。
歌舞团的朱宽涵老师说,最初“嘎秧舞”从劳动生活中产生,例如起步舞、采花舞、泼水舞、纺车舞等,每一类舞蹈都有固定的手型。后经原州歌舞团卫明礼等几位老师编创,20世纪80年代开始普及,传到各乡镇,当村子里有喜庆事或者岁时节日时,大家就会聚在一起“嘎秧”。民间“嘎秧”的特点在于:虽然动作简单,但是很整齐,注重人群自发感受,伴有呼喊声。村委会的金小团介绍说,这些舞步有些为耕作的动作,有些是除草的动作,还有一些是收获的动作,一般转两圈更换一次动作,到现在发展有二十多套,但都不会跳完了,跳完时间至少要半天多,每次更换动作由前面的领队根据圈数更换下一组动作,每组动作都有自己的表意内容。
(三)“嘎秧”的身体律动释义
以上所述的几种舞类可以看作舞态在民俗文化中的显现样式,舞态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通过肢体动作来表达情感的艺术形式。尤其对于一些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而言,许多历史文化被保留在肢体律动的形式中,无声地呈现着民族发展进程中的各种文化信息。
“干朵节”中的“嘎秧”,象脚舞的鼓点韵律对于“嘎秧”不仅仅是伴奏,它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调整舞步和舞速的功能。其节奏一般为中速行进,村中的“嘎秧”不像城市里的那样,往往需要适应各个年龄段,营造群体性特征,因此节奏原则以平稳为主,突出节奏变换时,领队内往往会有一个总指挥,等到“嘎秧”第三拍时在一旁喊“日哇喔喂”的口令,领头人根据下一组的律动拉长或缩短或根据喊的人的速度调整动作,打象脚鼓的人和打镲的人会换成下一个动作的节拍。以此类推之后的动作,我们或可在这种变化的理念中感觉到,乐与舞、肢体和音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组织关系,继而调整着男女在队中的协调与配合。
“嘎秧”在男女分工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的调整和规定,在各自的分工中呈现出傣家人的民俗意蕴。“嘎秧”在过去原本为男女配对而跳,男子在外圈,女子在内圈。但由于新农村建设下生产关系的变动,男子大多外出做工,村子里的男子很少会跳,因此调整为女性为主的“嘎秧”。然而不管如何调整,傣族的“嘎秧”都离不开其生存环境,其作为岁时节日下的舞蹈,不完全是意识形态所支配的肢体运动,肢体表现出的形态与表情达意的内涵相辅相成。以采花舞为例,在跳的过程中有采花的样子,可以构想为生活中妇女采花的样子与神态,其手势和神态的交互(舞体)构成舞蹈的语言,由舞体发出,同时又被舞体感知,所包含的意美之感体现的是人类的共识部分。
然而,在呈现过程中,“嘎秧”作为肢体语言体现出的舞蹈语言,虽没有舞词做衬托,但在岁时节日与乡村仪式中所营造的生态环境以及“干朵节”里的诵经声,包括人们的说话嬉笑声,已经是息息相关。女子跳舞时不固定于舞蹈动作中,交谈互动随处可见,使我们在观测“嘎秧”与环境关系的同时,也不由自主地关注民俗文化属性下的独有舞汇。此时的舞蹈语汇不再是对自身形态的具体切割,而是加以提炼的表意审美单位,在文化差异中逐渐凸显出自身的人文内涵和价值体系。要认知这样一种舞蹈,必须将外部形态与外部环境同局内人表情达意的内涵建构于一体,才能知晓局内人对于嘎秧的热爱。
(四)“嘎秧”在时空下的属性变化
“嘎秧”作为民俗中音声和舞蹈组合而成的产物,同时还是由时间和空间共同塑造而成的“身体民俗”,它强调在具体的文化场景中,隐藏在身体行为背后的特性和意义,继而体现出这种民俗乐舞在身体上经过日常生活和民俗活动沉淀下来的传统与记忆。1依托我们所看到的“嘎秧”,其原生态下的意向性表达来源于乡村生态环境,然而城市中的人理解乡村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就中国的民间村落结构和民俗文化而言,节气时令、伦理道德、礼法宗教等思想观念以及其中显现的图腾崇拜、祭祀祖先等内容皆是民俗文化中的独特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群观念中的精神和思想渐渐沉淀于本民族的传统仪式和活动中,逐渐被赋予文化符号的印记。村民肖喊宝和金小团口中的“嘎秧”,表现的便是在这样一种时间性和空间性的集合下,存身于民间仪式的场景与时段当中,并以一种“文化认同的集体观念”表达出的艺术形式和民俗中的生活范畴。在民间,它在不同的地点体现不同的表述意向,例如,在“出洼”仪式“干朵节”和泼水中,如果奘房的位置在院场的中间,人们一定选择绕奘房跳,此时村中的男性和女性分列,动作上维持基本划一的状态,人们集中在一起发出吼声,这种仪式规约更多侧重于人们对于节日的心理表达。(见图3)
村民金小意说,“干朵节”前一个月,村里不熟悉“嘎秧”的女性会为节日而排练,延续到“出洼”那一天。我们所看到的“嘎秧”配合,实际上是傣族人长期潜移默化下的過程渗透,只是民间“嘎秧”在节日没有严格的动作规范,其更多的文化内涵在地点和过程的集合,或许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歌舞音声并非以审美为最终目的,歌之舞之的族群趋同,强调的是过程里载负的思想和道德内容,由此达到转运的功用。2
作为傣族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嘎秧”丰富着人们的情感表达,增添文化认同感。在“出洼”过程中,村民午饭后,妇女聚在另一处休息的高台上打开录音机围在一起“嘎秧”,伴奏的音乐与场所不再以奘房为中心,却形成一条世俗与宗教的分割线,隐喻族群在世俗性和宗教性之间的属性切换和情感延伸。通过这种切换,我们窥探到民俗文化流动发展甚至变迁的节点,继而理解这类族群如何在变迁中求得发展。在这个时空内,身体既是生理层面上的躯体,又是包含无数个体心理感受和生命经验的肉体,一定程度上,还寄予特定社会、历史和文化中思想、意志等形而上的能指。3民俗仪式中的乐舞既可看作一种乐种曲体的有机组合,同时象脚鼓是具有配合性以及驱动性的声音载体,和“嘎秧”的十几套动作又不完全是舞蹈动作的规训,它作为一种民俗,在不同场域下开展,影响着人们的日常心情和审美体验,体现出民间话语的叙事性和表意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关注仪式流程、人群关系、村落制度、舞蹈、音声,更要观察仪式过程中影响“嘎秧”的其他因素,比如仪式中的人都做了什么,他们是怎样做的,在这个“做”的行为过程中有哪些细节值得留意。
结语
现如今,“嘎秧”在德宏州的各个村落中继续发展,逐渐走进城市和学校以及社区,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潮流,并在这种文化潮流中表达自己的美感特征,延伸出一套符合现代审美的评价体系,由此加深了“嘎秧”的规范性,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审美观念下,逐渐形成新的舞动序列和舞目。这样一种转化,实际上揭示了人类不同群体的心理特征变化,从驱除心理恐惧的民间集体信仰到艺术化的审美关系鉴别,体现的是民间法器与城市乐器的分野以及乐舞和艺术化舞蹈在语言和语境上的差异。同时说明,民俗艺术除了在乡村,也在逐渐满足精英群体对于民间“嘎秧”的感性体验,并不断向社会化进程延伸,维系德宏傣族的民俗展演在不同场域下的表意内涵和精神根脉的同时更具时代意义。
1额瑜婷、郭田:《傣族象脚鼓舞舞蹈形态研究》,《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1曾希卓:《基于“身体民俗”视角下的民俗舞蹈研究》,《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2申波:《大理古戏台的文化学意义》,《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3胡亚敏:《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