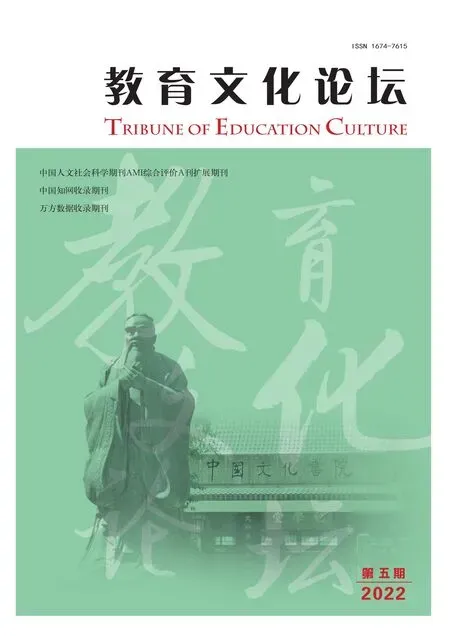时代趋势、区域环境、多重文化及教育整合
——笔山书院孕育一代精英探析
韩继伟
(百色学院 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百色 533099)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极为剧烈的危机、动乱和变革的转型时期,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在西方武器和思想的双重冲击之下逐渐式微与衰变,地方政治势力异军突起、势不可挡。在此背景下,偏踞黔省西南一隅的地方宗族势力刘氏家族迅速壮大,在政治权利和军事资源达到一定积累后迅速触及地方文教领域,几度兴废的笔山书院犹如战火纷飞中涅槃的凤凰,再次焕发荣光,培养造就了黔省乃至中国近代史上一大批社会精英和风云人物,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目前,学界对历史上的笔山书院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究和梳理:有的从笔山书院的历史渊源视角展开探究,有的从书院文化影响层面进行梳理,还有的则是从书院相关风云人物思想性格视角进行研究。而自时代趋势、战略区位、区域环境、多重文化以及教育整合等综合视角和多个层面对笔山书院进行全面阐释还不多见,有必要对该问题进行更加深入和系统的探讨。
一、时代趋势因素的影响
时代趋势是影响笔山书院兴起的政治前提。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体秉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治国理念和伦理信条。清末民初是一个自传统专制国度向近代宪政国家曲折转变的时期。一向以“上朝天国”自称的大清王朝,在西方外力和内部民乱的双重撞击下逐渐走向衰败,在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王权止于县政”的时代背景下,类似“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逐渐发展为盘踞一方的政治势力,从而登上历史舞台。在清末民初的边省贵州黔西南,以刘统之为首的刘氏家族就是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起义风起云涌,晚清中央政府无力维系地方秩序的情势下成功起家的地方政治势力的典型代表,它打破了满清王朝在黔省地区的统治体系和控制机制,加快了传统政治体制在贵州盘江八属区域的解体速度。兴义刘氏政治势力因其崛起的合法性而被纳入新的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填补了黔省西南区域地方公共权力的真空,俨然“盘江小朝廷气概”[1]。至此,刘氏家族以兴义城附近的永康堡为根据地,以盘江八属为政治外围,逐渐主政兴义府城的大小事务,实现了刘氏客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华丽转身。当然,刘氏势力所在的兴义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处,远离黔省中心贵阳,位置偏僻,满清政府鞭长莫及,这也是造成刘氏势力急速发展和快速扩张的一大客观因素。但其之所以能够快速走出盘江,夺取黔省政权并很快形成影响全国政局的兴义系军政集团,与刘氏家族重修笔山书院、兴办教育事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讲究“马上”得天下,“马下”方能治天下。武能安邦,文能治国,教育文化具有武力所不可替代的潜移默化的安抚作用,即所谓的教化。“黔省穷荒固随,必崇文治,而后可以正人心,变风俗,非如他省行化俗美者比,合应仰吁圣化之隆,仁义渐摩,翻致土风之厚。”[2]一方面,统治者可以通过创办书院、开办庠序来教化人民,“左右人心”;另一方面,通过开办教育,引导后生走向仕途,还可光宗耀祖。当时的兴义刘氏集团代表人物刘统之也未能逃脱这一历史窠臼。首先,从造福盘江和发展乡梓的视角看,鉴于兴义置县以来仅有胡尔昌一人中举的尴尬局面,在当时重文轻武的历史大背景下,振兴地方文教事业便成为当地士绅义不容辞的事;其次,从振兴门风、猎取功名的视角看,虽然兴义刘氏家族通过镇压历次农民起义成为“盘江八属”的至尊人物,但身份上仍属“土豪”之类,很难跻身于黔省书香门第的望族之列。在刘统之看来,“武功外悠,文化内辑”的中原文化思想方是国家治理的核心理念。他认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武功只是一时平乱权宜,并非整饬地方之计”[3]。因此,刘统之为改变自身形象,巩固家族地位,对“省会文士,拔其优秀酌予津贴,俾为延誉。院司幕友门丁,月有馈岁终有献遗”[4]。如此,重建和振兴笔山书院的历史重任便落在了以刘统之为代表的当地士绅身上。
二、区域环境因素的影响
区域环境是影响笔山书院兴起的自然前提。德国语言学家及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人洪堡曾说过,“人口从来就是与他附近的一切相联系在一起的”[5]。地理环境是形成人的文化取向的重要因素,因为地理环境直接影响人的思维格局和行为方式。一般情况下,所谓地理环境包括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部分。兴义位于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可谓“三省通衢”的旱地码头,山高谷深,地形崎岖,高海拔低纬度,属于典型的边缘中的边缘。“山虽绵亘,而有疏密相间之形;地虽空旷,而有灌溉相滋之利。”[6]西、北、南部属于云贵高原的一部分,多为山地;东面属于自高原向平原的过渡地带,多为山地、丘陵与小盆地交叉的地形,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民间谚语有云:“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百步不同土”,可谓是对清末民初盘江八属地区气候特征的最好写照。尽管现在那里的气候整体上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但历史上的此地,却以“烟瘴之地”的形象出现在历史的记载中,独特的气候、环境为有毒植物的生长创造了条件。据《兴义府志》记载:“全境气候,雨即寒,晴即热……气候热而多瘴……一日之内,乍寒乍暖;百里之内,此燠彼凉。”[7]其中,盘江八属与云南交界的广南以及与广西交界的册亨等区域瘴气更甚。据后人研究,产生瘴气之原因除了与自然气候有关之外,更与生物物种变化有关——曾有人统计,仅盘江八属地区的有毒植物就多达260种[8],可见当时该地区实属地理条件较为恶劣的区域。
那么,清末民初盘江八属的社会环境又是如何?可以说,晚清时期的盘江八属堪称一个动乱的区域。据相关史料记载,该地区在“改土归流”之前是一个未开化的区域,一个蛮荒之地,当地人被贴上“强盗”“彪悍”“野蛮”等标签。“改土归流”之后,大量客民迁徙到盘江八属地区,引发了一系列客民与土著民之间的利益争斗和冲突。最初的客土争斗主要表现为清乾隆末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其冲突原因主要是当地土著的土地被客民盘剥占据。当然,有时冲突也发生在“土”与“土”之间及“客”与“客”之间。在迁徙客民越来越多、土地却愈来愈少的情势下,地少人多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愈加尖锐。清嘉庆二年(1797)爆发的盘江南笼起义就是由于苗民土地不断被客民侵占而引起的,而咸丰年间席卷整个贵州的苗民大起义甚至引发了大规模的瘟疫流行。此外,大量客民的陆续涌入,亦给原先单纯的社会风气带来了不少变化,赌博、盗窃等风气在盘江八属地区日盛。清初,来自江南地区的大多客民尚能勤俭持家,但从嘉庆年间开始至清末民初,有“内地边缘”之称的盘江八属地区“三省通衢,距城窎远,匪徒易于丛集”[9],赌盗之风开始蔓延,以至于该地有“盗贼渊薮”之说,社会秩序严重恶化,进而演变为一大社会问题。鉴于当时盘江地区恶劣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地处三省交界、远离区域中心城市以及交通不便的现实,再加上1748年黄草坝筑墙造城的实际(1)《黔南识略》最早记载了开始建造兴义城的时间为乾隆十一年(1746),《民国兴义县志》则对兴义造城过程给出了更为详尽的阐释:“今稽城门石额作乾隆戊辰孟冬,当以十三年(1748)为是。否则当为经始于十一年,竣工于十三年,刊石额于十三年十月也。”,最终迫使那些来自江南地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并定居该地的绅耆士庶决定开设学堂、择师授课,为家族子弟读书科考创造条件。
三、多重文化因素的影响
多重文化是影响笔山书院兴起的文化前提。盘江八属毗连三省,悠久厚重的历史一再证明一万年前便有“兴义人”在此繁衍生息。然而,千百年来,这座地处僻壤的边城兴义一直被人们视为“化外之地”“文化末兴”,直至明朝永乐年间方作为省级下辖的行政区出现,而设置县政则推迟至1797年的清嘉庆年间。实际上,历史上的盘江地区是一个交通闭塞、政治松弛、经济贫瘠、文化滞后的地区,自明代开始就成为中国西南地区一个重要的移民区域。经“调北填南”和“改土归流”之后,中原儒家文化经过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以及滇黔山地文化的层层过滤与裹挟,逐渐汇融于此,形成了深远悠久的文化格局和丰厚肥沃的文化土壤。移民的迁徙过程也是文化的流动过程。作为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移民群体,来自江南地区的客民在生存方式和心理活动方面均显示出独有的文化内涵,家乡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已成为一种心理积淀,无论他们走到哪里,生存环境发生如何变化,这种无意识的心理积淀均会影响他们的思想意识、思维格局和行为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儒家文化的影响
“一个人在特定境遇下的反应,主要暗示了他从文化模式中接受了什么。”[10]当时迁徙至盘江地区的移民主要是来自江苏、湖南、江西、安徽等传统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自西汉时期被确立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以来,儒家文化影响中国社会几千年,其积极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坚定“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主张“忠、孝、信、义”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道德标准和思想素养。明代中后期,朝廷出于军事目的,安排大批移民迁徙至盘江地区,这些移民大多把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作为人生准则,把驻守屯兵和维护社会治安看作神圣的社会职责与人生理想。
2.荆楚文化与湖湘文化的影响
“人的本性,是由文化,即习俗塑造的,而不是生物学遗传的天性。”[11]明朝时期的很多军事移民来自于有荆楚文化和湖湘文化背景的两湖地区。该地历史上属于楚国,山高林深,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为战胜恶劣环境,赢得生存,楚人历来就是一个崇尚武力的民族。经过数百年的征伐,楚人终于战胜了周边小国,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可与中原诸国相抗衡的强国。尚武精神是荆楚文化的精华与核心,“楚人尚武,气质刚勇,勇武爱国,乐战轻死的民族性格,蕴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荆楚地区民族风格。”[12]湖湘文化则是指两宋以后发展起来的仅限于湘省区域内的地域文化。湖湘文化之所以能在全国独树一帜,主要是受“湖湘学派”的影响所致。“湖湘学派”是两宋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以及儒学地域化的结果。它注重经世致用,主张理欲同体。作为笔山书院培养出的精英之一的刘显世,就是受荆楚文化与湖湘文化影响和熏陶的代表。
3.吴越文化的影响
作为华夏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吴越文化又称江浙文化,是江南文化的中心与代表。该文化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包括沪、江、浙、皖、赣等相关地区。吴越文化一般具有以下特点:海纳百川,聪慧机敏,经世致用,敢为人先,朴实低调。盘江移民中的王姓、何姓等移民均受到吴越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4.岭南文化的影响
盘江地区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不可避免受到岭南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灿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原生性文化,以农业文化和海洋文化为源头,在不断汲取和融汇中原文化及海外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身“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等特点,其核心内容就是“维新变革、救亡图存”。岭南文化一直得风气之先,开学习西方现代科学与民主思想之先河,寻找救国强国之真理,从洪秀全到梁启超再到孙中山,都是岭南文化大放异彩的表现。
5.滇黔山地文化的影响
云南的古滇文化主要是指以滇池为中心的山地青铜文化,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包容”和“开放”,特别是在楚汉文明汇入融合后,形成古代中国西南边疆与内地相互融合、和谐相处的文化典范。贵州的夜郎文化主要是以贵州为核心,同时包括滇东、桂西及湘省芷江等区域的山地文化,具有民族性、历史性和未知性等特点。盘江地区的兴义属于典型的山地文化,山地人粗犷、剽悍、坚韧的性格养成与兴义境内蜿蜒起伏、水环四境、山地险峻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绝不是单一文化因子的“传”或“递”,也不是各种文化传承方式及路径的简单叠加。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本质,在于多种文化基因“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在于诸种传承方式的相互协调、相互融合与相互作用,从而使文化具有再生性、流动性和延续性。多重文化对盘江移民人的影响主要集中于社会心理层面的潜移默化。社会心理是一种低层次的处于自发状态的社会意识,而要对人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高级社会意识产生巨大影响,不得不依赖于书院教育的培植和滋养。
四、书院教育培植的因素
书院教育是孕育一代精英的重要因素。书院最初由古代的“精舍”“精庐”“学馆”演变而来,是中国封建科举制特有的产物,其目的即“裁成文士,为国储材”。它产生于隋唐,兴起于宋明,止于清末,历经千年之久。书院办学以民办为主,秉承“教学相长”“知行合一”之教学原则,是封建王朝实施教化的重要体现。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笔山书院,几度兴废,经历清代乾隆至宣统七个朝代,终于在兴义士绅刘统之、兴义知府孙清彦的帮助下,在光绪年间重现辉煌。由笔山书院培养出的社会精英达三十余人,书院无疑创造了近代黔省乃至全国的教育奇迹,造就了中国文化学中的一种“次生现象”。古老的书院文化之所以光芒四射,究其原因,不外乎笔山书院独特的办学理念、教学方法、管理模式和独树一帜的文化精神。
1.强调道德教化,注重人格完善
鉴于黔省盘江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书院产生时间较晚。乾隆时期,孝廉王赞武兄弟所建的首座笔山书院历经多次兴废,规模逐渐扩大,其中第四座书院——新书院最具规模和影响。书院建成后,刘统之以重金广聘省内外名流贤达前来执教。据相关史料记载,自1883年创办新书院至1905年改名为高等小学堂止,刘统之以年俸三四百两先后聘请十五六人担任笔山书院的山长(院长),这些人均有进士或举人头衔,且来自于山东、江西、四川、湖北、云南等不同省份。清末著名教育家雷廷珍、山东曲阜进士桂馥、湖北进士喻鸿均、江西进士吴成熙、云南举人陈光祖和周辅成、四川举人曾佩林、“一代通才”姚华、贵阳进士熊范舆、留日精英徐天叙等先后执掌山门,使笔山书院学风为之一变,学风日盛,人才辈出。
1905年,兴义县立高等小学堂的王文华等13人前往投考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贵阳一中前身),“结果13人以第1至13名的优异成绩全被录取,震动全省学界”[13]。当时的笔山书院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与书院历来秉承的文化传统,即强调道德教育,注重道德修养,将人格完善与知识传授有机结合起来密不可分。
首先,从笔山书院不惜重金聘请省内外学术名流的视角来看,刘统之之所以如此慷慨解囊,首先看中的就是这些社会贤达与饱学之士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道德操守和人格魅力。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他们通过躬身力行对学生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充分体现出笔山书院人格教育的影响力。其次,笔山书院参考由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制定了学规(2)学规,即规范和约束书院师生的言行举止,提升道德品味的规章制度,亦称为学则或揭示。,设有“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从学规的内容上看,“五教之目”为德性伦理;“为学之要”是学习方法;“修身之要”是修养方法;“处事”与“接物”之要,则是儒学核心价值“仁”与“义”的具体体现,即书院培养人的“理义养心”[14]。也就是说,书院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成人达己与成己为人”,教之以为人之道、为学之方,而不是追求所谓的功名利禄。这一办学理念对于规范书院人的言行,提升书院人的修养,完善书院人的道德,均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再次,从笔山书院的教学内容看,从书院初期开设经史子集、八股试帖和诗词歌赋等课程到后期讲授经学、国文、历史和伦理等课程,人文通识教育无不贯穿其中。可以说,笔山书院自始至终弦诵之声不绝于耳,真乃“人才之薮,教化之渊”。
2.推行经世致用,倡导教育革新
笔山书院最初的教学目标主要是以八股诗赋为主,以撰写八股文和试诗帖为主要内容,教学缺乏创新性和科学性,仅仅培养了一批所谓的秀才和贡生。1899年,鉴于国事日蹙之现状,刘统之重金聘请近代著名教育家雷廷珍为山长——其执掌笔山书院将近三年,为笔山书院山长任期最长之人。他同时聘请省内外大批进士和举人来笔山书院任教,这些饱学之士云集笔山书院,教学在一定程度上虽然依旧为封建科举考试服务,教读之内容基本上亦以“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为主,但鉴于西学以及维新变法思想之影响和渗透,这些来自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圈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将新思想和新知识融入笔山书院的教学之中,这就使新书院与原先历座笔山书院的做法完全不同。当时雷廷珍为经世名儒,名冠江南,史载其时黔英俊多出其门。他极为欣赏清初顾炎武等人所主张的经世之学,亦研读西方各类书籍,与时任贵州学政的严修共过事,始终积极践行经世之学,改革教育思想。他在学生刘显治的极力邀请下来到兴义,为笔山书院带来了丰富的办学经验,注入了新式的办学理念。雷廷珍执掌笔山书院期间,极为重视生员的基础教育,除了教授学生经学、小学之外,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读经和文字音韵训诂的训练,指导学生写读书笔记和作文,并设立奖学金对优秀学生实施奖励。在刘统之的支持下,雷廷珍还派人自武昌和长沙购进大批经、史、子、集之类的书籍以及各类实务书报供学生阅读。此外,他还从日本购进各种与近代科学相关的图表、书籍、仪器等学习用品,以供学生学习使用。“书院向习八股诗赋,自戊戌,雷廷珍提倡经学、小学,住院生月呈日记,亦当堂课给奖,广置实务书报及经、史、子、集,以供涉猎,学风为之一变。”[15]
时任湖广总督、曾在兴义府安龙度过青少年时光的张之洞,听闻雷廷珍主持笔山书院成绩斐然,且知其与己政见相投,遂派人邀请雷廷珍赴武昌两湖书院讲学,雷廷珍欣然前往。离开之前,雷廷珍向刘统之推荐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姚华和熊范舆接替自己担任笔山书院山长一职[16]。姚华,被誉为“旧京都的一代通才”,任笔山书院山长一年——实际上,鉴于其后来北上参加会试,真正的任职时间仅半年。熊范舆几乎与姚华同时返回贵阳参加乡试。他们大体遵循了雷廷珍所定的书院规制,但有所改进和创新。特别是姚华担任山长时期,拟定新的《书院学约》,分为辩业、明礼二条;其后甄别院生,取正调文生二名,备调一名;正调文童六名,备调十二名;更订院中课程及分程书目表[17]。姚、熊二位山长除了授课教徒、埋头著书之外,还经常与学生一起吟诗作赋、切磋书画技艺。此外,姚华还尝试创作了一种泼墨加拓法的“水画”技法,引导学生们进行创新。姚、熊二人之后的笔山书院山长是自日本京都大学留学归国的徐天叙。他在担任山长期间,几乎沿袭原先之规制,认真负责,大胆施教,分类批阅学生呈交的读书笔记,且每月还召集当地有学问、有文化的人举行讲演会,让学生开阔眼界,解放思想,不受一门一派之局限,因而,笔山书院学风日盛,成绩斐然。1905年,徐天叙带领笔山书院十三名学生投考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囊括前十三名,震惊全省。
1902年,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废除科举,各县书院改设学堂。于是,兴义的培文局改为劝学所。1905年,刘统之将笔山书院改为兴义县立高等小学堂,又积极创办各类初等小学堂以及女子学堂,在书院内增设师范讲习所(后改传习所)。刘统之又任命其子刘显世总管学堂事务,刘显世马上聘请陈树潘、端小江、谢正初、尤远春等省内外名师担任各科教学,任命本校出国留学归国的李映雪、赵显彬担任高等小学堂堂长并执教。1910年,学董刘显世又邀请王文华、魏树楷、王慎一、袁祖明、窦居仁等具有革新意识的知识分子进入学堂执教。此后,学堂逐渐取消“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课程,大力购买白话文教材,积极开设数、理、化等西方新式课程,并添加音乐、体操、画画等科目,甚至把跑、跳、打拳之类的玩耍也列为功课,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18]。此外,更名后的笔山书院还积极顺应历史潮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当时“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民主运动的兴起,推动了全国各地积极选派留学生到日本和西方留学的热潮,希望他们将学习到的先进科学技术作为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工具与“武器”。1905年,由兴义劝学所出资,笔山书院首先选派刘显治、王博群、保衡等五人留学日本,至辛亥革命前,又选派二十二人赴日本留学[19]。当时选派的留学生中,除留日学生之外,还有留学美国的何纵炎、刘汉东、刘达仁以及留学意大利的蒋镇澜。总之,鉴于笔山书院自清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世致用理念的实施及教育革新措施的推行,盘江教育一度辉煌,教育质量冠于贵州,造就了大批人才。
3.强调天人合一,力主兼容并蓄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书院讲究天人合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而形成了较为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笔山书院继承了传统书院的这一特色:首先,笔山书院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知”与“行”的统一,“情”与“景”的交融,进而形成了书院和谐的文化风格。从传统哲学的视角看,“天人合一”是“知行合一”的前提与基础,人们生活在苍穹与大地之间,必然要有一定精神层面的诉求,而要做到这一点,须在道德层面做到言行一致,“知行合一”,方能实现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再到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这一点从首座笔山书院的选址即可看出。第一座笔山书院位于兴义老城西南一隅的水井坡,书院坐西北朝东南,背靠水井坡,面对笔架山,前临花水河,笔山与牛场之间有水田相连,风景如画,几乎完全符合传统堪舆学之要求,天人合一的理念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充分说明笔山书院的开创者们充分认识到大自然对人的陶冶功能,实现了书院环境与书院文化的协调和融合,符合儒家学人择胜而居、潜心读书、寄情山水、修心养性的高雅诉求。其次,笔山书院在强调天人合一的同时,力主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主要表现在山长(堂长)及教习的聘用、招生录取以及教学课程的开设等方面。在笔山书院山长(堂长)和教习任用方面,不管是笔山书院时期的刘统之,还是高等小学堂时期的刘显世,对山长(堂长)和教习的任用,不分地区籍贯,不管家庭出身,唯坚持名儒大家、“唯才是举”之标准,从山东名儒桂馥到“经史名家”雷廷珍,从思想名流徐天叙到“维新”先锋张寿龄,无一不是饱学之士。教习的聘用亦是如此,既有云贵举人,亦有中原进士,教习出身几乎囊括小半个中国。在学生的招生方面,早期仅限于黄草坝一隅之地,后期特别是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之后,由于人才汇聚,设施先进,理念超前,教法独特,教学成绩独占鳌头,学堂名气与日俱增,本省盘江八属的学生以及邻省云南、广西的学生纷至沓来,每日都有千人之余前来求学。在教学课程的开设方面,既有早期开设的讲经课、读经课,又有后期开设的算学、历史、伦理、体操课等西学课程;既有讲授课,又有自学课;既有“讲演会”,又有“讲会制度”(对话式的教学方式)。这些教学课程的开设目的就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总之,清末民初的兴义笔山书院是中国式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时代的一朵奇葩,揭开了非常时期中国西南边陲教育的一角。它之所以能够在贫瘠之乡和僻远之壤长成挺拔的神奇之树,形成如此肥沃丰厚的文化土壤,演绎了一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化失而求诸于野老”的教育大戏,孕育出了一大批群星璀璨的社会精英,既有时代趋势、战略区位、区域环境、多重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又伴有笔山书院独树一帜的办学理念、管理体制、教学方法和书院文化精神的培植与滋养,是当时各种因素综合发力、相互促进的历史产物。虽然笔山书院往昔的辉煌荣光业已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但书院独具匠心的教育理念和文化精神将永远照耀在盘江的两岸,同时亦给后来人和接棒者留下极深的思想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