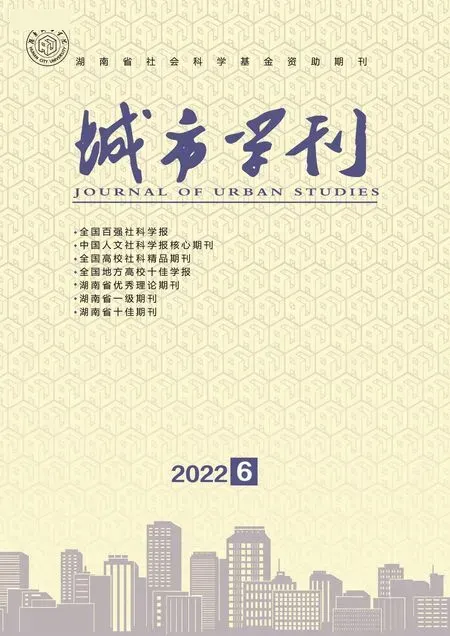现代性批判:新媒介时代网络诗歌的城市书写
徐 杰
(西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成都 610041)
空间并非冷冰冰的物理事实,它被文学和艺术历时性地赋予了多重的情感性、审美性和意义性。人们将对文学空间的感受赋义于现实空间,使之脱离纯粹的物理空间而成为富含多元意义的审美空间。迈克·克朗认为传统的地理学是一种“数据确定的现实”,而文学地理学则通过语言艺术赋予空间以情感意义。文学并非简单地对物理空间的描述,而是对空间的一种意义创造。人对意义生产的天性渴求,正好形成对文学空间“主观性”的辩护。[1]与此同时,在现代性社会之中,匀质性、连续性空间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的、异质性的、非连续性的空间。网络诗歌所呈现的空间的分裂、碰撞和越界是审美现代性必然涉及的主要话题。诗人对城市空间的书写并非试图原封不动地呈现其真实样态,而是凸显现代性空间的意义以及对人类精神世界所造成的异化。
一、城市空间的生态原罪
城市书写之中存在一种“回归”的美学情绪,回归到“原初”的状态。这个“原初状态”也就是去工业化社会、去商业化关系以及去技术化生活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书写并非意味着回到原始蒙昧状态,当然这也不现实。当代文学之中,城市被书写为现代性的“恶之花”,于是文学书写具有了“反城市化”和“去城市化”的倾向。在当代文学中,“乡野不仅被赋予神性,而且常常被描绘成被城市伤害的角色,将城市加上生态‘原罪’,强化了对城市的‘反乌托邦’批判。”[2]网络诗歌也秉持此种现实写作立场,其生态书写其实是一种对城市化、现代化的排异性反应,也是对长久身处的自然世界的守护。城市空间集中体现了现代人生存发展的理性诉求与生命质态的感性体验之间的冲突,[3]这也是现代性的基本冲突。在现代社会,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的冲突在网络诗歌中往往被塑造为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技术文化与自然文化、商业文化与本真文化、成年文化与童年文化等之间的矛盾。城市作为“草原”或“村落”的反面,以“破坏”原初纯粹状态为意象特征。
其一,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破坏和颠覆着传统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明。诗人左右从农家小院的桃花苞蕾想起老家变迁:“乡下千里良田没了,良田里撒肥的农民没了/ 农民犁地的耕牛没了,牛背上欢爬的春虫没了/ 天空中边捉虫边低飞的花燕子没了/ 燕群眼中牧羊的村童没了//很多年了,家家户户往昔的农事,早已不见踪影/它们已被发达的科技与器械代替”。[4]城市现代性进程绞杀了农村春耕秋收的生命节律和生活方式。流竹的《风进入城市》以大自然的、自由自在的“风”作为意象,书写其进入城市之后受到的约束、产生的异变和滋生的痛苦。“一阵风进入城市,就再也不会轻松了/ 大片的旷野在这里死亡/ 无数巨大的四方盒子勉强让出一些/ 被人群和车群挤得无法呼吸的路”。[5]最为自然的和自由的“风”在城市空间都被束缚并失去自我,“风在城市里遗失了声带”。王二冬的《春天》充满着对故乡的思念以及对故乡改变的失望。果园、麦田、棉地变成了以商业利益至上的密植林。“对于那些速生的草木,我始终认为/ 它们被运到城市后,长不出春天/ 长不出河流,也就长不出鸟语、花香/ 和一个孩子惊讶不已的梦”。[6]沐心的诗歌《阿妈,看不见了》通过对儿时草原的记忆与现代文明的破坏进行对比:在同一个地方,小时候可以看到“天上的云每天给我表演魔术”、无数的羊和马、麦穗中阿妈的影子;现在却在阿妈指引下看到的是“挖掘机”“工厂”“一堆堆石头”和“一片片黄沙”。“孩子,那些白晃晃的是我们的羊群吗?/ 不,阿妈,那是一堆堆石头/ ‘孩子,那些黄灿灿的是秋草吗?’/ 不,阿妈,那是一片片黄沙。”[7]人通过劳作诗意地栖居的世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征服和破坏带来的城市文明。熊森林的诗歌《海南黎族》控诉了现代文明对原生态文化的破坏,“船形屋败给砖瓦结构/ 一方混凝土,骄傲地展示艳俗文明/将炊烟与农具抬入博物馆,在幽暗的山腰上/ 它们消散,从此再与黎族的日常无关”。[4]34当我们用人类学知识来研究和保护黎族生活方式时,从某种意义上便是让其僵死和灭亡。关于它的知识与它本身的诗意存在是截然不同的。尕玛才让的《百灵鸟消失的日子》描绘了一幅自然生态被人为破坏后的景象:“百灵鸟”折断翅膀,“花朵”和“溪流”从老牧人眼中消失。沙粒漫天,草原无草,没有生机。“沙粒长出羽翼在漫天飞舞/ 草原衣衫褴褛,寂静无声”。捕鸟的铁丝网与沙化的草原让鸟儿们失去家园。动物们没有食物,“一只饥渴的藏熊/ 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美丽乡村”。等待它的却是人布下的陷阱,“暮色中,布满刀光剑影的阴谋”。[8]城市里人工制作的鸟巢与大自然中百灵鸟的“巢穴”隐喻着城市与草原、工业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对立关系。工业文化的破坏效应不是一时一地的,即便在遥远的小镇,牧场也走向“衰老”。工业化社会制造的人工现实一步步祛除了自然之物:“酸奶”放于工业材料制成的“塑料桶”,“掉色”有工业垃圾作为材料的嫌疑,添加各种原料的“酸奶”却讽刺性地努力靠近最原初的“蒙牛”的奶香。“蓝色的小药丸”就是指“伟哥”,强迫“健硕的藏獒”吃壮阳药其实是想表达现代社会对欲望的无限刺激,金钱的欲望替代了藏獒的自然欲求。城市被诗人塑造为“欲望”和“诱惑”的符号,给人带来的是灵魂的迷失。
其二,速度作为时间概念决定着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体验和评价,现代社会的标志是速度对人的控制。“对速度利益的享用是以丧失对生命情绪的细腻感受为代价的,而缺乏后者,现代人就难以在瞬息即逝的生活表象背后寻找到意义、价值和信念的归宿,从而无法确切地把握生活或把握自我。”[3]10“加速”的现代化社会,诗歌书写已经被网络媒介带来的消费文化稀释。城市快餐文化和技术文明杀死诗歌和诗意的生活。就像罗铖的诗歌里所写:“快餐时代/ 写在纸上的字,死于饥饿// 我来自穷乡僻壤/ 习惯将字写在石头上,泥沙上,水上/ 写在邻居的门扉上,我还曾写下脏话/ 母亲说,写吧,干干净净地写,别做流氓// 后来,我干脆把字写在空中/ 让它们有充足的氧气,有灿烂的阳光”。[9]邱正伦更是将网络媒介视为对诗歌的戕害,“用网络打捞失踪很久的女人与纸质的月亮/网上的新婚充满喜悦,无名的疼痛布满诗歌的身体”。语言因为网络而变得苍白和透明,“诗歌的天空早已不复存在。语言的碎片/成为玻璃,白色的杀伤,白色的寂静/失血过多的诗歌成为可以搬迁的黑夜/ 很难走出尽头,监禁成为唯一的家园// 从此,诗中不再出现月亮/ 不再有浪漫情人从最理想的地方出现/不再充满花朵的温暖,没有体温/ 一切将弥漫后工业的包装痕迹”。[10]速度改变了媒介形态,重新调整了主体的感知比率,这就是维利里奥所说的“距离专政”到“现时专政”。速度使得空间被压缩为时间,空间的时间化。时间不再是绵延的意味,而是瞬时的碎片构成。速度通过占有无数的瞬时给予人以轻松和自由,但却让现代人处于无根的漂浮和空虚状态。因为散点的“现时”被碎片化,不能承担历史的连续性,历史感、传统和自身身份都丧失了。然而,连贯性和统一性又是人的本能情感,怀旧便成为速度的心理副产品。[3]12城市的迅速发展对传统城市慢节奏生活也是一种破坏。韩放的《速度》中,“老街”还处于慢生活中,“轿车”比“挖掘机”走得慢,人比“推土机”走得慢,商品价格比“破拆机”走得慢,看似不合逻辑的比较却写出人对空间节奏的真实感受。“水泥森林”的疯狂扩张,“挡住了照向老街的阳光”。[11]人与周遭环境的和谐、稳定和自在的关系被快捷的现代化进程打破。昌政的《消息》中以“推土机”为符号标志着城市化进程的坚定不移,带来的却是“不自然”的生活状态,扼杀了无数诗情画意。[5]94“春天逃进电梯”,遮阳伞带来的是“人工阴影”,“水表在墙角计算着主人”,老虎回头看见的森林已然变为“铁栅栏”。
二、城市文明与技术现代性
现代技术破坏了生态世界,“技术化”社会成为生态书写所批判的典型空间。“世界变得技术化与合理化了。机器居于支配地位,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节奏。时间被编排成井井有条、平均分布的年代。大规模生产商品是工业社会的特征,这里,能源代替肌肉提供生产动力,成为提高生产率(即以少获多的艺术)的基础,从而对商品的大规模生产起着决定作用”。[12]
首先,城市空间的工业化和技术化割裂人与自然之间天然的亲近感,造成当下人的灵魂空心化。人类灵魂的外包形成自我奴役化,而令人讽刺的是动物尚有自由的本能冲动。一杯无的《那个人一直跟着狗走》中,诗人掠取了生活中傍晚遛狗的一个场景。“白狗”的“白”与暮色的“白”;“黑衣的人”的“黑”与暮色合上之后夜的黑。色彩上诗人进行着对应,“白”代表目标、方向和希望;“黑”代表茫无目的、浑浑噩噩的存在状态。动物凭自己的天性跑着,“那只狗在跑,方向不定/ 迂回曲折的路,是狗自己的路”。人却没有自己的路。人毫无自由,甚至已经不知道自由是什么。于是,将自由的方向托付给“白狗”。“或者他需要一只自由的狗带他行走/ 他不需要黄昏的光影,黄昏的风/ 来放慢他的脚步/ 他只需要暮色里的一点白/ 带着另一个他的灵魂行走”。[13]诗中人与狗的关系折射出现代人的生活状态。人类生活早期,狗作为狼族的一种为了生存,与人类之间建立起“互补”的“生态位”关系:狗为人类照看牲畜,人类将剩余不吃的骨头掷于狗群。时至今日,狗早已沦为人类的宠物。人类最引以为傲的“自由”却被自己赠送与心爱的“宠物狗”。城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剥夺了传统栖居的诗意状态。才让东智的诗以一种城市“寄居”者的视角回望那“陌生了熟悉的风景”。当带着城市印记和气质,开着现代文明的标志的越野车回到尕海湖边时,“尕海湖边越野车的轰鸣/不及少年时/ 草原上马蹄落地的声音”。[14]阿苏越尔在诗中表达对自然空间所携带的纯粹性和浑然一体性的向往。“在青海湖畔/ 当车窗外掠过六字真言/ 我顿然失语// 骑上高原的大马,似有所悟叩拜连绵,力量挣脱源泉/ 但语言坚硬、板结”。[15]城市代表理性、语言;青海湖代表超理性、非语言。城市和草原、汽车和马、语言与“真言”成为空间二元对立的表征。
其次,从网络诗歌的媒介技术书写中,我们看到诗人对技术文明保持着批判和反思态度,批判它带给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和主体精神的理性异化。陈小三的诗中,城市的现代工业产品以沉默的方式制造最大的噪音,“摩托车”“汽车”和“耳机”带来的是“地下的引擎”发出的声音和“凄厉的秦腔、高胡齐鸣”。[5]92在李满强《死去的人如何描述他生活过的时代》中,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被描述出来:“转基因稻谷”“激素鱼”、快速交通工具、“隆胸美容”、网络虚拟生活等,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它们远离了自然的存在和真实的生活。现代社会让我们沉湎于技术逻辑、感官享受、快节奏和虚拟人生,却不知原生态的动植物和交通方式的价值。我们失去了对真理的思考和追寻,只剩下武力来维护话语权;也失去了向内探求的“禅悟之道”,只剩下外在肉体美的打造。“我曾在互联网上,用一天过完漫长平淡的一生/ 最后死于与“物”的战争。我曾用娱乐的灰烬/ 深深掩埋过自己”。[16]就像马尔库塞所说的,人被工具化了。“技术逻各斯被转化为持续下来的奴役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成为解放桎梏;这就是人的工具化。”[17]城市现代生活被“计算”标准化,并在精确的计算中不断加速。欧阳白的《归零》中,我们在床上就已经计算去办公室的时间,在办公室又计算“日子与工作量之间永恒的递进关系/ 业绩增长和头发稀少的剪刀差”“我们计算知识更新与电脑换代/ 的某种关联/ 我们在复杂的运算里/ 把一堆数字除以年龄/ 以算清楚得失分率”。[5]147然而,当所有的计算数字不管除以还是乘以零都“归零”,我们并未获得任何东西,也未失去任何东西。薇安在《电视机谋杀案》中写出了现代媒介技术造成人们的精神异化以及人们享受异化的生活状态。“我离不开你,我需要你制造出的垃圾/ 所营造出的种种拟态环境/你的嘴里不断抛出空乏的吻/ 塑料花,过期糖果及玩具/ 我统统照单全收,这一切多么像爱情!”电视机告诉我们何谓热闹,何谓世界和平等,我们习惯于它制造的噪音,“聒噪的声音”让我们安心。“你数十年如一日地履行着你的职责,/成功地杀掉了我宝贵的闲暇,/ 杀掉了我的眼睛,我的耳朵/ 和我的判断力”。[9]64电视机以隐蔽的方式在我们来不及反抗时将我们击毙。胃里填满垃圾食品,脑子里装满垃圾信息。薯片填满身体,书籍被束之高阁。生活在电视媒介拟态环境之中不再深刻、不再严肃,一切思想都被灌输,一切现实都被“娱乐”,我们在娱乐中死去(尼尔▪波兹曼)。西娃用“公交车”意象写出城市文明如何以“加速”的方式制造出“单面人”。“隐形公交车”存在于城市各个地方,富于想象力的诗人、具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有反叛精神的青年以及具有换位思考能力的“二度思维之人”,在标准化的“公交车”规约下成为“一个模型的人”。[18]除了单面人的制造,现代媒介技术让沟通变得便捷的同时却让人与人变得疏远。子夜的灯在《一个停机的朋友》中,“手机”是现代文明的技术产物,与资本和情欲关联,而与真正的情感无关。在郑毅诗歌《关机的某一天》之中,手机成为我们焦虑的根本来源。手机作为网络终端,为我们带来信息的海洋,然而这些信息绝大多数与“我”无关:“飞机失航”“地震滑坡”“精神病患”失联、“发小的儿子”出生、同学的爹“车祸死亡”等等。但与己无关的信息让我们越来越“渴”,我们成瘾于各种媒介事件之中,随时浏览手机便成为每个人戒不掉的习惯。我们渴望透过这“屏幕之窗”刺激疲惫的神经,于是手机关机就会如戒烟般让我们焦躁不安。殊不知手机关机,生活依旧,“手机关机后/ 什么都没发生/ 爸爸从公司回来电话依然发烫/ 东南洼里的荒草越过了麦穗/ 四点的太阳开始脸红/ 广场上的鸽子又一次完成起飞”。[16]89“手机”作为新世纪以来现代技术发展的标志,却剥夺了“前手机”时代的缓慢的、宁静的诗意生活。若非的《手机》写出的是现代技术工具带来的内心孤独。通过手机人与人看似很近,心与心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从前置摄像头看得见你的脸/看不见你的心”。手机让世界变得“通透”,“但你我之间/隔着无形的墙/ 而我只能独自与自身为伴/ 与孤独的影子/ 与一只和你一样冰冷的/ 手机”。[6]24冈居木的《团圆》写出的是一家人的团圆却因为各自沉浸于手机世界,人与人的情感越来越疏离。“一家人吃完饺子/ 回到客厅/ 弟弟妹妹妻子女儿/ 都抱着手机在看/ 80岁的母亲/ 在一边看电视/ 女儿起身去洗手间/ 随手将手机丢到沙发上/母亲顺手拿起来/ 不知如何摆弄/ 最后对着手机黑屏/ 整理起白发”。[6]113“手机”对子女来说是与家人无关的虚拟世界,对于老母亲来说是整理白发的镜子。诗歌反思着以城市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构。
三、空间错位的现代性悖论
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的冲突主要体现于现代社会的欲望式扩张与传统乡村生活之间的错位,于是荒诞和悖论是网络诗歌的主要表现方式。德乾恒美的《马城》,诗歌标题“马城”与内容形成巨大的张力。从诗歌我们看到所谓的“马城”不过是在高楼大厦簇拥的广场人工草皮上吃草的十几匹马。“空荡荡的城/ 空荡荡的高楼大厦/ 广场的人工草皮上/ 十几匹漆黑的马/ 不动声色/苏鲁锭的流苏/ 在风中呼啦作响/ 更远处/ 两匹矮小的马/ 依偎在一起/ 低着吃草”。[19]当马生存的空间从真正的草原被置换为草皮之后,我们看到城市化对生态的根本性破坏。继而,马的后代成为“马城”的原住民,一代代彻底背离曾经自由奔驰的大草原。
首先,在城市空间的或者即将被城市化的农民往往通过植物种植来回归乡村生活状态。张尹在《土豆》中叙述了“进城的老人”在阳台种“几盆土豆”,每日“耕作”。[20]然而这些茂盛的土豆只能伸出“金属防盗网”开花,老人和黄昏并置的意象是逝去乡村生活的诗意性符号。“阳台”与“田地”、防盗网中的“土豆”与乡下成片的庄稼,都透露出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韩放的《城市农夫》更是诗意化地书写了“父母”以种菜的方式来拯救“泥土”。“城市日渐肥胖,田野愈加消瘦/ 泥土被迫退守山谷/ 来不及撤退的,长眠于混凝土下/ 还有小部分,被父母从挖掘机利爪下/ 抢出来,搬上楼顶// 赶在泥土心冷前,父母精心栽种/ 悉心照料,执意用一小畦蔬菜/ 拯救庄稼”。[11]93与具体种庄稼不同,“父母”种的是乡村生活的精神。就像独钓“寒江雪”的渔夫一样,诗人眼中的父母并非为了种庄稼而生活,而是守住那颗自然生命在大地生长的心。阿成的《断裂》书写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搬迁”带给乡村文化的伤害。两个已经搬迁走的老人回到“几代人”生活的村落,“遗忘的身体离开了,惯性的脚步/ 将你拽回”,看到的是“残垣断壁”,他们似乎唯有不停地荷锄、劳作才能稍微将自己内心栖居于这村落。老人的耕种只是传统乡村文明的最后挣扎和坚守,“芦苇、杂草支起的网/已把结痂的伤口覆盖”。[11]92同样地,刘坤军的《栽花》也写出城市化进程中人对土地的情感。面对同一块土地,村里的一家人有着不同的打算:老人种庄稼、年轻人栽花、小孩打土仗,最后年轻人栽了花却误了田。“遍野的花田,每一朵怒放的花朵背后/ 都有一颗乡民紧缩的心”。作为农耕文明的传承,老年人心中的地永远是庄稼,而年轻人则以急功近利的方式对待土地,将其视为挣钱的捷径。诗歌传达出一种农业文明的哀歌,也看出诗人对人于大地上自然劳作状态的守护。
其次,城市空间遵循的消费逻辑将一切视为占有和消耗的对象,人在商业化社会之中失去原有的情感关系,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在城市化的商业性之中,一切纯洁和崇高的对象都会被污染和抹平。生活在彼岸,空间的区隔恰好制造了人类本性的渴求和欲望,漂浮的欲望没有根。流竹诗中的“城市”只是充满压抑和欲望的空间,比如《鸟瞰城市》中,人们在城市空间中是混乱的、迷茫的,“人们晕头转向,迷路,失去自我/ 分不清生存与生活的关系/ 懒得理爱情与情爱的关系/ 他们只愿把床弄得夸张地响/恨不得把激情一夜耗完,然后/ 冷静地离开陌生的彼此/ 在生存的轨道上,跟着上帝的筷子/ 转向,转向。”[5]12上帝筷子的搅动牵引着所有人的步伐,因为他们除了情欲之外就是名利场的生存而已。城市之于人来说,意味着“生命在变质”,欲望在蔓延。庞华通过诗歌写出现代生活的消费化倾向,“红高跟鞋”可以被清炒和“破黑皮鞋”可以被炖成汤,这是男女身份和欲望的符号。“红黄绿三色交通”本应该严格遵守公共秩序可以变为喝的“混乱酒”;充满禁忌和敬畏的“骨灰”被调制成新鲜的“败火水”;背景音乐充满欲望与死亡的迷狂。最后的主食(“新闻主食”)是消费人世间种种悲惨事件的“大拼盘”。[18]60城市高房价以及背后的商业逻辑将人“动物化”。老德的《蜗居》这样写道:“一间卧室躺着/ 一条蛇和一只壁虎/ 另一间卧室住着一只蛙/ 在客厅的鱼缸里/ 还游着十七条热带鱼/ 中午了 这些/ 冷血动物才会起床/ 爬到餐桌上/ 吞噬着一些比它们/ 更小的动物/ 有时也会/ 放下筷子/谈谈华尔街的金融危机/ 今天太阳很好/ 这些小动物商议/ 明天是否该早起/ 开车到郊外去踏踏青。”[5]100陆地动物、两栖动物和水生动物之间少有交流和共处的可能性,这就是城市里合租于紧张空间里的人群写照。动物化的人之间互相攻击蚕食,吃饱后思考的依然是金钱的欲望。即便是“踏青”这种回归自然的行动依然是通过“汽车”来完成。玉上烟《野花》写出城市空间以欲望的方式糟蹋着自然纯洁之物,乡村空间里的生活的野花“菊儿,小桃,山杏,玉兰,红梅”离开村庄,在城市的夜幕下,变为发廊、洗浴中心等情欲场所的床单上的“花花绿绿”,浓烈的香水遮掩了“与生俱来的香”。[5]108天然植物指代乡村女性,她们被城市空间的商业气息所污染。同时,城市扩张消解着文化中的“崇高性”。东篱的《碑影》以唐山地震后修建的“抗震纪念碑”为对象,写出城市化及其背后的商业资本对城市空间布局的瓜分、支配。狂躁的城市犹如“冰冷的塔吊”伸出“膨胀的欲望之手”不断向自然攫取,“土地已瓜分殆尽/ 新的势力范围,早在密谋敲定中/ 白云老无所依/ 小鸟狭窄的航线被挤占/ 风只能在庞大灰森林的缝隙间/孤独地哀嚎”。城市化进程坚定不移的步伐中,“抗震纪念碑”即便代表着经历苦难的亡灵,携带着国人心灵中的创伤,依然无法避开城市“围剿的步伐”,“纪念碑广场终将成天井/ 日夜被四周巨大的阴影/蚕食”。[9]98-99城市化与城市空间背后只有利益和欲望,所有的伦理精神和崇高符号都在蚕食中变为“天井”。城市是失去信仰和追求的,黑光《暮晚》中的意象表征便是“肥胖”。“我们的城市个个肥胖/ 孩子也个个肥胖/ 如果有一个瘦的/一定是在教堂受洗过的那个小孩/ 他的两条细长腿像双筷子/ 总是替我夹起青菜一样清淡/ 的礓礤小路——/ 在暮晚的斜坡上”。“肥胖”成为城市人精神臃肿的符号,受到信仰洗礼的人是清瘦的,因为他懂得舍弃对物质生活的贪欲。然而,即便是这样轻灵的、清淡的“小孩”是在“暮晚的斜坡上”,[16]147随时滑向城市文化制造的漩涡。宁延达在《我惊愕于这样的生活》中批判城市将我们生活深深地异化,让我们陷入金钱、虚伪、信仰缺失、崇洋媚外、毫无道德底线等。“我惊愕于这样的生活/ 一天不能赚取钞票便多一层忧虑……我惊愕于这样的痛苦/ 城市越来越光鲜/而人们迷失于坚守的主义/ ……惊愕于越来越多的寺庙/ 拯救不完烧高香赎来的命运”。[6]107现代化的城市文明看似繁荣,背后带来的却是真真实实的精神危机:工业文明对环境的破坏、商业文化对人自私的彰显、城市空间对人与人淳朴关系的肢解。
网络诗歌自诞生起已然处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之中。故而,它对于空间的理解和表现不同于网络小说。网络小说将乡村视为落后愚昧的意象,将城市塑造为“进步都市主义”,[21]而网络诗歌则祛除了乡村空间保守落后的维度,将其表达为“田园牧歌”式的精神栖居场所。对城市空间的言说,除了上面所说的“欲望化”和“破坏性”书写,还有更为复杂的维度:意义空心化。王鹏程认为对“城市”生成的价值判断与人性内在矛盾情感相关。“‘乡下人’在城市时,城市充满诱惑和罪恶,乡土则充满温情,令其眷恋;一旦回到乡村,乡村则是穷山恶水,令人厌恶,城市则成为现代和文明的象征,令其无限向往。这价值观念上钟摆式的摇晃,固然有农耕文化所积淀的‘排斥乡土——依恋乡土’的矛盾的心理情感结构”。[22]网络诗歌中,乡村空间属于漂泊异乡者精神归属的“母体”空间,它为文学主体创伤的心灵提供的慰藉;城市空间是具有“弑母”倾向的“子体”空间,它以“资本”“欲望”和“技术理性”作为自己的表征。当网络诗人在进行“原乡”书写时,即将乡村视为人性的、自然的、健康的和“纯洁”的孕育场所,顺理成章地会以二元对立的思维对城市进行判断,城市往往被言说为“污染”“欲望”和非家园化的象征。
文学并不是对空间景观的单纯反映,文学的审美想象对空间建构是一种反向“赋义”。网络作家凭借直觉和想象建构起来对空间的审美意象。在网络诗歌的城市书写中,我们看到的是标榜科学、理性和进步的启蒙现代性给当下人的处境所造成的焦虑。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在诗歌意象上的不同表征,本质上折射的是网络诗人对待现代化存在的矛盾心态:希望人民能享受到现代生活的福利,又担忧灵魂跟不上变化的节奏。[23]3两种空间之间是一种不连续的断裂关系,其背后有工业化、商业化和技术化扩展等带来的后果,正如卡林内斯库所说,现代性带着一个最根本的使命就是“与生俱来的通过断裂与危机来创造的意识”。[24]鲍曼也认为现代性社会追求的是确定性、清晰性、连贯性、合逻辑性。然而,真实世界是一种情境化的存在,不可能天生是秩序性的。换句话说,事物的秩序是非自然的。艺术天性携带的“秩序的非自然性”便将现代性设计所追求的目标与其反作用的“他者”揭示出来,即“不可界定性、不连贯性、不一致性、不可协调性、不合逻辑性、非理性、歧义性、含混性、不可决断性、矛盾性”。[25]值得庆幸的是,网络诗歌对空间断裂性往往采用的是弥合式的诗意书写,比如边宗的《在一座花园里安顿自己》就脱离具体空间的情绪书写。“就把世界当成一座大花园/ 逛完刚好用去一生的时间”。[26]空间在诗人这里并没有分别,只是一个人徜徉其中的心灵居所。“逛”其实就是一种“散步”的心态。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之所以将“美学”与“散步”并置,其意图是将诗意的、美学的存在状态表达出来。“行走”具有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功利目的,而“散步”并非为了到达某个地方,其意义就是到达的过程之中。故而,诗人将人所生存的空间诗意化,唯有诗意化的审视才可以将乡村和城市空间之中的异质性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