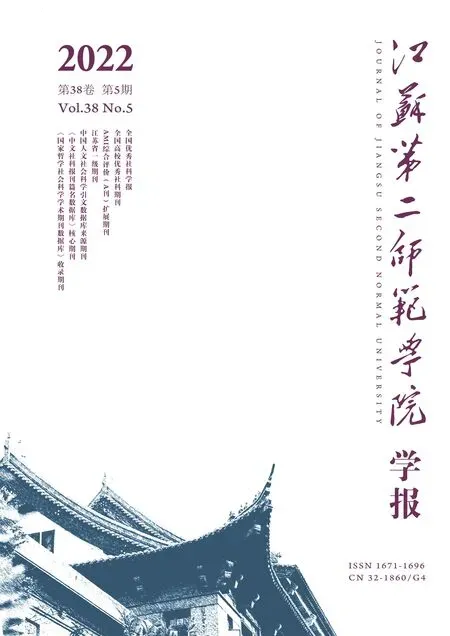从美女之死到向死而生
——爱伦·坡小说中的女性生命*
徐 薇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1200)
一、“美女之死”
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爱伦·坡倾其一生来打造理想之美,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近乎完美的女性形象。《椭圆形画像》中画家的妻子是举世无双的美人,像幼鹿一般爱淘气;纯洁无瑕的艾蕾奥瑙拉美得像天使;贝蕾妮丝敏捷、优雅,充满活力;莫蕾拉学识渊博,智慧无双;丽姬娅容貌恬淡灵秀,内心激情似火……在坡笔下,这些女性形象无一不具备无与伦比的美貌、完美无缺的性格、不同凡响的才华,这种极致的美似乎不属于俗世的凡人,而应属于梦中的女神、丛林的精灵或是水中的仙子。
坡钟爱塑造美女,却又不遗余力地将这些美女置于死亡的阴影之下。女性的生命是那么美,却又是那么脆弱。画家的妻子被幽暗的画室摧残了身心,在画像完成的瞬间倒地而亡;艾蕾奥瑙拉红颜薄命,早早撒手人寰;贝蕾妮丝身染顽疾,时常癫痫发作;莫蕾拉柔弱憔悴,在生育中衰竭死去;丽姬娅更是形销骨立,病入膏肓……
爱伦·坡热情地赞颂了女性的美,却也冷酷地摧毁了美。在《创作哲学》中,坡鲜明地提出了“美女之死”的主题。他指出“当其(死亡)与美结合得最紧密的时候”最具诗意,由此,“美女之死无疑是天下最富诗意的主题”——而这主题如由悼念亡者的恋人口中说出则再恰当不过了[1]251。坡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美学理念,美女与死亡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同时这也不可避免地为其招致了不少非议。在坡笔下,完美的女性逐渐失去生机,她们脸色苍白,头发凌乱,目光呆滞,双唇干瘪,最终都走向了死亡。坡在“美女之死”的故事中所设定的女性命运在急切地向世人做出某种警示。
二、多舛的女性命运
坡的小说每每凸显了多舛的女性命运,勾画出一道道极为相似地从美女到亡妻的命运线。坡似乎在不厌其烦地做出暗示:女性的悲剧大多由男性造成。波伏娃曾说过,“爱情被看作女人的最高使命”,女人视男人为天主,“习惯于跪着生活”[2]529。尼采也在《快乐的科学》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女人对爱情不顾一切,“不仅仅是忠诚,这是身心的全部奉献,毫无保留”[2]496。《椭圆形画像》中画家的妻子“心里那么爱着他”[3]143;艾蕾奥瑙拉难以掩饰“激动心弦的热恋”[3]130;贝蕾妮丝长久地思慕着埃加乌斯;莫蕾拉则远离社交,一心专注于丈夫……
一旦爱情成为女性的生活全部,那么与爱情捆绑在一起的女性命运就注定走向悲剧,因为“爱情在男人的生活中只是一种消遣”[2]496。《椭圆形画像》中的画家只钟情于艺术,即使妻子作为模特终日被他“凝视”,他也注意不到妻子的萎靡消瘦;艾蕾奥瑙拉的那位信誓旦旦的情人更是轻而易举地移情别恋;埃加乌斯非常确信自己从来没有爱过贝蕾妮丝;莫蕾拉的丈夫甚至无法忍耐妻子手指的触碰,无法忍受她的声音、她的眼神……《丽姬娅》中的丈夫看似深情,实则自私凉薄。即便丽姬娅将她的全部爱情和财产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丈夫,丈夫也记不得是在何处与她邂逅,甚至连她的姓氏也一无所知。丽姬娅的病重貌似对丈夫影响极大,让他手足无措、痛苦崩溃,但他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妻子的命运,而是自己的幸福;他关心的也不是妻子的病情,而是惶恐自己的安逸或将随之中断。当丽姬娅在临终前紧握住丈夫的手,“倾吐泛滥胸怀的衷曲”,抒发“强如热恋的痴情”时,他竟表现得怯懦软弱,只会埋怨着自己“活该倒霉”[3]22。
这种反差几欲令人发指。男人们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妻子对他的爱情,却吝啬给出一丁点的回报。莫蕾拉临死前的控诉振聋发聩。“啊,多么少!——这就是你对我,莫蕾拉的感情!”[4]154无爱的婚姻使妻子饱受摧残,男权社会下的生存困境让女性举步维艰。故事中的男人们冷漠而胆怯,如火如荼的爱情让他战栗,一往情深的女人令他畏惧,他不仅无法给出爱的回应,反而成为谋杀妻子的直接或间接的凶手。在这种境遇之下,死亡的阴影已经弥漫在女性呼吸的每一寸空间,每时每刻、朝朝夕夕。
三、异化的女性生命
坡塑造的美女热爱生活、亲近自然、向往真理,可惜,故事中没有哪位女性从男性那里得到真情厚爱,却无一例外地被男性扼杀了生命力。丽姬娅迥乎寻常的才学远远超过她的丈夫,丈夫“像孩子一样安心,听凭她指导”[3]21。莫蕾拉的卓绝才华足以使丈夫在很多事情上成为她的学徒,“缠绵在她身旁”,“受她指引,并坚定不移地进入了她深奥复杂的研究中”[4]153。但是女性的知识和思想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好运,反而由此导致的夫妻主从地位的改变引起了丈夫的警觉。“快乐突然隐入了惊恐,最美丽变成了最可怕。”[4]153敏感的男人被愤怒、厌恶的情绪所驱使,他不再接受来自妻子的教诲和同化,与妻子愈加疏离。无论是在画室,还是塔楼、古堡……,被孤立的女性最终离群索居,被丈夫、被婚姻囚禁在了一方狭窄之地。
如果说,“美女之死”由悼念亡者的恋人讲述最是让人震动,那么“美女之死”由其来实施则更是让人胆战心惊。贝蕾妮丝的丈夫执拗地认为妻子的“每一颗牙齿都是思想”[4]135,这思想让他嫉恨,让他疯狂,让他妄图掠夺占有。莫蕾拉的丈夫更为直白地向妻子发出死亡的诅咒,“在热切而强烈的渴望中盼着莫蕾拉死去”[4]154。在坡的故事中,男女双方走向了最终的决裂,女性的命运被推向了死亡。坡不惜笔墨地讲述女性的惨痛,甚至刻意凸显女性的疯狂。他几乎架空了所有故事的历史时空,并由此创造出这一共性的特征。他用尖锐的笔触去揭露真相:在喧嚣的世界中,女人孤独地活着,天性被压抑,才华被无视。她们没有生存的空间,冰冷的婚姻终将成为她们孤寂的坟墓。她们的生活已经变成一片虚无,死亡渗透在生命的每一次喘息之中。
画家的妻子生性温良,乖乖服从了喜怒无常的丈夫的所有指令,直至最后生命被封印在三尺画布之中。单纯的艾蕾奥瑙拉轻信恋人的誓言,甚至感动得“痛哭流涕”,“安心等死”,最终成为一抹幽魂[3]131。在男人眼中,她们不过是个孩子,是被男人摆布的玩偶,是被男性驯化的工具。顺从、忍耐、宽容、忘我、奉献、牺牲……这些被男性标榜的女性美德给她们带来的只有灾难。而事实上,这种所谓的完美女性已经化作符号弥散在整个男权社会里。坡通过一个又一个故事,一个又一个血的教训警示世人:被驯化的女人注定将失去生命的本真。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生命的“异化”。
在层层的重压之下,坡近乎逼迫般地将女性置于生死一线的选择之中:是恭顺认命地死去,还是奋力挣扎着寻求新生?如果说画家的妻子和艾蕾奥瑙拉屈从了前者;那么后者则是莫蕾拉、贝蕾妮丝和丽姬娅的抉择。
四、向死而生的生命体验
坡对女性的悲惨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在揭示女性悲剧宿命的同时,更竭尽全力为女性开启新生。他以此鲜明地告知世人,死亡并非是女性的唯一结局。即便如画家的妻子和艾蕾奥瑙拉一样沦为了男权社会的牺牲品,莫蕾拉、贝蕾妮丝和丽姬娅仍在死亡的威胁下坚持了自我,甚至以死亡否定了女性存在的无意义。她们品尝了死亡的滋味,她们奋力抗争,置之死地而后生。
丈夫亲手把莫蕾拉送入了坟墓,莫蕾拉也决然地在弥留之际诅咒了丈夫的命运,“你的日子会充满痛苦——那痛苦是最持久的感受,就像柏树是最不朽的树木”,“你快乐的时光不复,生命中不再有喜悦,不像帕斯图姆的玫瑰能一年盛开两次”[4]154-155。死去的莫蕾拉借助女儿的身体重生了,从此丈夫命运的星辰从天际陨落,永远摆脱不了莫蕾拉的阴影。
贝蕾妮丝在神志昏迷时就被活埋,甚至还被偏执的丈夫残忍地拔下三十二颗牙齿。孱弱的贝蕾妮丝面对丈夫的暴行发出了尖利而刺骨的叫喊,并进行了殊死抵抗。即便坡没有直接进行场面的描写,读者也能从丈夫满是泥泞和血迹的外衣以及被用指甲抠过的道道痕迹中想象出这场搏斗的惨烈。在暴行过后,贝蕾妮丝“被寿衣覆盖的丑陋身体还在呼吸——心脏仍然跳动”[4]136,她不甘心就此死去,倔强地活着,从死亡中重生。
垂死的丽姬娅绝不肯向命运屈服,她满怀热切的企盼,甚至可以说是满腔的怨愤,高举双手,对天发问,“难道这种情况始终不变?——难道这个霸王永远称霸不成?难道我们不是上帝您的骨肉?”[3]24她坚信意志的永生不灭,“凡人若无意志薄弱之缺陷,决不臣服天使,亦不屈从死神”[3]24。故事的最后,丽姬娅神秘地借尸还魂了,重返那条曾无情地舍弃了她的人生之路。
被丈夫送入坟墓的女人,如同复仇女神一般,从死亡中归来。坡承认了女性的成长和强大,并将最终的胜利赋予了女性。无论是莫蕾拉、贝蕾妮丝,还是丽姬娅,坡笔下的这些女性都表现出卓绝的勇气和反抗的精神。她们都经历了死亡,但死亡并未使她们绝望,反而成为她们反抗的手段。她们勇敢地直面死亡,忠于自我,遵从内心。在死亡的体验中她们获悉了生存的意义,验证了生命的力量,认识了自我的价值。通过死亡,她们告别了过去,摆脱了恐慌,重塑自我,获得新生。
五、觉醒中的女性生命意识
女性命运的改变有待于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生命意识是指生命个体对自我生命的自觉认识。女性的生命意识在经历过觉醒和发展,创造出独属于女性的生命经验,才能真正改变女性沉默的社会边缘化传统。在坡的故事中,这些“被剥夺”“被压迫”甚至“被死去”的女性的精神主体在死寂中复苏,在苦难中成长。这些女性披着带血的尸衣重返人间,她们强大的毁灭性力量颠覆了男权社会的生存法则,成为对男性而言未知的、不确定的、不可预测的、陌生且极具威胁的存在。她们被赋予了涅槃重生的勇气,她们的向死而生体现了女性主体拥有强大的生命潜能,也彰显了女性生命特有的价值。
“死亡可能成就一种脱胎换骨,成就一种超现实的降临,也成就一种新意义的产生。”[5]194坡在《莫诺斯与尤拉的对话》中也曾提出过死亡的净化作用,“对于这个整体上染疾的世界,我看只有在死亡中才有可能新生”[6]508。坡重构了生命的形式,以死亡为起点重新诠释了生存的意义。对于坡而言,死亡已经成为获得精神不朽的唯一途径,死亡正是新生命的开始。对于坡笔下的女性而言,这是穿越坟墓方才获取的新生,也是突破男权社会的藩篱方才寻觅到的生命的入口。
“一切死亡都是诞生,正是在死亡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生命的升华。”[7]在以“美女之死”为主题的小说中,坡深刻地反思了女性的生命形式和存在方式,他肯定了女性生命的价值,彰显了女性生命存在的意义。反抗压迫,“向死而生”,实现自我生命的升华,这是坡给予女性的最珍贵的生命体验。坡相信,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女性生命仍在顽强地生长,执着向前,渴望超越。
坡铺陈了女性的死亡,宣泄了女性的悲愤,同时也唤醒了女性的生命意识,为女性开启了新生。在女主人公们睁开双眸,重返人间的瞬间,坡的故事戛然而止。重生的女性的命运将通往何方?坡没有告知读者答案。坡不屑于去预知重生者的未来,也无兴趣再做出新的安排,他要将女性的命运真正交在她们自己手中。他相信能够从死寂中突围出来的女性有勇气,也有力量去重塑一个自己,重写一段人生。放手由她们创造一个明天,这也是坡留给世人,留给弱者的一份感性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