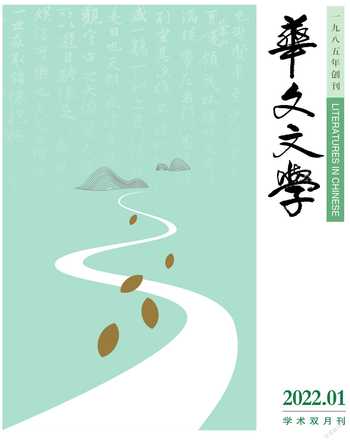文本内外:茅盾的《腐蚀》与香港
陈蓉

摘 要:1941年茅盾在香港创作的《腐蚀》,因文本选取的人物、背景以及整个故事的进展没有表现香港而被认为是“和香港无关”。而从作者、作品、读者、編辑的关系出发,结合文本,可以看到茅盾采用了一种站在香港读者立场、并积极将读者的阅读趣味纳入创作思考之内的书写方式,《腐蚀》的创作和发表与香港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主体三个部分分别阐释了抗战时期香港读者群建构与对作家的具体影响,促成《腐蚀》能够迎合本地读者,使得茅盾在香港的小说写作转向的两个条件,以及《腐蚀》在形式和内容上所体现的香港因素。
关键词:茅盾;《腐蚀》;香港;读者;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2)1-0005-09
抗战时期茅盾曾有两次较长的香港旅居经历,除了编辑《文艺阵地》、《立报》副刊《言林》以及《笔谈》外,他还发表了长篇小说《你往哪里跑》《腐蚀》,短篇小说《某一天》,另外还有大量的短论、书评、杂文、札记等等,可以说是非常多产的①。但与之相对的是茅盾这一时期的创作所遭到的单一评价:他的作品往往因政治色彩浓厚而被和谐地纳入他整个政治书写的圆圈中,形成了一个闭环,而内里隐含的香港因素却消匿了,成了文学史中“与香港关联不大”②的存在。以《腐蚀》为例,现有最多的解读就是从茅盾的政治立场出发,或以叙事学、女性主义、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文本。借用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框架来看《腐蚀》的研究③,显然作家、作品、世界三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研究者关注最多的,这样的研究固然有其学理性和系统性,但仍稍显不足够,比如过于侧重文本内部的世界——重庆,而忽视了文本产生和面向的世界——香港;读者与作家、作品之间是怎么样互相而非单向作用的专门研究较少等。作为“茅盾创作中读者意识最强、读者与作者互动最多的一部”④小说,要客观评价《腐蚀》以及茅盾在港期间的创作,他为入乡随俗所作的文艺调整,有必要先回到文学生产的历史现场,将抗战时期的香港读者群构建带入考察,并借此打开重新解读《腐蚀》的路径。
一
香港的新文学萌发较晚,也没有产生可以称为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的标志性“断裂”。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虽然已经呈现新文学兴盛的景象⑤,但新文学土壤还是贫瘠的:一方面,热心新文学创作的作家主要集中在有限的青年学生圈子内,如当时最活跃的本土新文学作家谢晨光、龙实秀、侣伦、张吻冰、岑卓云、易椿年等,都是初登文坛的新秀,除了极个别的作家作品,大部分仍显稚嫩,没有形成独有的风格;另一方面,在一般市民间新文学处于边缘地位,读者对白话文的接受度较低,如平可所说,“中年以上的人几乎都反对白话文。许多青年也反对白话文,纵不反对,也认为白话文会贬抑中文的价值。”⑥由于先天不足,香港的纯文学杂志少之又少,仅有的新文学杂志如《伴侣》《铁马》《小齿轮》等发行的时间很短⑦,文学作品的主要发表途径是报纸副刊,但是在茅盾眼中,这些报纸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香港的报纸很多,大报近十种,小报有三四十,但没有一张是进步的……除了几份与香港当局有关系的大报外,其他都是纯粹的商业性报纸,其编辑人眼光既狭窄,思想也落后。至于大量充斥市场的小报,则完全以低级趣味、诲淫诲盗的东西取胜。⑧
客观说,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能完全归因于编辑人的眼光狭窄和读者欣赏水平低下,而要与香港的历史实际结合起来看。毋庸置疑,香港有着与祖国大陆不可分割的文化传承,但港英政府的长期管治和华洋杂处、人口频繁流动的社会现实,也孕育出了自己的特色,造成文学发展与母体的不同步。20世纪初期,港英政府实行的统治策略使得中文一直受到压制,直到1926年,总督金文泰提倡中文教育,才创办了香港第一所中文学校——官立汉文学校,香港大学也增开了华文科。但由于官立的中文学校数量少,且教授的仍是传统中文(旧国学),与同时期的内地相比仍是落后不少的,因此有不少本地青年北上入读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的大学⑨。以上海、北京这些城市的文化标准来看待香港,南下的作家们难免会感到大失所望,如茅盾所言“似乎进入了一片文化的荒漠”⑩。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加剧,尤其是上海、广州的相继沦陷,导致大量难民涌入香港。这些战乱移民往往是举家迁移,且带有一定资产,和早期南下的单身且受教育有限的劳工不同。人口的激增,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金技术,也导致香港的教育面貌发生变化,如私立中文学校的大量出现。有资料统计,1930年香港的中文学校学生有45436人,英文学校学生有17561人,到了1938年在校学生人数已经超过11万,而在中文学校肄业者多达83000多人,这一数据到了1941年还在持续扩大{11}。中文教育的发展无疑有利于智识阶层的扩大,尤其是作为新文学主要拥护者的青年学生及拥有一定教育基础的产业工人人数激增,此外,移民或流亡者中不乏一些接受过良好教育、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士。
由于受教育、经济、年龄、性别等因素影响,读者的阅读趣味未必完全统一。岑卓云回忆,抗战初期香港一般市民喜欢的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三类是:豹翁用古文写的黑幕小说,灵箫生延续徐枕亚派风格的哀情小说,以及黄天石以杰克为笔名发表的通俗文学作品。豹翁的作品色情气味很浓,读者很多,大都是三十岁到五十岁的男性中年人;而灵箫生的作品用的是浅文言,亦能吸引不少香港和广州的读者。{12}这两类正是茅盾所极力批判的“诲淫诲盗”、“低级趣味”的作品。1939年8月18日《国民日报》刊载了王幽谷的一篇《怎样在华南写小说?》,他转述兄长小说家王香琴的话,“华南读小说的人,欢喜曲折而离奇的事实,尤其,言情以及社会写实的小说,最会得欢迎。”{13}由此可见,当时一般读者在小说阅读上的趣味已引起创作者的注意。
如果说上海能够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是与此时在上海形成了一批初具规模的文化消费群体密切相关的话{14},那么,在香港,读者群体的扩大和构成多元化,读者的阅读趣味也必将与文学发展紧密关联着,从而影响在地作家的创作和整个文学生态的面貌。王幽谷就曾给外来的“北方的小说作家”提议:“在华南写小说,不论文言白话,只要大众化,有场面,事实广而曲折,对上中下人都能有所描写,尤其,注意一点总标题,要醒目,能引人入胜,那自然博得读者去看!”{15}显然,他是以读者而非审美或政治宣传的目的为导向来指导小说的创作。
值得留意的是,也正是在1938-1941年间,早期曾积极推动新文学创作的黄天石、岑卓云、张吻冰等本地作家发表了不少通俗小说。有研究者将这种变化归因于南来作家的“排挤”,使得本就艰难求存的本土新文学作家无法在文坛立足,被迫转向了通俗文学的创作,这无疑是有失偏颇的:黄天石在1934年已经开始发表他的“港岛传奇”,而南来作家云集香港则在1938年之后。更何况,通俗化转向在香港也算不上是“倒退”,这恰恰说明,无论是外省作家还是本地的新文学作家,都面临同一个困境:在一个商业性很强的城市,作家要如何处理创作和读者的关系。
岑卓云是该时期非常受欢迎的小说家之一,1939年他开始为《工商日报》的副刊《市声》撰稿,有过以下一番思考:
我从事创作时老是有意无意地以“自己”为中心,所写的是自己喜欢写的东西,而自评优劣时也以自己的喜恶为标准。但我逐渐察觉:这个态度只能适宜于撰写留供自己欣赏的文章;如果文章是准备发表的,那就不能不理会读者。{16}
正是由于这份对读者的认识,他发现《工商日报》大部分读者是在工商业服务的人,于是以笔名“平可”连载的小说《山长水远》就是以一个三十余岁的男子为主角,表现他赤手空拳在香港的工商界打拼的经历。除了岑卓云,张吻冰以笔名“望云”在《天光报》连载《黑侠》,原因也是考虑到《天光报》是“入家庭”的报纸,内容要通俗。《天光报》属于《工商日报》集团,是当时香港销数最多的报纸之一,主要面向的读者是家庭主妇和已在社会做事的成年人以及学生,而黄天石、张吻冰和岑卓云等人就是为它撰稿的主要小说家。所以说,本地的新文学作家们的通俗化转向是基于广大的、多元的本地读者的阅读趣味所做的一个调整,也因此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而作为旁观者,本地作家还看到了当时的南来作家存在的问题:“他们的作品对典型的香港市民缺乏吸引力,而当时一切报刊所努力争取的读者正是人数众多的典型香港市民。”{17}对南来作家来说,要适应香港的文化气氛,即便是有《怎样在华南写小说?》这样的写作指南,但要成功做到迎合读者也非易事。以茅盾为例,在《腐蚀》之前,他已经在香港连载过长篇小说《你往哪里跑》,当时他就秉持着要顾及香港的读者水准而又能提高读者的原则去写作。但很快茅盾就意识到,如何能让阅读趣味偏向武侠神怪色情、对抗战生活疏远的读者接受自己,并不简单,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不能为那时的香港读者所接受了”{18}。从茅盾创作《你往哪里跑》的经历可以看出,如何在作品中融合香港本地色彩,让读者感到亲切,对南来作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1938年的茅盾,即便有心也无力写出能让自己满意也让读者满意的作品。直到1941年茅盾再次到香港后,他反思自己的创作要吸引“本地读者”——包括工人、知识界和一般市民三个层面亦即岑卓云所谓的“典型的香港读者”{19},并适时适地调整自己的写作方法,从而成功催生了颇受读者欢迎的小说《腐蚀》。
如果只是将《腐蚀》与香港读者的联系局限于茅盾的读者意识上,是有些单薄的。单从读者认可的角度去看,《你往哪里跑》的失败和《腐蚀》的成功{20}反映的并非是茅盾读者意识的有无,而是这一客观事实背后隐含的推动因素。在对《腐蚀》的文本做进一步的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厘清促成《腐蚀》能够迎合本地读者,使得茅盾的书写转向的两个条件。
二
连载小说常常被报章杂志当作吸引读者、增加发行量的一种手段,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可以憑借一部连载小说带动报刊的热卖,这也是抗战初期转移到香港办刊的南来文人宣传抗战的策略。茅盾创作《你往哪里跑》的起因便是萨空了希望他在《立报》副刊《言林》连载一部长篇小说:“一则可以吸引读者;二者也有利于版面的调剂”{21},萨空了相信名作家的小说可以带动《立报》的销路。《腐蚀》的产生也如出一辙:“有人提出刊物最好有一连载的长篇小说,内容能够吸引香港的读者,否则,全是硬性的政论文章,他们接受不了,就会影响到刊物的销路。”{22}作为进步报刊的《立报》和《大众生活》虽然本质上和香港的一些娱乐消遣性很强,追求盈利的商业报章不同,但是争取读者仍是他们的目标,有了读者,观念才能传播出去。
茅盾的这两部小说都与负责连载刊物的编辑有着密切联系,但最后的结果却不同。萨空了是《立报》的总编辑,他向茅盾邀稿时就鼓动他写一个“通俗形式”的长篇:“香港的读者水平很低,你就写一部通俗化的小说”{23}。茅盾的创作思路是受到萨空了的影响的,虽然最后这个“通俗化”并没有成功实现,《立报》更是日渐艰难:“那时候《立报》销路不好,天天赔钱,大有维持不下去的样子。原因当然是《立报》‘孤军作战’,敌不过那些盘踞香港几十年的黄色小报。”{24}而本地的研究者看法显然不同:
外省报人来港办报,最终铩羽而归,如邹韬奋的《生活日报》,大抵疏忽了当地(香港)的报纸必须具有当地的地方色彩,方便吸引读者的亲切感。一味怪责读者的程度太低,算不得公道话。且有时环境特殊,报纸读者口味亦异,也会造成外地人来港办报,有时会患上“水土不服”。{25}
“水土不服”是存在的现象,但南来报人未必是顽固不通变,或是抱着“将在国内适用的思想原封不动地搬到香港来,视之为天经地义”{26}的中原心态。笔者认为,作为个体的编辑和作者在入乡随俗方面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萨空了要求“通俗化”的主张可反映出他的在地关怀{27},但他初次到港,虽认识到香港读者水平低,却还没有更多的写作意见给茅盾,且他在《立报》复刊四个月后就离港转赴新疆。茅盾亦于同年12月前往新疆,《你往哪里跑》只得匆匆收尾。与此相对的,《腐蚀》的创作和发表就体现了《大众生活》的主编邹韬奋和茅盾的努力改进。
1936年6月邹韬奋在香港主编《生活日报》,日销曾达到两万户,订户遍及全国和东南亚各地,但不到两个月后就因经济困难迁回上海。因为有前车之鉴,第二次到香港开展文化工作的邹韬奋对香港的在地文化有了一定认识:
他不止一次说过,他办刊物的经验是亲自抓“一头一尾”。“头”是社论,“尾”是答读者来信……而他花精力最多的,则是“答读者来信”。有一次私下谈话,他对我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是脱离群众的,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要接近群众也不容易,所以我只能从读者来信中摸到一点群众的脉搏。”{28}
显然,邹韬奋是很清楚自身“脱离群众”的弱点,但短时期内想要获得本地读者认同实有困难,此前南来文人在办刊和创作上已经多次碰壁。夏衍在广州办《救亡日报》时就曾感慨“人生地疏,语言不通(当时广州对于大批涌到的‘外江佬’是看不顺眼的)”{29},更何况是较广州更为边缘、有着几十年英国殖民管治历史的香港。所以邹韬奋才通过“答读者来信”的方式去沟通刊物与本地读者的联系。
《大众生活》发行30期(1941.5.17-1941.12.6),据笔者统计,“简复”{30}共收入约166则读者来信的回复,读者来源分布如下表:
由表格可知,“本港读者”(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数目最多,如第5期的4则“简复”全部是来自“本港读者”,第19期14则“简复”有11则来自“本港读者”。可以说《大众生活》主要面向的应该是以港澳地区和南洋华侨为主的读者群,约占总数的91.6%。而来信的主题五花八门,大至政治和政治人物议题,当下的中国抗战及世界局势问题,也有非常多的来信关注个人的求学、职业发展、婚姻爱情、妇女工作、人际关系等问题。“读者信箱”和“大众之声”也有不少带有鲜明的本地因素的来信,如第14期的“我校的□□”{31},读者就是一名香港本地学校的初三学生谭智生,此外还有第23期的“改善教师生活”,第24期的“一个女人的历史”等等。在108则本港读者来信中,读者的身份包括青年学生、工人、妇女、小学或中学教员、图书馆职员、商人、来自沦陷区的难民等。这反映,与主要在青年学生间产生影响的《立报》不同,《大众生活》的读者群构成更宽泛,而且本地读者一直是刊物的主要拥护者,也是《腐蚀》所面向的主要读者群体。
邹韬奋还会根据读者的一些要求调整刊物,茅盾原本计划是写一个中篇小说,写到第14期小昭被害就结束了,结果“读者们要求给她一条自新之路。《大众生活》编辑部接到这样的读者来信一天多似一天,以致编辑部终于向我提出,要求我予以考虑……发行部要求我多拖几期……我不能不接受这两方面提出的对于我的要求。”{32}读者和编辑对作者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编辑作为文学生产的重要一环是促成《腐蚀》向本地读者靠拢的外部因素,那么抗战时期茅盾“文艺大众化”思想的变化,则作为内在动因影响了《腐蚀》的创作。茅盾对“文艺大众化”的关注可以追溯到30年代初左联时期,1932年他曾就文艺大众化问题与瞿秋白展开了争论,最后争论不了了之,不过通过《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一文初次表明了他对文艺大众化的认识:作家们要努力使用大众的语言创作大众读得出听得懂,能够接受的文艺作品,手法上要多动作少抽象暗示的描写{33}。但是,这一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还是较多的限于文人圈子内部的讨论,在实践的意义上缺乏代表的作品。此后,茅盾也没有停止思考“大众化”、“通俗化”的问题,他对文艺大众化的理解是在理论构筑和创作实践中不断变化和完善的,实际上,1938-1941年间他在香港创作发表的两部长篇小说就与他的理论思想变化有着紧密联系。
1938年初茅盾南下广州,又辗转经长沙、武汉到汉口,途中他看到这些地区的作家们深入民间,创作了不少新粤讴、新编湘剧和新鼓词,感触很深。很快他写下并发表了《关于大众文艺》《关于鼓词》,提出大众化要吸收民间文艺的基本要素,即:故事的逐步展开,秩序井然;主角和配角分明,以故事系于人物,人物为骨而以故事的发展为肉;抒情和叙事错综融合{34}。而同年2月14日茅盾在汉口作的一次《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演讲中,更加明确了大众化的核心。他认为,大众化就是用各地的方言,大众的民间的艺术形式来写作品,必须从文字的不欧化以及表现方式的通俗化入手。他还列举了符合大众化形式的几个原则:故事要从头到尾说;要抓住一个主人翁,故事以主人翁为中心顺序发展;多对话和动作,故事的发展通过对话叙出,人物的性格则用叙述的说明{35}。
虽表述略有差异,但无论是学习民间文艺还是大众化问题,茅盾所关注的主要是“形式”问题,是围绕语言、叙事展开的,而稍后不久创作的《你往哪里跑》就是这一理论的实践。当萨空了提议让他写一个“通俗形式”的小说时,茅盾遵循的就是“形式上可以尽量从俗,内容上切不能让步”的原则,“力所能及地把一些典型的人物事态组织进去,同时在形式上做到‘通俗化’”{36}。比如,小说的语言尽量去除欧化色彩,做到通俗易懂,行文上模仿了传统小说常见的“说书”形式等等。即便有这一番努力,茅盾在写到一半就意识到自己写失败了:“失败在内容,也在形式”{37}。
《你往哪里跑》為何失败,如何失败在此不欲扯开细说,但确实是这一次的失败,促使茅盾再次反思大众化的问题,1938年的香港文化生态也让他明白:文艺大众化仅仅从形式包括语言上着眼是不行的,必须同时解决内容问题,而且内容更为重要{38}。如果作品不考虑在地的文化环境,内容不能贴近大众,只有形式的通俗化,最终仍然无法为读者接受。当时有不少文人主张“在现阶段加紧运用旧形式,通过旧形式去争取这类读者到新文化的领域里来”{39},而茅盾的这一认识上的转变无疑是有先见性的,是基于实际的创作实践得出的结论。1940年代后期在香港文坛展开的一场关于“文艺大众化与方言文学”的讨论中,茅盾“老调子重弹”,再次强调大众化的问题确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内容也不是投不投小市民之所好,而是要有思想有血肉,碰到小市民生活上痛痒的地方{40}。
从主张“形式”的大众化到相较“形式”,“内容”更为重要,茅盾的文艺大众化理论最终是在香港这个文学生产的场域里发展并趋于完善的。通过细读文本可以发现,《腐蚀》几乎契合了他所提的“形式”大众化、“内容”大众化的诸多原则,如故事始终以主人公赵惠明为中心顺序展开,避免了《你往哪里跑》中缺乏结构、书中人物安排太多且几乎全是“没有下落”的弊端。而茅盾在文体、语言、故事情节等方面做出的新尝试,后文将再详细分析。
在南来作家中,茅盾是较早认识到香港的特殊性的:“香港满街是中国人,然而香港不是中国地……抗战的生活对于大多数香港人是生疏的”{41}。曾经,他对香港以及香港读者的评价不高,将之称为“畸形儿”,“醉生梦死的小市民”,但他并非一味持高高在上的批判之姿并将之排除在“大众”以外,而是另寻一条既能保持艺术水准,符合当前政治的宣传需求,又能使香港读者接受的创作道路,直到在《腐蚀》中给出了答案。
三
固然,《腐蚀》中的人物、背景以及整个故事的进展看似与香港并无关系,但茅盾通过迎合本地读者实现了在地关怀:这是站在香港读者立场、并积极将读者的阅读趣味纳入创作思考之内的一种写作方式。
首先,就文体而言,《腐蚀》与茅盾此前的小说是有明显不同的,它是茅盾唯一一部日记体小说,甚至改变了他不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惯例:
然而写长篇,总要预先有所准备:写个提要,列个人物表……一周时间无论如何是不够的。于是决定采用日记体,因为日记体不需要严谨的结构,容易应付边写边发表的要求。我一向不喜欢用第一人称的写法,这时也不得不采用了。{42}
这段话透露了如下信息:日記体小说的结构不严谨,对作者的写作水平要求低;日记体小说适合连载,写起来更轻松;日记体也好,第一人称写法也好,并非作者喜爱认可的写作方式。结合其他材料可见,作为已颇具名望的小说家和理论家,茅盾对日记及日记体的评价并不高。丁玲初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时,引起了茅盾的注意并给予高度赞赏,但显然引发他关注的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43}的莎菲女士,丁玲在日记体叙事的成功运用并没有进入茅盾的批评视野。
日记体小说是以日期的变更来组织小说的结构,包括文言日记体和现代日记体二类,分别在1914-1919年以及二、三十年代经历了创作的高峰,通俗作家包天笑、了青、李涵秋、周瘦鹃、吴绮缘和现代作家丁玲、沈从文、庐隐都有重要作品流传于世,更不用说被称为第一部“现代小说”的《狂人日记》(1918)就是采用的日记体。可见,日记体这一小说样式不区分新旧、雅俗,能为不同风格、背景的作家所用。但到了40年代,日记体已不那么受内地小说家的青睐,也不再新鲜、时髦。反而是在香港,仍不乏以日记体创作的小说,比如连载于《工商日报》副刊市声的《青年高步律之日曜》(1935.1.5-1.8,作者署名华),抗战时期最受本地读者欢迎的小说家黄天石以浅文言写就的日记体小说《生死恋》(1940,原名《丽绯馆忆语》)等等。即便是到了1947年,高雄以“经纪拉”的笔名连载的《经纪日记》不只受到了大众的欢迎,批评家对它的评价也很高。
而当时普通香港读者的阅读偏好还是有迹可循的:
关于小说的体裁,当时香港的一般读者已经接纳白话文,也已不认为标点符号碍眼,但根据我的观察,他们对“欧化”文体还未完全接纳。他们所说的“欧化”文体,是指“新文艺”作者所通用的那种文体。换言之,他们对《红楼梦》、《水浒传》等的文体较有亲切感。{44}
由此可见,在文体的接受上,相比较国内,一般的香港读者是比较偏传统、通俗易懂的。1941年的茅盾放弃了《你往哪里跑》里全知全能的说书模式的尝试,并非意味着通俗化方面探索的中断,回到他所熟悉的五四文学的样貌{45},而是因地制宜,将通俗化大众化跟他所观察到的香港实际结合起来:舶来的日记体一方面既为本地新旧小说家常用,香港读者已经不会觉得陌生难懂,又与传统笔记体小说有相似,的确是一个可以顾全大部分香港读者阅读趣味的选择。1945年后《腐蚀》在内地再次掀起热潮,但读者对此就颇不满意:“许多人不喜欢这种体裁,有些人嫌它太缺少结构”{46}。茅盾也表示:“如果我现在要把蒋匪特务在今天的罪恶活动作为题材而写小说,我将不用日记体……《腐蚀》既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47}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呢?简而言之,就是1941年在香港发表且主要面向香港读者的这一限定条件。
另外,《腐蚀》正文前有一段小序。在正文前面加上小序,这在日记体小说中也非罕见。最典型的是《狂人日记》,日记部分是用的白话文,但正文前用文言作的小序大致交代了日记的由来以及主人概况,可谓是布局巧妙。沈从文的《篁君日记》是一个白话小序,而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就没有序。除了叙事的需要,笔者觉得小序的存在另有一层深意。不同于鲁迅的文言小序,也不同于沈从文的白话小序,《腐蚀》的序使用的是“半文半白”的语言。试摘一段以作说明:
所记,大都缀有月日,人名都用简写或暗记,字迹有时工整,有时潦草,并无涂抹之处,惟有三数页行间常有空白,不知何意。又有一处,墨痕漶化,若为泪水所渍,点点斑驳,文义遂不能联贯,然大意尚可推求,现在移写,一仍其旧。{48}
整篇小序不过一千多字,都是文白交错进行,有古趣但并不晦涩难懂,和正文部分的语言风格如“近来感觉到最大的痛苦,是没有地方可以说话。我心里的话太多了,可是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让我痛痛快快对他说一场。”{49}截然不同,与茅盾在《蚀》三部曲、《子夜》《林家铺子》等作品中的语言也很不同。对于小序的由来,茅盾曾表示:“为了吸引读者,我在书前加了一段小序,假称这本日记是我在重庆某防空洞中发现的。”{50}但除了通过交代日记由来、以假作真来吸引读者,这种半文半白的语言风格也是贴近了香港读者大众的阅读习惯。与当时香港非常受一般读者欢迎的《生死恋》对照,二者小序部分的语言风格有不谋而合之处:“一日,余得二书,为余母者……此函则用日记体裁,缠绵而哀恻,有类夜莺之悲啼,余意译之,较原词恐未尽达也。”{51}中国古代正统雅文学是以文言为其最明显特征的,以文言为雅,以相对的白话为俗,直到五四运动后白话取代了文言成为文学的主体。但在香港,到了1930年代白话文也没有在文坛取得支配地位。如上文所提及的流行小说家豹翁擅用古文,“遣词造句往往诘屈聱牙,以示古拙”{52},而灵箫生用的是浅文言,原来用白话文写作的黄天石、岑卓云此时也转用了一种被称为“放脚式”或“折衷式”的介于文言和白话之间的语言,部分小说家还会将粤语入文。对茅盾这样的左翼作家来说,他必须坚持小说主体部分以白话文所著的原则(《大众生活》的办刊原则也是要求白话文,不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就如同1938年他“不得不写抗战”{53}一样,但他也可以在主体之外的“小序”做一些妥协,以达到吸引读者的效果。
从本质上说《腐蚀》和《你往哪里跑》的主题是有相似的,都是关注抗战背景下青年人走一条什么路的问题。但是,前者的故事情节更为曲折,这与茅盾对读者心理的把握有关了:“香港以及南洋一带的读者喜欢看武侠、惊险小说,这种小说我自然不会写。不过国民党特务抓人杀人的故事,以及特务机关的内幕,却也有一层神秘的色彩。”{54}此外,茅盾放弃了写他最熟悉的上海而改以不那么了解的重庆作为小说的背景,反而更能吸引那些同样不怎么了解重庆,但对重庆政府、防空洞、空袭等充满好奇的普通市民——1940-1941年香港本地报章上也经常刊载重庆的新闻事件。《大众生活》第16期和第18期曾分别刊登了两封非常重要的读者来信——《把惠明救出苦海》和《对“惠明”的又一看法》,是《腐蚀》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读者回馈。虽两者对是否要将惠明“救出黑暗的苦海”有不同看法,但都表明希望茅盾继续写下去。赵惠明的懦弱反复和在险恶环境中的挣扎,她和小昭的爱情悲剧,确实是“引人入胜的”{55},唤起了当时的读者的同情。巧合的是,《腐蚀》与黄天石的另一部流行小说《红巾误》(1940)亦可对照阅读,两者呈现出很多有趣的呼应:身陷重庆的女特务赵惠明和在香港从事“导游女”{56}职业的乡下姑娘阿甜,原本毫无关联的两人,竟然产生一种对话的意味。
李永东曾中肯地指出茅盾对战时的重庆了解有限,由于欠缺实际生活经验导致《腐蚀》虚构过多,有着很强的观念化色彩{57}。《腐蚀》中想象的成分自然是有的,但也不全然是虚构:“我曾听人讲过,抗战初期有不少热血青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用战地服务团等假招牌招募了去……韬奋就接待过这样的青年。”{58}他还专门撰文谈及由于特务工作深入学校,身处大后方的青年所遭受的痛苦{59}。此外,《大众生活》第9期刊登了一篇《我第一次体味到人世间的血腥——□□□□□逃出来的一个女孩子的自白》,作者是一个来自重庆的女学生,她在文中描述了学校施行军事管理以后自己的遭遇,控诉这种“特务化”的政策对青年学生的迫害:
在我们学校,是有一位舍监被雇来公开检查信件的,她察看我们行动……教务主任(他是新由党部派来的)软硬兼施,说党部有命令给学校,已查实有据。详询校内有何秘密组织,有那几个是活动分子,与其他各校的联系若何……我压抑着不能自持的激怒,把眼泪一颗一颗吞进肚里,接受了xx先生的劝告,加入了青年团{60}。
部分细节与小说后半部分赵惠明去學区检查学生信件的情节相似,而遭受了青年特务盘查、学校多次谈话,最后被逼加入青年团同流合污的这位高中女生便是《腐蚀》中“N”的原型,只不过茅盾做了艺术处理,并将故事场景从高中转到更富有话题性、易于展开情爱纠葛的“大学区”。甚至“老表”和K都能在信中找到对应人物:“是三青团的负责人(卑鄙无耻的走狗),令我调查一位他们认为在校内活动的同学,随时注意她的行动,按时交报告……”{61}显然,茅盾是从读者来信中获取了小说的灵感和素材。
综上所述,《腐蚀》在文体、语言和故事情节上更明显地向在港的读者的阅读偏好倾斜。文学作品被认为可以借由读者的阅读、欣赏、认知、评价、研究、传播和应用对地方构成影响{62},反之亦然,最终《腐蚀》所体现的在地关怀,是凭借着本地读者复数的阅读和反馈、拒绝和接受实现的。或许南来作家始终无法真正走入香港市井,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茅盾、邹韬奋等文人曾做过的努力以及香港曾给予他们的作品“香港性”。诚如茅盾所说,《腐蚀》的产生是有一定历史条件的,脱离了那个时间——皖南事变后的1941年,那个地点——小说生产和面向的香港,又何来今日所见之《腐蚀》?
① 第一次是1938年2月底至1938年12月底,第二次是1941年3月下旬至1942年1月,茅盾曾于1937年除夕从上海坐船经香港到广州,因只是中站且无实际文化活动,本文不做比较。而这两次旅居中茅盾的具体活动,香港学者卢玮銮曾撰写《茅盾1938年至1942年间在香港的活动》一文做了全面的梳理。见卢玮銮、黄继持编《茅盾香港文辑(1938-1941)》,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版。此外,林焕平在《茅盾在香港和桂林的文学成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中最早分析了茅盾在港期间的创作和评价。
② 黄万华:《百年香港文学史》,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③ [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雅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④ 阎浩岗:《个人主义者的悲剧——重读茅盾的〈腐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⑤ 侣伦曾回忆:“那一期间的香港报纸差不多每一种都辟有一个新文艺副刊,纯粹登载新文艺作品。”《香港新文化滋长期琐忆》,《海光文艺》1966年第8号。
⑥ 平可:《误闯文坛述忆》,《香港文学》1985年第3期。
⑦ 《伴侣》共发行8期,《铁马》发行1期,《小齿轮》发行1期,发行时间最长的文学刊物是月刊《红豆》(1933.12-1936.8),由于获得梁国英药局支持,共发行四卷24期。
⑧⑩{18}{21}{23}{24}{36}{37}{38}{41}{53} 茅盾:《在香港编〈文艺阵地〉——回忆录(二十二)》,《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⑨ 例如早期新文学重要作家袁振英1915年从香港皇仁书院考入北京大学,30年代黄庆云到广州读初中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
{11} 王齐乐:《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56-357页。
{12}{17}{44}{52} 平可:《误闯文坛忆述》,《香港文学》1985年第7期。
{13}{15} 王幽谷:《怎样在华南写小说?》,《国民日报》,1939年8月18日,第8版。
{14} 张登林著:《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16} 平可:《誤闯文坛忆述》,《香港文学》1985年第6期。
{19}{22}{38}{42}{50}{54}{58} 茅盾:《战斗的一九四一年——回忆录(二十八)》,《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20} 注释:根据茅盾的晚年回忆录可知,他对《腐蚀》的评价是高于《你往哪里跑》的,而两部小说发表以来所引起的读者回馈和研究亦可印证这一点。可参看笔者《〈腐蚀〉的出版及版本变迁》(《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一文,此处不再赘述。
{25} 周正伟:《抗战前香港华人文化之发展(1931-1937)》,香港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文学硕士课程同学会2012年版,第65页。
{26} 赵稀方:《小说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2页。
{27} 注释:萨空了在香港主编《立报》期间,在他主持的副刊“小茶馆”里开设读者来信,也涉及一些香港地方话题,详见樊善标《抗战时期南来香港文化人的国家想象与在地关怀——萨空了主编〈立报〉“小茶馆”副刊的个案》一文,《谛听杂音:报纸副刊与香港文学生产(1930-1960年代)》,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07-143页。
{28}{29} 夏衍:《懒寻旧梦录》,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00页,第265页。
{30} 注释:“信箱”栏目在前两期名为“简复”,到第3期开始分为“简复”和“读者信箱”,第21期“简复”栏目更名为“信箱”,“读者信箱”更名为大众之声,第24期又重新调整“信箱”,分为“简复”和“来信”。
{31} 注释:由于香港当时的报刊检查制度,如有违反规则的字词句,会以“□□”出现。这在《大众生活》等进步报刊中是很常见的,有些甚至全文被删,只留一个空白的版面,下文不再另行注释说明。
{32}{47}{48}{49} 茅盾:《腐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9页,第299页,第3页,第5页。
{33} 茅盾:《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月报》1932年第1卷第2期。
{34} 茅盾:《关于大众文艺》,《新华日报》,1938年2月13日,第4版。
{35} 茅盾:《文艺大众化问题:上月在汉口量才图书馆的讲演》,《新语周刊》1938年第1卷第2期。
{39} 杜埃:《旧形式运用问题的实践》,《大众日报》,1938年3月20日。
{40} 茅盾:《反帝,反封建,大众化——为“五四”文艺节作》,香港《文艺生活》1948年总第39期。
{43} 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艺月报》1933年第1卷第2期。
{45} 侯桂新:《文坛生态的演变与现代文学的转折——论中国现代作家的香港书写:1937-1949》,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页。
{46} 木君:《“腐蚀”(书评)》,《新旗》1946年第3期。
{51} 黄天石:《生死恋》,见黄仲鸣主编《香港文学大系通俗文学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24页。
{55} 消愁:《对“惠明”的又一看法》,《大众生活》1941年第18期。
{56} 注释:三四十年代香港有私人办的“导游社”,雇佣能说上海话和北方话的青年女子,专门给新到香港的游客作游玩时的向导,称为导游女/导游娘,实际是变相的妓女,茅盾在《劫后拾遗》中也有对这一畸形现象的记录。
{57} 李永东:《逆写战时国都——1941年茅盾在香港的创作》,《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59} 茅盾:《青年的痛苦》,《华商报》,1941年6月30日,第3版。
{60}{61} 林华:《我第一次体味到人世间的血腥——□□□□□逃出来的一个女孩子的自白》,《大众生活》1941年第9期。
{62}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04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In 1941, when Mao Dun wrote his Corrosion in Hong Kong, it was deemed to have’ no relationship with Hong Kong' because the characters, the background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whole story did not feature Hong Kong. However, if we start off by looking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thor, his work, the reader and the editor, in relation to the text, we may see that Mao Dun took an approach to his writing by including in it the reader’s taste from the position of the Hong Kong based readers as the cre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novel is closely related to Hong Kong. The three parts of the subject respectively explicate the concrete influ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groups of readers in Hong Kong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had upon the writers, the two conditions that induced Corrosion to cater to the taste of the local readers and that caused Mao Dun’s Hong Kong-based novels to take a different turn and the Hong Kong effects reflected in Corrosion in terms of its form and contents.
Keywords: Mao Dun, Corrosion, Hong Kong, readers, popularization